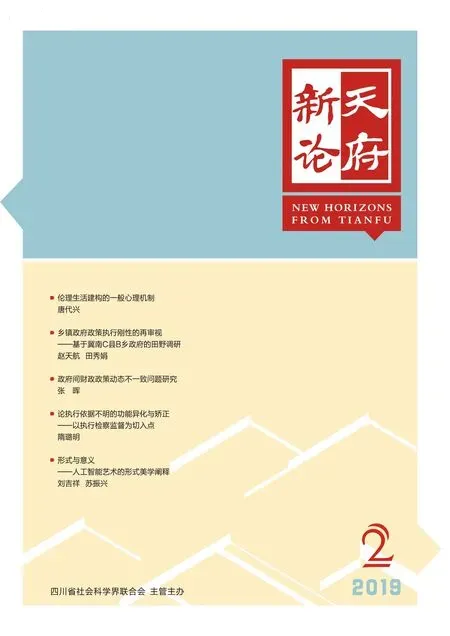《诗经》“婚恋时中”思想研究
——以《大学》《中庸》的引诗为例
于 涛
《诗经》的“婚恋时中”观是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婚恋过程中适婚主体对“中”与“时”的合理把控,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吸收和创见的过程。它在《大学》《中庸》中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婚恋观念,适应不同时代境遇的要求。要想达成“婚恋时中”的状态也绝非易事,需要从儒家思想层面的解读去入手,领会其要义,还需常与西方伦理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互相借鉴,经年累月方有精进。
一、何为“婚恋时中”
对于“婚恋时中”的解读,应遵循“时”、“中”—“时中”—“婚恋时中”的逻辑发展来展开。何为“时”、“中”?《尔雅》释“时”为:“是,是也。”[注]《尔雅》,管锡华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148页,第152页。即此、这之意。释“中”为:“殷,齐。”[注]《尔雅》,管锡华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148页,第152页。即中间、当中之意。《说文解字》释“时”为:“时,四时也。”[注]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134页,第8页。释“中”为:“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注]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134页,第8页。对《尔雅》的“时”与“中”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康熙字典》又对两者加以补充,释“时”为,是也、伺也、中也等;释“中”为,民受天地之中、举正于中,天地之中、民则不惑、宅中圆大等,又丰富了“时”与“中”的内涵。由上述考释可见,“时”与“中”合意有得当、恰好、当中之意。何为“时中”?源头当寻至《周易》,《彖》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注]《周易》,杨天才、张善文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54页。即要亨行与合适的时机。“在达成‘时中’方面,‘中重于正’,‘中须以正为先’。‘正’是前提,凡事须先确定是非曲直,然后才能在程度上有所选择与斟酌。但‘正’未必‘中’,‘中’必会‘正’,凡事应依据具体情况有所取舍裁定才能确定是否为‘正’。”[注]李群,于洪波:《〈周易〉的“时中”观及其教育镜鉴》,《当代教育科学》2016年第3期。《周易》的“时中”思想被儒家吸收形成“中庸”,首创于孔子,子思进一步丰富了中庸的“时中”、“中行”和“中和”内涵。何为“婚恋时中”?这需放入《诗经》婚恋诗歌中去谈。《诗经》全篇虽未曾出现有关“时中”的明确字眼,但不能就此否定《诗经》婚恋诗中没有“婚恋时中”的思想。《诗经》的婚恋诗歌大部分集中在十五国风中。据学者谢晋青的研究,除了《魏风》《桧风》《曹风》《豳风》外,其余十一国风均涉及婚恋问题。仔细观察这些婚恋诗歌会发现,“婚恋时中”思想已十分明显。以《周南·关雎》与《陈风·衡门》为例,《关雎》有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注]《诗经》,王秀梅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2页,第271页。《陈风·衡门》有云:“岂其食鱼,必何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注]《诗经》,王秀梅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2页,第271页。这两句诗歌看似前后没有密切联系,其实不然。“雎鸠”、“食鱼”已涉及“婚恋时中”之娶妻“以时”的思想。日本学者白川静曾在《诗经研究》中对雎鸠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一直都是善鸟的结论存有疑虑,认为这可能是深受《关雎》整体诗风影响所致,因为雎鸠是一种栖息于河边食鱼而生的水鸟,把它用作淑女和君子的代名词未必恰当。张启成教授对此以“食鱼”隐喻为“娶妻”的解答就顺意畅达很多,这与《关雎》所表达出的君子如何努力践行娶妻“以时”而得佳人与家庭的诗旨配搭吻合。《衡门》诗旨在表达君子本该娶齐姜这样的高贵妻子,但由于贫困而娶不起所引发的两个反问是对娶妻“以时”不当的追悔烦思。显然,“雎鸠”、“娶妻”与“食鱼”密切相关,“婚恋时中”亦贯穿始终。在婚恋过程中,应知晓有“中”无“时”,会闭塞婚恋之道,无法适应不同境遇的要求;知晓有“时”无“中”,也会因缺少变化的标准与最终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驰。因此,“时”与“中”表里为一,缺一不可。“时中”就是在个人所处不断变化之时势环境等情况下,“得其时而中,使无过与不及”,而“婚恋时中”就是在具体境遇中的实践运用。
二、 “婚恋时中”在于《大学》《中庸》
从“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孟论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注]朱熹:《四书集注》,王华宝整理,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页。中可见《大学》之于儒家思想的特殊地位。子思学派对《中庸》的诠释,同样被视为“孔门传授心法”为后世所推崇。《大学》与《中庸》原本只是孤存于《礼记》中的单篇,但到了宋代朱熹时,却被升格为与《五经》并称的《四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四书》的阅读次第中,两者呈现呼应之势,这对儒家“一以贯之”之道无疑提供了许多思考的空间。故想以《诗经》中《小雅·桃夭》《小雅·棠棣》二篇为线索,在重新梳理《大学》《中庸》内在联系的基础上,以“时中”思想为切入点,再度探索“婚恋时中”的内涵。
第一,《桃夭》之于《大学》。《周南·桃夭》是《诗经》中的名篇,位于《周南》第八首。之所以要提《桃夭》与《大学》的关系,是由于两者之间实则蕴含着一种很特殊的内在关系。这一点仅从一个基本事实中可见一斑:《大学》虽篇幅不长,却多处引用《诗经》。然而,其所引文句多来自雅、颂,唯一一处引用国风中的诗句便出自此诗,“故治国在齐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於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注]朱熹:《四书集注》,王华宝整理,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0页。此段出现在《大学》第九章,即论述“齐家”的一章中。在《大学》中引选自《大雅》《周颂》的诗句屡见不鲜,但为什么偏在《大学》中引《周南》这一句?《桃夭》与“齐家”思想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对此我们还需返归到文本中。关于《桃夭》的诗旨,毛序云:“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已正,婚姻以时,国务鳏民。”[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40页,第40页。郑玄所做的笺注也认同此说,仅有的补充只是对“鳏”进行了解释:“老而无妻曰鳏。”三家诗以及后世对此都基本认同。例如朱子认为:“文王之化,自家而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注]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6页,第24页。由此可见,《毛诗序》所言几乎就是传统经学的标准解释。而其核心观念便是“时”——“婚姻以时”。《桃夭》首章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宜其室家。”桃花并不能永久绽放,流逝的时间会冲刷一切美好,人事自然不能逃脱,未免有些伤感。但反观《桃夭》的二、三章就给了我们答案,“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子之于归,宜其家人。”从花到果实再到叶蔓,从其宜其“室家”到“家室”再到“家人”,此种情绪不降反升,且通过桃花与佳人的呼应,形成了一派万物祥和、蓬勃向上的大气象。这一极不寻常的诗意表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思契机。为何会出现如此一以贯之的美好?前文《毛诗序》已经给出了答案,即“婚姻以时”。这种“合时”就是对妙龄女子美好青春的真实保留。在恰当的时间点,做出恰如其分的决定,就会得到满意的回报。诗中的女子确实是循序渐进的遵循“婚姻以时”的原则。女子的幸福就是一家人的幸福,自然与《大学》中“齐家”思想不谋而合。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桃夭》是民间嫁娶之诗,《大学》何由即指为实能宜家而可以教国?详《易林》之语,似是武王娶邑姜事,然则《大学》引之非虚词矣。”[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40页,第40页。即认为诗中的桃花女子并非虚指或指普通家庭的女子而是特指武王与邑姜的嫁娶之事。但无论与否,倘若不遵循“婚姻以时”,想必武王也不会名留青史,武王伐纣建立周朝的卓越功勋不也从侧面证实了《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这一点与《大学》之理念不谋而合。所以,我们应当从《桃夭》的义理层面去阐释与《大学》的关联,而不是固守一家之言、一面之词。正因如此,“时”这一概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时”可理解为“时中”,这样就又与《中庸》密切联系起来。
第二,《棠棣》之于《中庸》。《小雅·棠棣》也是《诗经》中的名篇,位于《小雅》第四首。 《中庸》中引用《诗经》多处,但涉及婚恋方面的诗仅有《棠棣》,“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而室家,乐而妻帑。”[注]《诗经》,王秀梅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335页,第331页,第331页。朱子对此论述道:“夫子诵此诗而赞之曰:人能和于妻子、宜于兄弟如此,则父母其安乐之矣。”[注]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6页,第24页。可见,这是对君子之道的实习,夫子要求从容易之事做起,循序渐进,这样才能“父母其顺矣乎”!其实“宜而室家,乐而妻帑”就是对《大学》倡导的“齐家”理念的一个思想指导。关于《棠棣》诗旨,毛序云:“《棠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注]《诗经》,王秀梅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335页,第331页,第331页。郑玄作笺注认为此诗的作者是召公,“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之以亲之。”[注]《诗经》,王秀梅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335页,第331页,第331页。虽然关于此诗作者是何人,学界历来颇有争议,但其诗旨终可断定。《棠棣》《桃夭》诗名都以植物显题,《棠棣》以诗中描写的花萼、花蒂来暗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道理,在表达“救难以时”,也可以引申为“治世以时”,正是由于“二叔”不和才直接导致周本族内乱,想借《棠棣》告诫周本族人团结的重要性。这里的“二叔之不咸”之“咸”应以“和”解。接着, 《棠棣》三、五章写道:“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咏叹。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有生。”这几句形成鲜明的对比,兄弟与朋友的真情与假意,更能呼应“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中心思想。把握好“以时”就会带来“和乐”,虽《棠棣》主要在于歌颂兄弟情义,但其中从未忽视对“婚恋时中”的强调,这在上文提及《中庸》所引《棠棣》七、八章句就可以见得。“兄弟既具,和乐且孺”的结果取决于“妻子好合”、“是究是图”,后者是前者的保障,也是父母“其顺矣乎”的保障。“兄弟既翕”、“妻子好合”都体现了“时中”的思想,这无疑体现着《大学》“齐家”的思想。可以说,夫妻和睦、妻子好合是兄弟相亲的前提。孟子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齐家”理念因蕴含着儒家倡导的“孝”思想,孔子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论语·为政》)就曾产生很大质疑,对此孔子提出了行“孝”的成熟看法,即“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其“父志”中固然包含子女成家立业之说,因此《中庸》之《棠棣》蕴含着“政治时中”和“婚姻时中”两层含义。《中庸》有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人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注]朱熹:《四书集注》,王华宝整理,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8页,第18页,第19页。朱子对此评论道:“中庸者,不偏不倚、不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惟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注]朱熹:《四书集注》,王华宝整理,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8页,第18页,第19页。可见,“时中”思想涉猎范围广泛,绝不仅仅只是上述婚恋、治世、君子修养方面这么简单,要想达到“时”与“中”的合宜绝非易事,因为“中庸其至已矣,民鲜能久矣”[注]朱熹:《四书集注》,王华宝整理,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8页,第18页,第19页。。
第三,《桃夭》《棠棣》之“婚恋时中”思考。《棠棣》所提出的“政治时中”和“婚姻时中”是《中庸》普遍原则的体现,而《桃夭》中的“婚姻以时”是此原则的具体化,它与“婚姻时中”是一种体与用的关系。《大学》之引《桃夭》是《中庸》里“婚姻时中”原则的具体演绎,主要体现在《中庸》之引《棠棣》所体现出的“婚姻时中”原则是一个概括性总纲,它与《桃夭》之“婚姻以时”都有对《大学》“齐家”之重要佐证,但对如何“齐家”,二者存有区别:《大学》之引《桃夭》旨在细致地阐释一个女子婚嫁、生子和显荣三段时光,把“婚姻以时”具体体现在这每一个阶段的恰如其分,我国自古就有多子多福的观念,而《桃夭》一诗之多子观念就体现了我国古代婚姻与家族繁衍的密切关系,这是“齐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展示,《桃夭》强调了周礼之重生育的观念。《中庸》之引《棠棣》旨在从兄弟情义入手,间接引出“婚恋时中”思想,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何时以“时”何处而“中”具有抽象性,《棠棣》较与《桃夭》相比并不局限于家族繁衍,而是包含了对周礼之重妇功的全面概括。细究起来两者都隐含有一个共同的时中概念——如何达“孝”,因为“齐家”上承“修身”,下启“治国”,在忠、孝、仁、义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中,“孝”无疑处在根源性地位。在家是孝子,在庙堂才能是忠臣,为官才可能守中正造福一方,而居“齐家”之首“孝”莫属成家立业,平民百姓家如此,王公贵族更是如此。一定程度上那些适婚女子无疑就成为尊“孝”的重要媒介,尤其是在贵族阶层适婚女子更是没有太多婚姻自由可言。因此,在当时婚姻作为买卖也好还是作为政治联姻的手段也罢,处理的“时中”得法才有可能得到较好的结果。笔者认为之所以《桃夭》《棠棣》被官方文献所引,主要在于表彰其“时中”到位,总览《诗经》全篇,尤其十五国风中未能达“婚恋时中”而悲惨者数不胜数,“婚恋时中”被儒家所发扬旨在宣扬“时中”得位,这里涉及对心、性、情、行的合理培育。“婚恋时中”承认婚恋行为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婚恋时中”的本质在于依时而中,依据时位、时势的变化而因时制宜,随时处中,“婚恋时中”的实质在变通,在于时新,在于执两用中,在于协调长久,在于处事适度,不卑不亢,随时而中。
三、 “婚恋时中”与“幸福中道”的伦理差异辨析
《诗经》“婚恋时中”和亚氏“幸福中道”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这主要基于二者不同的社会基础、文化境遇等所致。通过二者的差异辨析,似乎会更加关注中西伦理文化虽有不同视域的阻碍,但其伦理思想核心却着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这就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的思想之源,本就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或者共通的原点来为之架以思想之桥梁,让人们在其研习的过程中可以循着启思从而加以突破创新。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有:
第一,《诗经》“婚恋时中”和亚氏“幸福中道”都与人的社会性相关,都是对他人友善的利他美德。《诗经》“婚恋时中”可以说是孔子诗教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婚恋时中”夹杂了孔子“中庸”的思想,据查“婚恋时中”就来自儒家《中庸》。换句话说,《中庸》一书就是出自《论语》,细究起来还会发现不仅“中庸”一词明见于《论语》,而且《中庸》全书与《论语》相似语句者居多。《诗经》“婚恋时中”强调“婚恋以时”,就是《中庸》“时中”思想的一个体现。“婚恋时中”在于扭转一成不变的婚恋思想,给适婚人群以“时”与“中”的合理把握,即便是在封建保守的社会中,只要适婚人群充分认知“度”的价值就可以较为和谐的生存。《桃夭》与《棠棣》的“婚恋时中”思想在此已表示得很清楚,故不再赘述。对于亚氏“中道”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在感情与实践中,恶要么达不到正确,要么超过正常。德性则找到并且选取那个正确。所以虽然从其本质或概念来说德性是适度,但从最高善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极端。”[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0页,第26页,第14页,第25页。这就表达了类似于“时中”的思想。为何亚氏会强调“中道”也是一种对他人友善的利他美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幸福作为最高善”、“幸福的获得”等中可以找到答案。虽然《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真正目的是宣传亚氏的政治学主张,“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行为的人。”[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0页,第26页,第14页,第25页。但伦理道德作为政治学其中的内涵元素就绝不容忽视。故幸福包含了两种构成因素:一是德性,二是现实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在占有和使用中把握最高善,还是在表现品质和现实活动中把握最高善,此中却有大区别。”[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0页,第26页,第14页,第25页。一个人在具有了德性品质之后,还必须进行现实的活动,才是幸福的。亚氏的“幸福”获得要涉及对诸多德性的恰当运用,然而如何自由的使用就涉及到“中道”,因为“德性的报偿或结局必定是最好的,必定是某种神圣的福祉。”[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0页,第26页,第14页,第25页。所以,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能以德性对待他人,而不只是对待自身。亚里士多德承认自爱的合理性,但却反对自私。
第二,《诗经》“婚恋时中”和亚氏“幸福中道”都诉诸某一规范作为衡量标准。《诗经》的“婚恋时中”用礼来解释,即按照礼的标准来“克己”以“时中”,使礼和“时中”不可分离,避免以“时中”作为随意判断的工具。如《诗经·大雅》中就有许多预祝周文王百子的诗歌。在这些诗中还是独以《周南·桃夭》为类诗之典型。《周南·桃夭》末章就以桃树满荫为起兴,明显是在传达新婚后只有治家有方才可使家繁荣兴旺的诗旨。需要注意的是,“新婚后治家”显然越不出三纲五常、伦理尊卑等礼法限制,《周南·桃夭》所有的美好描述都是以此为基的。亚里士多德更看重公正,虽然他认为政治和幸福并不是同一回事,但幸福的生活总是需要立法去支撑。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获得应由法律控制人类生活的整个范围,并且加强适合所有美德的行为。在他看来,在勇敢、节制等美德中,其标准与其说是外在的不如说是内在的,而公正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其最终要求是与社会和环境的标准相一致。尽管《桃夭》“婚恋时中”的礼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获得存有很大不同,但两者在寻求普遍性规范这一层面上,却有着一致性。即表明了双方对社会道德的运行都有关切和对践行道德行为过程普遍化的底线都有要求,对认识德性需要后天的培养,尤其是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一步步内化其行为规范,遵守行为规范都有认识。
第三,《诗经》“婚恋时中”和亚氏“幸福中道”都包含、统摄、指导着其他德性。如《小雅·棠棣》的“婚恋时中”就是以“婚恋以时”加以具体表达,“婚恋以时”又包含、统摄、指导着诸如妇德之“善”、妇言之“顺”及妇功之“真”的合理使用等。此外,总览《诗经》所有的婚恋诗歌,对于婚恋“时中”进行包含、统摄、指导的具体方面大致有以下几类:其一,以夫妻情义为内容的“时中”指导(《周南·关雎》);其二,以婚姻缔结礼数为内容的“时中”指导(《周南·雀巢》);其三,以生育为内容的“时中”指导(《周南·桃夭》);以妇功为内容的“时中”指导(《周南·葛覃》)。从这些分类中可发现,《诗经》婚恋“时中”所包含、统摄、指导着其他德性都是在以周朝礼乐为核心,所引代表诗歌也都是以周时最盛为例。可见,婚恋“时中”观不仅仅只是周时的一个处世细节的体现,更能上升为周朝的国家行政方略。从微观层面来说,婚恋“时中”包含“礼乐”思想,婚恋“时中”统摄所有婚恋德性,婚恋“时中”指导实际的婚恋行为;从宏观层面来说,婚恋“时中”必以“礼乐”为核心,以“时中”为方法,以“君子”为践行标准。亚氏“幸福中道”包含、统摄、指导的其他德性也都是为达其“幸福”而服务的。亚氏“幸福中道”包含着彰显每一个德性最大的价值贡献,如亚里士多德谈及“慷慨”,他明确提出要预防吝啬,要理性区分与“慷慨”相关的实际情况,因为有的时候过多使用“慷慨”适得其反,使用“慷慨”亦要持守“中道”也亦更加凸显这一德性的价值。亚氏“幸福中道”统摄着不同德性之间的恰当适度的配合,如在财富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谈完“慷慨”后紧接着又谈及“大方”,“大方意味着大数量的适度的花费,但是数量的大是相对而言的……所以花费的适度是相对于花钱的人自身,又相对于花钱的场合和对象的。”[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2页。由此可见各个具体德性之间是需要综合运用的。亚氏“幸福中道”指导着如何获得幸福的实践路径,在这需要明晰的是理性、中道与幸福的关系。在亚氏“幸福中道”中,“中道”是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依据,“幸福”是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目标,但在此之前还需要一个道德选择的理论前提,即“理性”。所以“中道”包含、统摄及指导其他德性是以一个宏观的综合视域来看待的。
与此同时,二者也有不同之处:
第一,《诗经》“婚恋时中”和亚氏“幸福中道”的研究视角不同。《诗经》“婚恋时中”以礼乐教化为研究视角。《诗经》婚恋诗歌中充斥着对传统道德的反叛,这种反叛更多的是由贵族们的败德行为来展现的。如《卫风·新台》《卫风·与子偕老》等。前者《诗序》云:“刺卫宣公也。”后者据《毛序》所言专刺姜宣。促使婚姻关系败坏的原因正如李山所言:“从内在原因上说,是贵族人物忘却了婚姻‘厚别附远’、‘合二姓只好’的政治含义……从外在方面来说,卫地之风所显示的贵族的堕落表明是东方野性婚恋习俗浸染的结果,殷人的风俗和性情浸染卫地的姬姓人群。”[注]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25页。因此,“婚恋时中”更显其价值性。亚氏“幸福中道”以政治教化为研究视角。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就在于行“中道”,每个人只要合于“中道”而行动应能达到幸福。以“中道”原则为理论依据,他对勇敢、节制、慷慨、诚实、公正、友爱等道德范畴进行了详细论证。其目的无非就是要证明“中道”是唯一正确的道德原则。人们只有遵循这一原则,并顺应理性,才能成为有德性的幸福的人。在亚氏“幸福中道”中,“理性”是道德选择的理论前提,“中道”是道德选择的依据,“幸福”是道德选择的目标,但倘若要达到其目的就必须借助政治的力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幸福末章的总结可阐释为,幸福一定需要立法来支撑,立法可以对伦理道德进行更多的指引,法律的特点在于强制与遵守,而幸福在于行“中道”,倘若幸福在行“中道”之时受到阻碍,那么就需要法律来惩正。
第二,《诗经》“婚恋时中”和亚氏“幸福中道”的道德层级不同。《诗经》“婚恋时中”对象为贵族阶层、民众。其实主要还是针对贵族阶层,民众为次。要知道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要想恢复礼制,贵族阶层是首选。这里体现一种上行下效之法,待等礼制光复,再进行广泛的教化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政治手段。亚氏“幸福中道”主要针对统治者、贵族阶层、业界同行和城邦青年。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所涉道德层级更为广泛。这一点基于亚里士多德吸取了他的恩师柏拉图以及苏格拉底的经验教训,一味地纠正别人的错误而不给予适当的肯定往往非善举,再加之极度捍卫自身所坚信善的理念,忽视实际的政治生存条件,多少会导致理论与实践在某些方面的严重脱节,至亚里士多德这里开始有了调整。他开始注重把自己的理念传授给更多适宜的受众群体,上至国王,下至青年,开始有步骤分次序的传播自己的观念。这样做的益处在于,既传播了理念又给他人以思考审视的空间,既尊重了知识又尊重了人格。
第三,《诗经》“婚恋时中”和亚氏“幸福中道”的运行机制不同。《诗经》“婚恋时中”是情的投射,道德主体之间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所以《诗经》“婚恋时中”的真正落实在于形成强烈而稳固的道德感,即情感是儒者行仁义、守礼的动力和保证。而亚氏“幸福中道”认为公正和合法是理性的叙事,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述公民关系中那样,“需要似乎是把双方联系起来的唯一的纽带”。此处的“需要”是指物质交换的需要。所以,如何达成一个能互利互惠的双赢关系必然诉求于理性的定夺,即一个能获得“幸福”的人根本在于他是一个理性人。
——对《物理学》8.6(259b1- 20)的一种解读
——“自由落体”教学中的物理学史辨
——《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一课的教学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