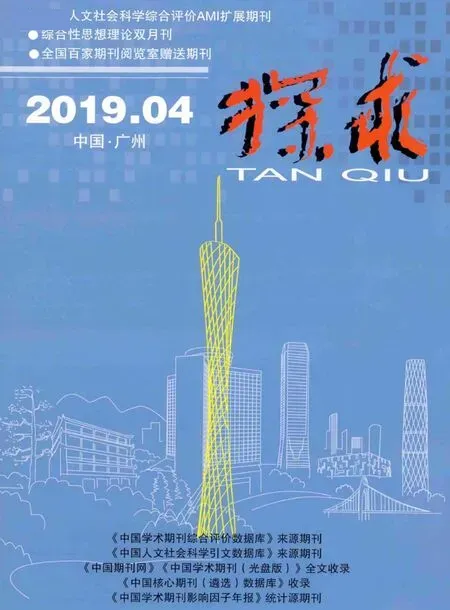政府创新研究:基于国外文献的评述
□郑佳斯 李缌缌
国外对一般“创新”和“公共部门”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对两种创新进行了差异性研究,继而提出了“政府管理创新”的概念。美国学者Mar k Moor e(1997)和英国学者Jean Har t l ey(2013)将创新与政府创新进行了区分,认为“一般的创新(尤其是私营部门)更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产品和流程的创新以改善组织发展境况,公共部门创新作为一类‘特殊的创新’,旨在通过跨部门决策,财政及公共产品供给等系统的重新整合以促进社会发展”。[1]他们认为目前关于政府治理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协调机制,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创新上。因此,需要对政府管理创新进行全面系统的边界界定。梳理目前的国外文献,学者们关于政府创新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创新的内涵特点和类型、政府创新的动力和形成机制、政府创新的实践等几个方面。
一、政府创新的内涵、特点和类型
对创新的操作性定义至关重要。Becker和Whisl er(1967)对创新的定义是“一个有相似目标的组织中的第一个或早期使用的想法”。[2]因此,必须“首先或早期”采纳一个想法才能被认为是创新的。Weber(1999)认为“创新的定义中没有价值判断”。[3]创新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生产率或某些组织过程效率,也可能会降低生产力和效率。此外,创新也可以具有道德因素,因为它们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实现不道德的目的。在商业上,创新被市场使用的程度被用来判断是否创新。而政府的创新是正式政治话语和普通公众辩论的主题,因为目标冲突会导致创新[3]。另外,同企业相比,政府对于成功的创新行为是缺乏奖励的,而且一旦创新失败还会导致相当严重的后果(Abr amson,2002)。Hal vor sen,Hauknes 和Mil es 等(2005)发现,政府比企业更愿意引入改善组织结构和管理的工具,更愿意从事组织和技术上的变革。
关于政府创新的特点,Zal t man,Duncan 和Hol bek(1973)通过对创新扩散的研究确定了创新的21 个特征或属性。Tor nat zky and Kl ein(1982)对75 项有关创新特征与创新采纳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发现与创新采纳重要相关的三个特征:兼容性、相对优势和复杂性。Downs 和Mohr(1976)从组织层面上将创新分为“主要属性”与“次要属性”,主要属性能区分组织间的创新,次要属性使组织内部能够区分创新。Bor ins(2000)基于对福特基金会1990 年至1994 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创新奖中217 名入围半决赛者完成的调查问卷发现:“49%的创新者是低于机构主管级别的职业公务员;创新通常是为了解决在危机发生前已被确定的机构内部问题;创新通常是一个在实施中进行过调整的全面计划。
在创新的类型方面,早期研究将创新概念化为单维结构”。[4]马斯洛(1967)对主要和次要创新进行了区分:“一个为实现自我从事创新的人被认为具有主要创造力,而在工作领域展现创新则被认为是次要创造力”。[5]同样,Boden(1994)对心理和历史创新进行了区分,“前者代表个人创新而后者是人类整体的创新”。[6]Ekvall(1997)区分了轻微的创新和重大的创新。Tayl or(1959)讨论了创新的五个类型,包括有表现力的创新、生产性创新、创新能力、发明性创新和应急性创新。Finke(1995)将创新分为保守现实主义、保守唯心主义、创造性现实主义和创造性理想主义四种类型。Ward,Smith 和Finke(1999)区分了以目标为导向的创新和探索性创新,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创新,特定领域创新和普遍创新。Boden(2000)描述了组合、探索和变革三种类型的创新。Nandhini Rangarajan(2008)在Unsworth(2001)提出的四种不同类型的创造力和St ernber g(1999)的八种不同类型的创造力的基础上,使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管理的政府创新奖(1990-2001年)获奖者样本,评估了某些类型的创造力在政府组织中是否更具代表性以及研究了某种类型的创新倾向是否会因不同的政府和不同的政策领域呈现出差异。结果发现,各种类型的创造力最多的是在地方和州一级;尽管积极主动地参与创造性行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创造性行动的效果只是渐进性的,且这种创造性行动被看作是被迫对问题的回应而不是主动创造机会。
二、政府创新的动力、采纳和扩散
鉴于目前大量的政府创新实践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因而,国外关于政府创新的动力和采纳、扩散机制研究也主要面向地方政府,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和相关的实证分析。制度主义者认为,创新的原因因组织类型而异:技术经济力量应该在“效率型”组织中引发创新,而社会和文化力量则应该在“制度化”组织中激发创新。Nancy C.Roberts(1992)认为,“公共创新是组织结构、组织激励、管理者个人特征三者互动的结果”。[7]
Caroline Tol bert,Karen Mossber ger,Ramona Mc Neal(2008)的研究为地方政府创新或政策创新提供了一个多重维度的分析视角。他们认为,“不同时期对于政府创新的动因的研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具体而言,早期的研究只有‘创新的采纳’这一个维度,随着电子政务的发展,创新动因的研究维度也日趋多元化,包括创新政策的质量、范围、复杂性、持续增长程序等等”。[8]
Richar d D.Bingham(1978)利 用Downs 和Mohr提出的创新决策模式来研究创新采纳。他通过对1960 年人口在5 万以上的美国城市的住房机构、学区、公共图书馆和市政府进行分析,检验了方法创新和产品创新,确定和衡量了决定地方政府采纳创新的因素,同时检验了公共政策和创新采纳在地方官僚组织中的关系,并研究了创新采纳的顺序和过程。
Faribor z Damanpour(2009)使用美国725个地方政府采用25 项创新的调查数据和专家组的数据对公共组织中的创新特征、管理者特征和创新采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特征和管理者特征都会影响创新的采纳;然而,他们并没有揭示管理者特征对创新特征与创新采纳之间关系的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发现有利于推动公共部门创新采纳的相关研究作进一步的讨论。J.Victor Baldridge 和Rober t A.Bur nham(1975)认 为,创新扩散研究应从个人向组织结构和环境因素转移。
三、政府创新的实践
关于政府创新实践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各国已有的政府创新奖项目的案例进行研究。例如,Bor ins(2009)介绍了美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并构建了具有一定分析力度的政府创新概念框架,对政府创新进行了全方面的讨论,包括经验介绍、国际比较、概念发展、现有成就与不足和未来发展趋势等。
第二类是地方政府创新的比较研究。Borins(2000)就通过对美国的地方政府创新奖和加拿大设立的公共管理创新奖的33 项申请个案的比较分析,讨论了二者公共管理创新的特点,其中包括了对公共部门创新的特点、组织创新的起源、创新源于计划还是摸索、创新面临的阻碍以及克服办法、创新取得的成果以及其是否能够被复制等一些问题的讨论。El aine Kamar ck(2004)回顾和梳理了过去几十年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政府创新实践,并指出虽然各国政府改革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政府的改革与创 新 是 一 种 全 球 现 象。 Pär na O 和 von Tunzel mann N(2007)从公共服务创新过程中学习和管理两个维度出发,对英国、丹麦、芬兰和爱沙尼亚四个国家的公共服务创新进行了实验调查和比较分析。其研究表明,与创新相关的学习和内部管理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创新,且国家特定的差异也在影响着公共部门服务的创新过程。Vigoda-Gadot E等人(2008)利用对欧洲八个国家的公共部门发放的626 份有效问卷,从公民的角度考察了影响欧洲公共部门创新的因素及其带来的影响,并试图总结出一种可以概括欧洲公共部门创新的理论模型。其研究表明,“公民对行政领域中‘响应性’和‘领导力与愿景’的看法是影响公共部门创新的重要因素;而公共部门创新又影响了公民对公共行政的信任和满意度”。[9]Ar undel A(2015)等人根据2010 年对欧洲3273 家公共部门机构的调查,利用因子和聚类等分析方法总结出自下而上、知识扫描和政策依赖三种类型的创新方法。Tor ugsa N(2016)等将公共部门的创新分为政策创新、服务创新、交付创新、行政和组织创新以及概念创新五个方面,并通过对澳大利亚政府雇员的问卷调查数据检验了这五个维度带来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类是从技术层面对地方政府创新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电子政务。Ghyasi 和Kushchu(2004),Pot nis D D.(2010)提出了创新管理评价体系(IMMF),评估和分析了当时各国电子政务的基础条件和发展状况,并提出了六项相应的改进意见。Ant t ir oiko A V.(2010)介绍了Web 2.0 及其在公共服务和治理中的逐步采纳,并指出政府在其治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遵循着Web 2.0 的逻辑;Cr iado J I 等人(2013)介绍了社交媒体在电子政务基本领域的作用,包括政府信息的可用性、创造和提供创新的政府服务等,并进一步提出和发展了政府社交媒体中的工具、目标和主题;Mor abito V(2015)通过对巴塞罗那的智慧城市建设和海地政府在地震期间的应急管理两个案例的研究,讨论了由大数据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转变;Meij er A(2015)提出了一个关于电子政务创新的理论模型,并利用荷兰警方与公民合作的技术系统的案例对此进行了探讨,该模型强调了创新过程中的阶段以及政府、公民、结构和文化可能对创新带来的阻碍。
四、总结及愿景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政府创新在西方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进展较快,研究内容日趋精细化。具体表现在:
一是从政府创新内涵、类型和特点方面,将创新、政府创新和企业创新等概念进行区分。相比一般创新,政府组织的创新并不一定指的是新事物的发明,采纳一个新项目、新政策或者做出对于政府组织或与其相关的环境来说的新改变也属于政府创新;而相比企业创新,政府创新在目的上是为积极回应公众需求、提供公共服务,以提高政府合法性,而非追求私人利益。因此,已有关于政府创新的研究在借鉴有关创新和企业创新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政府总结了出各种类型的政府创新形式,并概括出一些政府创新的特点。
二是学者们着重围绕政府创新环境、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者特征进行成因和动力探讨,并研究政府创新的历史演进趋势、可扩散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创新扩散带来的变异、后果和影响等。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政策创新领域,并试图通过大量实证对政策创新的动因及扩散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
三是政府创新的实践方面,侧重于在地方政府创新的海量案例库上做实证研究,并着眼于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和创新对政府绩效的影响等进行研究。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于某个特定国家的创新案例库或者某特定区域的联合创新项目。在分析方法上,更加强调实证研究,但以案例研究为主;在研究对象上,较多关注技术层面的政府创新,其中电子政务就备受关注且其已突破传统电子政务的概念和形式。
然而,目前的政府创新研究也存在几方面的不足:
一是规范性研究有所欠缺,在概念、内涵和评估标准等方面缺少必要的共识和基本观点。由于缺少共识,当前研究对于创新的评估和测量标准还不明确,政府创新理论较多借鉴企业创新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实证研究,多为即时性的政策研究、个案研究以及针对大量“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多案例分析和较少大样本的量化研究,过于强调对实践的解释也导致了理论的碎片化,容易出现“一个案例,一个理论”的现象,概念和理论之间难以有效对话。
二是缺乏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研究路径之间存在话语区隔。政府创新理论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研究范畴,不同学科都有所涉及,包括行政学、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虽然当前研究也在尝试将这些学科中发展得较为成熟且具备一定分析力度的理论引入到对政府创新的研究中,例如利用组织行为理论或者交易成本理论来分析政府创新的动力机制,但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拿来主义”或者“浅尝辄止”,研究者们通常急于采用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来分析政府创新而忽视了知识的积累,因此也难以有理论上的突破。同时,目前这种跨学科的多元化研究也相对较少,研究层次和话语体系都有所不同,学科之间难以对接,无法形成有效的理论交流和互补。
三是全球化视野有所不足,对全球性政府创新实践的关注不够。目前大部分实证研究立足于地方性、本土性的创新案例和创新实践,而鲜少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创新行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全球流动性的加快,政府创新向全球范围的扩散和采纳行为也在迅速增加。这种全球范围内政府创新行为的动力机制、扩散机制,以及创新行为在当地的变异和影响呼吁理论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四是在研究主题上,国外关于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和制度化问题的研究较为欠缺;对政府创新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的关注也较少。由于政府创新在实践方面有较多案例,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往往都集中于对过去积累下来的案例资料进行内容分析或者将大量案例进行量化分析,因此在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方面关注较少。政府创新究竟是可持续的还是昙花一现?较少学者通过对过去的创新案例进行回访或跟踪调查来进一步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力及其制度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此外,目前的研究也比较偏重于对政府创新内外部宏观因素的研究,例如政府组织内部特征及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环境,缺乏对微观作用主体的关注,例如在政府创新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利益群体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