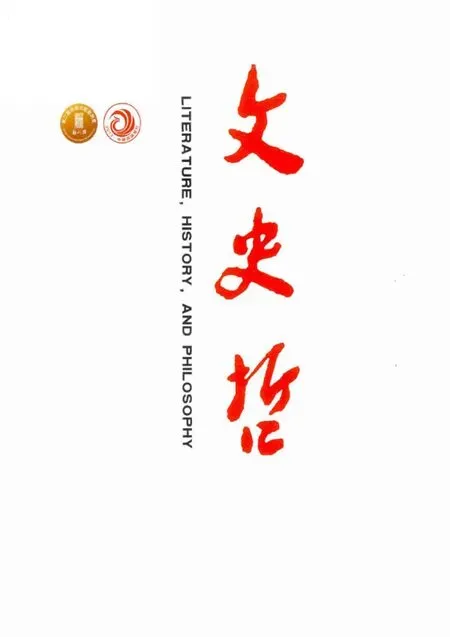“人对自身情感的责任”的现象学前提
——早期萨特情感理论的核心承诺
徐法超
关于人类的生存活动,自古以来就有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争,讨论我们是否能够以及——如果人毕竟是自由的——如何决定自己的行为和存在方式。只是,在常见的形态中,人们并不坚持某种强势的自由意志或决定论主张,也即并不坚持人是完全自由的或完全被决定的,而更倾向于维持某种形态的二元论立场:人在某些生存活动中是主动的、自由的,在另外一些生存活动中则是被决定的。在最普遍的倾向中,诸如判断、推理和自愿行动等等,被认定为人类灵魂的自主运作,是属人的活动,体现着人的自由。与之相对,感知、激情等运作则被认定为人类生存中的被动方面。人们把它们归于本能、动物灵魂或某种机械论意义上的、对象化的身体,其运作归属于决定论的领域,人类在其中并无自由。如同萨特所指出的那样:

这种二元论构想深刻地规定着我们对于自身存在的领会。比如,在关于我们的情感生活的惯常想象中,那些激烈的、不可自制的情感反应往往被等同于某种自然过程。人们倾向于认为:激情(passion)是生物本能或人的形而上本性等等在外在刺激下的被动反应;我们在激情中是不自由的,因此不能也无须对它们承担责任。关于情感生活的传统哲学讨论(除了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等少数例外情况),因此也往往放弃承担论证“人对于自身激情负有责任”的任务。传统哲学在这个议题上所涉及的显赫或最本质的问题仅关乎如何处理“不受限制的自由和被决定的心理生活过程之间的关系:如何控制激情,如何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利用它们”[注]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569.。也就是说,它们倾向于如同对待一种自然现象一样,外在地对待我们的情感活动。然而,以这种方式对待我们的情感生活,不仅会(1)使我们无法获得关于人类存在之本性的融贯解释;也(2)使得内在地,或在阿奎那的意义上,“高贵地”控制我们的情感成为不可能。

在本文中,笔者要求自己克制这种“自然”反应,着力辨析萨特上述论断的确切涵义,检视它们是否有其(现象学)依凭。如果萨特关于“人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的论述被证明有其合理性,那么,它就不但是解决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争的重要探索,而且必然会加深我们对情感本性的理解,而开启与各种情感科学深入对话的可能性。
一、传统二元论假定所面临的困境
如果人类的存在被描述为“一个被规定的整体过程包围着的自由能力”,自由的行为仅等同于自愿的行为,感觉和激情则归属于被规定的领域,那么,人们似乎就只需为自愿行为负责,而无需承担对于自身激情的责任。比如,我们似乎对自己在凶猛的野兽面前的恐惧无能为力,无法为自己在长途跋涉后的身体的疲倦负责,不能随意地改变我们对食物的偏好,等等。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但在萨特看来,这种对于人类的存在方式的刻画包含着根本性的困境,因为它在“人的实在”内部设立了某种无法克服的二元性。如果激情被宣布为处于决定论的领域,其发生表现为一种不依赖于意识的建构与参与的自动性,那么,它与(作为纯粹自主性的)理性、意志就属于不同的存在类型,我们的心灵也就被分割成了两个相互不能通达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心灵的统一体(l’unité psychique),一种自发性的活动就会成为无法设想的:
无法想象,一个作为“一”的存在,却在一方面作为一系列互相限定的事实被建构起来,而在另一方面,又能作为决定自己的存在并只揭示自身的自发性……[注]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570.
作为异质的存在类型,激情与理性、意志之间无法相互规定和影响。一方面,物质的、自在的存在无法影响和规定精神的、自为的存在。如果激情是自在的、机械性地发生的,那么,它就根本无法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意志。另一方面,我们的意志也将无法(内在地)干预自在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自发的活动是无法设想的。更一般地说,如果“人的实在”必须被假定为这两种存在形态的某种综合,则关于其存在只能有两种结论:
要么人是完全地被规定的(这是不能被接受的,特别是因为一种被规定的、即被外在地产生的意识将成为纯粹的外在性本身,而不再是意识了);要么人是完全自由的。[注]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571.
换言之,如果一种自发的行动毕竟是可能的,或一个心灵统一体是可以设想的,则人就必须是完全自由的,其所有的生存活动——包括情感活动——都必须被理解为自发性活动。西方传统在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所建立的严格区分必须被放弃掉:“一种对于自发性的现象学描述,将使得在行动和激情之间的任何区分,以及任何关于自主的意志的概念不再可能。”[注]Sartre,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 trans. by Andrew Brow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27.
这种推论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要论证人是完全自由的,就必须证明“人的实在”的所有存在形态都是自由的。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任务就是证明:人在(通常看来不自由或不包含主动性的)情感活动中,竟然是自由的。而这正是萨特对情感活动的现象学考察的首要目标。
二、对情感现象进行决定论解释的内在因由
在指明了上述二元论解释的困境之后,萨特开始究查这种传统的关于我们的情感生活的决定论解释的内在因由。如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在对情感生活的解释中,决定论或者说机械因果论的立场通常更具吸引力。人们更习惯于对之提供一种生理学的、机械论的解释:是我们的生理机制,或我们的生物性遗传、教育、阶层、童年生存经历等等决定了我们面对特定的事物时的情感反应。萨特把这些立场都归于一种心理决定论,其本质是:通过把意识与连续的无定限因果序列看成相似的东西,把意识移交给存在的充实体,由此使它进入存在的无穷整体。也就是说,“人的实在”的存在被刻画为一种充实的、连续的过程,意识的作用或我思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由此,人成为一种惰性的、物性的存在,成为具有固有状态、性质和特征的存在者。同时,心理决定论假定,正是这些状态、性质和特征决定了我们对于特定事物的反应——我的过去决定了我当下的活动——以至于我“不能不这样做”(could not have done otherwise),不得不如此感受世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显然不能也无须为我们当下以至所有的存在方式负责。于是,在萨特看来,一种在心理决定论形态下对人的存在的描述,实质上是为放弃我们对于自身存在方式的责任,逃避我们的自由而诉诸的自欺的辩解。
而成就这种自欺的辩解的认识论依据,是人们从“他人的眼光”——或者说“自然态度”——出发描摹“人的实在”的存在,把人的生存活动描述为一种发生在实体间的因果性活动:某种外在的刺激作用于具有特定状态、性质、特征的实体性自我,产生出确定的反应。相反,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在这种立场中确立的诸如状态、性质、特征、实体性自我等概念,实际上都是一些虚构的心理学偶像,误解了“人的实在”的存在或意识行为的现象学实情。萨特指出,意识(或“人的实在”)在其真实的发生中,总在指向对象的同时表现为“面对自身在场”,表现为内在否定的结构,而不是某种不包含自反结构的、与自身无间距的自在存在。因此,没有任何自在存在——无论外在事物还是我的过去、我的邻人、身体、语言等实际性(facticity)——可以决定意识的存在,意识在任何时刻都必须承担、选择自身。换言之,人的所有生存活动,只要在指向对象的同时表现为一种“面对自身在场”的自反性结构,就在萨特的意义上是自由的,要求我们承担对于它的责任。萨特宣称的人的“绝对自由”,要求“人对于自身的所有存在方式负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论的。当然,为了论证这种观念,萨特需要揭示“人的实在”的所有存在形态——尤其是我们的情感生活——都在指向对象的同时表现为一种“面对自身在场”的自反性结构,而不为自在存在所决定。
在我们的生存实践尤其是自愿行动中,可以轻易地找到支持上述立场的证据。萨特举过一个关于赌徒的例子。当这个赌徒又一次站在赌桌前时,他对于自己的处境和存在可能性总有某种反思或前反思的觉识。他知道自己可以坐下来赌几把,也可以毅然离开。之前戒赌的决心并不能决定他不再回到赌桌(正如他赌博的习惯也不能决定他再次坐到赌桌前一样),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选择。他在此是自由的,被迫地、命定地自由的,因此也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然而,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情感生活领域中时,人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含混迟疑。我们觉得:自己是被情感袭临;我们在其中是被动的;我们对其无所作为;它似乎是机体、动物灵魂、无意识机制等等的运作,我们只能外在地控制它……总之,它们被理解为是机械地、非理性地或无意识地发生的,不包含某种“面对自身在场”的自反性结构,从而不是意识的某种有机形态。只是,如同前面指出的那样,一种融贯的关于“人的实在”存在的构想,要求人们打破主动与被动之间的界限,以便能够证明我们即便在情感生活中也是自由的,或者说不是纯粹被动的(这样的说法比较容易让人接受,但所宣布的仍是和萨特一样的诉求)。
实际上,这种诉求在各种传统哲学体系中也一直被隐秘地坚持着,只是没有成为人们理解情感的明确方向。比如,笛卡尔在其关于激情的解释中,就表现出消解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严格区隔的意图:“尽管施动者和被动者通常非常不同,但行动与激情则总是一个东西,是依据两个不同的相关主体给出的两个不同的名称。”[注][法]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贾江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页。而他在《论灵魂的激情》中所提供的,依然主要是一种机械论的解释方案。或者说,某种顽固的自然主义倾向支持着他(以及西方传统哲学主流)对情感采取“实体因果”性解释,从而阻塞、遮蔽了对这种立场进行明确、融贯之论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直到现象学运动兴起之后,才渐渐显豁出来。
三、“人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的现象学承诺
现象学运动在其早期阶段就萌发了考察情感活动之本性的意愿。在《逻辑研究》中,为了证明意识行为的一般结构,胡塞尔提出了对感受领域的意向性特征进行论证的要求。舍勒则在其建构一种质料的伦理学体系的目的下,揭示了意向性感受的特有的意向对象——价值,并对各种层次的感受进行了系统的现象学考察。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存在论刻画,也提供了关于人的情感生活的深刻的“生存论存在论”规定。尽管这些研究都不是直接以论证我们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为目的,但它们给出了一种区别于自然主义立场的、关于感受活动与其对象之间关系的理解,从而为萨特看似激进的主张提供了重要前提。

这样一种立场,已然使任何将感受把握为单纯被动性的尝试变得不合法。这却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如同萨特那样,承诺我们在情感中是自由的,对于自身的感受负有终极责任。因为,人们完全可以在承认经验结构与世界结构之间的对应性的同时,否认我们对自身与对象的意向性/超越性关联的建构负有责任。实事上,在一种普遍的倾向中,海德格尔以及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诸多自觉地回避意识哲学的思想、思潮,更愿意强调我们与对象的超越性关联是被给定的,是被存在的天命、文化的深层结构或社会的型塑等等所设定的。换言之,我们已经被抛进与存在者的特定存在关联中,这种关联决定着事物向我们呈现的可能方式,也因此决定了我们遭遇它们时的感受。
反过来讲,这也就意味着,要主张我们对于自身感受的责任,就需要承诺更多的东西:不仅要承诺具体的感受行为中包含着基本的主动性,而且要承诺我们可以不完全遵循社会给定的自身与事物的意向性/超越性关联,甚至参与它们的设定(用情感社会学的概念讲,参与制定制约人们感受和表达规则的文化脚本),从而不能把决定我们与事物的意向性/超越性关联——也即世界向我们显现的方式——的权责完全交付给“客观”的社会、文化结构或存在的天命。我们看到,萨特试图强调:恰恰是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必然会在某种意义上改变这种关联,“人总能够创造出某些用以塑造他的东西之外的东西”。而个体何以能够通过选择和行动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存在关联,从而改变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无疑是辨析萨特论断合理性的关键。在此,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与海德格尔的相关观念加以比较,凸显萨特的立场。
在思想主题或格局上,萨特与海德格尔具有明确差别。如同杜小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萨特所热烈关注的,认为海德格尔为他提供的“人的实在”的思想,海德格尔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这是两个人的最终“境界”的不同:萨特关心的是“人的存在”,而海德格尔则是要追寻那个最本原的“存在”。[注]杜小真:《存在与自由的重负:解读萨特〈存在与虚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进一步讲,萨特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是“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他坚持历史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物,断定“意识”“能动作用”“选择”“责任”等等对于理解历史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与海德格尔等反人道主义者所坚持的“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的观念恰好相反。
将上述观念贯彻到对于情感本性的考察上,在《时间概念史导论》和《存在与时间》之中,一方面,海德格尔满足于揭示现身的“生存论存在论”含义,满足于把它确定为此在在世的一个组建环节,而并没有就现身与“自我”或萨特意义上的“人的实在”(作为海德格尔的Dasein的主体化)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在谈论现身的“生存论存在论”含义时,海德格尔强调的始终是其对于我们的“被抛境况”的揭示作用,强调任何对于现身的理性把握都把现身把握得太浅薄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反省不足以穿透感受发生的存在论机制,从而不会承诺个体在决定世界之向我们呈现的方式上拥有自由[注]当然,这里的自由概念显然比萨特的“本体论自由”概念具有更多的实践承诺。。
与之相对,萨特思考的起点是我思或人类主体,强调世界的意义总是相对于前反思的我思呈现出来的,他关注的也始终是我思/人的实在在世的具体方式。依据这种关切,他指责海德格尔“从此在中剥夺了意识的范畴”;指责他从未提及人除了是一种对于存在有所领会、有所承担的存在者外,也是一种由于其谋划而使世界产生本体上的改变的存在者。从海德格尔的立场出发,要寻求存在的一般意义,揭示存在的真理揭蔽的机制,并将我们的存在境域的根由追溯至存在者整体、追溯至存在本身,则必须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剥夺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因此,抛开对于具体的意识体验的考察,不对个体之于自身、世界的责任提供积极的主张,在海德格尔这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萨特而言,从处境中的我思出发,很容易发现个体的选择与行动对于其自身处境、自身以及世界的存在方式的影响,或者说对于我们与事物的超越性关联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我终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皈依后的我与权力金钱以至整个世界的关系自与皈依前不同,世界也会向我呈现出不同的行动要求。再如人们学习狩猎技能,装备武器,或借助各种社会手段驯化自然,这样人们就不必再像我们的先人那样,把山林当作凶险而需要规避的对象,而是把它们当作欣赏和游玩的处所。换言之,世界总是基于我们的自我选择和行动,向我们呈现出特定的活动要求。正是这个意义上,萨特强调我们对于自身存在之处境或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方式负有责任:

萨特并没有粗暴或轻浅地认为,我们的某一个选择、行动甚至认知的变化,就足以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改变世界之向我们呈现的方式。相反,他宣称,是我们反复选择的自己所是的欠缺结构或者说基础谋划,决定着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方式。当然,这种欠缺结构或基础结构并不是自立的,它总由意识固有的虚无化能力敞开、维持以及引发变更。要之,由于感受源于对我们的存在处境和应对它的倾向的复杂觉知,处境又相对于我们的谋划呈现自身,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感受承担责任。至此,我们获得了萨特论证“人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的基本框架。但为了更确切地把握萨特的立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在激情中是自由的”以及“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等论断实际上承诺了什么。
如同前文指出的那样,为了维护其绝对自由观念,萨特需证明“人的实在”的所有生存活动都是自由的。在我们的情感生活中,他需要肯定的不只是“我们在激情中是自由的”,而是我们在所有的感受活动中都是自由的。即,我们不仅在那些可以主宰、控制的情感活动中是自由的,在激烈的情绪中,在心境、在紧张、松弛、疼痛等非意向感受中依然是自由的。早期萨特情感理论的核心部分,实际上就是为此提供论证。不过,他对于我们在感受活动中的自由的承诺,在实践上是非常有限的,或者索性与“获得的自由”无关。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一方面,他宣称我们在意向性感受活动中是自由的,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面对自身在场”的意向性结构或者说“前反思的意向性我思”。这也就是说,情绪总是指向某种对象或处境,把这种对象或处境把握为(建构为)对于自身活动的要求,情绪活动即对于这些要求的特殊应对方式。同时,我们也总对自身活动保持着前反思的自我意识,对于自身活动的可能性的不同觉知,将根本性地改变情绪活动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情绪活动绝不表现为单纯的被动性。另一方面,无论意向性感受,还是心境、感觉等非意向感受,都在我们的基础谋划中,或者说在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中获得规定。我们的基础谋划,或者说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并不是自立的。我们不得不选择和行动,而选择和行动又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种谋划或关联,从而改变我们对于特定事物和处境的感受。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所有的感受中都是自由的。
必须明确,早期萨特对于我们在感受中的自由的承诺仅止于此,即:我们在感受中的自由仅仅是一种本体论层面上的自由,而非“实践的自由”或者说“获得的自由”。举例说,萨特会肯定:只有我不再安于贫穷,我的贫穷才会难以忍受。我努力获取财富,而在享受了珍馐美味、锦衣华服之后,就可能觉得之前的粗茶淡饭不好吃,粗布衣衫不舒服。但萨特不会承诺我想要不再贪慕虚荣,便即可不再贪慕;不承诺我们努力尝试获取财富便可获得财富,即使富贵了也不必然觉得粗茶淡饭不好吃;等等。换言之,萨特并不承诺人可以随意地改变情感活动的发生进程,改变其发生的“生理物理”机制。进而,他也不承诺我们拥有通过理性运作,笃定地达到对待特定事物和处境的特定感受的自由。
相应地,萨特要求我们担负对于“自身以及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的普遍责任。我们不只要对自身的理性、自愿的行为负责,也要对激情等非自愿行为负责。进而,由于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总会参与引发世界的本体论改变,我们需要“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不过,他之要求我们承担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并非因为感受是我们自愿决定的,而是因为:首先,自为总表现为“面对自身在场”的自反性结构,总在指向对象的同时也是对自身的前反思的自我意识,这样一种主体性结构保证我们有介入自身意识过程的可能性;其次,我们的(不能确知其结果的,又不能不进行的)选择和行动必然会在某种意义上影响我们的谋划、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从而影响我们面对特定对象或处境时的反应和感受。于是,这里的责任概念也有别于人们通常赋予它的含义。我们不止应该对那些取决于我的自愿行动负责,而且应该为我们的选择和行为引发的不确知结果负责。在萨特的比喻中,他是在“(对)是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对象的无可争辩的作者(的)意识”这个平常的意义上使用“责任”这个词的。一本书,在其流传中总已经脱离了作者的控制,会衍生出诸多作者不可预期的解释和结果。但毕竟是作者的创作使得这些解释和后果得以可能,故而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尽管不是完全责任。在这个特殊的意义上,我们确乎无由逃避对于自身感受的责任。
四、对萨特立场的评估
根据以上对萨特立场的阐述,萨特关于“我们在情感中的自由与责任”的诸论断,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违逆常识,它们尤其可以与那些包含社会历史视野的情感观念达成和解。一个个体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基础谋划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意向的改变,其感受、应对世界的方式自然会发生改变。其间,个人的选择和行动自然是成就这种改变的决定性力量。与此同时,所有个体参与其间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流变,必然会改变我们的生存处境,改变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从而改变我们面对特定事物和处境时的感受。实际上,这也已经是发展心理学、情感社会学等情感科学自发贯彻的立场。只不过,它们不曾如萨特般“激进地”宣告: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自己面对事物时的特定情感反应,我们应该承担对于自身感受的责任。
同时,萨特冲决决定论或二元论解释,坚持“人的实在”对于自身所有存在方式(当然包括感受活动)的责任,正是依赖于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启示的某种特殊综合[注]根据在1947年向法国哲学会宣读的论文中说法,他试图“把胡塞尔的静观的和非辩证的意识与我们在海德格尔著作中发现的那种辩证的但却是非意识的(从而是无基础的)设想综合起来,前者使我们静观本质,后者则让我们发现首先要因素是超越”。转引自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477.:海德格尔激励萨特把“人的实在”的所有存在形态收纳到其在世存在活动整体之中,从而使“人的实在”的所有存在方式的统一成为可以设想的。在胡塞尔的方向上对于意识结构的深入考察,则支撑着他对于意识“面对自身在场”的主体性结构的坚持。换言之,萨特在其特有的意义上要求“我们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其立场拥有切实的现象学依据。
或许是因为揭示感受活动的基本主动性的任务太过急迫——在情感生活的被动性特征得到了普遍以至非法的强调的情形下——早期萨特没有充分地论述情感活动中的被动性、延续性特征。是以,人们普遍会对其理论产生如下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选择我们的信念和思想的方式选择我们的情感。”[注]Robert C. Solomon ed., Thinking about Feel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3.或者说,我们似乎可以轻易地,甚至随机(by chance)地变更对于特定对象、处境的感受。另外,萨特热切伸张的“人对自身情感的责任”,仅仅是本体论层次上的。至于在具体的生存实践中,我们应在何种程度上承担、以及如何承担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早期萨特显然无暇顾及。于是,抛开那些粗暴的外在批评,人们对早期萨特情感理论的指摘就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轻忽了对于情感生活的被动性、延续性的探究。
这种观点的最鲜明的代表是Joseph P. Fell。尽管他对萨特的情绪理论寄予了很大的同情,肯定萨特对于我们的情感生活的间断性、主动性特征提供了精致的说明,但在与杜威、怀特海(以及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比较中,Fell指责萨特不能充分地说明我们的情感生活的被动因素及其稳定性:
作为一个整体,萨特哲学的最深刻和基础的吸引力在于它寻求分析人类在何种限度上是脆弱的、非实体性的、不确定的、革新的,与世界和其过往是间断的。这是任何一种关于人的完备理论的必要方面。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尤其在讨论情绪问题的时候[注]Joseph P. Fell, Emotion in the Thought of Sart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238.。
相应地,在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中,萨特的情感理论被认为只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认知主义情感理论(cognitive theory of emotion)。即他与经典的认知主义情感理论分享着共同的基本假定:我们对世界的情感反应源于对自身处境的判断(judgment)。萨特的情感理论因此也经常被指责为:只强调情感活动中的认知因素,忽略了或无法把身体维度(以及其他“实际性”要素)结合到对情感活动的描述之中,以至于难以使之与其他的对于意义的非情感性的判断或自愿的行动(action)区分开来,也难以说明那些顽固情绪(recalcitrance)的存在。
(二)不能对我们应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承担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或者说控制自身的情感生活、改变限定情感体验和表达规则的社会文化脚本的方式——提供确切的规定。
由于专注于论证本体论层次上的自由,而不是究查“获得的自由”的现实可能性,早期萨特并没有开展对各“实际性”要素制约我们生存活动的方式的深入分析。因此,他对我们在各种生存方式(包括情感活动)中的自由和责任的规定,就显得空泛而含混。如同梅洛庞蒂所指出的那样:萨特所宣称的“我们具有改变我们的原始谋划的可能性”——这是支撑萨特的自由观念的核心论断——中的“可能性”,是一个混杂的概念。因为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程度的;无论自由行为不再可能,或仍然可能,自由都是完全的。简言之,‘可能’是无意义的。”[注]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by Colin Smith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513.因此,我们在不同感受活动中的自由与责任也是含混而未加区分的。相反,梅洛庞蒂则倾向于对我们在不同活动中的责任作程度上的划分:某些存在方式是依赖于我们的选择的,另外一些则不能归于我们的选择,虽然它们都依赖于意识才可能发生;另外,外在的阻挠或胁迫也会制约我们的选择的可能性,如此等等。在相似的意义上,在现实的生存实践中,我们在情感生活中的不同程度的主动性也应该加以区分。与萨特含混地宣称我们有绝对的自由与责任相比,这些区分显然更具实践品格。在这样一种含混中,我们控制自身情感生活、参与改变限定情感体验和表达规则的社会文化脚本的方式,自然得不到实践性的规定。
萨特情感理论的上述欠缺,最终又会被归结于其方法论选择(如果不是其存在论设定的话)。除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对其主体意识哲学倾向的一般性指责外[注]德里达和福柯都表达了对于主体意识哲学的抵触,他们也对“主体的自由”或“意识的自由”概念保持警惕。但是,德里达所指出的“我对‘自由’这个词是不信任的……因为这个词,往往包含对主体或意识(即以自我为中心的逻辑主义)过多的幻想的形而上学假设,似乎这些主体和意识具有不依赖于冲动、计算、经济和机器的独立性”时,我倾向于认为,对萨特的自由学说的核心主张并不构成挑战。相反,萨特之强调自由是“人总能够创造出某些用以塑造他的东西之外的东西”的主张,与德里达“自由是指超越一切机器游戏,超越一切决定论机器游戏的‘过度’”(转引自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上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页)的说法,是相契合的。,那些本质上同情现象学的思想者也会判定,萨特的现象学方法本身不足以为人类生存活动(包含作为特定在世方式的情感活动)提供一种完备的解释。随着人们对现象学方法论合理性范围的省察的深入,以下观念愈发明晰:单纯凭借对于意识的现象学反思,不能完全把握我们的历史性的生存结构和机制;要实现这个目的,应该把现象学的直观描述方法和其他学科视角有效地结合起来。比如,利科的解释学方案,强调一种在现象学方法之外的结构主义或符号学研究的必要性,强调应该依据那些散落在世界上的符号,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把握人的在世存在的结构。而在那些试图综合现象学与社会学启示的意愿中,萨特情感理论的方法论欠缺就更为明显。根据吉登斯的观察,萨特的现象学实践,作为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首要关注的只是行动与意义,对于制约我们的生存实践的社会结构少有涉及,因而无法细致地刻画我们的生存活动(包括情感活动)发生、开展的现实机制。与此同时,当下学界综合现象学与精神分析、神经科学、历史文化研究以考察我们的情感生活的尝试,也都是修正这种方法论缺欠的努力。
于是,尽管我们可以用以下理由为萨特辩护:一方面,早期萨特的情感理论从属于论证其绝对自由观念这一首要任务,因此,上述要求超越了早期萨特情感理论的核心目标与承诺。另一方面,虽然萨特没有展开对制约我们的情感生活的要素的经验性考察,但其情感理论并不拒绝向这些考察敞开。在《情绪理论纲要》中,他强调,“人的实在”的“实际性”使得我们在考察情感现象时“必须惯常地诉诸于经验”[注]Sartre, The Emotions: Outline of a Theory, trans. by Bernard Frechtman (New York: Carol Publishing Group, 1993), 94.。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确切地规定我们在自身情感生活中的自由与责任,了解控制我们自身情感的方式,那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萨特已经提供的启示,而必须进一步考察情感活动发生的结构性要素及其内在关联,考察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的再生产和变更的机制。
关于第一项任务,特纳等情感社会学家的工作尤其值得重视。至于第二项任务,福柯等引领的文化哲学、各种试图包容解释社会学立场的社会学思想等等,都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启示。这些研究,更为充分地考察“人的实在”的“实际性”或社会文化力量对其生存活动的制约,也具体地描述了行动者超越这些制约的可能性和方式。比如,吉登斯在其“结构化”(stucturation)理论中,把我们的行动或社会实践描述为包含对行动的自我监控、理性化及动机激发的一系列过程——它们受到各层次的结构性制约,但结构性制约总是通过行动者的动机和理由发挥作用——并把这些“紧密渗入时空的社会实践”确立为“同时建构主体和社会客体的根基”[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3页。,从而确立了一种从具体的社会实践出发,分析社会规范再生产及变更机制的方法。可以看到,这样的立场,本质上与萨特在其主体意识哲学形态下阐发的自由观念并无冲突,却又提供了分析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的再生产和变更机制的手段。如果能够将它们结合进现象学对于情感的存在论规定之中,那么,“我们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问题,必然会获得更为系统、深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