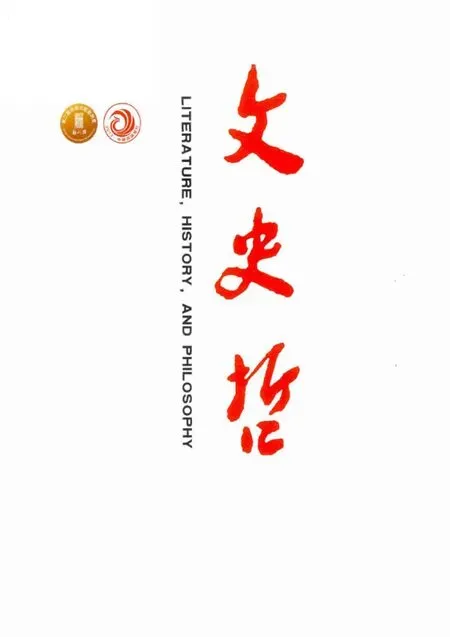在王权与教权之间
——论欧洲中古后期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及其体系
顾銮斋
中古后期,基督教教会学者立足教会和国家的政治现实,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取得了重要成果。笔者考察后发现,这些理论虽参差不齐,多有瑕疵和缺陷,一经收拢聚合,却也互济互补,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一体系由珍重生命起始,以作为个体的人的基本权利立论,经“同意”或“共同同意”的路径,推至两个并立的权力顶端,形成了对王权和教权的限制与约束。体系的形成,使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贯彻,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克服了重重险阻,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拟对这些理论及其体系作一概要的探讨,主要考察和分析这些理论的指向、目标、制度设计以及体系的构架、层次、实践与历史影响,以获得一个整体的概念,同时也就学术界讨论多年、似已形成定论的几个问题如会议至上主义运动、教皇专制主义提出管见。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客观认识教会学者的理论和体系,公正评价中世纪基督教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一、立论的起点



教会学者的权利意识无疑是强烈而敏锐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理论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有一定的东方文化背景,对这种意识和价值就不难感受和认识。如果情况相反,则无妨将视界放宽些,将目光聚焦东方宗教和教职人员的语境,或审视教俗知识精英的文化活动,那时你就会觉得,这种权利意识和理论价值在人类文明史上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也并不多见。

随着教会学者对自然法认识和思考的深入,特别是在自然法以自然权利作为基本内涵之后,所谓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也就成为教会学者政治理论建构的起点和基石。
二、理论的建构
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无疑表达了作为生命的人的最基本的诉求,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方式或途径实现这种诉求,以使生命获得适宜的生存环境。教会学者给出了答案,这就是“同意”的表达。因为按人的基本权利的概念,涉及作为个体的人的基本权利的事务需要当事人直接介入,这样才能反映当事人的意见或意志。

既已有“同意”的表达,教会学者的理论创新或升华表现在哪里?这些同意与12世纪以后的同意又有哪些不同?在笔者看来,古典文化、日耳曼文化和基督教早期文化中的“同意”,还主要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操作活动,因而,上述记录所反映的只是素朴的原生态特征,还停留在习俗的层面而未进入学理。或者说,作为一个意涵隽永的政治词汇,还几乎没有从具体的表决过程中剥离出来。古典文化中虽已有自然法的概念,也偶见自然权利的提法,但这些都还十分空洞、粗疏,特别是自然权利,几乎是一个空壳,是中古后期教会学者的理论建设,填充了这个空壳,赋予了相应的内涵。而无论作为遗产还是作为现实,这些原生态的“同意”只有获得了学术的设计和引导方能健康成长,结出硕果。这正是中古后期教会学者的使命。
教会学者的自然权利将人的基本权利作了最低限度的界定,即作为个体的人至少应享有这些权利。人们需要选举权、需要信仰权,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人们需要吃饭壮体,需要穿衣御寒。没有这些权利,前面的权利再好也都是空洞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又提出了穷人的基本权利的命题。遗憾的是,这些在古典文化、日耳曼文化和早期基督教文化中都没有触及,斯多葛派哲学家在意识到人的平等问题后就止步了。而如果仅仅有同意的形式而缺乏应有的内涵,所谓同意,也可能走向机械的、只有形体而无灵魂的同意。在学术界,这种同意已经饱受争议和诟病,因为它可以在专制政体下出没,为政客和暴君所操纵,成为专制君主的统治工具,变成政治打手,遏制甚至窒息民意。不仅如此,“同意者”虽然表达了“同意”,却未必能表达本人的意愿和基本权利的诉求。这样,所谓民主的成长与发展,也就难免演为悲剧。由此可见,权利意识的敏锐和感知的准确是多么重要,自然权利的理论建设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意识和准确的感知为前提。

检索教会史可见,从这时起一直到14、15世纪,关于“同意”的讨论显著增多,这显然与教会学者对权利认识、思考和研究的深入有关,反映权利学术研究的新趋势。有些学者的思考甚至更加细致具体,以至触及了“同意的范围”问题。这里之所以将相关研究概括为“同意的范围”,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些事项的表决可以在几个或多个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会议中进行。一个涉及全民利益的事项如果仅由几个人表决,那么,这是一种寡头政治;同样的事项如果交由贵族表决,则是一种贵族政治。规模和层次的不同可以反映权利诉求的程度,表决的结果也通常因程度的不同而出现差异,这决定了范围选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了充分挖掘同意的资源和价值,教会学者注意了同意范围的选择问题。因为仅有公众的同意是不够的,它可能只是在较低的程度上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却没有将民主的资源和自然权利的价值充分表达出来。而选择的结果,是大多将这个范围扩大化甚至最大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民主意识。英诺森三世的教令在强调同意的重要性的同时,即将同意的范围最大化,所谓“征得公众的共同同意”,就是将乡村教堂堂长的选举最大化的法律表达。
必须看到,英诺森三世的教令实际上反映了时代的趋势和要求。而这种趋势和要求的形成,主要是由教会学者的思想意识和理论创新所致,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果缺乏教会学者的理论支持,或未经一定范围的同意,身为教皇的英诺森三世或许不会发布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教令,因为那样就等于铤而走险,将自己置于广大教职人员特别是教会学者的对立面,这显然是教皇所不为的。而我们之所以选取英诺森三世的教令集作为分析案例,是因为这样的材料能够反映基督教会思想意识和政治理论演进的一般状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由于教令集编订的目的之一在于规定下级或低级僧侣的纪律,普及率很高,以致英国许多主教教区逐字逐句辑录了这一教令[注]Ibid. 264.。

强调教会学者在继承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与创新,并非漠视古典文化、日耳曼人文化和早期基督教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在这里,所谓创新,是指继承前提下的创新;而所谓继承,是指对三种文化遗产的继承。没有继承,所谓创新是不可想象的。
“同意”是人的权利诉求的基本途径,是权利的体现。随着关于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长期而深入的讨论,“同意”等概念便被赋予了自然权利的内涵,久之,这些内涵便进入了人的观念层面。这样,如果说此前人们谈论的同意,还基本不存在自然权利或虽有存在但还很模糊,那么,现在只要提到这些概念,就是蕴含着自然权利的概念,自然权利也就在人们的心理中浮现出来。这由教会学者政治理论的影响所致,是历史的进步。

当赋以新的内涵并取得社会共识的“同意”由教会、社会和国家的最小单位同时启动并依托不同层次的宗教、社会组织或国家政区逐级贯通扩展、形成序列的时候,“同意”的构架也就形成了,而作为通达权力峰巅的介质的意义也由此得以凸显。同时,当这个“同意”的构架得到了教会、社会和国家不同的、众多的法律文件的规定时,所谓“同意”,也就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同意”的表达,对权利诉求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有助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宣扬与坚持。这种宣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提升民众素质,抑制政治邪恶,巩固和扩大所享权利,直接影响政治力量对比的格局,营造健康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政治环境,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使善政成为国家治理的常态。更重要的是,通过同意的表达,可以制约两个顶端权力,即王权和教权,减少恶政,营造优良的生存环境。
三、王 权
在教会系统,教父、教皇、高级教职、后来的会议至上主义者、包括一些普通教士在内的教会学者群体,都具有敏锐的理论意识,他们围绕权利的解读、讨论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蕴含着强烈的限制王权的精神。

教父、教皇理论中分权限权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但受时代或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局限,这些理论还只能致力于教会的独立或与国王的分权。这对后来教皇国的建立当然产生了影响,而且构成了后世教会学者政治理论的重要基础,并在教会史上居于隆崇地位。但是,它们却难以预测分权后王权的走向,更不能超越时代制约分权后的王权。事实上,教皇与国王两分天下并不能避免国王可以在世俗系统中走向集权甚至专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靠后世教会学者的理论研究、设计和实践。这样,这一历史的使命也就必然地落到12世纪之后的教会学者的肩上。

受这种强烈的分权限权理论的支配,在8世纪建立教皇国的基础上,11、12世纪的教会进一步扩大它的范围。而受封建扩张的挤压,各国王权都受到严重削弱,法国王室领地甚至仅仅局促于“法兰西岛”的一方之地。所以所谓封建,首先反映了王权衰微、私权林立、多元并存的社会现实。这为教会学者以分权限权为重要内容的法权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极大便利。再看这时的教会势力,已经几乎渗透到欧洲的每一个角落,教堂已成为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圣经》原典和神学著述更成为民众倚重的思想和精神支柱。高级教职如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副院长等,构成了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凭借作为教职身份的神学影响和崇高的文化地位,几乎垄断了宗教和文化活动,大部分文化工作如法规制定和文书起草等,几乎都由他们负责。而在世俗系统,相应事务也都少不了教职人员的参与,且因教会的行为在那时具有榜样的效应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西欧中古国家形成约束和限制王权的政治权力格局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这里,王权受到严重限制,与东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政治制度内容庞杂,这里难以面面俱到,而仅将论述的重点置于征税和立法两个方面,通过考察王权的地位和状况,来认识教会学者政治理论的构建和效应。赋税是国王和国家事业的经济命脉,没有赋税,任何事业都将一无所成;而法律,是国家和社会安定的工具,是王权实施和巩固统治的保障,也是测定王权性质的标尺,没有法律,社会和国家就会陷入纷乱甚至走向解体。二者对于认识教会学者这种政治理论制约下的王权状况,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同东方国家一样,欧洲中古国家的赋税征收也依据一定的赋税理论,这种理论有层次之分,我们将贯穿整个中古时代并反映这个时代赋税制度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的那个层次称为赋税基本理论。从本质上说,赋税基本理论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必然反映,但它是以教会学者为主体的时代精英顺应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赋税征收过程中勇于论争、勇于实践的产物。从这种意义上说,赋税基本理论也是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在赋税问题上的反映或表现。这种理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和共同同意[注]Refer to G. L Harriss, King, Parliament, and Public Finance in Medieval England to 136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S. K.Mitchell, Taxation in Medieval England; P. Spufford, Origin of English Parliament (New York: Barnes & Amp, 1967).。各部分都包括“共同”一词,蕴含着征税者与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之间个体、群体并立或分立的理念。比如一位伯爵、一位主教、一位国王都是一个个体,一个城市、一个行会、一个修院都是一个群体。所谓“共同”,是指国王的征税要求代表了各个体、群体而不仅仅是国王一己、几人或少数人的要求。在这里,相关个体和群体之间是一种分立的关系,而分立就意味着一定的平等,由此决定了制税过程必然是一个提出要求,讨论协商,有时是讨价还价的过程。而征收与否,最终取决于纳税人是否同意。
教俗封建主在赋税问题上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教会学者基于自己的知识和理论素养,具有表达这一诉求的优越条件。世俗贵族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理论素养,他们的利益诉求更多表现为一种本能的反应。但他们具有强烈的个人和民主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构成了利益诉求的内在动力,驱使这种本能的反应必须化茧成蝶,上升为理论。而要上升为理论,就必须有知识阶层代为表达,或在知识阶层的引领下进行表达。那么,世俗贵族是否需要教会学者为他们代言呢?这取决于他们在赋税问题上的诉求是否一致。教俗贵族本属于两个利益共同体,但在赋税征收以及与王权的关系等众多问题上,他们的诉求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在具体的征税过程中看得很清楚,因而决定了他们形成一致或合作的可能。另一方面,教会学者主要从事宗教活动,居于社会上层,掌握话语权,自然为世俗贵族所倚重;加之两者在与王权关系上的一致性,世俗贵族需要也希望教会学者将自己的诉求表达出来。而对教会学者来说,要使教、俗贵族的利益诉求得到恰当的表达并取得理想的结果,必须在权力执掌问题上寻求突破,这就将赋税问题与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与国王分立、并立和对话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征税活动所必须依据的赋税基本理论。

协商的结果,必然形成一定的组织,进而形成一定的制度。英法税收习惯曾以个人同意为其主导形式,即同意的决定只约束表达同意的个人。后来,为了征得纳税人的共同同意,国王便不时在王宫召见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久之,便催生了议会组织。在英国,议会形成后,开会的方式仍然保留了议会形成之前的传统,贵族会议单独召开,城乡代表另外集会。后来,便形成了议会的上、下两院。在法国,“美男子”腓力为了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得民众支持,召集代表参加会议,“三级会议”由之产生。同时期的尼德兰、伊比利亚半岛的卡斯特、阿拉冈等王国也各自形成了议会组织。至此,中世纪的欧洲,也就大体完成了权力格局的议会化。
基于上述原因,教会学者,主要是高级教职,在议会活动中也居于主导地位。学术界在谈到议会构成时通常将议会划分为若干等级,而无不将高级教士置于等级之首,这就肯定了教会学者或高级教职的主导地位,也反映了封建等级关系的实际。因为如前所述,在国家事务的重大和众多场合,高级教职也通常处于主导地位。1327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遭受罢免,罢免文件《斥国王书》即由温彻斯特主教起草并宣读,然后经过议会全体人员同意,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罢免。《大宪章》等众多的重要封建文件也都是由教会学者起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会学者或高级教职主要从事宗教和文化事业,具有其他等级所不具备的素养与识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相关事务自然主要由他们负责处理,并因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为社会其他群体或等级所敬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在议会形成很久以前,教会学者在宗教和国家事务中就已经发挥其主导作用。英国的贤人会议如此,贵族会议如此,法、德等国家的同类政治组织也如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在具有民主诉求的其他等级或群体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由表4可知,42个待评价水样中Ⅰ类水质样本数为7个,占总数量的16.67%;Ⅱ类水质样本数为11个,占总数量的26.19%;Ⅲ类水质样本数为8个,占总数量的19.05%;Ⅳ类水质样本数为12个,占总数量的28.57%;Ⅴ类水质样本数为4个,占总数量的9.52%。优于地下水质量标准的Ⅲ类标准比例约为62%,其余水质均较差。由此可知,榆林市矿区周边地下水水质受到一定的污染。由各因子的权重W可知,主要的污染因子为NO-3,其次为SO2-4、NO-2,总硬度和TDS受污染较小。
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中,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都对王权形成了分割和制约。国王既缺乏充足的财政,又不能独自立法而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的政体便不同于专制政体,以“有限君主制”称之,或许更符合历史实际。
四、教 权
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使作为异己的王权受到了约束。那么,在同一政治理论体系之下,作为一己的教权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显然,从格里高利七世时期开始,教权已呈集中之势。英诺森三世任教皇之后,教权更是空前强化,但这是否意味着教皇专制主义的形成?从目前所见教会史著述可知,大多数的作者都作出了肯定性回答。那么,这一观点的形成是依据各个不同时代的专制或专制主义的概念衡量的结果,还是接受了中古教会学者现成的观点?问题涉及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的评价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作出分析和回答。

在宗教大会地位逐渐提升、教皇权力备受诟病的大背景下,欧洲诞生了许多杰出的思想理论家,他们竞相著书立说,矛头所向,直指教皇“专权”。在这些理论家中,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奥坎姆的威廉可称典型代表,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创建的理论、设计的政治目标反映了大多数教会学者的心声。他们将教皇斥为专制主义者,呼吁团结起来抑制教皇权力。马西利乌斯著《和平的保卫者》一书宣称,教皇对权力的贪得无厌破坏了教会的和平。教会的精神领袖是基督,而不是教皇。奥坎姆的威廉呼吁,教皇专权是基督教世界纷争的根源,只有抑制教皇的专权,才能够恢复教会的自由与和平。他们提出了共同体权利、选举、立法等问题,并由理论探讨进入操作层面,提出了各自的政治设计。马西利乌斯强调,“事关全民者,必经全民批准”,宗教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威,必须根据信众代表的意志选举教皇,制定教会信条,颁行相关法令[注][英]沃尔特·厄尔曼:《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夏洞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11页。。奥坎姆的威廉主张,真理和权威依存于教会或宗教会议,宗教会议可以不经教皇同意而召开,有权对教皇的权力作出限定,对教皇的行为作出裁决。他言辞犀利,惊世骇俗:如果教皇沦为异端,应该召开宗教大会,依据全体信徒的意愿,给教皇定罪[注]Denys Hay, Europ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td., 1989), 89;[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三,段保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他们都涉及了教皇的选举问题,认为选举活动必须由信徒或他们的代表进行,由他们来决定教皇职权,限制教皇权力。
这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受这场运动的影响,教会学者的权利意识使得他们对时代思潮作出了敏锐的反应。于是,关于教权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开始出现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趋势,这在两位理论家的政治设计中有明显的反映。而从现实出发,要想抑制教皇权力,特别是要实现巩固和扩大个体权利的目标,仅凭教会人员的力量显然有些单薄,必须联合俗界特别是王权。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两位理论家的设计都不仅考虑了俗权或政府的因素,而且都将他们作为制约教权的重要力量。奥坎姆的威廉认为,男女信徒都可以被委任为教区代表,参加主教会议或国王议会,相应选出宗教会议的代表[注][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三,第134页。。神职人员只有与俗人联合,才能框定教皇权力,将之置于公正的限度之内。马西利乌斯甚至坚持,只有世俗政府拥有立法和司法权,也只有世俗政府才可以召集宗教会议[注]王宗华:《中世纪基督教会议至上运动》,《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1期。。



第三,制定和颁行法令。康斯坦次会议制定颁布了《神圣法令》(HaecSancta或Sacrosancta)和《勤政教谕》(Frequens)两个法令,同时宣布:“本会议代表在世征战的基督教会,其权利直接来自基督,因此,凡会议决议,无论关于信仰问题、关于终止分裂问题,以及关于教会大小事务的改革问题,无论任何人,不问职位尊卑高下,即令位尊至于教皇,均当一体服从。”[注][美]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351页。巴塞尔会议则重申了宗教大会高于教皇的原则,并指出教皇无权延迟或解散会议,违反者将被视为异端。法令的制定是巩固宗教大会地位高于教皇的重要保证,上述法令和规定的颁行无疑体现了宗教大会的权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而这正是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的核心目标。
第四,改革税制与税法。马丁五世一经当选,即不得不顺应民意颁布《什一税及外邦教士之赋税教谕》,规定教皇征税必须满足“明显而紧急”的条件,且必须征得各王国和教省的同意[注][美]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三,第277页。。“明显”者,指征税的必要性必须显而易见;“紧急”者,指征税的形势刻不容缓,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教皇就不能征税,这就大大限制了教皇的征税权。此外,会议还取消了新任主教须将第一年收入上缴教廷的旧规,废止了教廷赖以生存的大部分捐税[注][美]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353页。。削弱或限制教皇的税权是限制教皇权力的重要步骤和内容,而赋税是教会体制的经济基础,教皇的税权既已受到严重削弱或限制,所谓教皇的专权便更不可能。
第五,实现了政教力量的合作。教权与王权是一对矛盾组合体。而政治权力在一定时期的一定国家是一个相对的固定值。在这个固定值中,两者应有相对合理的分工和相应的权力配额。像格利哥里七世和英诺森三世插手俗务,德皇亨利四世和英王亨利二世干预教务那样,显然都突破了权力的限度,因此引发了冲突。由此可见,在经历了13世纪初年英诺森三世的统治之后,实现政教力量的合作也就意味着进步。这种合作当然不能杜绝或者避免重蹈越权的可能,但基于前车之鉴,双方都应该有所收敛,如此不断前进,恰恰说明一种健康的权力调适机制正在形成。
第六,结束了教会的分裂局面。教会的分裂不仅是教会史上的丑闻,它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也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而挽救教会并实现统一正是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的重要目标。现在,这一目标实现了。
第七,确立了“会议至上”原则。如前所论,会议至上原则早在12世纪已经提出,而且在教会系统形成了共识。但在会议至上主义运动开始之前,所谓会议至上原则首先由教皇认定,这意味着如得不到教皇确认,这一原则就得不到实施。会议至上主义运动发生以来,经过长期研究、设计和博弈,会议至上原则终于在上述三次会议中得到了确认和贯彻。而且,会议至上原则的贯彻与宗教会议权威高于教皇权威原则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一原则也主要是在会议至上主义运动过程中形成的。
第八,引领了近现代政治制度的走向。上述理论与目标中的会议至上主义、选举、代表、立法、代议等制度都是近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的或重要的内容,所以,沃尔克说,“康斯坦次会议是教会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次尝试。它使教廷从绝对专制制度转为一种君主立宪制。教皇虽仍握有教会的最高执行权,但他要受到教会立法机构的约束,该机构每隔一定时间召开一次会议代表各基督教国家的利益”[注][美]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352页。。菲吉斯说:“康斯坦茨宗教大会所颁布的教令是当时世界最具革命性的官方文件,根据该教令,大公会议权威高于教皇,千年神权将转变为温和的宪政主义。”[注]J. N. Figgis, Studies of Political Thought from Gerson to Groti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3), 31.正是这样一种政治管理制度,不仅使教会管理形成了新的方向,而且为世俗政府管理树立了榜样,更重要的是为未来欧洲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正因为教皇专制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教会学者基于特定的语境提出来的概念,而由于年代久远且碍于种种不便,我们也就很难了解那时“专制主义”的真正含义。由多方面的信息推断,教会学者所谓专制主义在程度上很可能低于后世学者所界定的专制,也就是说,教会学者所谓专制主义的尺度与我们今天的专制主义的尺度不同,而以不同尺度归纳出来的所谓同一个概念,我们宁可认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教会学者有着强烈的民主和权利意识,对于教皇的某些强势行为自然难以接受,因此易于将这些行为列入专制主义范围。殊不知,在今天专制主义的概念里,这些行为很可能不具有专制主义性质。这里涉及一个概念史的演变问题,十分复杂,不宜深论。并非说在这个体制中就不存在或不会发生教皇专制的行为,但可以肯定,这种行为一旦发生,如前文所引据的案例那样,便必然引起教会学者和高级教职的不满和警惕,而抑制专制行为,甚至对教皇实施罢黜的情况也就必不可免。这应该是教会体制的基本状态。

纵览教会学者长达千年的政治理论的演化轨迹,感觉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似乎摇摆于王权和教权之间。在罗马帝国强盛之际,他们锋芒含蓄,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在教权软弱而需要壮大时,他们锋芒毕露,全力支持教皇从国王那里分权,并希望形成对王权的制约。在封建盛期各国君主身陷封建纷争而难以摆脱时,他们开始与王权对话,高调宣称教权高于王权。而当教权得到强化,限制了其他权利特别是个体基本权利时,他们又主张与俗界和王权联合,以限制教权,强化王权。身为教会学者,他们并不总是站在教皇一边,而似乎是不即不离却又若即若离;对于王权,也不总是敌视对立,同样不即不离,若即若离。这样一种走向可否理解为教会学者对权力运行采取了灵活的调适策略,因为只有给权力以适度的框定,才不至于形成集权与专制,从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维持人的自由,创造优良的生存环境。如果相反,结果就可能不同。处在权利意识演化轨迹中的教会学者,只关注了他们与前辈学者之间观点立场的共性与差异,却并未意识到他们其实是肩负着同一个使命,面向同一个目标,而不论扮演支持还是反对的角色,这也许正是西方中古政治体制的奥秘所在。
结 语
在中古后期的多元社会里,教会学者从教俗政治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理论,形成了富于思想深度的理论体系。在这里,单项理论多有一定的局限性,且效应比较单一狭窄。而一旦聚拢在一起形成体系,效果便截然不同。由于多种理论凝聚在一起,便大大增加了理论效应的力度和强度。不仅如此,由于切合中古教俗政治的实际,这一体系也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对现实政治体制及其未来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个体权利得到了较好的呵护和尊重;在权力顶端,如果说在12世纪之前,教会已经建立了教皇国,与王权两分天下,形成了教俗二元政体,那么,在此基础上,王权受到进一步的分割和限制,由此形成了分权限权的政治体制。在这里,王权不具备宣称或实施“王在法上”的条件,这样的政体可否称为“有限君主制”可以讨论,但与“王在法上”、不受制约的君主专制政体显然不同。而同为“君权神授”,在西方,国家权力分授教会,在东方,则判然有别。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学者并没有因为自身的教士身份而助推教权集中,而是将用于王权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教皇,因而在教会系统同样形成了分权限权的格局。由于建构了政教二元体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限制了王权和教权,中世纪欧洲各国的政体也就呈现出不同于东方的特征。正是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欧美启蒙运动、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欧美近现代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