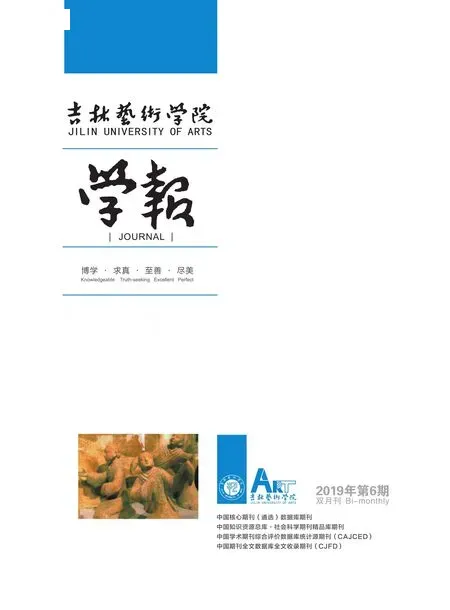《大神布朗》的假面游戏与伦理身份的危机
黄晖 黄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大神布朗》(1925)是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创作的一部四幕假面剧,也是他在戏剧革新方面较为成功的一次实验。该剧当年在纽约连续上演八个月,而且几乎是在百老汇剧场内,曾获得评论家和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1]285相比于《榆树下的欲望》《天边外》等知名戏剧,目前国内对于《大神布朗》的关注甚少,已有文章基本集中于研究面具的使用技巧,并未对其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大神布朗》看似只是讲述了一个关于三角恋爱的情感故事,实际上该剧涉及不少杀人夺妻、策划假死等挑战伦理规范的情节,证明其内核是一个伦理悲剧。《大神布朗》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塑造了一个信奉假面社交的伦理空间,剧中主要人物利用面具掩盖真实的自我,不惜在朋友乃至爱人面前上演一场伪装游戏。由此,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主人公的伦理身份为切入点,分析其身份焦虑和身份迷失的具体表征,进而探讨身份危机的现实意义及其伦理意蕴。
一、假面社交与身份焦虑
作为一部颇具实验色彩的假面剧,奥尼尔的《大神布朗》响应了20世纪的戏剧复兴潮流。事实上,在戏剧表演中使用假面并非是奥尼尔首创,而是一种古老的表现技法,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活动。据学者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面具在文学作品中亦经历了“从‘原型’到‘变形’,从‘面目缺失’到寻找‘真我’或‘本我’”的演变,其文化含义、符号功能等方面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在奥尼尔看来,假面剧可以塑造更为真实的人物,是“一种灵魂的戏剧和一种被面具所控制并构成他们命运的‘自由意志者’的历险。”[1]284-285在《大神布朗》中,奥尼尔对面具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主要人物迪昂、玛格丽特和西比尔从一出场就有专属自己的面具,而前期的布朗并未佩戴。为了掩饰真实的自我,他们三人不惜戴上面具,在朋友乃至爱人面前表演着另一个人,为布朗上演一场伪装游戏。身处这样一个假面社交的伦理空间,以真实面目示人的布朗不免产生了严重的身份焦虑。其中,兼具朋友和情敌身份的迪昂对布朗的影响无疑是最突出的。
聂珍钊教授认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3]263布朗的身份焦虑正是因其伦理身份而起的。伦理身份的种类多样,包括职业身份或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就其职业身份而言,作为一名建设师和商人,布朗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拥有着许多令人艳羡的资本。但事实上,这一职业选择是父母为儿子做的人生规划,并非出于布朗自身的意愿或能力,这就给布朗的职业焦虑埋下了祸根。在日后的职业实践中,尽管接受了良好的大学教育,但布朗却经常很难交出令人满意的建筑设计。对比迪昂,自打儿时起便表现出超强的创作天赋,首先就让布朗察觉到自身的资质平庸。而当迪昂戴上了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潘神形象,实现了从人到神的身份想象,摆脱了人性的孱弱,更是给布朗带来了莫大的压力,加剧其职业焦虑。据此,布朗利用商人的优势,将经济窘迫的迪昂收归到自己的公司,表面上为了接济朋友,实际上是为了缓解自身的职业焦虑,趁机将迪昂的设计创意据为己有。
在伦理关系方面,布朗原本成长于一个衣食无忧、父母恩爱的幸福家庭,后因为向玛格丽特求婚失败和父母的逝世,他在情感上成了无人依靠的“孤儿”。一方面,人到中年,无妻无子的“单身汉”身份使得布朗对重建家庭的渴望与日俱增,陷入严重的婚恋焦虑。另一方面,看似“一事无成”的迪昂,不仅借助艺术家的面具获得了玛格丽特的青睐,完成了布朗最渴望的伦理身份的转变——成为玛格丽特的丈夫及其孩子的父亲,甚至还能越过婚姻获得西比尔的情感慰藉。迪昂在情场上的无往不利使布朗心生嫉妒,其婚恋焦虑指数随之急剧上升。从两个女性角色来看,玛格丽特和西比尔利用面具分别表演着天使和魔鬼,对布朗则构成了截然相反的性吸引力。从少女到少妇,玛格丽特从未向布朗展示其真实面目,每次相见皆以面具为伪装,一直在布朗面前表演着“贤妻良母”的理想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布朗将玛格丽特视为情感伴侣的最佳人选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同于玛格丽特,西比尔戴着丑陋的面具出场,即“涂胭脂、抹口红、画着黑眼圈的狠心的妓女的面貌”[4]129,留给布朗则是一个诱人堕落的魔女形象。在长期苦恋玛格丽特而不得回应的情况下,布朗退而求其次,选择以金钱换取妓女西比尔的陪伴,但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婚恋焦虑。因为不管是深爱的玛格丽特,还是情人西比尔,她们皆表示心向迪昂。在这两个三角恋爱的伦理结构中,布朗始终处于下位,他所拥有的经济资本,与才华横溢的迪昂相比显得毫无优势。
随着主要人物的出场,面具在剧中所起的作用逐渐具象化。面具可以为人物提供了另一种与自我相悖的身份,是摆脱人性之弱点的一种有力伪装或反抗社会的一种自卫机制。譬如迪昂,安东尼的姓氏所代表的“自我虐待、否定生活的基督教精神”。[1]335因为儿时遭遇布朗的欺凌,迪昂对世间万物乃至自身存在怀有强烈的质疑和恐惧,并开始用面具来伪装和保护自己。但透过面具,迪昂给布朗呈现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美满幸福的假面形象,掩盖了自身的贫穷、孱弱、敏感。可以说,在假面社交的伦理空间内,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隔着一张面具,相互伪装,相互隐瞒,面具前后的人格形象发生了错位。荣格在《心理类型学》中提出一个人格面具的概念,即“人格面具是由于适应或必要的便利的原因而进入存在的一种功能情结。”[5]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迪昂等三人选择戴上面具,将真实的自我封闭起来,过着一种身份表演的“非我”生活。对于以真实面目示人的布朗而言,他们三人尤其是迪昂夫妇通过面具塑造超越自我的理想形象,实则构成了一种社交泡沫,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虚幻性。受其影响,布朗产生了严重的身份焦虑,其伦理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形之中已被卷进了身份表演的泥沼里。
二、双重人生与身份迷失
出于缓解自身焦虑的目的,布朗将自我放逐在假面游戏之中,不曾想却因此加剧自身的身份危机。前期的布朗以真实面目示人,并未在社交泡沫中迷失自我,但在杀死迪昂后,布朗戴上他的面具,主动以身份表演作为新的生存策略。为了彻底占有迪昂的身份,布朗不惜策划一场“自杀”,彻底掉进了他者身份的陷阱。在双重人生的生存压力之下,布朗在自我与他者身份之间来回切换,深陷身份迷失的伦理困境而无法自拔。
布朗与迪昂的身份置换是剧中最精彩的情节。迪昂等三人只是利用面具来改变自我的形象,实质是为满足一种身份想象,而布朗的身份表演却是顶替另外一个实际存在的个体,这是现代法治的伦理规范所不容许的。在假面社交的伦理空间内,“偷龙换凤”的操作实践显得十分简单:只要戴上迪昂的面具,布朗便可以完成从自我到他者的身份置换。而当布朗自以为能实现事业与爱情两得意之时,现实却给他当头一棒。他非但没有解决自身的身份焦虑,反而迷失在双重人生的生存困境之中,被迫过上了自我分裂的生活。“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3]257伦理身份的转变对布朗构成了新的道德约束。首先,布朗戴着迪昂的面具,如愿获得玛格丽特的爱情。作为一家之主,布朗必须承担迪昂的伦理责任,接受玛格丽特温柔的“规训”,真正成为一名勤恳赚钱养家、戒掉酗酒恶习的好丈夫、好父亲。而为布朗所不知的是,迪昂和玛格丽特的结合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玛格丽特自始至终迷恋的只是迪昂的面具,而非迪昂的真实形态。为了满足玛格丽特的期待,迪昂戴上潘神面具扮演着完美丈夫,其真实自我早已被面具摧残得不成人形,就连面具自身也染上了梅菲斯特的魔性。在此情况下,布朗不仅需要扮演迪昂,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以谎言弥合谎言,去成就一个不曾存在却极具魅力的迪昂。
与此同时,为了在世人面前维持其成功者的形象,布朗戴上了专属自己的面具,这是极其无奈的选择。由于受到魔鬼面具的反噬,布朗原来的面孔变得既憔悴又扭曲,成为最不受人待见的第三张“面具”。正如奥尼尔所说,“他以为他获得了创造性生活的能力,而事实上他偷到的只是因完全失望而变成自我毁灭的那种创造力。这个喜爱嘲讽怀疑的恶魔使他很快丧命。”[1]336更有甚者,受害者与杀人犯身份之间的相互冲突,使得布朗长期处于精神的“修罗场”,既享受着逍遥法外的自由,同时也承受着自我谴责的折磨。定期以迪昂的面具活动,布朗是可以完美遮蔽其杀人犯的身份。但布朗十分清醒地知道——在假面社交的伦理空间里,“灵魂”不死是可以实现的。肉身之死并不代表生命的彻底终结,他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迪昂面具带来的致命性威胁。犹如其呼:“你死了,威廉·布朗。死后连复活的希望都没有!是你埋在花园里的迪昂把你给杀了,而不是你杀了他!”[4]158当布朗摘下迪昂的面具,再次试图以真实面目告白之时,换来的却依旧是玛格丽特冷冰冰的拒绝。这一身份实验的失败,实际构成了压倒布朗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催生他的“自杀”计划:抹除自我的存在,并将全部的“遗产”留给迪昂。
回到人物自身,一个是拥有瞩目的商业财富,一个是拥有出众的创作才华,布朗与迪昂在事业和艺术方面各有其成就。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及了两种精神:一为沉湎于物质外观的幸福幻觉的日神精神,二为迷醉于个体内心的痛苦本质的酒神精神。[6]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精神可以分别对应布朗和迪昂的人生选择。然而,在看似迥然不同的两项选择之后,实际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境遇,皆因其欲求不得而痛不欲生——事业有成的布朗苦于求爱失败,而家庭美满的迪昂则毫无出头之日。就此而言,他们的关系与其说形成了一组绝佳的对比,不如说是一种吊诡的镜像。如同福柯所言,“从镜子的角度,我发现了我对于我所在之处的缺席,因为我在那儿看到我自己。”[7]。迪昂的存在,真切地折射出布朗最热烈的内心渴望和最现实的人生缺憾。正因为如此,布朗才会无法抗拒迪昂身份的诱惑,企图遁入他者的人生去寻求解脱,从而走向了抹杀自我身份的极端。殊不知,这出自导自演的“死亡”使“迪昂”成为万人通缉的杀人犯,布朗被迫拾回自我身份。从自我到他者,又从他者返回自我,布朗在双重人生之间不断徘徊,却始终无法获得相对稳定的身份认同,最终丧失了对伦理身份的正确判断。
从认同假面游戏到将其付诸实践,布朗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出现严重混乱。在杀人之后,布朗以迪昂的身份活动,试图掩盖自身的罪行,甚至不惜策划一场“自杀”来成全自己。而令其始料未及的是,在迪昂婚姻美满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如此之多的不为人知的伤痛与谎言。纵使布朗借助面具得到理想的爱情,他同样没有能力扭转迪昂人生的悲剧性。伦理身份的置换并不只是伦理关系的简单变动,还牵扯着身份背后的伦理责任与生存压力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朗在自我与他者身份之间来回切换,深陷身份迷失的伦理困境而无法自拔,其实是无法平衡双重人生的生存压力。换言之,为了取代他者的自我“牺牲”,终究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斯芬克斯之谜”的现代变奏
联系剧本创作的历史语境可知,《大神布朗》所塑造的假面社交的伦理空间并非奥尼尔的天马行空,而是基于美国20世纪20年代普遍繁荣却暗藏危机的时代语境的合理想象。在此背景下,主人公布朗由假面游戏引起的一系列身份危机,具体指涉的是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讲,布朗的身份危机实际是“斯芬克斯之谜”的现代变奏,体现了现代人对于“我是谁”的追问与思索,具有深刻的伦理警示意义。
在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研究者回到特定的文学空间,即“进入文学的历史现场,而不是远离历史现场的假自治环境”。[8]以此推论,奥尼尔笔下信奉假面社交的伦理空间,其实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在文学领域的一个变形。传统史学界将这一时期定义为咆哮的二十年代,据美国学者重估,认为普遍繁荣的美国形象绕过了最贫穷的社会阶层。这种过度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电影和电视媒体,因为它们往往将富裕、魅力四射描述为美国形象的规范。[9]28在此话语体系下,当时社会存在的贫富分化严重等不稳定因素是避而不谈的。通过奥尼尔的戏剧创作,今日的我们大体可以窥测其中一些蛛丝马迹,如破产落魄的迪昂、任人摆弄的西比尔。
在众多人物中,“相貌漂亮、衣着讲究、办事能干”[4]124的布朗身份最具有典型的美国性。布朗所从事的建筑行业是20年代经济繁荣的标志之一,其事务所承接的业务主要是反映美国现代气派的市政厅、州议会大厦、商业住宅等建筑。研究显示,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建造了570万套新式住房,现代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莱特的草原式住宅尤为风靡。[9]38正是建筑行业这潜在的利益空间,导致了布朗的事业野心膨胀。换言之,布朗的职业焦虑与其说是因迪昂而起,不如说是由于无法应对日益庞大的建筑市场。在故事结尾,布朗撕毁了设计生涯中最成功的议会大厦作品,不仅是拒绝“迪昂”成为下一个被利欲熏心的自己,更是对建筑行业之商业化大势的强势反击。巧合的是,在《大神布朗》开展巡演后不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爆发了房地产泡沫,首先戳破了咆哮年代的瑰丽美梦,在几年后,另有一场更为浩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美。由此可见,奥尼尔以布朗的悲剧性结局,预见性地宣告了美国黄金二十年代的终结。
从更深层的伦理意蕴来看,布朗的身份危机反映出人类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在现代社会的较量与博弈。聂珍钊教授指出,从伦理意义而言,人类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斯芬克斯因子是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的,并通过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发挥作用。”[10]对于布朗而言,迫切渴望成功的物欲和为玛格丽特执着的爱欲构成了人生中最难攻克的两重关卡。为了解决自我的身份危机,布朗曾一度受欲望和自由意志的蛊惑而放弃了自我的底线。正如现代社会的浮士德,布朗以出卖灵魂的代价与魔鬼共舞,彻底掉进了伦理犯罪的深渊。他利用商人的经济优势强取豪夺,不仅将迪昂的设计创意及其情妇西比尔占为己有,更是不惜实施杀人夺妻、“自杀”计划等伦理犯罪来满足自我的欲望。
布朗最后的死亡是基于理性做出的伦理选择。面对警察的追杀,布朗最后一次戴上迪昂的面具,选择接受伦理犯罪的惩罚。“奥尼尔意在表明,渴望同时戴上成功者和艺术者的面具,是人类自我斗争的一部分。”[11]在迪昂身份的诱惑面前,布朗曾经试图用面具扮演一个事业和爱情两得意的人生赢家,不曾想就此陷入身份危机的僵局。在最后的理性忏悔阶段,布朗赤裸上身匍匐在地,祈求上帝的宽恕,结果靠自己参透了身份表演虚无性的实质。假面游戏所能实现的只是一种想象性建构,并非实质性的转变。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指出:“表演者可能完全为自己的行动所欺骗;他能真诚地相信,他所表演的现实印象就是真正的现实。”[12]当日常生活完全变成假面游戏,表演他者身份成为一种常态,主体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便会出现错乱。甚至可以说,假面游戏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不过为布朗提供一个逃避现实的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假面社交的伦理空间里,同一桩死亡事件实际发酵出不同的故事版本。面对布朗的死亡,事务所委员们悼念的是面具形态的布朗,而玛格丽特眼中只有面具形态的迪昂。唯有西比尔看到了布朗真实状态的死亡,并最终肯定了他作为“人”的姿态和尊严。据奥尼尔所说,西比尔既是“古希腊大地母神茜贝勒的化身”,同时也是“注定会受到隔离”的弃子。[2]336由于身处社会底层,西比尔很早以前便洞穿了假面社交的游戏规则,曾试图以其觉醒者的身份将迪昂从泥沼中拉出来。反观玛格丽特,一直抗拒赤裸的真相,不知不觉中变成加剧迪昂和布朗走向幻灭的推手。据此,玛格丽特和西比尔之于布朗的角色定位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反转。“玛格丽特开始时是光明女神,实际代表着更具破坏性的魔女;而西比尔最初是传统意义的黑暗女神,却成为布朗和迪昂的最终救赎。”[13]在布朗死后,玛格丽特同样没有觉醒,而是选择与迪昂面具度过余生,永远沉迷在幻象与假面之中。
廖可兑先生在《论〈大神布朗〉》中认为奥尼尔批判的是布朗所代表的商人形象,其特征是“只知道追求物质财富,没有灵魂……都是物质富有但精神空虚的人。”[14]在笔者看来,布朗的身份危机不仅指涉富裕的资产阶级,而应与现代社会的个体皆有关联,隐射的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伦理生态问题。布朗的悲剧真正在于将自我放逐在假面游戏之中,企图在他者期待与真实自我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空间,实际是在自由意志与理性意志的博弈中丧失了自我的本真。
四、结语
基于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现实,奥尼尔认为单纯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是不够的,而应该关注现代人内心的精神危机。在此期间,奥尼尔转向假面剧的实验创作,尝试以假面拓宽人物的表现维度。这不仅是为了借鉴古老的面具技法经验,更是试图通过钻研古希腊悲剧崇高的文学传统,进一步确立自我的戏剧理想,书写人类在光荣伟大又具毁灭性的自我斗争之中的永恒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