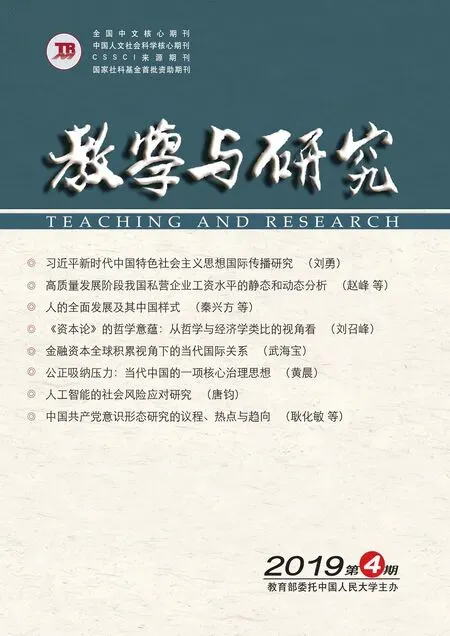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研究的议程、热点与趋向*
意识形态是解读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发展史的重要向度。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施意识形态建设,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属性,而且构成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本文旨在检视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中共意识形态”)研究的议程与热点,揭示所存在的问题,展望未来研究的趋向。
一、既有研究的议程回顾
中共意识形态研究议程依据语境、议题与方法的转换,可划分为起步、发展与深化三个阶段。
从1978年到1992年,中共意识形态研究在启动改革开放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下,在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原典与党史文献的整理出版,以及对外开放与国外研究成果的传入等因素的推动下,具有了研究起步的时代条件。[注]仅就国外研究相关成果而言,参见[德]J.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赵鑫珊译,《哲学译丛》1978年第6期;[波兰]L.柯拉科夫斯基:《意识形态和理论》,俞长彬、钱学敏译,《哲学译丛》1980年第2期;[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3期;[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等等。其研究议题先是“正本清源”,中经“体制改革”,归于“意识形态斗争”。学界先是集中批判清理“文化大革命”,重新审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试图廓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美学家朱光潜提出意识形态非上层建筑化的命题,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意义不在于观点的是非,而是开启了解释意识形态的新维度。[注]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一些刊物于1979年、1980年发表多篇同朱光潜商榷的论文。自1987年始,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改革成为新命题,研究视角从理论层面扩展到体制层面,涉及意识形态机制结构与松绑管理权、开放言路、舆论监督等改革思路。[注]参见冯仑:《关于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理论月刊》1987年第6期。此后至1992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应对“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的语境下,学界研究视角转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和平演变”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重新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要矛盾与意识形态斗争,分析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路径。[注]参见石永义:《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何善昌、简永福:《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与意识形态斗争》,《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丛世新:《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理论探讨》1992年第2期;等等。就研究方法而言,在“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下,传统的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核心范畴的解释框架依然具有解释力,同时意识形态研究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重新思考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开始走出运用单一理论寻求解释的旧路。
从1992年至2012年,该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语境下,进入发展阶段。党和国家文献的规模化出版,特别是中共宣传工作文件集的推出,提供了基础史源。[注]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49—1992)》(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92)》(1—4册),学习出版社,1996年。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指导。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国外社科信息的涌入,开辟了新视域。[注]国内译介的西方研究成果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英]大卫·麦克莱伦:《意识形态》(第2版),孔兆政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等等。其研究扩展不仅在于产生中共意识形态通史论著,确立阶段分期、核心事件与历史评说,而且出现一些精深的理论著作,讨论极左思潮、“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等问题。[注]前者参见吴建国等主编:《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朱育和等主编:《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林国标:《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彭继红:《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研究(1949—2009)》,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后者参见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台北洪叶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崔保锋:《国内学术界“政党意识形态”研究综述》,《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服务现实的意识形态建设类成果,更是数量可观。[注]有关代表成果参见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张衍前:《网络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叶启绩:《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张骥:《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可见,这一研究在数量与质量、广度与深度、视角与方法等方面均有新成就。
2012年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创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的语境下,该研究进入深化阶段。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发表重要论述、作出重要决策和出台重要举措,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和理论指导。从破解时代之问来看,执政党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目标和任务,对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则进一步促进了学界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内在自觉。新时代的新研究气象,表现为研究范畴更加向现实服务倾斜,研究课题更加新颖,研究维度更加丰富。经由国外引入和国内改造,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权力等概念得到应用,丰富了意识形态的诠释方式与解释空间。例如,学界提出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语境下,中共十九大首次将其写入党代会报告。[注]从中国知网检索情况看,它首次在论文标题中出现于2004年,作者先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十年后直指“意识形态话语权”。参见侯惠勤:《弱化与强化:意识形态的当代走向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6期;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201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成立国内首家专门思想智库——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的重镇。再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意识形态安全成为学界的新课题,至2014年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要求建立国家安全体系后,该研究进一步升温。[注]从中国知网检索情况来看,2001年国内首次发表以意识形态安全为篇名的论文,揭示了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有关研究成果参见马振超:《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稳定》,《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杨永志等:《互联网条件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蒯正明:《中国共产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房正宏:《网络政治参与与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胡伯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郝保权:《多元开放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等等。
二、既有研究的热点追踪
中共意识形态研究根据研究主题与方法,形成一些研究热点,集中在意识形态概念话语、意识形态发展史、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思想等方面。
1.中共意识形态概念话语研究。
如何定义和分析意识形态的概念话语是该研究的首要问题。概念的认知不同,会造成概念运用的不同,进而形成在研究对象、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与研究取向上的差异。学界对此存在否定性(批判性)、肯定性与中性(描述性)三种属性的用法,形成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两种基本解释传统。
从概念的起源来看,“意识形态”源自19世纪初法国托拉西的《意识形态概论》,原义“观念科学”,指在可靠感觉经验的基础上重新阐发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观念,后由于拿破仑将托拉西指斥为虚构观念的“空论家”,始具“虚幻性”的否定性含义。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下,马克思首先从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认为它是对现实世界的歪曲反映,并以资产阶级为言说对象,建立了其与“虚假意识”的通约关系。与这种单向度的用法不同,列宁运用阶级分析的二分法,划分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延续前者的否定意义,赋予后者正面的肯定意义。列宁的概念改造不仅改变了马克思的用法,而且经由斯大林、毛泽东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双元论”,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否定意义上的“虚假意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肯定意义上的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科学”,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竞争与对抗。自五四运动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以“教科书体”(教科书)、“编译体”(评著)、“领袖体”(党的领袖著述)三种方式在中国得到传播和接受,学术界亦有发挥和贡献。[注]参见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理解史》(第5章),人民出版社,第284-351页。
西方学界在自由主义长期盛行的语境下,形成“中性叙述”和“党派偏见”两种传统。享有盛誉的政治学辞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关于意识形态词条的解释,就非常典型地表现出这一点。首先,社会学家曼海姆在马克思的“虚假意识”的否定性用法后,进一步区分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个概念,将乌托邦界定为某个有抱负的阶级所指出的一种不可能的理想未来而实施的对思想的扭曲。知识社会学的这种用法为政治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打开了概念中立化的视窗,最终形成意识形态是符号系统的“元解释”。在宽泛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术语被多样化地使用,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被界定为意识形态。尽管西方学界试图保持“中性”立场,将其界定为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但受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竞争的影响,一些学者基于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长期给它贴上“党派偏见”的专属标签。在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这一术语具有强烈的贬义色彩,认定只有“那些精心雕琢、自成一体和居垄断地位的党派学说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注]参见[英]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8页。。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意识形态的多元理解和概念革新,成为国内学界特别是中国政治学建构的重要方向。在国内,意识形态概念的上述属性都有应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式及其载体构成的思想体系,即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域。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反省西方政治学原理,立足中国政治实践,着力构建原创性的中国政治学。在国内出版的政治学教材中,意识形态概念呈现出一种回归中性叙述和话语更新的趋势。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教材为样本,可观察到如下现象:有的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功能;有的提出意识形态是一套自洽的观念体系或者世界观,对于现存秩序提供了一种维护或变革作用的解释;有的将中共意识形态分为“价值—信仰”、“认知—阐释”与“行动—策略”三个组成部分,总结了调适性的变迁。[注]参见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2页;景跃进、张小劲主编:《政治学原理》(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7页;景跃进、陈明明、肖滨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6页。还有学者在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之外,提出作为第四种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权力”,它通过语言、文化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力量。[注]参见杨光斌:《论意识形态的国家权力原理——兼论中国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问题》,《党政研究》2017年第5期;杨光斌:《应重视“意识形态权力”》,《北京日报》2018年1月15日。有的通过对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绩效的关联研究,提出“去意识形态化”的中立性国家的概念,认为中立性国家最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绩效。[注]参见任剑涛、朱丹:《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绩效》,《学海》2018年第2期。上述概念创新的趋势表明国内学者在阶级分析的传统维度外,增加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叙述和结构功能分析,揭示出中国政治学本土意识的增强。
2.中共意识形态发展史研究。
依据党史国史的分期,为意识形态研究填设历史坐标系,是中共意识形态史研究的目标。依循1981年历史决议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分期,中共意识形态历史研究基本确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1949—1956)、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曲折发展(1956—1966)、“文化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空前灾难(1966—1976)、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四个阶段的通史叙述框架。
与史学研究关注具体语境下的“过程”、“事件”和“人物”不同,政治学追求意识形态在大历史时段下为何、如何发生变迁的结构性解释。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引发了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划分了“新继续革命论”、“实践检验论”、“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论”四个阶段的变迁,提出“改革精英创造性转换”的解释,强调转换动力来自执政党工作重心的转变,利用旧意识形态的“库存资源”和开发“新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内部的创新。[注]参见萧功秦:《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萧功秦:《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有学者则认为中共提出的“以人为本”代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向,标志就是文化上的“兼容并蓄”、价值上的“共建共享”。[注]参见林尚立等著:《改革开放30年: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政治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254-262页。有学者将1949年后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三个时期,提出意识形态总体呈现从超越性到世俗性、从排斥性到包容性的变迁特征,建立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绩效的关系评估框架。[注]参见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4-293页。这些跨时段的结构分析,深入中共意识形态的内里,有助于提炼总结一些规律性认识。
3.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思想研究。
学界认为,中共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既有继承一脉相承又有发展创新,集中表现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袖人物的有关思想。
关于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取得相当进展。既有对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发展过程的历史考察,也有对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学说的概括分析。既有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与发展的阐发,也有对毛泽东晚年意识形态思想的揭示。学界认为:毛泽东的贡献在于形成了一套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可划分为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文艺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双百方针、思想教育、意识形态斗争、知识分子问题、现实政策和对外政策等;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系统分为本质论、阶级斗争理论、意识形态发展理论与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还有的分析毛泽东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意识形态”观,等等。[注]参见方志:《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论述及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1年第4期;阎志民:《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学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韩强:《试论毛泽东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3年第6期;黄世虎:《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卢永欣、吴林芳:《论毛泽东的“文化——意识形态”观》,《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S2期;等等。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意识形态观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建设性的意识形态观,一种是理想主义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观,后者由毛泽东发展至“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化,并提出宋明以来中国形成的本源论思想模式的解释框架。[注]参见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第71-73、113页。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意识形态思想亦受到学界关注。邓小平意识形态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型;邓小平意识形态思想的内容,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意识形态思想建设灵魂,把清除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作为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的必要手段,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战略举措,以及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的意识形态建设目的,注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等。[注]参见何怀远:《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杰出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7期;邹放鸣:《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冯虞章:《邓小平与意识形态工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王真:《邓小平意识形态观及其时代价值》,《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1期;田改伟:《挑战与应对——邓小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王永贵、夏禹:《邓小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期;等等。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中,产生一些江泽民、胡锦涛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成果,主旨是展现中共领导集体在意识形态思想上的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的特征。[注]参见何怀远:《论江泽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战略思想》,《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蒋淑晴:《江泽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战略地位和作用的科学阐释》,《学术论坛》2010年第1期;方章东:《江泽民同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方法论创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3期;龚正荣:《胡锦涛同志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稳定思想论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3期;龚正荣:《论胡锦涛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建设的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等等。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受到高度关注。习近平文献的陆续出版,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文献基础。[注]在目前公开的权威文献、主流报道中,集中表达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是2013年、2018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部分。其研究焦点是在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框架下,阐释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结构、地位和贡献。有的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层结构,有的归纳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文艺观、新闻观、军队政治观、意识形态安全观、哲学社会科学观、思想政治教育观、意识形态责任制等8项内容,有的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参见唐爱军:《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王文慧、秦书生:《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战略思想探析》,《理论与改革》2016 年第1期;刘希刚、王永贵:《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整体性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陈建兵、梅长青、胡姣姣:《论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其意义》,《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辛向阳:《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北京日报》2018年9月17日;甄占民:《意识形态工作强起来的战略任务》,《求是》2018年第20期;等等。这些成果主要是解读习近平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组成部分,显示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4.海外中共意识形态研究。
意识形态问题是海外中共研究的传统课题。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竞争并未“终结”,国际学术界仍然持续关注。伴随21世纪的中国日渐崛起,中共学更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热点。
冷战以来,台湾地区的中共研究经历了从服务政治到回归学术的变化。台湾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东亚研究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从服务于国民党反共需要的“匪情研究”到逐渐中立的“中共研究”,从社会化的“大陆研究”再到全局性的“中国研究”的研究转换,成为台湾研究气候变迁的缩影。[注]参见寇健文:《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台湾“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角色:历史进程与变化特征》,夏璐译,载杨凤城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55-181页。台湾的相关研究深受西方政治学范式和岛内政治格局的影响,如李英明的《中国大陆学》、《中共研究方法论》就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进行的反省,检讨了1950年代极权主义模型下官方制定标准意识形态的特性、1960—1970年代派系政治模型下最敏感最常见的意识形态争论、198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模型下意识形态的调整等议题。[注]参见李英明:《中国大陆学》,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第20、73页。另可参见李英明的《中共研究方法论》(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相关章节。吴安家的《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与持续(1949—2003)》认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变迁分为共产主义的实验与修正(1949—198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1982—1991)、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增加(1992—2003)三个阶段,把中共意识形态的性质描述为一种与民主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极权意识形态,体现出作者的反共立场。[注]参见吴安家:《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与持续》,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27-31、222、574页。林奎燮则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作中共构建的“文化霸权”,目的是实现意识形态由“西方中心”向“中国中心”的过渡,由此意识形态从依靠马列主义作为合法性工具转变到中国主体的建构。[注]参见林奎燮:《文化霸权与有中国特色的中共意识形态》,台湾政治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第5页。总体来看,老一代学者深受国共内战思维和冷战思维的影响,新一代学者逐渐摆脱旧式解释框架的约束,以更为客观的立场审视意识形态问题。
在海外研究中,有经典意义的是美国舒曼的著作《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作者把意识形态分为“纯粹的意识形态”与“实践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研究的“双元面向”,为西方学界从政治理论、政治行为两方面讨论意识形态开辟了空间。[注]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21.
从研究焦点来看,西方学界长久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传统构成和重要来源,但它与经济发展绩效、民主政治、民意基础等其他因素相比,在人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是一个复杂的变化的过程。美国李侃如认为,相比较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挂帅,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意识形态作为中央权力运作资源的作用和政策协调工具的能力遭到破坏,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特征就是把“为民众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作为新的合法性源泉。[注]参见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0、192-193、142页。德国海克·霍尔比格认为,中共把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创新作为执政地位重新合法化的主要来源,在灵活性与连续性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以解决党的执政地位所面对的“政绩困局”。[注][德]海克·霍尔比格:《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构:决定因素、进展和局限》,载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5、17页。玛利亚·邦德、桑德拉·希普等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注][德]玛利亚·邦德、桑德拉·希普:《意识形态变迁与中共的合法性:以官方话语框架为视角》,周思成、张广译,《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8期。美国沈大伟以“收缩与调适”作为描述1978年以后中共意识形态双重状态的关键词,认为中共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立足本国国情,发明“中国特色”的新意识形态,强调意识形态的性质与功能发生根本变化,即从政策产生的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变成一种事后为政策决策论证和辩护的工具。[注]参见[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51-153页。新加坡郑永年将意识形态划分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两种类型,认为前者不能取代后者,执政党需要完成从革命为核心到以建设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转型,强调再塑意识形态是中共执政合法性和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注]参见郑永年:《再塑意识形态》,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59-161页。上述观点紧扣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的关联性,注重政治学理论框架下的学理分析,既有研究视角、理论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又难掩“西方中心论”的痕迹和“政党—国家”中心论的偏好。
三、未来研究趋向的展望
当下的中共意识形态研究已形成以现实关怀为导向的阐释型主流意识形态研究、以史事描述为导向的经验型史学研究和以理论建构为导向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三足鼎立之格局。第一种研究范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研究,聚焦中共理论创新,着重从理论政策层面阐发马列主义原典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着重从现实层面分析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以为执政党的决策和意识形态工作提供论证。第二种研究范式是以党史国史视角下意识形态的演化为考察对象的意识形态史研究,宏观上廓清中共意识形态历史脉络,中微观上考析意识形态历史上的人物、史事与节点,以展现中共意识形态发展的语境化与复杂性。第三种研究范式是从政治学视角下讨论中共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采用解构“西方中心论”和建构“中国经验”的取向,分析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以推动中共意识形态理论的再建构。
通过回顾研究历程和比较研究范式,不难发现这一研究的特点。首先,中共自身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决定了该研究的视角转换和议题设置。换言之,正是中共的“当下”决定了学界对于意识形态的历史追溯、现实剖析与未来追寻。其次,多元性的研究取向造就了日益丰富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解释框架。前述三种研究范式都有学术解释的正当性、合理性和独有贡献,同样也都存在各自的价值优先和阐释限度,但无疑已经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单一话语和解说方式,深化了中共意识形态的丰富认知。再者,追求学术创新是日益强烈的研究冲动。针对曾经长期流行的僵化教条式的理解,第一种研究范式强调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原典和阐释中共意识形态理论;针对历史坐标系的缺失,第二种研究范式强调历史的语境与流变;针对“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第三种研究范式强调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建构。
从未来发展的考量出发,新时代中共意识形态研究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曰“史”“论”分离的现象,即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尚未产生有意义的交集,前述三种研究范式存在自我循环、自说自话的倾向,意识形态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并未形成内在统一。主流意识形态研究要想避免成为政治宣传与决策注脚,历史研究要想避免仅发思古之幽情,政治学研究要想避免成为理论法则演绎的沙盘,其不二法门就在于走出封闭研究的“孤岛”,放宽眼界,拓展视野,更新方法。一曰学科建设的“荒原”现象,即学科意识不足,学科边界不明,研究领地有待开垦。笔者检索文献过程中常感困惑之处是学界没有中共意识形态学的学理讨论,对于其概念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方法等一系列基础问题缺乏基本共识,以致先入为主地使用概念,各自为战地开展碎片式研究。
由上出发,未来研究之进路,首先在于“史”“论”的再平衡。“重史轻论”与“重论轻史”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化。唯有坚持历史与理论的并重,在历史理论化和理论历史化的结合中,方能更准确地绘制中共意识形态研究谱系。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中共意识形态学。中共意识形态因其课题之重大、历程之复杂、经验之丰富,足可独立为学。中共意识形态学可视作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中国政治学等相关学科存在密切关系的新兴交叉学科。建立学科体系,是中共意识形态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学科自觉意识的产物,是科学指引中共意识形态研究的内在要求,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走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地位使然。由此,中共意识形态学或可成为未来讨论的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