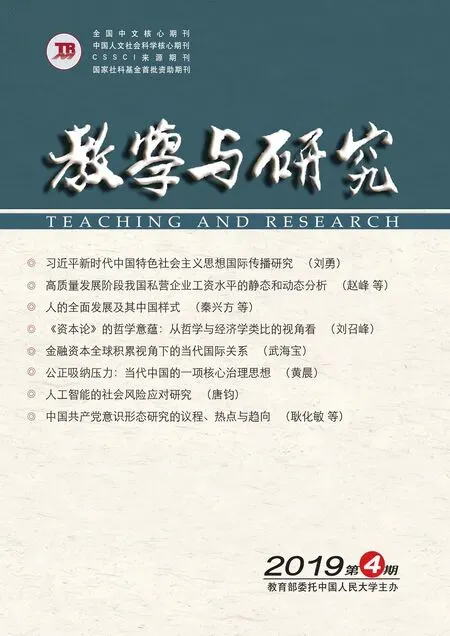德语世界《资本论》研究的互动与传承
——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到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
国外马克思学的发展是在各个理论流派和学者之间的理论交锋与互相借鉴中不断前进的,如果抛开马克思研究者所属的理论谱系,仅以马克思研究为中心做一个学术史的考察,我们会发现来自不同理论谱系的马克思研究者之间存在大量我们长期忽视的理论互动与学术传承。比如就《资本论》的研究而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早期苏联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作为其理论传人的“新马克思阅读”之间就存在着许多的理论互动与学术传承。笔者试图从学术研究的互动与传承的角度,对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到德国“新马克思阅读”之间的《资本论》研究做一个思想史考察,以理清这几个理论流派之间的理论互动与学术传承的思想史线索,也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一、德语世界早期的《资本论》研究: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为中心
德语世界拥有深厚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早在1886年,考茨基就在《新时代》(DieNeueZeit)杂志上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一文,对当时刚发表的德文版《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第二卷做了评述,在评述《资本论》部分,考茨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对比研究。[注]Day, Richard B., and Daniel Gaido, Responses to Marx’s Capital: From Rudolf Hilferding to Isaak Illich Rubin, Brill, 2017.p.129.然而总体而言,《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并没有引起德语世界的广泛关注,收到的多是流于表面的批评和攻击。[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围绕马克思〈资本论〉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史概论(1867—1967)》,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5-129页。德语世界《资本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之后,虽然就研究数量而言,此时的德语世界《资本论》研究尚不能与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理论盛况相比,但就研究质量而言,丝毫不逊色于此后的研究水平。从区域来看,德语世界的《资本论》研究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在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维尔纳·桑巴特在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就在历史学派的刊物《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上发表《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一文进行回应;另外柏林大学的统计学家博特凯维兹也在1906年和1907年分别发表了《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和价格问题》和《论〈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结构的改正问题》两篇论文,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转形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然而准确地说,当时德语世界《资本论》研究的重磅成果主要来自奥地利。奥地利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重镇主要缘于两点:一是奥地利的大学在制度设计上不像德国的大学那样歧视马克思主义者;[注]See Hobsbawm E.,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Reflections on Marx and Marx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30.二是当时的奥地利大师辈出,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助推了奥地利马克思研究的崛起,其中不少学者都参与了马克思相关的研究与讨论,比如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凯尔森的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庞巴维克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另外,维也纳大学还活跃着各种与社会主义理论有关的学术社团,[注]Bottomore, T.B.and P.Goode, Austro-Marxism,Clarendon Press,1978,p.9.比如米塞斯参加的马克思著作研讨会、[注]See Hülsmann JG.,Mises: The Last Knight of Liberalism,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7,p.363.熊彼特参加的马克思价值理论研讨会[注][丹麦]埃斯本·安德森:《约瑟夫·熊彼特》,苏军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27页。等。总之,在这种自由而活跃的马克思研究氛围中,奥地利催生了一批优秀的《资本论》研究成果。在19世纪末,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就围绕《资本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有过不少评论,其中论述最系统、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庞巴维克1896年发表的《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终结》一文。虽然这篇文章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作为一篇严肃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论文,事实上它将西方学界的《资本论》研究推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注]张亮:《早期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的〈资本论〉:批判的再评价》,《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如果说桑巴特和博特凯维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评总体还是温和的,那么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批评则是釜底抽薪的,他直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背后的方法论基础。他在《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终结》一文中,断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提供任何经验上或心理上的证明,而只是纯逻辑演绎的结果,并且推断《资本论》第三卷中平均利润率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劳动价值论,也预示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终结。[注]Paul Sweezy,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by Eugen von Böhm-Bawerk and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by Rudolf Hilferding,Merlin, 1975, p.63.
面对庞巴维克的诘难,当时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并没有马上给出有效的反驳,直到近十年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一文的发表,庞巴维克的文章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回应。作为当时德语世界声誉卓著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专家,[注]希法亭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成果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比如他发表在《新时代》第21期的《论价值理论的历史》(1903),在《国民经济与社会政策杂志》(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第12期上发表《评维尔纳·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1903)一文,在《新时代》第23期的《卡尔·马克思关于理论经济学问题的构想》(1905),在《新时代》第29期的《马克思经济学史前史》(1911—1912)等。See Day, Richard B., and Daniel Gaido, Responses to Marx’s Capital: From Rudolf Hilferding to Isaak Illich Rubin, p.129.希法亭的《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一文对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很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看来,希法亭的这篇文章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营垒内对庞巴维克所做的唯一的全面答复,而且也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对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正统经济学之间观点上的根本差别所作的最清楚的表述。[注]Rudolf Hilferding,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edited by Paul M.Sweezy, Augustus M.Kelley,1949, p.xix.希法亭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在于,他洞察到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特殊联系,他试图回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中,用社会的和历史的观点阐述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意义,即对劳动的社会性分析和对价值的历史性分析,实际上他已经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解读提高到了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注]See Joan Robinson, Reviewed Work(s),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by Eugen von Böhm-Bawerk;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by Rudolf Hilferding; “On the Correction of Marx’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by 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 and Paul Sweezy, in The Economic Journal, 1950,60 (6):358-363.就这一点而言,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基本都在他开辟的研究方向上。希法亭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无疑是早期《资本论》研究的一座理论高峰,对此列宁、考茨基、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等人都对希法亭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给出了极高的赞誉。[注]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顾海良、常庆欣、刘和旺、鲍金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99页。然而由于希法亭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成就太过耀眼,我们非常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希法亭这座高峰之下耸立的是整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群山——几乎所有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都参与到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讨论和研究当中。比如奥托·鲍威尔也是一名优秀的马克思经济学专家,[注]值得一提的是,奥托·鲍威尔在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指导教师就是庞巴维克。鲍威尔在《资本的积累》[注][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6页。一书中,用不同生产部类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比例失调来解释危机的形成,据此反驳了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的相关论述,该文直接构建了格罗斯曼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分析框架。此外在190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40周年之际,他又在《新时代》第26期发表了《〈资本论〉的历史》一文,该文对《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范畴进行了类比研究,比如把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质”“量”“度”等范畴分别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使用价值”“劳动”“抽象社会必要劳动”等范畴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试图表明《资本论》中黑格尔式逻辑结构,这比列宁在1914年《哲学笔记》中关于《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相关论述要早了整整七年。此外鲍威尔还在1910年《斗争》(DerKampf)杂志第3期发表了面向普通读者的《剩余价值理论》一文,对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学体系做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梳理与研究。另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埃克斯坦(Gustav Eckstein)的《资本论》研究也值得我们关注,比如他在1906年《新时代》第24期发表的《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一文,就以马克思的第二卷《剩余价值理论》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不彻底最终造成了其在解释租金和价格形成方面的失误,并且他认为,就方法论的清晰程度而言,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对地租和绝对地租的表述要比《资本论》第三卷中更为出色。
总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研究构成了20世纪早期一个极有价值却又容易被人忽视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而且我们将会看到,这一传统在整个德语世界的《资本论》研究中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思想史效应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研究工作对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与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理论互动与学术传承中。首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理论互动与传承。它们两者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梁赞诺夫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1911年的学术合作,[注]刘仁胜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这种合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成立之后。就《资本论》研究而言,苏联早期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专家鲁宾(I.I.Rubin)的经济学研究就是在希法亭的工作基础上进行的。[注]遗憾地是鲁宾遭到了苏联30年代政治清洗,其代表作《马克思的价值论文集》(1928)的理论影响足足中断了数十年。鲁宾在《马克思的价值论文集》中对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反驳就是沿着希法亭《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一文的思路继续的。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文集》中,鲁宾大量引用希法亭的著作,并对希法亭的研究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尤为关键的是鲁宾继承了希法亭开辟的从社会历史哲学角度介入《资本论》研究的理论路径,他与希法亭一样,认为社会形式的逻辑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建构中起决定性作用,强调价值的社会决定性,而不是单纯地强调价值的生理的或技术层面的因素,认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高明之处正是其哲学穿透力,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分析具体劳动时间和生产价格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的层面。[注]Boldyrev I, Kragh M.,“Isaak Rubin: Historian of Economic Thought during the Stali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Soviet Russi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15, 37(3):363-386.当鲁宾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被发表之后,他在书中关于劳动价值理论与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研究极大地启发了西德一批左翼青年学者,成为二战后西德马克思研究的理论荒漠中一股理论活水。[注]从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所编的《PROKLA.批判社会学》等期刊中可以发现,鲁宾的价值形式研究对西德的理论影响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1970 年代在西德出现了各种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辩论,如“国家溯源辩论”“世界市场辩论”及各种各样的试图对资本的当前运动进行“真实分析”的尝试。See from 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4/10/29/state-violence-state-control-marxist-state-theory-and-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其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也有极深的渊源: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就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律恩贝尔格担任,所以早期社会研究所的研究理念基本就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研究传统的延续。就《资本论》研究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经济学家格罗斯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可以看作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延续。马丁·杰伊在《法兰克福学派史》一书中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经济学家亨里克·格罗斯曼无论在年龄还是在思想上都更接近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注]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25 页。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从澳大利亚左翼经济学家里克·库恩撰写的格罗斯曼传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格罗斯曼确实深受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气质的影响:他早在1908年就到维也纳从事经济学研究,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希法亭、鲍威尔、格律恩贝尔格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 并系统研究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库恩认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两个方面对格罗斯曼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是他们科学的马克思研究立场,力图从马克思那里为社会主义运动找到坚实的经济学基础和哲学基础; 二是他们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格罗斯曼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就是在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密切接触中生成的。[注]格罗斯曼1929年在格律恩贝尔格主编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上发表的代表作《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分析框架上,都深受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格罗斯曼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强调运用马克思所创立的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就具体的分析框架而言, 格罗斯曼也基本延续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威尔和希法亭的解释经济危机的思路,即用不同生产部类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比例失调来解释危机的形成。[注]Rick Kuhn,“Henryk Grossmann, a Marxist activist and theorist: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2000,18(2):111-170.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格罗斯曼还专门就《资本论》的创作问题展开研究,并于1929年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原始计划的变化及其原因》一书,在书中他批判了罗莎·卢森堡和卢卡奇关于《资本论》不完整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对同一问题在不同地方的表达是按照整个问题的各个要素来表达的,所以他断定马克思主要经济学著作在方法论上是完整的,《资本论》实质上是完成了的和没有空白的体系。[注]总之,在某种意义上,格罗斯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几乎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延续,而且我们会发现他的《资本论》研究在马克思研究专家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zdolsky)那里得到传承和发展。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纳粹恐怖之下几乎没有人再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只有极少数的德国本土学者坚持独立的马克思研究工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马克思研究学者是罗曼·罗斯多尔斯基,他的《资本论》研究也是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格罗斯曼”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进行的。罗斯多尔斯基出生于奥匈帝国的伦贝格(今属乌克兰利沃夫市),他一生辗转,最后去世于美国底特律。然而他从事马克思研究工作的学术训练与学术积累却是在维也纳完成的:他于20世纪20年代移居维也纳,并在1926年后开始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驻奥地利科学记者,从事搜集失散在维也纳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工作,1929年又以《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非历史民族问题》一文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而且迁居美国后,他又于20世纪50年代末再赴维也纳进行长达三年半的学术访问。罗斯多尔斯基长期在维也纳学术圈的经历使得他对奥地利早期《资本论》研究成果非常了解,在他的代表作《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8)一书中,罗斯多尔斯基就对希法亭等人的《资本论》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另外他在具体的观点上也与格罗斯曼存在某种延续,他在书中非常赞成格罗斯曼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竞争、使用价值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也认同鲍威尔和格罗斯曼的危机理论研究中对卢森堡的批判。[注]此外,罗斯多尔斯基在书中运用了当时新出版的德文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以下简称《大纲》)的资料,通过对《大纲》和《资本论》之间关系的系统性分析,他断定马克思已将最初预计出版的有关土地财产和雇佣劳动的著作的材料归入《资本论》一书,于是他得出了与格罗斯曼相似的结论:即他也认为《资本论》本质上是一项完整的工作。但是在对《资本论》写作计划改变的时机和原因的解释上,两人有着明显的分歧:格罗斯曼以1863年8月15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为依据,认为《资本论》写作计划的改变发生在1863年;而罗斯多尔斯基通过对《大纲》的研究,认为这种改变至少发生在1864年之后。[注]Rick Kuhn,“The Change in the Original Plan for Marx’s Capital and Its Causes”,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3, 21(3):117-137.虽然罗斯多尔斯基的个别观点在马克思《1861年—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新的经济学手稿的披露后,不断得到马克思文献学家的修正,[注]Rick Kuhn,“The Change in the Original Plan for Marx’s Capital and Its Causes”,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3, 21 (3):117-137.但是不可否认,这部专著一直是西方学界公认的相关主题的最为系统的理论成果。更为开创性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大纲》的研究,罗斯多尔斯基从马克思《大纲》中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大量引用进一步确认了《资本论》中的黑格尔辩证法因素。他在书中写道:“《大纲》的出版意味着若没有首先对马克思的方法和他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就不能写出关于马克思的学术评论。”[注][英]罗伯特·法恩:《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这种以黑格尔辩证法解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思路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威尔把《资本论》与黑格尔式逻辑结构的对比研究开始,就一直浮现在西方马克思研究者的视线里。列宁在《哲学笔记》也有相似的提法——不理解黑格尔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然而,这种以黑格尔解读《资本论》的做法的大量运用却始于罗斯多尔斯基,也正是在罗斯多尔斯基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辩证法的重新连接的意义上,德国马克思学者扬·霍夫(Jan Hoff)和埃尔贝(Ingo Elbe)等人认为这对二战后兴起的以价值形式“辩证法”为研究主题的西德“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注]See Hoff J.,Marx Worldwid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n Marx Since 1965, Brill, 2016, p.16.
三、德语世界《资本论》研究的复兴:“新马克思阅读”运动
按照埃尔贝在《西方的马克思》一书中的介绍,“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是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列的第三个理论范式,它最早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西德法兰克福大学,该传统以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研究为特色,并在新世纪以来日益成为德国马克思研究领域的重要范式。“新马克思阅读”的早期核心代表人物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和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都在20世纪60年代求学于法兰克福大学,且都受教于阿多诺的课堂,其中莱希尔特更是跟随阿多诺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且在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的指导下于1970 年完成博士论文《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这篇文章也成了“新马克思阅读”的经典文献。根据扬·霍夫和埃尔贝等人的介绍,“新马克思阅读”首先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生长起来的。[注]See Hoff J.,Marx Worldwid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n Marx Since 1965, Brill, 2016, p.16.我们知道,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格罗斯曼、波洛克等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经济学家,在霍克海默将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转为社会批判理论之后,这种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就被隐匿了起来。然而这种隐匿并不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不再重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相反,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就提示我们,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对当代意识与历史的疏远现象的分析运用就是一种经济学方法。[注][德]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历史与结构》,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3页。另外,据沃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等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一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关系更密切。Bonefeld Werner,“Negative Dialectics and the Critique of Economic Objectivity”,i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2016, 29(2): 60-76.施密特的这种理论洞察一方面缘于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稔熟于心,另一方面缘于他自身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浓厚兴趣与深入研究。所以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被暂时隐匿起来,那么在施密特这里,政治经济学又成为施密特的直接理论对象。在其代表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的1971年版后记中,施密特总结说这是首次利用马克思中期和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特别是利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著作进行的哲学解释。施密特认为,西欧理论界近20年来对马克思的过度人本主义化解读需要得到纠正,特别是以新存在主义(neo-Existentialist)为代表的基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主要是1844年《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把马克思思想简化为一种“非历史”的人类学的马克思解读倾向。[注]See Hoff J.,Marx Worldwid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n Marx Since 1965, p.77.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和《大纲》的重新出版后,这种过度人本主义化的马克思思想解读面临更大的质疑,西方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著作与早期哲学著作的联系。这种认识在施密特之后的巴克豪斯与莱希尔特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新马克思阅读”的奠基之作《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注]该论文最早形成于1965年阿多诺的社会理论研讨班上的课题研究,受到了阿多诺的高度肯定,1969 年正式发表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主编的《马克思的认识论》这一文集中。中,巴克豪斯就将《启蒙辩证法》中的经济分析方法凝练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从而试图从马克思晚期的经济学著作出发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革命等理论问题。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在施密特等正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那里,还只是作为批判理论的重要方法论资源得到重视,那么在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开启的“新马克思阅读”这里,政治经济学研究则是他们直面的理论任务——将其理论探讨全面地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本身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是“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兴起的内在原因,那么罗斯多尔斯基和鲁宾著作的发表或重新发现则给当时的西德马克思研究者以新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视野。“新马克思阅读”的理论聚焦与理论特色就是巴克豪斯的奠基性文本的书名所展示的,即“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笼统来说,其理论聚焦可以被拆解为两部分来理解,即价值的“社会”形式及其辩证运动。这两部分分别体现了他们对前人价值理论研究的批判性继承:一是继承了希法亭—鲁宾以来的社会历史哲学的解读视角,二是继承了鲍威尔和罗斯多尔斯基等人的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解读视角。实际上,自希法亭与庞巴维克的理论交锋开始,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差别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现代西方经济学日益专注于经济现象的数量化分析与经济过程的精确化控制,然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则显然不是“纯经济学”,它更强调的是一种哲学探讨而不是生理或技术层面的定量分析,其理论视域更是包含社会的本质及其未来这样的哲学主题。所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必须从哲学的视角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希法亭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中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分析,[注]Rudolf Hilferding,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edited by Paul M.Sweezy, pp.130-131.奠定了该文成为价值理论研究中的经典地位,此后的鲁宾的《马克思的价值论文集》基本上是延续这样一种路径。在“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巴克豪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种分析路径的继承与完善。首先巴克豪斯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本身,就是对于现实社会、劳动过程、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把握,所以对价值形式的逻辑结构的分析不能与对其历史社会内容的分析相分离,必须对“形成价值的”劳动的历史社会构造进行追问。所以,他特别强调对商品、货币、资本为代表的这些价值形式的社会性分析,即他认为这些形式本身不再停留于经验现象和主观心理层面上,而是深入到了社会关系的层面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与社会理论之间展现出一种内在的一致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把“新马克思阅读”的价值理论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宝贵财富。[注]参见李乾坤:《“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的一种新纲领的探索》,《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其次,受到罗斯多尔斯基等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研究的直接启发,巴克豪斯回到了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资本论》解读传统。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为了符合大众读者的阅读要求对价值形式理论做了过度简化的处理,从而弱化了价值形式理论的辩证性。所以巴克豪斯试图从马克思的大量经济学手稿和相关评论中重新挖掘并建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整体性,恢复价值理论的辩证思想。通过对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的研究,他指出对价值的研究必须从价值自身差异运动中得到解释,用黑格尔的语言,即把价值理解为通过中介的运动不断展现自身的“主体”,而非僵化不动的“实体”。[注]参见李乾坤:《“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的一种新纲领的探索》,《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实际上,“新马克思阅读”所强调的价值形式的辩证运动,本身就构成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半个世纪的理论互动与传承后,德语世界的《资本论》研究在“新马克思阅读”运动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