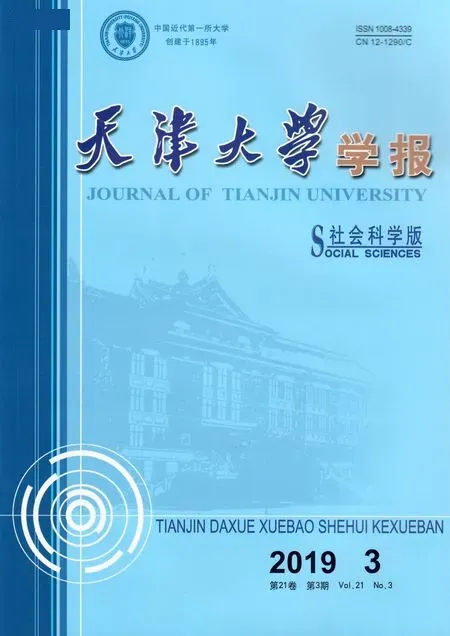从译者文化姿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看译者主体性——以林译小说为例
熊建闽
(福建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福州 350016)
晚清社会处在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与倾轧、新旧思想交锋的时代,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秩序处于崩溃边缘,面对欧风美雨的强势冲击,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儒家道统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中“失语”,渐渐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解释权威和引导作用,天朝皇权濒临瓦解。
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失落,边缘化的文化境遇使晚清文化精英们感受到空前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原有的社会关系下,自我价值实现方式的有效性被剥夺,个体徘徊于新旧社会系统之间,如何在新的社会生态系统中获得价值认同,书写新的文化姿态,是摆在晚清文人群体面前的时代命题。戊戌变法失败后,国民性的改造被提到议事日程,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呼吁“新民为中国之第一急务”[1],“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而欧美小说正切中使民开化的宗旨,能够“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2]。于是,翻译域外小说,成为许多晚清文人参与“新民”的当然选择。可见,这场以“新民”为旨归的翻译小说风潮,文学审美与文学艺术的借鉴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重点关注的目标,意识形态上的经世济民才是主要的文化方向。晚清文人译者怀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文化忧患意识,承继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以“文化启蒙者”的姿态走进翻译文化系统,投入到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体系与文化话语权的建构当中,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也因此形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特有的翻译现象。在这一时期,被后世翻译评论界所诟病的误译、随意增译和漏译、自我发挥式的译述等个性化翻译大量出现。本文以林译小说为例,试图从译者文化姿态与文学(小说)翻译的互动角度分析译者主体性,厘清译者是如何在主、客观环境下发挥“受动中的能动”,产生“创造性叛逆”的译作。
一、 林纾的文化姿态:文化守成与中西融和观
译者文化姿态是译者基于特定的文化时空背景和个人主体意识,面对自身文化境遇时所作出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反应。它是一种无意识的历史结构,又是个体意志下的文化行为。
林纾自幼年时期就开始接受传统的古诗文教育,并坚持不懈地“穷日夕读”儒家经典著作,经年而得经史之腴的林纾由此奠定了今后为人治学的人生基调。直至四十岁后,他仍对“《诗》《礼》二经及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梁肉”[3],在去世之前还写下“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这些足以表明林纾追随儒家传统的拳拳之心。
林纾在坚守儒家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声疾呼引进西学:“以新学之明,证旧学之暗。自知为暗,则可以向明。”早在进入西学翻译实业前的1897年,他在他的《闽中新乐府》白话诗歌集中,就表达出对先进文化的渴望:“我徒守旧彼日新,胁我多端气莫伸”[4];“长官屡屡挑欧西,西学不与中学齐”[4]299。同时,对满腹道德文章,却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的饱学之士大加鞭挞:“外间边事烂如泥,窗下经生犹作梦”[5];“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5]87。
“学嗜宋学,文尊古文”的林纾在自我文化身份认同上,感受到两个方面的冲突。首先是中西冲突,在那个时代,当大清国体已摇摇欲坠,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念已逐渐风行的时候,“引西救儒”呼声高涨,但究竟是完全照搬西学,还是有限度地接受?其次是由此引发的中学内部新旧话语权的冲突:古文(文言文)及其所承载的儒家教义是否应该让位于由现代性话语扩张而构建起来的新质文学(文字)规范和价值体系?
传统伦理和中西融合的文化立场,既是林纾翻译小说所遵循的价值依据,也是其社会转型时期身份确认的文化标志。林纾以古文(文言文)翻译西方小说的方式直面上述两个问题。在晚清,古文与小说之间的距离不可谓不遥远:在文体形式上,一个高雅,一个通俗;在文学地位上,一个正统,一个边缘;在叙事内容上,一个讲究真实与严肃,一个则是虚构与娱乐。林纾以史汉笔调译西方小说,主张“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用传统道德观为西学辩护,借西学经验为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辩解,不仅消解了士大夫文人的文化焦虑,拉近了古文与西方小说之间的审美距离,还策略性地营造了一个言说自我的现代性话语想象空间,让读者和他一道关注和思考国人内外交困的生存环境。
一边是对传统文化的殷殷护佑,一边是对西方文学的热情拥抱,这种相互抵牾的思想特征共融于借外来文学之名,行“鼓民力、新民德”之实的功利主义的西学翻译实践中。然而,林纾毕竟是古文大家,古文的概念与儒家意识形态已在其脑海中深深地扎根,以古文观物(西方文学),物物不可避免地附着其主观的古文色彩。当林纾以古文家启蒙者的文化姿态参与小说翻译,遭遇西方小说所呈现的异域社会分工与民性时,其内心的文化观念必然通过翻译文本映射出来。
二、 文化姿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1. 文化姿态对译本选材方向的影响
作为实施翻译行为的第一步,译者对原语文本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和译入语环境的时代需求、读者阅读取向、译者自身的文化态度相关联。既是以“救国、保种”为宏旨,林纾在选择翻译文本时自然“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他的选材主题与译书动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林译小说的序跋中,可见当时翻译小说主题的时代性流变及林纾‘救国、警世、正德、求新’的译书动机。”[6]他的翻译选材广泛,但“所译孝义、政治、志怪、探险,以及男女爱悦之情,伧荒侠烈之行,侦探滑稽之事,且无一不寓革新故社、激劝世人之微意”[7]。林译小说“一部有一部之微旨”[8]:译《黑奴吁天录》,“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译《鬼山狼侠传》则欲以“盗侠气概”“御外侮”;译《爱国二童子传》“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自振”;译《雾中人》,“学盗之所学,不为盗而但备盗”;译《洪罕女郎传》,“极力策勉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每一部小说都透露出林纾以西学为镜,改良社会,激劝人心的志士热肠。
2. 文化姿态对翻译策略和语言风格的制约
林纾一身二任,把坚守文化传统和肆力引进西学矛盾地统一于他的文化使命之中。在晚清社会转型初期,如何认同与接受西方思想,形成了广大民众与西学之间最初的对抗心理。基于社会现实,西学翻译面对的是一个两难抉择:是恪守还是修正文化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林纾的翻译立场和策略。
这种两难境地清晰地在林译小说中呈现出来。晚清庞大而老迈的社会躯体迫切需要引入新鲜的异质血液来灌注,而这种异质血液在最初输入时,不啻他者的文化暴力行为。林纾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尽力在儒家礼教框架内消解这种文化暴力。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书中人物的道德信仰、宗教(基督教)信条给人带来精神安慰和力量的文字描述,以及原著中所引的《圣经》原文或宗教诗歌等均被林纾或者大加笔削,或者牵强附会于儒家伦理,其结果是传统道德观取代了基督教义,成为拯救和感召黑奴的精神力量。对于这种翻译处理,他的解释是:“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至,语多以教为宗。故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述,识者谅之。”[9]
“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述”,或许可以被原谅,但当原著中的情节有悖纲常名教时,林纾却坚持“述其已成之事迹”。在译本《红礁画浆录》序言中,林纾为婀娜利亚丈夫有外遇之事这样辩解:“……而其外遇者,又为才媛,深于情格于礼,爱而弗乱,情极势逼,至死自明”;在《剑底鸳鸯》序言中,林纾虽然认为侄儿与其叔父的未婚妻结婚“此在吾儒,必力攻以为不可”,但依旧照实译出,其辩解理由为:“达敏、意微岑始已相爱,休鼓不审其爱而强聘之,长征巴勒士丁三年不归,二人同堡,彼此息息以礼自防,初无苟且之行。……然中外异俗,不以乱始,尚可以礼终。不必踵其事,存其文可也。”在林纾眼里,上述行为虽有违伦常,但因为不逾礼,就可以接受,不属“当削则削”之列。而当林纾传译出《迦茵小传》中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的情节,再也无法用“不逾越礼防”来解释时,只得求助于《资治通鉴》:“美恶杂陈,俾人君用为鉴戒:‘鉴’者师其德,‘戒’者祛其丑。至了凡、凤洲诸人,删节纲目,则但留其善,而悉去其恶,转失鉴戒之意矣。”[8]292这里,引进西俗的价值标准由是否“用情之正”、“逾越礼防”转换成了是否具鉴戒之功用。因为“须知无外道之忧,亦不足以见正法眼藏”。
于此,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林纾的文化心理冲突和为启蒙、新民做出的种种努力。其实,在翻译《迦茵小传》时,林纾完全把迦茵定制在中国式审美价值框架下:比如林纾译迦茵为“操守至严”(原著:a considerable power of will);原文一句平常的表述:“(Joan) watched him while he slept”,林纾却美译成:“(迦茵)流目盼亨利”;他把原著中迦茵生下女婴但不久夭折,在爱与失去中,生活里的种种苦痛最终化成迦茵的尊贵历练,归化成中国古典语境中林黛玉般的柔弱与狐仙鬼魅之美:“而风貌之美,较前尤绝。似剪发新齐,覆额作螺旋状,秀媚入骨;且病后眉痕,及一双愁眼,已非生人之美,殆带愁带病,似仙似鬼之佳人也。”[10](原著:Perhaps she was more beautiful now than she had ever been,for the chestnut hair that clustered in short curls upon her shapely head,and her great sorrowful eyes shining in the pallor of her sweet face,refined and made strange her loveliness;moreover,if the grace of girlhood had left her,it was replaced by another and a truer dignity—the dignity of a woman who has loved and suffered and lost.)这些对异国女性的中国式美化似乎在解释迦茵“未婚先孕”也是情有可原,毕竟“然女子善怀,是其恒状”。可见,林纾是把中国人传统审美观与一位崇尚婚姻自主、爱情自由的勇敢的西方女性嫁接在一起,他把持的价值评判标尺既不是纯粹的儒学经验,也不是西学标准,而是经二者融合、取舍后的“第三种尺度”。这种具有现代性新思想的价值尺度决定了译者的文化姿态,在这种文化姿态的指引下,林译小说中中学背景下的西学新质突兀出来,中西思想的反差和对立激起的文化“陌生”感带给读者新鲜的味道和强烈的阅读欲望。
这种文化“陌生”感也从林译小说运用的语言文体策略中显露出来。林纾虽然用古文翻译小说,但他的译文已是较为通俗、富有弹性的文言文,夹杂着许多外来流行词语、白话口语、“欧化成分”和“说部之词”,这或许可以解释成是林纾针对古文创作和小说翻译所持的不同文化审慎态度。但是,视古文书写为生命的林纾一定也感受到古文文字表现力的不足,于是俗言欧体合并在高古而风华的古文中,这既是林纾扩展古文生存空间的努力尝试,也是他中西融合文化观的具体体现。在这样的文化姿态底下,中西道德观念、中西文化异俗和新旧文体共冶一炉,林译小说因此形成以具有现代性思想的价值尺度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他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既有的中国文化立场,他用中国文化立场来理解和整合西方文学,实现了西方文学的东方化过程。”[11]
三、 文学翻译实践丰富和改造译者的文化姿态
清末知识分子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封建王朝固有的华夷观念被炸裂,“过去一线单传的文明‘道统’被多种文明齐头并进的图景代替,于是就引来了相当深刻的观念变化”[12]。即使这样,封建士大夫文人阶层仍有文化心理优势,林纾也认为,“吾中国百不如人,独文学一门,差足自立”[13]。然而,随着文学翻译实践不断深入,林纾中西文化比附和融合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他在西方小说中发现了与古文同质甚而高明于古文之处。他多次强调“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其现实意义不在文学本身,而在于为晚清读者铺就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心理基础。中西文化的相融、会通之处为文化比照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西学顺利进入读者视野提供了心理认同的保障。在这个基础之上,帝国文学独大的心理防线也随之渐渐崩塌,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接受成为可能,也为西学合理参与新的文化构建补充了养分。
古文因文见道,“雅多俗寡”,庄简矜重。专意“美人名士”、英雄豪杰,或神佛仙怪,往往崇尚大题目。林纾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受到迭更司等文学名家的启发,从传统“贵族文学”中挣脱出来,关注平民社会。他认为“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叙战,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决脰溅血,生气凛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笔施之,亦尚有其人。从未有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净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则迭更司者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14]。相形之下,“以史公之书,亦不专为家常之事发也。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著笔为尤难”。在林纾看来,迭更司及其作品存在的社会意义在于“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15]。他在《贼史·序》中提到:“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无迭更司其人,如有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林纾认为,记市井琐事,写小人物和小事件比用“雄深雅健之笔”写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要艰难许多。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文道“寒气逼人”,已严重阻碍了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存名失实之衣冠礼乐、节义文章,其道不足以强国。”[7]175在迭更司等西方文学家的影响下,“神仙鬼怪和才子佳人团圆式的传统小说由林氏而扫荡,小说的形式由林氏而改造,小说的范围由林氏而扩张”[7]35,林纾着意使用小人物来穿针引线,以小人物的视野观察社会积弊,并展现社会发展的风貌,体现出现代小说意识。他的《剑腥录》、《冤海灵光》等四部小说均采用以小人物描写大时代的创作风格。从历史演义到以小人物描写大时代,从传统“贵族文学”到极具平民意识的文学观,对旧文学传道文章的指摘和对迭更司小说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林纾写作姿态和文学观念的改变。
林纾的文化姿态表现出其古文家的人文渊源和启蒙救国的时代使命,这种既追“新潮”也念旧统的文化性格注定其译作也呈现出双重性。于是译文读者既能看到因文见道的古文印痕,又能感受林纾椎心泣血,为时代也为生存而呼喊的文字。
四、 关于译者主体性的再思考
在中西新旧思潮间的夹缝中求得自身价值的实现是晚清文人的普遍诉求。林纾在中西思想、古今文化之间的挣扎、选择与取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人特色。林译小说的成功与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中西文化权力关系、本地文化需求、译者的价值诉求等因素息息相关。林纾在晚清社会空前的文化变革与转型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植根于儒家道统的启蒙者的文化姿态来进行文学翻译与创作,于此,他无法挣脱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巨大影响,并能够发现和汲取西学中能为我所用的积极的文化力量,他跨越了中西、古今的思维藩篱,以其敏锐而卓越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其特有的文学美感和艺术渗透,向民众传达他的文化想象、焦虑和期待,在为民族危机而呼号的宏大叙事中,为广大民众也为自己建构起新的文化生存空间。
在这场由晚清文人发起的译以致用、具有功利主义性质的文学翻译热潮中,小说翻译实质上成为译者经世济民的实业活动。林纾在中西文学最初的相遇和交际过程中,以启蒙者的文化姿态促使他作出时代抉择,他的翻译活动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投射出鲜明的“以译救国”的译者主体性,藉此构成他的翻译主体身份。他的译本选材“一部有一部之微旨”,译文以中国传统伦理调和西方自由和人文精神,赋予西方名著儒学价值内涵,译著中含有大量的“创造性叛逆”和“思想性误读”。然而,林译小说“打破了中国文学长期的雅俗阻隔,使‘异端’与传统得以调和;同时,这个空间所容纳的西方价值,成为孕育反叛传统的现代精神的温床,相当大地影响了五四一代的文化选择”[16]。可见,林纾的中西文化调合意识催生了林译小说中的现代价值,“异端”与传统之间形成的文化张力在顺应晚清文人读者阅读期待的同时,更赋予了他们具有现代精神的人文素养,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
林译小说中不断强化的译者主体性取向是晚清社会文化生态的缩影。林译小说中,文言与白话的相容与相争、西方文学形象的中国化、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西方现代女性和谐共存。在译者中西调和文化观念的调度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顺应时代的需求,译文的“应时化误读”是译者主体性的策略性体现,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译者及其主体性的发挥之于文学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不难看出,不同历史阶段译者的主体创造性、意向性和选择性的发挥都有其时代特点,有其具体的内容和主旨依归。林纾的译者主体性是其国家民族意识和内心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在映现,也是他对于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接受及其适用度和中国传统的承继及现代价值思考后的文化反应。这经由西学翻译引起的文化反思既给译者带来了现代性的文化观念,更激发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新的历史机遇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得以用启蒙主义的文化姿态参与中国现代性的话语构建,书写彰显其身份的文化新姿态,并“带给译者强烈的归属感,提升了译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价值,塑造了中国文学翻译的现代品格”[17]。
同时,林纾在翻译过程中“既表现出基于自身审美倾向及翻译思想的主观能动性,又表现出在译入语文化系统面前的受动性”[18]。“主观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角力需要理性的权衡,这期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文化及文学相互渗透、相互征服的情形。这种“受动中的能动”效果在林译小说中获得极好地诠释。林纾准确找到了异国文学之间审美情趣和文化伦理的通约性,在共同的人性和审美价值的观照下,通过挑战现实与传统,中西融通,林译小说艺术性地走进读者内心,获得启蒙民众、改良社会的潜能,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去认知与接受现实世界的新知识。
在今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背景下,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以译入语环境的接受效果为导向,将译者的创造性、意向性和选择性取向与译入语环境的文化需求、现实需要以及译入语读者的阅读审美惯习等紧密结合起来。林译小说的成功给我们当下探究中国文学走出去路径提供了启示:第一,西方对他者文化的接受具有文化功利主义的选择性倾向,若一味强调中华文化原汁原味地输出,而不考虑译入语环境的实际文化需求,只能造成文化文本跨文化旅行时水土不服,迷失在新的文化空间里,而无法满足译入语的读者期待,因此,对跨文化文本做一些相应调适或者改造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第二,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应该具有独立的文学品格,立足本土而又超越本土意识,包含有为世界所理解和认同的现代性人类精神和人文价值理念等关乎人类的共同命题,以接受多元化文化视角的解读,推动中国文学更好地进入国际视野。
——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