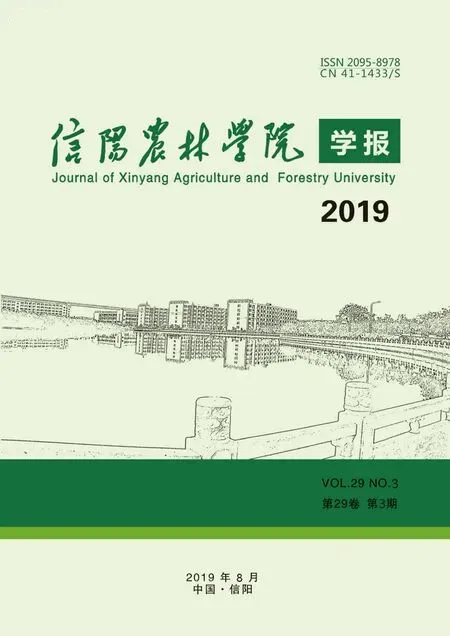城市空间与女性写作
郝艺霞
(延边大学 朝汉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1 丁玲小说创作的城市书写
“城市中一个公寓里住着一位飘零在外的女性写作者”,详细地诠释了女性作为劳动者的独特身份。首先,女性写作者来自于外面的世界,并非本土城市人,因而城市中原本并没有她的位置,她以外来者的身份闯入城市,必定要经历并不断适应城市带来的一系列病态生活环境:外界的喧嚣、现代文明的入侵、无可依靠的孤独、经济的窘迫、情感的缺失等等;其次,公寓带来的全方位封闭式结构为女性提供了相对的安全感,使得女主人公坚守其中很少外出。对她来说,窗户外面就是热闹的大街,是宏大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是行动着的现代历史,而公寓内的女性只能枯守在隐私的机械时间中,无法参与,也被拒绝参与到其中,与外界沟通的唯一路径就是看报纸和与来访者聊天。在自我的双重困境中,“女性写作者”对外界的一切渐渐痛恨,拿起笔书写无尽的血泪和孤独是寓居公寓的知识青年唯一倾吐苦闷的方式,“女性写作者”和公寓在无形中建立了一种私密式的关系,因此公寓周围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作家的生活和创作。而与城市外在环境的对抗,也就成为写作群体对稳定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吁求,在尚未承认居家写作者职业身份的社会中求得安稳,以此来完成自我空间的认同。丁玲从十八岁起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瞿秋白作为她的俄语老师指引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作为女性写作者,在五四革命落潮时期身份异常尴尬,当她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震动五四文坛时,很多追捧者和文学爱好者似乎带着好奇的、异样的心态看待这部以探索女性写作者微妙心理世界为主要情感线索的作品。面对外界环境的质疑[1]527,丁玲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女性生活,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她笔下这些女主人公的日常活动范围是一个狭小的公寓,即在一个完全私人化的空间内记录女性写作者的私人生活及情感诉求,因此公寓本身的环境以及外界的大环境对女性写作者的创作尤为关键。“对于游走于公寓间的青年而言,或许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公寓’不只构成了栖身、交往的物质性环境,某种空间想象也会连带发生,并潜在关联了一代人的身份认同。”[2]131而女性写作者正是在对城市的空间想象中完成了自我个人情感的喷泻,她们苦苦困守在并不友好的城市里,隐忍着生活,坚守着这一块尚未被现代都市文明入侵的神圣之地,渴望向城市空间宣告自己的身份。
公寓周围的噪音分为两种:一种是邻里之间的噪音,如:小孩子的哭闹叫喊声、大人们吵架打骂孩子的声音、邻里间打牌娱乐的声音等等一系列由家庭生活所引起的噪声,不断折磨着居住在其间的写作者,而且因其此起彼伏、循环往复的特征,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侵扰着作家脆弱的神经;另一种是交通噪声,如:大马路上尖锐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大卡车过马路时轧路声、马车夫甩鞭子的声音等类型丰富、千奇百怪的城市噪音对脑力工作者形成无理的挑衅。《鲁迅日记》中时常有这样的记录:“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因而属发音稍低,而此人大漫骂,且以英语杂厕。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3]16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噪音折磨到经常搬家的一位作家,他因为自己的生活习惯与旁人不同,白天在客厅同来家中拜访的读书人和朋友聊天吃饭,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更没有机会安心看书和写作。萧红曾经在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提到他每天白天家中客人络绎不绝,接待客人、陪客人吃饭、探讨问题需耗费大量时间,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鲁迅身体大不如前,但工作量似乎并没有减少,相反在不断增加。因此对鲁迅自己而言,能够安静写作的时间异常宝贵,一般他都是在深夜读书和作文,一是人们都已经休息了,没有人和事情打搅他的思路;二便是除此之外他再挤不出其他的时间,只能消耗睡觉的时间来完成工作。但即使如此安排,深夜似乎也无法让他心静,陈漱渝在《鲁迅的左邻右舍》中谈到与鲁迅日记中相似的情形,许广平作为鲁迅的妻子,在《景云深处是吾家》同样写到鲁迅被邻居的噪音折磨得异常痛苦,无计可施,而她对此也忧愁无奈。可见噪音对作家的精神造成很大危害,也对文学的创作带来很大损失。
中国作家为此苦恼郁闷,国外的许多诗人、作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叔本华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论噪音》,他写道:“偶然会有一种轻微但持续不断的噪音在打扰我,过一段时间我就清楚地感觉到,我的思路越来越困难,就好比是腿上负了重却还要尽力行走一样费力,最终我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4]493在涉及噪音问题方面,这些以思考和写作为主要职业的人们将这些打乱他们写作节奏的噪音归咎于噪音的发出者,面对人们嘻嘻哈哈的笑声、男人将死女人哭泣的叫喊声,作为文学启蒙者的鲁迅说:“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5]101城市及其衍生物的喧闹,打破了创作者的思路,影响他们的日常写作。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写作者同样避免不了噪音的影响,这些在外人看来平常的声音,侵犯着她们脆弱敏感的神经,加重了她们的精神疾病,同时从两者的决斗中也可反观女性写作者对私人空间的坚守,以及对沦落于城市空间内人们的蔑视。
2 女性日常生活的空间建构
丁玲早年曾经也有过这样一段侨寓经验,因此对在如此生活境遇下的“室内写作者”格外偏爱,而且这样的小说在丁玲早期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些年轻女性被城市噪音困扰着,恶化了她们的情绪,威胁着她们的生存。《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是一个居住在城市公寓中的青年女性写作者,她的私人写作空间每时每刻都被外界的噪音干涉:
“天天一听到从窗外走廊传来的那些住客们喊伙计的声音,便头痛,那声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嗄,又单调;‘伙计,开壶!’或是‘脸水,伙计!’这是谁也可以想象出来的一种难听的声音。还有,那楼下电话也不断的有人在电话机旁大声的说话。”[6]42
邻里间的吵闹声令女性写作者身体痛苦,精神无法集中,从莎菲对声音描写的“粗、大、嗄”可以反观她对空虚单调城市生活的司空见惯,重复性的日常城市空间与主人公作为作家的身份格格不入,这里带有莎菲对噪音发出者人格素质的怀疑,以及对他们阶级身份的蔑视。主客之间的关系,似乎包含在洗脸水这个日常生活形态内,阶级性无形中为被服务者设定了服务对象,这样的既定关系不需要人为设置,无形中已经扎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内,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人认为这样的大吼大叫是提升各自价值、在现代城市中张扬自我位置的一种方式,因此他们对噪音浑然不知,恰巧认为这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丁玲在这里建构了以噪音为主要元素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劳动人民表现得强势而野蛮,他们是噪音的生产者、天才思想的扼杀者;知识分子则往往是委屈、弱势的一方,是噪音的被动承受者、无力反抗者[7]192。知识分子对噪音的认识,与其他不同阶级的人们对噪音的看法大相径庭。对劳动人民来说,吃饱穿暖才是他们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写作是他们的职业,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体力和脑力劳动者之间天然存在着一层隔膜,城市人对公共生存环境的侵犯,是知识分子痛恨噪音、反抗城市现代文明的主要原因。
莎菲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记笔记,到第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历时九十多天。十二月她只写了3篇日记,可见北京的日常生活无法触动莎菲的写作欲望;一月份从一月一号开始陆陆续续写了10篇,凌吉士的出现为她的生活带来希望,使她内心燃起了爱情的火焰;整个二月份因生病莎菲停止写作;三月份从四号开始,她几乎每天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写日记,共记21篇。凌吉士将莎菲从日常生活中解放,但同时加速了她离去,从莎菲前两个月和后两个月的日记来看,日常生活作为抽象概念,是消磨女性意志、耗费女性精神的罪魁祸首。《日》中的年轻女性同样面临着噪音的困恼,但是比起莎菲,她更加痛苦无奈。
伊赛生活在由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管辖的城市,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使她根本没有思考和反思自我的机会。城市空间的变态发展,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作家丧失了写作能力,彻底沦为日常生活的奴隶,被其控制、受其折磨,因而作家身份地位的不断恶化是这一时期丁玲反复思考的问题。伊赛因久久居住在公寓内,皮肤显出一种病态的苍白色,患有与侨寓女性相同的精神疾病,她深深地为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噪音所困扰,似睡似醒的生活状态迫使她放弃写作,每天过着简单而单调的生活,早上将她从梦中叫醒的不是清晨美丽的景色,而是城市空间的衍生物——噪音。
“她已成了习惯,一种不良的习惯,使她不能安安稳稳睡去,常常为了稍大的响声便惊醒了。譬如隔壁家里的小孩哭了,或是对门家里的麻将牌玩得重一点,这些普通人都不介意的小小吵闹,都能扰了她。这时,每天都从马路上传来垃圾车的响声,铁轮轧在柏油路上,从街口涌进了另一部铁车。推车的人,大声吼着。每一家的女仆、女主人,都慌忙从楼梯下的黑床上翻身起来了。一股浓烈的臭气升起,在高墙密屋之中,四处散发,百十个篾制的扫帚,百十个妇人拿在手上的木质的桶里面洗刷,不规则的‘沙,沙’声,夹杂着水声使每一家的薄壁都为之震动。伊赛每一个清晨便为这有次序的倒马桶的闹声所扰醒,而且为此苦恼。”[6]243
《日》中清晨所发生的一连串声音,在中国每个城市都会以相同的方式上演。忙碌的凌晨,劳动者赶着现代都市生活节奏,无暇顾及他们行动背后产生的噪音。在伊赛这里,她对制造噪音的城市憎恶,这些由于交通工具及机器、资本和制度产生的噪音是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副产品,它象征着权力、力量、现代性与城市生活[8]。在伊赛看来城市中为生活忙碌的底层男人与女人是愚蠢的,她尤其强调女人的生活地位,外表粗糙、身体肮脏、思想愚昧固执,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失去女性特有的气质,成为现代化都市中的生产机器,无可救药。伊赛站在上帝视角俯瞰这些在城市中挣扎生活的底层被剥削者,鄙视现代文明及其衍生出的一切,包括底层劳动妇女,她们在机械般的日常生活中与城市一同沉沦。
作为家庭写作者,伊赛未尝不被现代文明所规约。当钟表时针指向八点的那一刻,工作的时间到了,厌恶城市生活的她不得不从幻想中剥离投入现实生活,首先被她感知的是声音:“街里,热闹起来了。许多小贩,连续的叫嚷着,有的是用铃子或者铜锣来代替的。光那些买旧东西的担子,她从声音上,就辨得出不在十个以下。每家的小孩,为了零星事物的诱惑,都在各自的后门口哭笑。有的小孩目的达到了,喜气洋洋,有的是不足,大声的闹着还要。”[6]244没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引起伊赛的注意,新鲜的、鲜活的声音早已被繁杂的、日常的生活同化,惟有这位知识分子坚守着自我,在小房间里做一些无聊的事情来消磨时间,梦想是她在现代城市里的唯一安慰。在黄昏来临夜幕坠落的时刻,伊赛终于无力支撑早已疲倦的身体,做着与昨天同样的梦,醒来又过着与昨天同样的生活。
3 城市对抗中的人格坚守
身体和思想被现代文明割裂开,理想主义者的两位女性在现实面前没有任何办法,用莱辛的话来说:“她们在用知识分子的法则与日常生活庸俗化作战争”,现代人需要用噪音来驱逐笼罩在他们内心上对个人存在的空虚感,但是知识分子痛恨这种缺乏规范化的喧嚣生活,并且为了安静要与这种噪音抗争,守护女性自己的“一间安静的屋子”。
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中谈到她从小喜欢一个人在寂静的地方看书学习,沈从文在《记丁玲》和《记胡也频》中反复谈到两人多次搬家,只为寻找适合他们写作的一间小屋[9]131。在二十年代以书信、日记、小说等构成的文体的价值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在文学虚构与自叙传的真实之间,它们也像一份历史档案,记录了一代文学青年在都市中的生存境遇,以及文学认同建立的过程[2]166在现代城市面前,知识分子表现出更为持久的抵抗力,女性写作者以其特有的坚韧性与现代性展开搏斗。
噪音作为一种带有摧毁性力量的城市符号与困守在公寓中的女性构成对照,即日常生活对女性意志的消解在知识分子看来是可克服的,但是对于普通底层劳动人民以及沉醉于感官刺激的上层享乐主义者,他们无法抵挡现代的诱惑,并且甘愿做城市的奴隶。女性写作者与城市空间的对抗,不仅仅是对城市文明繁殖下噪音及其他垃圾的厌恶,而是从抗争中获得城市对其身份的认同。
——重读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解析《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