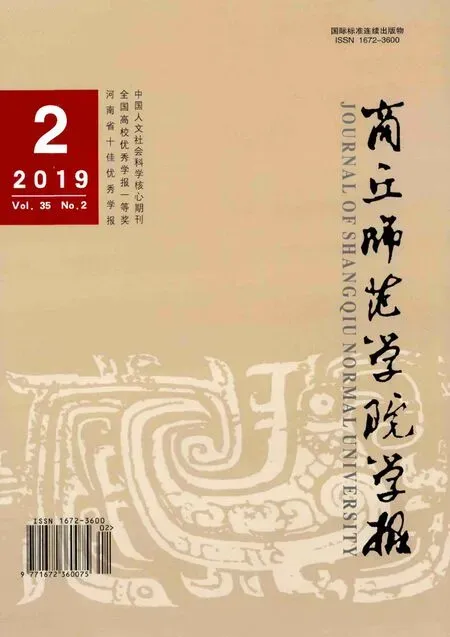《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分类渊源与归类调整
——以经部为中心的考察
连 凡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关于《文献通考·经籍考》(简称《经籍考》)的分类体系及其与历代目录的因革关系。学术界虽然已有不少相关研究[1],但基本停留在大的宏观类目及个别例证的分析上,还缺乏对全书中的分类异同及其书目归类调整的全面系统分析。为此,笔者从穷尽分析《经籍考》所引前代目录书籍的条目入手,分析其整合过程。进而对其分类体系与归类调整作出自己的评判。具体则以《经籍考》经部全文作为考察范围。
一、《经籍考》经部的分类渊源
笔者通过建立“《文献通考·经籍考》全文分析数据库”,将《经籍考》3938条书目下的6074条引文与其文献来源一一链接。其中《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新唐书·艺文志》(简称《新唐志》)、《崇文总目》(简称《崇文》)、《郡斋读书志》(简称《郡斋》)、《直斋书录解题》(简称《直斋》)是《经籍考》分类及书籍归类的主要依据。于是笔者提取《经籍考》引文材料中来自此六部主要书目的共计4693条材料进行各部类的统计分析。
表1 六部书目的辑录条数在《经籍考》总叙及四部中的统计表

由表1可知,《经籍考》引用这六部书目的材料中以《直斋》与《郡斋》为主体,这两家再加上《崇文》是《经籍考》分类体系与书目归类的主要依据,而来自《汉志》《隋志》和《新唐志》的材料则基本是在各部类小序和小计中出现,以反映该部类学术源流与兴衰。
下面以《经籍考》经部引用这六部书目的情况为中心进行具体分析。

表2 《经籍考》经部引用六部主要书目的统计表
由表2可知,《经籍考》经部条目以引用《直斋》经部条目为最多,引用《郡斋》经部次之,《崇文》经部再次之,三者占《经籍考》经部引用此六家书目总条数的78.16%。除前代书目的经部外,《经籍考》经部还涉及这六部书目的史、子二部,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经籍考》经部引用六部主要书目
由表3可知,《经籍考》的经部范围与前代书目的范围有比较多的交错现象,前代书目中归入史部、子部的书目有不少被《经籍考》归入经部中。这种调整往往有其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下文将以《经籍考》经部的各二级类目为次逐一进行分析。这里先列出《经籍考》经部各二级类目引用这六部主要书目的构成情况如下:

表4 《经籍考》经部引用六部主要书目之情况一览表

续表4

续表4
由表4可知,《经籍考》经部与作为其著录与归类之主要来源与依据的六部主要目录的相关类目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即从具体书目归类的差异上升到类目范围的诸多差异。因此笔者认为,应将《经籍考》与作为其主要来源的六部书目之间的类目关系的分析与具体书籍归属调整的分析结合起来,即宏观分类与微观归类的分析相结合,同时注意将对象放在整个目录学史与学术史的发展过程中予以考察。
二、《经籍考》经部分类及其调整的具体分析
(一)易类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易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易类1条、《隋志》经部易类3条与《新唐志》经部易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其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经部易类14条、《郡斋》经部易类44条与《直斋》经部易类78条,共计141条。(小序中亦引有《崇文》之一条)由表4可见,《经籍考》经部易类所收书籍未超出此前书目易类的范围,其中引用《直斋》条目达一半以上。
(二)书类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书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书类1条、《隋志》经部书类3条与《新唐志》经部书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书目下的解题又引《崇文》经部书类4条及《郡斋》经部书类18条与经部经解类1条,又引《直斋》经部书类28条,共计56条。可知《经籍考》书类也基本来源于前代书目之书类,只有一条是来自《郡斋》经部经解类,即《经籍考》卷四经部书类“《古三坟书》一卷”条下引用“晁氏曰”,此解题系来自《郡斋》卷四经部经解类著录的“《三坟书》七卷”。此书晁氏以为是宋代张商英伪撰。《经籍考》此条下引《直斋》云:
陈氏曰:元丰中,毛渐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辞诡诞不经,盖伪书也。《三坟》之名,唯见于《左氏》右尹子革之言,盖自孔子定《书》,断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无征不信,不复采取,于时固已影响不存,去之二千载,而其书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谓之“坟”,“帝”谓之“典”,皆古史也,不当如毛所录,其伪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张商英伪撰,以比李筌《阴符经》。[2]117
虽是伪书,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与《尚书》同类的古史无疑,当归入书类。所以《直斋》卷四将其归入经部书类,而《经籍考》从之。但《四库总目》卷十则将其归入经部易类,四库馆臣在其下用按语指出:
按,《左传》称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书序所解虽出依托,至刘熙释名则确属古书,据所训释,“三坟”乃书类,非易类也。然伪本既托于三《易》,不可复附书类中,姑从《易》纬之例,附其目于诸家《易》说之末。[3]137
《四库总目》因其内容包含了《连山》《归藏》《乾坤》三《易》而将其附在易类之末,从而使其分类符合其实际内容,较之前代书目无疑更合理一些。
(三)诗类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诗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诗类2条、《隋志》经部诗类3条与《新唐志》诗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而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经部诗类6条、《郡斋》经部诗类10条与《直斋》经部诗类20条,共计42条。可见《经籍考》经部诗类所收书籍也未超出此前书目诗类的范围。
(四)礼类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礼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礼类2条、《隋志》经部礼类2条与《新唐志》经部礼类1条,而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经部礼类7条、《郡斋》经部礼类24条与《直斋》经部礼类35条,共计71条。可见《经籍考》经部礼类所收书籍未超出此前书目礼类的范围。
(五)春秋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春秋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春秋类2条、《隋志》经部春秋类2条与《新唐志》经部春秋类1条,其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春秋类27条、《郡斋》春秋类41条与《直斋》春秋类63条,共计136条。可见《经籍考》经部春秋类所收书籍未超出此前书目春秋类的范围。
(六)论语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论语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论语类2条、《隋志》经部论语类2条与《新唐志》论语类1条,其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论语类1条、《郡斋》论语类17条与《直斋》经部语孟类22条、子部儒家类1条,共计46条。可见《经籍考》经部论语类所收书籍基本未超出此前书目论语类的范围。只有1条例外来自《直斋》卷九的子部儒家类,即《经籍考》卷十一经部论语类所著录的最后一家《孔子家语》,此书《郡斋》卷四亦归入经部论语类。《经籍考》在此条下首先辑录了王肃托名孔安国所作的后序云:
王肃注。后序曰:《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2]289
据此说,则《孔子家语》与《论语》本是同源,内容也相近。《家语》归于论语类似无可厚非,最初出于孔壁而由孔安国撰次的《孔子家语》确实是这样的,马氏在其下又辑录了汉代博士孔衍的奏疏云:
博士孔衍言:臣祖故临淮太守安国,逮仕于孝武皇帝之世,以经学为名,以儒雅为官,赞明道义,见称前朝。时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改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2]291
此书虽经孔安国整理,但因“巫蛊”事起而未立学官,到了汉末此书已亡佚。而魏王肃所得之《家语》实为其辑佚编纂而来。宋代以来多有人怀疑其为王肃伪造。陈氏对王肃的《家语》早已有所怀疑。《经籍考》所引《直斋》云:
陈氏曰:孔子二十四世孙猛所传。魏王肃为之注。肃辟郑学,猛尝受学于肃,肃从猛得此书,与肃所论多合,从而证之,遂行于世云。博士安国所得壁中书也,亦未必然。其间所载,多已见《左氏传》、《大戴礼》诸书。[2]291
陈振孙指出,王肃《家语》中的材料多见于《左传》《大戴礼记》诸书之中,认为此书可能是王肃辑录群书而成,非孔安国所得孔壁中原书,故将其视为王肃自己的著作而归入儒家,不得厕入经部论语类。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虽然在今天看来,王肃本《孔子家语》可称为辑佚书,称为伪书并不一定适当。但总之,孔安国所编的壁中书《孔子家语》可附入论语类,而王肃编纂的《孔子家语》可归入儒家。其后的《宋志》同《经籍考》归入经部论语类,而《四库总目》在认定为王肃伪撰后同于《直斋》将其归入子部儒家类中。
(七)孟子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孟子类的小计引《汉志》诸子略儒家类1条、《隋志》子部儒类3条、《新唐志》子部儒家类6条以及赵岐《孟子·题辞》,以叙述该类之学术源流,而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儒家2条、《郡斋》儒家10条与《直斋》经部语孟类6条、子部儒家类1条,共计29条。可见《经籍考》经部孟子类所收书籍基本未超出此前书目儒家类之范围。
“孟子”在《直斋》以前皆列为诸子之一而归入子部儒家类。唐代韩愈为了对抗佛道二教以重建儒学权威,提倡道统论,奉孔孟为儒学正统,认为上古以来儒家圣人之道传至孟子而断绝,并自任为道统继承人。其后随着孟子地位的提升,北宋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孟子》由“诸子”(儒家)之一家抬高到经书地位的所谓“《孟子》升格运动”,褒奖孟子赞成升格的“尊孟”与贬斥孟子的“疑孟”两派相互展开了争鸣。如李觏与司马光属于“疑孟”派,而王安石及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则属于“尊孟”派[4]92-138。伴随着以继承孔孟之道统为己任的道学(二程洛学)之兴起,特别是南宋朱熹的集道学大成之作《四书章句集注》的出现,《孟子》终于从诸子中脱颖而出,其经书地位得以确立。不过在《直斋》中《孟子》虽升入经部,但依然与《论语》并为一类,并未完全独立。到了《经籍考》才首次将其独立出来,后代因之不变。这是马端临在《直斋》基础上的一大推进。分析可知,虽然《经籍考》经部孟子类是参考《直斋》经部语孟类而设立,但具体书目却以来自《郡斋》经部儒家类者为多。
其中有1条来自《直斋》卷九子部儒家类,即《经籍考》卷十一经部孟子类的“《尊孟辨》七卷”。其下辑录《直斋》解题云:
陈氏曰:“建安余允文隐之撰。以司马公有《疑孟》,及李遘泰伯《常语》、郑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辩之,为五卷。后二卷则王充《论衡·刺孟》及东坡《论语说》中与《孟子》异者,亦辩焉。”[2]299
与李觏的《常语》一样,司马光的疑孟思想后来也遭到余允文与朱熹等人的批判。《尊孟辨》即是余允文反“疑孟”而主“尊孟”的一部考辨著作。《直斋》既设立有经部“语孟”类,理应归入才是,此条不知何以不入孟子类。《经籍考》在此予以调整,甚是。《四库总目》卷三十五亦将其归入经部孟子类。
(八)孝经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孝经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孝经类2条、《隋志》经部孝经类2条与《新唐志》孝经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孝经类5条、《郡斋》孝经类4条与《直斋》孝经类5条,共计19条。可见《经籍考》经部孝经类所收书籍未超出此前书目孝经类的范围。
(九)经解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经解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孝经类1条、《隋志》经部论语类1条与《新唐志》经部经解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而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经部论语类8条与小学类4条、《郡斋》经部经解类4条以及《直斋》经部经解类16条与子部杂家类1条,共计36条。可见《经籍考》经部孝经类所收条目的来源比较复杂。
经解类与孝经类、论语类、小学类、杂家类都有密切关系。在《汉志》中,“《五经杂议》十八篇。石渠论”这部经解类著作附在六艺略孝经类之后,而《隋志》卷一经部论语类则附录有“《五经杂义》六卷孙畅之撰”。对此张舜徽指出:
郑玄《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遭离散,后世莫知根原,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可知汉儒旧说,皆以《孝经》为六艺之大本,五经之总会,故《汉志》录《五经杂议》入《孝经》家。又《论语》所包亦广,不专一业,实亦概括五经,故《隋志》录《五经异义》以下诸家附《论语》之末,其例正同。[5]243
由此可知,在《汉志》与《隋志》中“经解”附于“孝经”或“论语”类之缘由,盖皆取其为“五经之总会”,所以在经解类设立之前,兼论群经的书一般都归入其中。其后《旧唐志》(《古今书录》)首次在经部设立了“经解”类,其卷上著录了“《五经杂义》七卷,刘向撰”。《新唐志》因之,在卷一经部经解类著录“刘向《五经杂义》七卷”。但《崇文》不从《新唐志》《旧唐志》,又退回到《隋志》,将“经解”类著作附在“论语”和“小学”类后,可谓保守而泥古。到了《郡斋》和《直斋》才真正确立了“经解”类的著录范围。《经籍考》因之。其中来自《直斋》卷十子部杂家类的“《匡缪正俗》八卷”,《崇文》将其归入“论语”类,《郡斋》将其归入“经解”类,《经籍考》从《郡斋》归类,较《直斋》的分类更合适一些。但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四库总目》卷四十将其归入小学类训诂之属,才算最终在四部体系中为其找到了恰当的归属。
(十)乐类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乐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乐类2条、《隋志》经部乐类1条与《新唐志》经部乐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经部乐类47条、《郡斋》经部乐类14条及《直斋》子部音乐类27条,共计92条。(又小序中分别引有《郡斋》与《直斋》小序各1条)。可见《经籍考》经部乐类所收书籍主要来自此前书目乐类的范围,以《崇文》为最多。而《经籍考》与《直斋》在乐类的归部上有所不同。《经籍考》卷十三经部乐类的小序引《直斋》子部音乐类小序云:
陈氏曰:刘歆、班固虽以《礼》、《乐》著之《六艺略》,要皆非孔氏之旧也。然《三礼》至今行于世,犹是先汉旧传,而所谓《乐》六家者,影响不复存矣。窦公之《大司乐章》既已见于《周礼》,河间献王之《乐记》亦已录于《小戴》,则古乐已不复有书。而前志相承,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以充《乐》类,与圣经并列,不亦悖乎!晚得郑子敬氏《书目》,独不然,其为说曰:“《仪注》、《编年》,各自为类,不得附于《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今从之。而著于子录杂艺之前。[2]320
《直斋》认为,原属先秦六艺(六经)中的古乐书已经亡佚,后世乐书不得再厕身于经部乐类,因此取消了经部乐类,并将后世乐书归入子部“杂艺术”类之前的“音乐”类。马端临对陈振孙的这种处理作出了调整。马氏直接在按语中指出:
按:古者《诗》、《书》、《礼》、《乐》,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六艺》,以为经籍之首。流传至于后世,虽有是四者,而俱不可言经矣。故自唐有四库之目,而后世之所谓《书》者入史门,所谓《诗》者入集门,独《礼》、《乐》则俱以为经,于是以历代典章、仪注等书厕之《六典》、《仪礼》之后,历代乐府、教坊诸书厕之《乐记》、《司乐》之后,猥杂殊甚。陈氏之言善矣!然乐者,国家之大典,古人以与礼并称,而陈氏《书录》则置之诸子之后,而侪之于技艺之间,又太不伦矣。虽后世之乐不可以拟古,然既以乐名书,则非止于技艺之末而已。况先儒释经之书,其反理诡道,为前贤所摈斥者,亦沿经之名,得以入于经类,岂后世之乐书,尽不足与言《乐》乎!故今所叙录,虽不敢如前志相承,以之拟经,而以与仪注谶纬并列于经解之后,史、子之前云[2]320。
肯定了陈氏所说的“乐类著录已非古乐”,必须相应作出调整的论断,但认为陈氏将乐书厕入“技艺”之间,又不免矫枉过正。在注重礼乐教化作用的马端临看来,历代朝廷制定的乐书是具有治国安邦作用的“国家之大典”,与民间不登大雅之堂的“技艺”存在雅俗之分,不可混为一谈。于是他提出了折中方案,即在保留经部乐类的前提下,将乐类的排序从原本紧跟“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之后下降到“经解”之后,虽然地位上已不能与“五经”相提并论,但毕竟位于子部之前。马氏以此传达后世制定的乐书虽非“先王之古乐”,但毕竟高于子部“技艺”的意思。这也集中体现了马端临的儒家正统思想。到了《四库总目》则循此思路对乐书进行了分化。其卷三十经部乐类小序云:
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3]500
《四库总目》将《经籍考》中萌芽的雅与俗、理论与技艺之区分正式确立下来,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正统礼乐观。而上述马端临的做法可谓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十一)仪注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仪注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礼类4条、《隋志》史部仪注类2条与《新唐志》史部仪注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书目下解题引《崇文》经部礼类8条,引《郡斋》经部礼类3条、经解类1条、小学类3条与史部仪注类5条,以及《直斋》史部礼注类38条与目录类3条,共计68条。可见仪注也是较有分歧的一类。
考《汉志》无“仪注”类,其中“《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弹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议奏》三十八篇”四部“仪注”类书籍皆附入经部礼类中。《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崇文》《郡斋》皆设“仪注”类(《直斋》在史部设有“礼注”类,名异实同),但皆归入史部之中,到了《经籍考》才调整上升到经部之中。“仪注”与经部礼类关系密切,《经籍考》的做法是经部礼类只著录古代“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及其相关的注释类著作,后代制定的礼书则归入经部仪注类,界限很明晰。《崇文》虽有“礼”与“仪注”两类,但其礼类除“三礼”外还著录有“《江都集礼》”(隋代)、“《开元礼义鉴》”(唐代)等后世礼书,同时《崇文》的史部仪注类也著录有《礼阁新仪》《唐礼纂要》(皆唐代)等后世礼书,这样便与经部礼类混淆了界限。因此,《经籍考》对其进行了调整,将8部在《崇文》厕入经部“礼”类的后世礼书归入经部仪注类。《郡斋》经部礼类著录的“《开宝通礼》二百卷”“《太常因革礼》”“《元丰郊庙礼文》三十卷”这3部和《崇文》中的归类一样,都是后世礼书厕入礼类,因而都被马端临调整到仪注类。《经籍考》对“三礼”和后代礼书区分的做法为《四库总目》所继承并予以细化,即在经部设立礼类二级类目,其下分立“周礼”“仪礼”“礼记”这些“三礼”之类,又并列有“杂礼书”“三礼总义”“通礼”诸类。
除此之外,《郡斋》卷四经部经解类著录有“蔡邕《独断》二卷”,《经籍考》卷十四经部仪注类收录此书,著录为“《独断》二卷”,其下辑录《郡斋》解题云:
杂记自古国家制度及汉朝故事。[2]349
又辑录《直斋》卷六史部礼注类下此书解题云:
言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2]349
《郡斋》将《独断》归入经解类当是着眼于其考证经义的著述形式,而《直斋》与《经籍考》的归类则着眼于其所论述之实际内容。《四库总目》从《郡斋》的做法出发,将《独断》归入子部杂家的杂考类。其卷一一九杂家类杂考之属的按语云:
按:考证经义之书,始于《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之类,皆沿其支流。至唐而《资暇集》、《刊误》之类为数渐繁,至宋而《容斋随笔》之类动成巨帙。其说大抵兼论经、史、子、集,不可限以一类,是真出于议官之杂家也。(班固谓杂家者流出于议官。)今汇而编之,命曰杂考。[3]1600
又《郡斋》卷四经部小学类著录有“《考古图》十卷”“《博古图》二十卷”和“《钟鼎款识》二十卷”,而《直斋》卷八史部目录类则著录“《考古图》十卷”“《博古图说》十一卷”“《宣和博古图》三十卷”,《经籍考》在辑录以上诸书的晁、陈两家解题后下按语云:
按:《考古图》诸书晁氏以入小学门,陈氏以入书目门,皆失其伦类。既所考者古之礼器,则礼文之事也,故釐入仪注门。[2]375
将以上诸书均调整归在经部仪注类下。《郡斋》将以上诸书归入小学类当是着眼于上述诸书考证文字的功用,《直斋》归入目录类当是着眼于其图谱的形式,而马端临则从其所体现的实质内容出发,认为其所著录之图谱皆古礼器,其记载皆与“礼文”相关,故将其归入仪注类。三家立足点不同,可谓见仁见智。《四库总目》从《直斋》的做法,在卷一一五将《宣和博古图》归入子部谱录类器用之属。
(十二)谥法
如表4所示,《经籍考》此类书目下解题引《崇文》经部礼类3条、《郡斋》经部礼类3条与《直斋》经部经解类3条,共计9条。马端临在《经籍考》中设立此类当是来源于《通志·艺文略》的“经类”→“经解”→“谥法”,只是将其三级类目“谥法”提升为与“经解”并列的二级类目。考《经籍考》卷十四经部谥法类小计后之按语云:
按:谥者,国家送终之大典,今历代史志,俱以谥法入经解门,则伦类失当。今除《周公谥法》、《春秋谥法》二项入礼门,而历代之谥法,则俱附于仪注之后,庶以类相从云。[2]346
《经籍考》卷八经部礼类著录有“《周公谥法》一卷”与“《春秋谥法》一卷”,前者相传源自周公,后者内容与前者相似,均被认为是先秦之谥法,属于先秦礼制的重要内容,故附入“三礼”之中,而将后世之谥法书单列于谥法类中。表4所引用《崇文》《郡斋》《直斋》皆出自书目下的解题。如《崇文》卷一经部礼类著录有“《谥别》十卷”“《谥法》四卷”与“《续古今谥法》十四卷”三书。《郡斋》卷二经部礼类著录有“《沈贺谥法》四卷”“《嘉祐谥法》三卷”和“《集谥总录》一卷”三书。《直斋》则将谥法类书籍归入经解类中,在其卷三经部经解类下著录有“《六家谥法》二十卷”“《政和修定谥法》六卷”与“《郑氏谥法》三卷”三书。《经籍考》皆将其归入独立的谥法类中。这种单立谥法类的做法与对前述仪注类书籍的处理类似,集中反映了作为朱子学者的马端临对礼制的重视和正统思想,但此分类后世很少采用。如《四库总目》便将“谥法”类书籍归于史部政书类典礼之属下。
(十三)谶纬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谶纬类小序与小计引《隋志》谶纬类2条与《新唐志》谶纬类1条,小序中又引《直斋》卷三十二经部谶纬类所著录的“《乾坤凿度》二卷”下陈振孙之按语1条,以叙述谶纬的兴衰,其书目下解题则分别辑录《郡斋》经部易类3条与《直斋》谶纬类4条,共计10条。考《郡斋》无谶纬类,因其所著录之纬书皆“易纬”,故将其附在易类之下,即《郡斋》卷一经部易著录之“《易乾凿度》二卷”“《坤凿度》二卷”与“《周易纬稽览图》二卷,《周易纬是类谋》一卷,《周易纬辨终备》一卷,《周易纬乾元叙制记》一卷,《周易纬坤灵图》一卷,《易通卦验》二卷”,《经籍考》由于设有单独的谶纬类,故将上述诸书调整到谶纬类中。
(十四)小学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小学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孝经类4条与小学类2条,又引《隋志》经部小学类2条与《新唐志》经部小学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而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小学类7条、《郡斋》经部小学类35条与子部类书类4条,又引《直斋》经部小学类38条、史部目录类1条以及子部儒家类4条、杂家类1条、杂艺类13条与类书类8条,共计120条。可知《经籍考》与《郡斋》的关系比较简单,只引用《郡斋》经部小学类和子部类书类之条目。《经籍考》经部小学类著录之条目虽以来自《直斋》经部小学类为最多,但除此之外,《经籍考》的小学类还引用了《直斋》史部目录类与子部类书、儒家、杂家、杂艺诸类之条目,反映了《经籍考》小学类与《直斋》类目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也使得《经籍考》的小学类所收书籍内容十分庞杂,除了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类书籍外,还包括工具、幼教、蒙学、书法诸类书籍。
工具类书籍如《直斋》卷八史部目录类著录有“《隶释》一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经籍考》将其调整到经部小学类。《直斋》把它视作分类编排的检字工具书,《经籍考》则着眼于其记载之对象本是文字而不论其实际功用(与下文所述书法类著作归入小学类出于同一理由)。但因其所载并非先秦古文字,而是隶变之后的今文。究其实质,工具书性质还是重于其文字考证之作用。故《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同《直斋》将其归入史部目录类。
幼教类书籍如《直斋》卷九子部儒家类著录有“《童蒙训》一卷”“《少仪外传》二卷”“《辨志录》一卷”与“《小学书》四卷”这四部“幼教”读物,是教授童蒙及初学者为人处事的具体行为规范的书籍(属于“事”的层面),属于儒家教育中的初等教育。在前代书目中一般都归入儒家类中,直到朱熹才特意将其从儒家中提出归入“小学”中,意在与讲述为人处事之道理的“大学”相表里(属于“理”的层面),以之作为修身立命之根基,并从而规定了修身治学的前后次序(先事而后理,先小学而后大学,下学而上达)。正如《经籍考》在“《小学书》四卷”之下引《朱子语录》所云:
修身之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这个是做人底样子。学之小大虽不同,而其道则一。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游倪曰:自幼既失小学之序,愿授《大学》。先生曰:授《大学》甚好,也须把小学书看,只消旬日工夫。[2]436
马端临依据朱熹的意见将幼教类书籍归入小学类中绝非偶然,是由其朱子学的思想立场所决定的。事实上,由《宋元学案》卷八十九《介轩学案》的记载可知,马端临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曹泾之门人[6]2972,属于新安朱学的传人[6]2977,并与乐平程登庸等学者相友善,都信奉朱子学[6]2980。这一事实反映在《经籍考》中便是马端临大量吸收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意见和看法。此例可见其一斑。
又《直斋》卷十子部杂家类著录有“《弟子职》等五书一卷”。《经籍考》辑录其解题云:
陈氏曰:漳州教授张时举,以《管子·弟子职篇》、班氏《女诫》、吕氏《乡约》《乡礼》、司马氏《居家杂仪》合为一卷。[2]437
《直斋》以其合五书为一卷、内容丛杂而归入杂家。《经籍考》则以其具体内容属童蒙修身之“幼教”书而调整归入小学类。两者侧重点不同,当以《经籍考》的做法为优。
蒙学类书籍如《郡斋》卷十四子部书类著录有“《蒙求》三卷”“《左氏蒙求》三卷”“《左氏纲领》四卷”与“《两汉蒙求》五卷,《唐史属辞》五卷,《南北史蒙求》十卷”,《经籍考》将这几部蒙学著作调整归入小学类中。同样,《直斋》卷十四子部书类著录有“《蒙求》三卷”“《补注蒙求》八卷”等八部蒙学故事集,与《郡斋》子部书类著录的4部情况一样。马端临因其本质为儒学初级读本而调整归入小学类中。《四库全书总目》则从《郡斋》和《直斋》归入子部书类中,当是着眼于其以一定的编纂体例汇聚故事而成书的特征。
书法类书籍如《直斋》卷十四子部杂艺类著录有刘次庄的“《武冈法帖释文》二十卷”、张彦远的“《法帖要录》十卷”、释适之的“《金壶记》一卷”、钱惟演的“《飞白叙录》一卷”、黄伯思的“《法帖刊误》二卷”、翟耆年的“《籀史》二卷”、姜夔的“《绛帖评》一卷”(《经籍考》著录为二十卷)、桑世昌的“《兰亭博议》十五卷”、桑世昌的“《兰亭考》十二卷”(《经籍考》著录为十三卷)、蔡端的“《法书撮要》十卷”与陈思的“《书苑菁华》二十卷”等13部著作。《经籍考》卷十七将以上诸书皆调整归入经部小学类中。并在陈思的“《书苑菁华》二十卷”后以按语说明其理由云:
按:以字书入小学门,自《汉志》已然。历代史志从之,至陈直斋所著《书录解题》,则以为《书品》、《书断》之类,所论书法之工拙,正与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于杂艺,不以入经录。夫书虽至于钟、王,乃游艺之末者,非所以为学,削之诚是也。[2]433
马端临首先承认《直斋》所谓论“书法”的著作为“技艺”与作为学问根基的传统小学不可混为一谈。但他在按语中接着又指出:
然《六经》皆本于字,字则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属乎偏旁音韵者则入于小学,属乎真行草篆者则入于杂艺,一书而析为二门,于义亦无所当矣。故今并以入小学门,仍前史旧云。[2]433
可见,马氏虽然从道理上赞成陈振孙的观点,但在书籍的具体归类处理上持不同的意见。他不赞成陈氏将“书法”类著作从小学分出的做法。因为在马氏的眼里,“书法”也好,“字书韵书”也好,同样都以文字为对象,虽然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没有必要分立两门。所以他没有依从《直斋》,仍然将“书法”著作保留在小学类中。
综上所述,《经籍考》将“工具”“幼教”“蒙学”“书法”类著作,分别从《郡斋》与《直斋》的目录类、儒家类、类书类、杂艺类中调整归入其“小学”类中。这些调整大多并非马氏首创,一般都有其历史渊源。《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经部小学类小序中指出:
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如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实字书,袁子让《字学元元》实论等韵之类)。悉条其得失,具于本篇。[3]526
由此可知,将“书法”著作从艺术类中分出归入小学类始于《新唐志》,将“幼教”著作从儒家类中分出归入小学类则由朱熹所倡导,并首先由赵希弁在其《读书附志》中予以实践(但马端临并未见到《读书附志》),将“蒙学”著作从类书类中分出归入小学类则始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经籍考》的小学类对此都予以吸收,可谓汇集前代书目小学类于一炉。这一方面是由其辑录体的特殊体制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端临本人的学术思想立场。不仅如此,马端临还自行将检字类“工具书”从前代书目的目录类中分出归入其小学类中,从而使其“小学”类所包括的范围更加庞杂。
作为清代考据学结晶的《四库全书总目》主张小学类中只载文字、音韵、训诂类书籍,而将“论幼仪”“论笔法”“蒙求”及“便记诵”之书各归其类,从而恢复了《汉志》的“小学”传统,使得“小学”类变得纯粹了。当然《经籍考》小学类的收书范围是建立在广泛汇集前代书目并吸收程朱理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而清代出于对宋明理学以义理解经的空疏弊病的批判和反思,提倡返回先秦儒学本义并对经典以予以忠实的解释,作为朴学家解经之基础的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小学”的研究兴盛,而官方出于钳制思想以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对于钻故纸堆与现实关系不大的小学也是大力提倡。正因为上述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与政治形势的影响,清代小学由经学附庸一跃而蔚为大观,所以反映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自然会主张恢复《汉志》的“小学”传统。两者的差别一方面是由《经籍考》与《四库全书总目》辑录体与叙录体的不同体制而决定的,更是直接反映了学术随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异,《经籍考》与《四库全书总目》都不过是各自予以忠实的记录罢了。
三、结语
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古籍分类中的分类类目及其归类中存在诸多问题。关于其原因,从客观分类体系上来说,古籍目录中的不少类目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清晰,所涉及的领域相近而容易混淆,并且随着时代学术的发展,类目的内涵和外延往往会发生变化。从主观立场上来说,编目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很可能将同一部书归入内容相关的不同类目中。这其中当然也不能排除编目者的疏忽大意,但总的来看,古籍书目中分类与归类的分歧大多有其历史背景和学术思想的深层原因。以上影响分类及其调整的主客观因素都在《经籍考》经部的分类中有所体现。马端临在辑录前代书目的过程中对其分类类目与具体书籍的归类进行了整合,这些调整往往都有其深层的学术背景,集中反映了学术思想的时代变迁。进而通过历代书目与学术史的分析,特别是与古籍四部书目的集大成者《四库全书总目》相对照可知,《经籍考》中的分类调整往往是继往开来的一环。其承前启后的经验与内涵均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