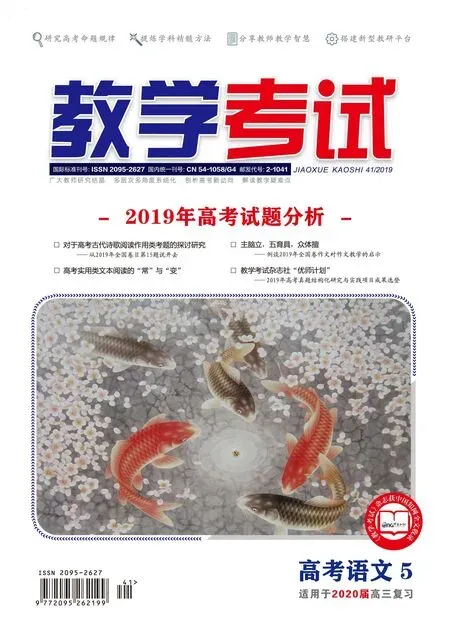雪
梁实秋
李白句:“燕山雪华大如席。”这话靠不住,诗人夸张,犹“白发三千丈”之类。据科学的报导,雪花的结成视当时当地的气温状况而异,最大者直径三至四时。大如席,岂不一片雪花就可以把整个人盖住?雪,是越下得大越好,只要是不成灾。雨雪霏霏,像空中撒盐,像柳絮飞舞,缓缓然下,真是有趣,没有人不喜欢。有人喜雨,有人苦雨,不曾听说谁厌恶雪。就是在冰天雪地的地方,爱斯基摩人也还利用雪块砌成圆顶小屋,住进去暖和得很。
一片雪花含有无数的结晶,一粒结晶又有好多好多的面,每个面都反射着光,所以雪才显着那样的洁白。我年轻时候听说从前有烹雪论茗的故事,一时好奇,便到院里就新降的积雪掬起表面的一层,放在瓶里融成水,煮沸,走七步,用小宜兴壶,沏大红袍,倒在小茶盅里,细细品啜之,举起喝干了的杯子就鼻端猛嗅三两下——我一点也不觉得两腋生风,反而觉得舌本闲强。我再检视那剩余的雪水,好像有用矾打的必要!空气污染,雪亦不能保持其清白。有一年,我在汴洛道上行役,途中车坏,时值大雪,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饥肠辘辘,乃就路边草棚买食,主人飨我以挂面,我大喜过望。但是煮面无水,主人取洗脸盆,舀路旁积雪,以混沌沌的雪水下面。虽说饥者易为食,这样的清汤挂面也不是顶容易下咽的。从此我对于雪,觉得只可远观,不可亵玩。苏武饥吞毡渴饮雪,那另当别论。
雪的可爱处在于它的广被大地,覆盖一切,没有差别。冬夜拥被而眠,觉寒气袭人,蜷缩不敢动,凌晨张开眼皮,窗棂窗帘隙处有强光闪映大异往日,起来推窗一看——啊!白茫茫一片银世界。竹枝松叶顶着一堆堆的白雪,杈芽老树也都镶了银边。朱门与蓬户同样蒙受它的沾被,雕栏玉砌与瓮牖桑枢没有差别待遇。地面上的坑穴洼溜,冰面上的枯枝断梗,路面上的残刍败屑,全都罩在天公抛下的一件鹤氅之下。雪就是这样的大公无私,装点了美好的事物,也遮掩了一切的芜秽,虽然不能遮掩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