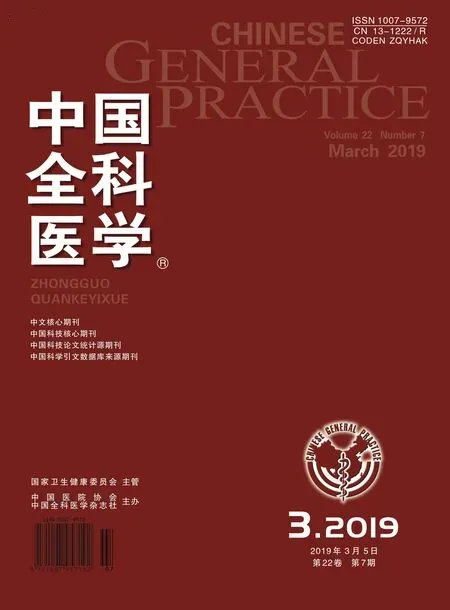全科医生法律保障的域外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李菁芸,刘兰秋
近年来,随着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行,基层首诊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基层首诊主体的全科医生群体成为分级诊疗制度能否顺利推行的关键。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和转诊、患者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全科医生20.91万人,其中取得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的13.15万人,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的7.76万人,平均每万人口拥有1.51名全科医生[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全科医生增长数量大,增长速度迅猛。但同时也发现,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的医生仅占总数的37.1%。因未形成对于全科医生完备的法律规范,其服务质量未能取得民众充分信任[2]。数据表明,2016年全国三级医院诊疗人次为162 784.8万人次,二级医院诊疗人次为121 666.5万人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诊疗人次为21 790.9万人次。多数居民在患病时首选到二、三级医院就诊[3]。为此,应完善全科医生立法,确定全科医生的定义、执业准入条件、执业范围、权利及义务,使全科医生这一概念在我国得到法律确认,在提高全科医生医疗服务能力的同时也提高其社会认可度。我国已经意识到全科医学立法的必要性,于2016年底初步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4],并在2017年12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进行了审议。以健全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规制医疗卫生系统,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域外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针对全科医生的立法,是医疗卫生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全科医生培养、注册、执业等过程的必要手段,是推进分级诊疗中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等环节安全有效进行的基本保障。同时,有关分级诊疗、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等医疗卫生立法,也对全科医生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本文旨在对域外全科医生立法经验进行分析与总结,以期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推进我国全科医生和分级诊疗的制度化、法治化提供借鉴。
1 全科医生法律保障的域外经验
1.1 英国 在英国,医疗服务分为初级、二级及三级。初级医疗服务最为普遍,针对一些较轻的疾病提供普通的门诊服务,提供者为全科医生;二级医疗服务的供方是医院,主要收治急诊、重症患者及需要专科医生治疗的患者;三级医疗服务则是为一些重症患者提供更加专业化的诊疗、护理服务。英国“将全科医生作为提供医疗服务主体”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11年颁布的《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该法律规定:“在英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中,所有16岁以上的受雇佣公民或是不受雇的但在本法中规定的公民均可以按照本法案规定的方式投保,所有投保人均有权享受本法案规定提供的健康保险和预防保健服务”。1946年《国家卫生服务法》(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正式确立了英国的国民卫生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该制度规定全科医生可以自行开业,为所有注册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私人诊疗服务,患者到专科医院就诊需要通过全科医生的转诊。法律规定公民或持6个月以上签证的外国公民必须注册全科医生,并与其签约,非紧急情况下,社区居民必须首先到全科医生处登记,由全科医生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全科医生决定患者是否可以接受二、三级医疗服务,确保全科医生首诊、转诊权利。1976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立法确立了全科医生的培训模式并建立了新的管理机构,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全科医生的培养制度[5]。
由此可见,在英国全科医生制度建立的关键环节和发展过程中,均是通过立法手段构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首先,英国的卫生法律对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分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包括分为哪几层、各层承担怎样的医疗服务内容、各层医务工作者的医疗权利与义务;其次,英国法律规定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以确保每位公民的健康权利受到保护,同时规定患者依据病情去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义务,以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再次,英国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是民众可见的、强制的、严格的、不逊色于专科医生培养制度的,这是英国初级医疗服务发展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1.2 加拿大 1984年,加拿大通过了《加拿大卫生法》(Canada Health Act)。这是加拿大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基石”,为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享受全民免费医疗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加拿大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了统一标准。加拿大医疗服务体系包括三级,其中第一级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提供初级医疗卫生服务的医生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守门人”,也是居民直接联系对象,是患者进入医院或专科门诊的控制点,主要由全科医生及其诊所组成,绝大部分是个体经营,具备很高的自由度,薪资与其名下注册居民的数量和工作量直接挂钩,居民可自由选择自己的全科医生,本类其他从业者还包括牙医、护士、药剂师[6]。由此可见,加拿大同样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并强调全科医生在此体系中的职业定位与职责,明确全科医生的首诊与转诊权利,特别规定了全科医生的薪资评估方式,建立了有效的绩效激励机制。
1.3 匈牙利 《匈牙利健康法》第2条第5款规定:“基于医疗等级架构和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满足不同疾病种类、不同疾病严重程度个体的健康需要为目的,对医疗服务体系进行设计”。该医疗服务体系根据每个人的健康程度提供不同等级的医疗服务,被称为渐进医疗。匈牙利的医疗服务系统分为基本医疗、门诊专科医疗、住院专科医疗三大部分。基本医疗是指患者在其居住地附近基于个人关系自由选择的长期且持续的医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医生向居民提供预防性服务,监控其健康状况,做出基础的诊断、治疗、护理及康复服务。而接受门诊专科医疗需要上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医生,即全科医生的转介;只有通过全科医生转介,患者才可以转到具有解决复杂医疗任务能力的高级住院专科接受治疗。另外,《匈牙利健康法》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其确定了全科医生进行上门服务的合法性,规定了在进行上门服务时医生的权利和义务。《匈牙利健康法》第87条规定:“医疗服务系统应以门诊的方式在住院处或患者家中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该法第88条具体规定了全科医生的服务内容并为全科医生上门服务提供了法律依据,第88条第2款规定:“如有需要,在患者家中诊断、治疗、护理及康复服务,并在患者家中进行专家会诊”[7]。综上所述,《匈牙利健康法》提出了渐进医疗这一概念,同时提出了全科医生在这一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特别对全科医生执业场所进行了规定,使全科医生进行上门服务有法可依,降低了执业风险。
1.4 瑞典 瑞典的卫生服务体系分为3个层次,即初级卫生机构医疗、州医院医疗、区域性医院医疗。初级卫生机构所提供的初级卫生保健是瑞典政府保障人民健康和医疗的基础,设法满足大多数人对医疗照顾、疾病预防和康复的需求。《瑞典医疗服务法》(The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Act)第5条规定:“区域性医院旨在为需要入住医疗机构的患者提供服务。患者入住医疗机构期间所提供的服务,称住院服务(in-patient care)。其他医疗服务,称门诊服务(out-patient)或非卧床服务(ambulatory care)。初级医疗服务系门诊服务之构成部分,不考虑疾病、年龄或患者类型,旨在满足整个人群基本的治疗、护理、预防及康复服务需求,此种基本需求不依赖医院或其他专门机构的医疗及技术资源”。此外,《瑞典医疗服务法》规定“郡对初级医疗服务供给的安排,应使生活于其辖区内的人,可以利用并可以选择稳定的医疗联络(permanent medical contact)。此等医生应具备全科医学的专家资质(specialist competence in general medicine)”[8-9]。
《瑞典医疗服务法》规定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是适用于全人群的入门级服务,确定了初级卫生保健在整个医疗卫生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保障了全科医生在医疗卫生系统中的首诊权利,并保证基本的医疗需求不会占用到高级别医院与专科机构的医疗资源。同时以法律形式规定郡负责提供初级卫生保健,并规定相应医生必须具备“全科医学的专家资质”,确定了全科医生的执业资质,确保患者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可以得到有效且及时的满足。通过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分层级诊疗、基层首诊、全科医生执业资质的立法规定,使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得到满足。同时立法规定了患者与医生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1.5 葡萄牙 《葡萄牙卫生基本法》第12节第1条规定:“卫生系统由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一切在卫生健康领域进行推广、预防、治疗工作的公共机构以及与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达成协议,可提供所有或部分上述工作的私立机构和自由专业人员构成”。该节第4条规定:“国家医疗卫生服务网包括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机构以及根据该法的规定签订了协议的私立机构和自由执业的专业人士”。第13节规定:“医疗卫生系统建立在初级医疗保健的基础之上,初级医疗保健应设立在社区中”。第32节第3条规定:“法律对于医疗职称的规范一视同仁,无论是否已根据专业分化建立了职称”。第40节第1条规定:“在独立执业体制下提供服务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这是为法律所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的”。第40节第3条规定:“独立执业体制下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应投保,以规避行使其职责时产生的风险”[7]。可见,葡萄牙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卫生系统的组成,与其他国家相同,明确了初级卫生保健的基础性作用,其特点在于同时确定了专业人士自由执业的合法性。《葡萄牙卫生基本法》还规定以社区为单位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并且立法保护全科医生权利,为全科医生在执业过程中规避风险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2 国外全科医生相关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国家均以卫生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分层次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并且规定了全科医生在体系中的作用与定位,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全科医生制度的成功实施,促进了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平稳发展。我国应将域外经验与实际国情相结合,建立适合我国实际的全科医生法律,完善我国医疗卫生体系。
2.1 应规定我国实行分级诊疗制度,明确全科医生在分级诊疗制度中的定位与职责 首先,应立法确立一个分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其次,强调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性,即基层首诊的重要性;最后,明确全科医生在基层首诊中的职责作用以及其在整个卫生系统中的“守门人”定位,重点突出首诊与转诊职责。目前正处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过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中已对此做出相应规定,其中第50条规定:“国家对基本医疗服务实行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实行首诊负责制和转诊审核责任制,鼓励非急诊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逐步建立起基层首诊、科学转诊的机制,并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
2.2 立法应规定全科医生定义 定义应包含全科医生的执业资格、注册准入条件及执业范围。首先,规定必须经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后才可以注册为全科医生,这在严格要求全科医生资质的同时也给居民一个心理保障,让居民知晓全科医生也经历过医学领域权威认定的合格医疗人才,使其信任全科医生的执业水平和质量。其次,现行全科医生准入条件虽然导致全科医生的注册率较低,但准入标准不应降低。部分全科医学生认为自身接受了与专科医学生同等的教育,却未在就业中享有与专科医学生同等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这是全科医生注册率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10]。针对这一现象,不能改变对全科医生的准入要求,而是应该着重提高全科医生在工作中对个人职业的满意度,包括提高薪资待遇、社会地位,增加科研、进修、职称晋级机会等。减少在基层工作的全科医生与在高级别医院工作的专科医生之间的薪资差距,扭转其“三级医院可以提供更大更好平台”这一观念。最后,定义应包含全科医生明确的执业范围,《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23号)中将全科医生的执业范围定义为:“主要在基层承担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预防保健、患者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可以将这一范围进一步法律化。可以通过调查数据进一步具体到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病种、预防保健内容、患者康复项目、健康管理内涵。在规定全科医生的执业范围时应特别注意减轻其工作负担,使全科人才更专注于自身医学知识与临床技能的提高,有更多精力从事健康教育与管理。
2.3 立法应规定全科医生权利 应在保证全科医生享有与专科医生相同权利的同时,增加全科医生的其他权利。(1)针对患者愿意选择二、三级医疗机构就诊致使全科医生失去诊疗权利这一现象,可以借鉴上述国家的做法,依法确立基层首诊,患者患病时必须先到全科医生处就诊,由全科医生依据病情决定是否转诊。(2)建议放宽全科医生的药物使用目录,保障其药物处方权。(3)建议立法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施设备齐全,使全科医生获得与本人执业活动相当的医疗设备基本条件,保障其检查权。(4)针对全科医生在从事医学研究、继续教育、职称晋升等方面相较于专科医生机会较少的问题,应立法保障其发展权的享有与实现。(5)针对全科医生上门服务风险较大的现况,可借鉴匈牙利的做法,明确全科医生提供上门服务的合法性,并给予其在上门服务期间的法律保障。
2.4 立法应明确规定全科医生的义务 在赋予全科医生权利的同时,应以法律形式规定全科医生在执业过程中应当履行的义务。在《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号)规定的医生应遵守的法律法规、遵守技术操作规范、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的基础上,还应针对医生和患者进行广泛调查,以确定全科医生应当承担的义务方向与具体内容,以数据为基础的有关立法才是真正完善全科医生制度的有效手段。
作者贡献:李菁芸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资料收集与整理,撰写论文;李菁芸、刘兰秋进行文章的可行性分析、论文修订;刘兰秋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
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