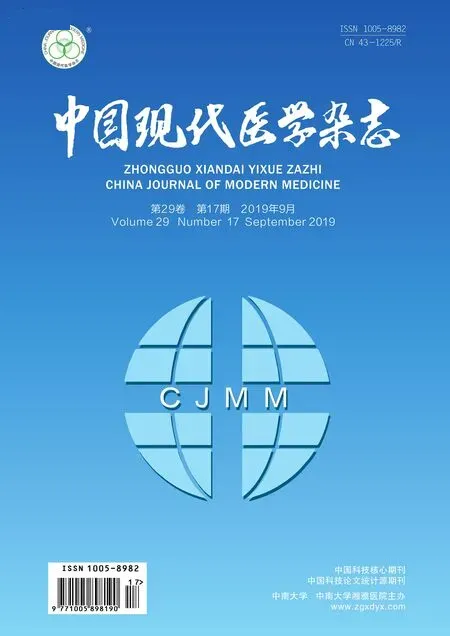丹参多酚酸对老年脑卒中患者血清半乳糖凝集素-3、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的影响*
王欢,魏书艳,杨凡,齐丹丹,李轩,王佩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河北 保定 071000)
缺血性脑卒中(ischemic stroke,IS)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脑卒中类型。中老年人为主要发病人群。根据类肝素药物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试验(TOAST)分型,大动脉粥样硬化(large artery atherosclerosis,LAA)型脑卒中是其重要分型之一。动脉粥样硬化作为其主要的发病机制,是以动脉管壁脂质斑块持续累积为主要特征的慢性进展性炎症疾病[1]。多种炎症细胞、炎症因子参与了炎症反应过程。炎症反应可加重动脉粥样硬化,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GLA-3)、超敏C 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3 C-reactive protein,hs-CRP)作为重要的炎症指标,与动脉粥样硬化性脑卒中密切相关。注射用丹参多酚酸是一种根据中医理论制成的中药制剂,有活血通络的功效。本文采用注射用丹参多酚酸治疗大动脉粥样硬化型脑卒中,并观察患者血清GLA-3、hs-CRP 的水平及近期疗效,为脑卒中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好的方案。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7年1~12月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就诊的发病时间在7 d 内的IS 患者,根据TOAST 分型,选取LAA 型202 例,对分型有疑问的患者予以剔除,以确保分型的准确性。年龄(72.27±11.13)岁。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经过临床查体、病史及MRI+ MRA、心脏彩超、颈部血管彩超、TCD 确诊为LAA型脑卒中患者;②无明显的脑梗死后遗症。排除标准:①所有患者排除注射用丹参多酚酸过敏史;②所有患者排除心源性脑栓塞、其他明确原因型及不明原因型卒中患者,严重的心脏病及近期发生的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严重感染、恶性肿瘤、血栓性疾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101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情等方面有可比性(P>0.05)。
健康组为本院同期健康体检者200 例,其性别、年龄与LAA 型脑卒中组相匹配。纳入标准:既往无脑卒中病史,颅脑CT 或MRI 证实无脑卒中病灶或明显脑缺血,经颈部血管彩超、TCD、心脏彩超、颅脑MRA 等检查证实无脑血管病变及心脏病变。排除标准同LAA 型脑卒中组。本研究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血栓通注射液静脉输液,1 次300mg,以0.9%氯化钠注射液250ml 稀释后使用,1 次/d;实验组给予注射用丹参多酚酸静脉输液,1 次0.13 g,以0.9%氯化钠注射液250ml 稀释后使用,1 次/d;治疗共14d。其余治疗方法基本相同,主要包括抗血小板聚集,神经营养,调控血压、血脂、血糖,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及康复治疗等。
1.2.2 标本采集与检测方法 健康组于体检日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4ml。LAA 型脑卒中患者入院第1 天(治疗前)、第14 天抽取静脉血4ml,30min 内分离血清,置入-80℃冰箱低温保存待测。采用ELISA 法检测,试剂盒购自美国R&D System 公司。操作严格按说明书步骤进行。此外,实验组与对照组入院第1 天、第14 天均抽血检测,血常规、尿规及肝、肾功能、血脂、心肌酶学、hs-CRP 等。
1.2.3 临床神经评分采用改良RANKIN 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由经过正规培训的神经专科医师负责评分并录入。治疗前(入院第1 天)、治疗90d 后分别评分1 次。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SPSS 19.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hs-CRP、GLA-3 水平
LAA 型脑卒中治患者疗前血清hs-CRP(6.28± 1.91)mg/L,血清GLA-3(13.55±3.13)ng/ml;健康组血清hs-CRP(2.75±1.39)mg/L,血清GLA-3(10.13± 2.31)ng/ml。LAA 型脑卒中患者组血清hs-CRP、GLA-3 水平均较健康组升高(t=21.169 和12.455,P= 0.000)。
2.2 对照组与实验组治疗前后血清hs-CRP 水平
对照组治疗前血清hs-CRP(6.13±1.49)mg/L,治疗后(5.01±1.33)mg/L;实验组治疗前血清hs-CRP(6.49±1.41)mg/L,治疗后(3.87±1.15)mg/L。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hs-CRP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63,P=0.222);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hs-CRP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20,P= 0.000),实验组低于对照组。
2.3 对照组与实验组治疗前后血清GLA-3 水平
血清GLA-3 水平,对照组治疗前(13.49± 3.02)ng/ml,治疗后(10.31±3.24)ng/ml;实验组治疗前(13.58±3.13)ng/ml,治疗后(8.87±2.95)ng/ml。治疗14d 后,两组患者血清GLA-3 水平均较治疗前均降低(t=1.763 和-6.520,P=0.222 和0.000),治疗14d 时,两组GLA-3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3.301,P=0.000),实验组低于对照组。
2.4 对照组与实验组mRS 评分比较
mRS 评分,对照组治疗前(3.78±0.73),治疗90d 后(1.32±0.61);实验组治疗前(3.98±1.71),治疗90d 后(0.85±0.42)。治疗90d 后mRS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t=1.972 和-4.641,P=0.165 和0.000),治疗90d 时,两组mRS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641,P=0.000),实验组低于对照组。
3 讨论
GLA-3 作为强大的炎症因子,可以通过促进活化炎症细胞、释放炎症因子以及抑制炎症细胞凋亡等过程,增强机体炎症反应[2]。最新研究发现,GLA-3 参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发展,并与斑块的不稳定性密切相关[3-4]。MACKINNON等[5]通过动物实验发现,GLA-3、载脂蛋白E(ApoE)基因双敲除的小鼠与单纯ApoE 敲除的小鼠均经高胆固醇喂养后,前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面积及体积均小于后者,且应用GLA-3 抑制剂可减小斑块面积。血浆GLA-3 水平对LAA 型脑卒中患者预后有预测性价值[6]。MADRIGAL-MATUTE等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外周血中GLA-3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是升高的[7]。国内也有临床研究显示,GLA-3 可能参与LAA 型脑卒中脑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发病机制及发展过程[6]。炎症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8]。GLA-3 作为炎症因子,在细胞增殖、巨噬细胞趋化、中性粒细胞渗出、氧化应激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相关[7]。
HERMIDA 等[9]发现,CRP 是非特异性炎症标志物,并具有代表性意义。hs-CRP 是利用对血清CRP含量高度敏感的检验技术而测得,能更精确地反映机体炎症因子的水平并揭示炎症反应的严重程度。hs-CRP 的升高提示机体内存在炎症反应,可造成血管壁硬化,动脉斑块形成。hs-CRP 可以诱导组织因子表达激活凝血因子,使组织纤溶失衡,激活补体系统,从而促进血栓形成。血清hs-CRP 浓度的升高与动脉硬化斑块的不稳定性息息相关,并与脑梗死的严重程度、颅内动脉的狭窄程度有关,在心脑血管预测方面意义重大[10]。血清hs-CRP 反映急性期脑梗死的严重程度,与脑梗死的体积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呈正相关,对评价其预后有一定的价值。脑梗死患者血清hs-CRP 浓度与NIHSS 评分呈正相关,hs-CRP 与急性脑卒中患者的临床转归和预后关系紧密[11]。hs-CRP 升高对脑血管的危害有以下几点:①hs-CRP 参与动脉内膜的局部炎症反应,引起内膜的增厚、斑块破裂,导致脑血管疾病的发生;②hs-CRP 可激活补体系统,参与炎症反应、组织损伤,促进血栓的形成;③hs-CRP 水平的升高可以影响凝血纤溶机制,引起缺血性脑血管病发生[11-12]。有效的降低hs-CRP,对脑梗死的治疗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显示,LAA 型脑卒中患者血浆中GLA-3、hs-CRP 水平较健康组均升高,提示GLA-3、hs-CRP与动脉粥样硬化、LAA 型脑梗死相关。
改善循环药物对IS 的治疗有重要作用,而注射用丹参多酚酸作为改善循环的中成药的一种,在治疗IS 得到广泛的应用。而其在治疗老年LAA 型脑卒中的疗效与机制报道较少。本研究中,实验组中患者血清GLA-3、hs-CRP 水平降低趋势较对照组有差异,提示注射用丹参多酚酸对GLA-3、hs-CRP 的表达水平有一定的抑制作用。LAA 型脑卒中患者在规范抗血小板聚集等综合治疗的基础上,神经功能可得到部分改善,而丹参多酚酸治疗组可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改善,且GLA-3、hs-CRP 的表达水平与此有关,从而推断出丹参多酚酸的治疗作用与降低GLA-3、hs-CRP 的表达水平有关,进而达到保护血管、改善神经损伤的作用。本研究显示,注射用丹参多酚酸较血栓通注射液,能更有效地降低患者的mRS 评分;治疗IS 方面,注射用丹参多酚酸较血栓通注射液治疗效果更好;可更好地改善神经功能缺损,促进神经系统功能的恢复,降低LAA 型脑卒中患者致残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减轻社会负担。但本研究对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的治疗机制的研究不够深入,仍需更深层次的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