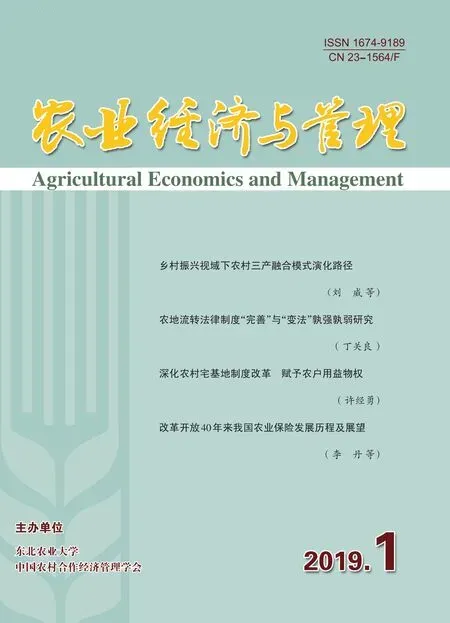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问题研究*
唐 浩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长沙 410128)
集体成员权是农民获得耕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的前提。只有集体成员权界定清楚,耕地承包权才会真正稳定,宅基地使用权方可真正落实,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才会无争议。但目前集体成员权并不清晰,需要进一步界定。自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起(分田到户),由于出生、婚嫁、就业、迁徙、死亡等原因,近四十年集体成员变化巨大。集体成员、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不明确,个人、集体和政府竞相博弈,滋生诸多矛盾纠纷,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由于土地增值收益不断上升,矛盾日益集中和突出。以“土地”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关键词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2018年6月5日),共102 251个判决案例。
一、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之争
学术界关于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争议较大。可分为两类,一是单一标准或以单一标准为主,二是复合标准或综合性标准。第一类:一是以户籍或以户籍为主的标准,王利明等(2012)认为考虑户籍主要是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可操作性强。但部分学者认为户籍不足以认定集体成员权,如空挂户、外嫁女等问题,因此应淡化户口作用(杨攀,2011;吴兴国,2006);二是以土地承包合同为标准,杨一介(2008)指出以土地承包合同为标准界定集体成员权,将集体成员权建立在法律行为基础上,当集体成员权利受侵害时,其请求权具有法律基础。但在“生不增地、死不减地”原则下,多数新增集体成员无土地,以此为标准易产生矛盾;三是以土地作为基本生存保障为标准(杨攀,2011;韩松,2005),但基本生存保障较难衡量。四是以履行村民义务为标准(王利明等,2012;魏文斌等,2006),但具体至村庄,村民义务较繁杂,界定难度大、争议多。第二类:一是以户籍与自治为标准,两者冲突时,遵循“约定大于法定”原则(徐志强,2014);二是以户籍与长期居住为标准,以户籍登记为原则,以在村庄长期居住事实状态确定集体成员权(吴兴国,2006);三是以综合标准为标准,如魏文斌等(2006)提出以村庄内部农业生产为基本生存保障,履行相应村民义务,具有村庄户籍,在村庄具有合法和固定住所四条标准确定集体成员权。
二、事实:国家和村庄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
(一)国家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
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标准主要包括法律、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司法规范性文件①为论述方便,将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及司法规范性文件关于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统称为国家标准。在农民心目中,上述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即国家标准。。法律界定集体成员权标准较抽象,主要集中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如《婚姻法》第九条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在地方性法规中,现有20个省或自治区(陕西、河北、湖北、浙江、青海、内蒙古、四川、江西、重庆、云南、海南、福建、新疆、安徽、辽宁、吉林、江苏、山西、山东、湖南)通过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或《农村土地承包条例》等提出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其中11个省或自治区(青海、内蒙古、江西、重庆、陕西、福建、安徽、山东、江苏、河北、湖北)提出的标准较详细。此外,广东省颁布地方政府规章《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6个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陕西、贵州、重庆、天津、海南)颁布司法规范性文件提出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上述标准包括一般标准和列举式的具体标准。界定集体成员权的一般标准主要由司法规范性文件提出,一是村庄户籍,二是在村庄或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固定的生产、生活,三是以集体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但上述标准在不同省份司法规范性文件中着重点不同。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集体成员权的确认,一般应以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户籍为基本原则,同时兼顾在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生产、生活。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对农村集体成员权的认定,以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作为基本依据,兼顾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及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固定的生产、生活作为判断标准。列举式具体标准由各省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或《农村土地承包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提出,在大部分地方性法规中,户籍在本村的以下三类人员为集体成员,一是出生于本村且户口未迁出,二是因婚姻或收养关系,户口迁入本村,三是政府组织移民迁入户口。此外,地方性法规一般规定大中专院校学生、义务兵和服刑人员享有集体成员权。对于外嫁女,地方性法规一般沿袭《土地承包法》规定,即妇女于承包期内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依然享有原村庄集体成员权。但司法规范性文件对于外嫁女集体成员权问题有不同规定,安徽、重庆、天津和海南四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规范性文件均规定,“农嫁女”户口虽未迁出,但已进入男方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应认定其为嫁入地的集体成员权;“城嫁女”未取得非农户籍,则应认定其为原集体成员权。上述国家标准未提及两点,一是基本未将履行村庄义务作为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标准②仅广东省颁布政府规章《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提及履行村庄义务,第十五条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二是集体成员权界定与享受集体成员权益未分离,实践中存在某些界定为集体成员的村民仅享有部分集体成员权权益。
(二)村庄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
通过深入分析95个村庄集体关于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文本和120个界定集体成员权的司法诉讼案例③95个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文本主要是通过多种方式收集的村规民约和村民委员会章程,笔者曾利用该资料研究农地制度,具体请参见《村规民约视角下的农地制度:文本解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四期。120个司法诉讼案例主要通过北大法宝搜集。,发现村规民约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标准庞杂,难以梳理出具体标准,极端情况下,各村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均不同。如外嫁女集体成员权界定问题既涉及本人,还涉及其子女及丈夫。外嫁女认定存在法律登记、农村习俗和事实婚姻的区别。许多村庄集体认为无论外嫁女户口是否转出均无集体成员权,部分村根据户籍和履行村民义务的标准,确定外嫁女具有集体成员权④广东肇庆市端州区睦岗镇沙街村、广东湛江市赤坎区南桥街道南桥村、四川成都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村、安徽云安市裕安区罗集乡松岗村。,部分村外嫁女具有部分集体成员权,即享受村庄集体部分权益⑤海南琼海市博鳌镇乐城村。。对于外村迁入户,部分村认定其集体成员权,部分村根据其迁入村庄年限赋予其部分集体成员权益⑥湖南常德市鼎城区灌溪镇五里岗村。,还有部分村不认定,迁入户不享有集体成员权益⑦海南澄迈县金江镇京岭村。。
村庄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虽庞杂,但根据文本解读和司法诉讼案例分析,可概括和抽象出村庄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的一般特征。一是保护村庄利益原则。由于村庄资源有限,在制定集体成员权标准过程中,必须突出保护在村人群利益,以保障其生存与发展。如大多数村庄对外嫁女及其子女不再赋予本村集体成员权,对外村迁入户按迁入年限给予部分集体成员权,均为保护村庄利益的表现;二是突出履行义务原则。村庄集体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标准与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的最大区别在于突出义务原则,将是否履行村庄义务及履行义务时间和贡献作为重要标准。义务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义务等。政治义务如参与村庄选举、村庄治理会议及民主监督等;经济义务如义务工和积累工、乡统筹和村提留、一事一议、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法律义务如计划生育等⑧如浙江绍兴县新华村村规民约规定:“凡居住在本村的年满18至55周岁的男性村民和年满18至50周岁的女性村民,除在校学生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外,都要担负义务工。凡符合出工条件的村民,每个人每年都要负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用于公益事业的“两工”,由村委会统一安排,对投工情况及时登记、公布,接受村民监督”。。三是维护村庄秩序原则。村庄集体将集体成员是否享有成员收益作为村庄治理手段,以维护村庄秩序,对于资源型村庄更是如此。如许多村庄对于违反计划生育、违反治安条例、不赡养老人的村民剥夺其部分甚至全部集体成员收益⑨如河南郑州上街区聂寨村村规民约规定:“对不赡养老人的,经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的,将按照多数村民意见,直接从子女的生活保障金中扣除费用交给老人,并全村通报批评。对于土葬的一经发现,停发死者当年的保障金、生活补助费等一切费用,再罚死者家属1 000元,情节严重的加倍处罚。浙江莲都区苏埠村村规民约规定:严禁计划外生育,违者一律按“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计划外生育的小孩,不享受本村组一切待遇”。;四是考虑生计道义与人情原则;如大学生仍享受集体成员权益,服兵役和服刑人员保留集体成员权,给予贡献大的人员集体成员权主要是考虑人情原则⑩参见张明慧等《社会界面视角下农村成员权认定的实践逻辑——基于湖南S村集体林权改革的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如湖南S村集体林权改革中,给予户口已迁出且不在村中居住的村民以集体成员权,主要考虑其父亲对村庄的贡献。
三、规范:集体成员权应界定给谁
综上,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可分为国家基本标准和村庄集体具体标准。各村庄集体具体标准存在差异,因此主要分析国家基本标准○11集体成员权界定须由国家和村庄集体共同完成,国家制定集体成员权界定基本标准,村庄集体制定具体标准。如何确定国家和村庄集体界定集体成员权的边界需另文专门探讨。。谁应享有集体成员权,或集体成员权作为资源应配置给谁,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公平问题。
从效率视角看,集体成员权分配应达帕累托最优,即何种改变均同时使至少一人受益而其余人不受损,因此实现集体成员权等公共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面临三个难题。一是在缺乏市场情况下,获取行为主体个人偏好信息困难;二是公共资源分配的行为主体间利益冲突;三是公共资源分配涉及政治可行性(阿马蒂亚·森,2014)。因此,从效率角度分配集体成员权缺乏可操作性。
从公平视角看,集体成员权应分配给其应得的成员,涉及公平正义观。从功利主义者角度看,集体成员权分配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为公平。功利主义注重后果,集体成员权配置产生良好效果则为公平。但良好效果如何界定?将集体成员权配置给最愿意留在村庄的农民,还是配置给只能留在村庄的农民,或是配置给最有利于村庄发展的农民是良好的效果,涉及村庄定位及国家集体成员权界定目标。功利主义根据个人效用总和排序评价事物状态(阿马蒂亚·森,2014),实现总效用最大化就是好的资源配置。由于个人边际效用递减,将资源从拥有资源多的个人转移至资源少的个人,社会总效用增加。因此,将集体成员权配置给拥有资源少的个人增加社会总效用。第一,平等自由主义,即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罗尔斯从“原初立场”和“无知之幕”推理出正义两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二是差别原则。在面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时,罗尔斯认为应使社会状况最差的人福利最大化,即最大最小准则(戴维·米勒,2008)。根据罗尔斯理论,集体成员权配置应有利于社会状况最差的农民。第二,平等主义,平等主义具有两种不同的有价值的平等,一是分配性平等,即某种利益应平等分配;二是社会平等,即人们被平等对待(戴维·米勒,2008)。根据平等主义观点,各潜在集体成员权分配主体应被平等对待,集体成员权益应平等分配给具有集体成员权的村民。第三,目的论或本性论,资源应配置给最会使用或发挥作用最大的人(迈克尔·桑德尔,2012),即集体成员权应配置给最有利于村庄集体发展或对村庄集体发展贡献最大的人。第四,自由至上主义,代表人物诺奇克反对公正的分配包含某种特定模式,认为只要程序合法即为公正,不应根据结果判断公正与否,哈耶克认为“社会正义”是一种“幻象”(邓正来,2004),认为正义是以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按自由至上主义观点,国家不应界定集体成员权的基本标准,只要村庄集体以合法程序分配集体成员权即可。不同正义观下,集体成员权分配标准不同甚至矛盾。从能动的实用主义角度看,集体成员权分配取决于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目的。
四、目标: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目的
目的对所有人类行为具有核心重要性,探索目的对现象具有揭示意义(丹尼尔·W.布罗姆利,2008)。通过梳理十九大报告、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十三五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关于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发现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纷争、规范管理、保护权益和促进发展。解决纠纷和规范管理是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近期目标,目前集体成员权界定缺乏统一标准和权威性,导致集体成员权纠纷和诉讼案件频发,为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带来挑战,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一般而言,经济发达程度与此类纠纷和诉讼案件发生情况正相关,即经济越发达地区,集体成员权纠纷和诉讼案件越多,主要原因是经济发达地区集体成员权经济收益越大;保护权益和促进发展是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远期目标。保护权益既指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权益,也指保护具有成员资格的集体成员权益。清晰明确、保护有力的集体成员权可给集体组织和个人稳定的预期,促进发展。不同地区通过界定集体成员权促进发展的内涵不同。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大城市郊区,通过界定集体成员权以明晰产权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通过土地和其他集体资产规模利用追求土地增值收益,以实现就地城镇化。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或纯农区,通过界定集体成员权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有利于集体成员权退出和实现新型城镇化。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纷争、规范管理、保护权益和促进发展,但目标具有一般性。两个具体目标,一是让已转移或愿意转移的农村人口真正实现集体成员权退出,实现新型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到2020年,使大约一亿具备条件、也有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各类城市和城镇;通过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就近的城镇化”。二是让愿意留在农村和只能留在农村的农村人口发展现代农业和实施乡村振兴。发展现代农业是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实施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载体仍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户或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主,让愿意留在农村的农村人口发展现代农业应成为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具体目标之一。2016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41.2%,按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速度,十年后仍有接近一半的户籍人口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既是中央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也是在村农民现实需求。
五、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的厘定
现实中,发生集体成员权纠纷主要在于“人员流动性”,即流入和流出的集体成员。对于未流动,一直世居于集体内部的集体成员权界定问题几乎无争议。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标准须引入时间变量,即自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时起(分田到户),户口未迁出,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成员及其子女为集体成员。而对于因婚姻、务工经商、入学参军、政策性或自愿迁入迁出等因素导致的“流动性”集体成员,国家需制定集体成员权基本界定标准。集体成员权通常涉及五个标准,一是户籍,二是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三是在村庄有较固定的生产和生活,四是履行村庄义务,五是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户籍是界定集体成员权的形式要件和必要条件,作为公民身份证明,记载和留存人口基本信息,因此用户籍作为界定集体成员权的形式要件简单明了、管理方便,具有普遍性。一般而言,户籍迁出意味着集体成员权消失,户籍是界定集体成员权的必要条件;土地财产权益是附着于集体成员权的核心收益分配权,集体成员权纠纷的实质是土地财产收益分配资格问题。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应作为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核心和实质标准。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需从长期和实质意义衡量,从短期看,外出务工集体成员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但收益具有不稳定性和短期性。从目前看,土地仍扮演农民基本社会保障的角色,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既是农村社会现实需要,也是基本正义观的体现。中国低成本现代化进程、稳定的农村社会、上亿农民工的有序流动、城市无贫民窟等均得益于农村土地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作用。在国家无法完全承担几亿农民社会保障的实际情况下,通过获取集体成员权,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具有兜底作用,体现底线正义和罗尔斯平等自由主义正义观,让农村居民生活有保障;在村庄有较固定的生产生活作为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标准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村庄共同体,以实施乡村振兴。若具有集体成员权的居民长期不在村庄集体生产生活,仅凭借集体成员权分享集体财产收益,此类集体成员即成为食利者阶层,长此以往村庄共同体必然瓦解。在村庄有较固定的生产生活作为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让愿意生活在农村的人获得集体成员权。对于在外务工的农村人口集体成员权问题,若符合两个基本条件,即户口在村庄集体,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应该界定其为集体成员;履行村庄义务作为集体成员权界定标准,主要考虑权利与义务对等。2004年国家宣布免除农业税费以前,村提留、义务工和积累工等作为村庄集体成员义务必须履行,否则集体成员权益将受影响。农业税费免除后,作为政府正式制度安排的集体成员义务几乎消失,在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发展战略下,集体成员不但无需履行义务,还有很多补贴和保障。具体至村庄内部仍存在集体成员需履行的义务,如村庄“一事一议”的筹款(很难实行)、环境卫生等。履行村庄义务不宜作为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基本标准;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作为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标准较苛刻,自《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施行以来,倡导“生不增死不减”的稳定土地承包权原则,大部分新出生和新迁入的集体成员未分得承包地,未与集体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但不妨碍其作为集体成员分配集体财产收益,土地社会保障功能以户为单位获得,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不能作为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基本标准。因此,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基本标准是,对于未流动、一直世居于集体内部的居民集体成员,即自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时起,户口未迁出,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成员及其子女;对于“流动性”集体成员界定的基本标准,一是户籍,二是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三是在村庄有较固定的生产和生活。
根据上述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基本标准,具体分析“流动性”集体成员权界定问题。一是因婚姻流动的集体成员权界定。女方嫁入男方,户口迁入男方所在村庄集体,女方获得男方所在村庄集体成员权;外嫁女分为农嫁女和城嫁女。对于农嫁女,若户口已迁出原村庄集体,集体成员权丧失;若户口未迁出,女方以户的形式获得男方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但不在原村庄集体生产生活,其原集体成员权丧失。对于城嫁女,无论户口是否迁出,若未参加城市养老保险,应保留其原集体成员权;上门女婿若户口已迁入,以户为单位以女方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在村庄有较固定的生产生活,可界定为该集体成员。但分享集体成员权益时需根据村庄集体界定集体成员权具体标准;对于离婚妇女,若户口未迁出,仍以村庄集体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应继续享受集体成员权。若户口已主动迁出,集体成员权丧失。二是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集体成员权界定。因务工经商离开村庄集体,不在村庄集体生活,若户口未迁出,仍以集体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应保留集体成员权。三是因入学参军而流动的集体成员权界定。对于入学的集体成员,在读期间,无论其户口是否迁出,均应保留集体成员权。毕业后,若户口未迁回村庄集体或从村庄集体迁出,其集体成员权丧失,有利于国家城镇化战略实施。对于参军的集体成员,入伍期间户口虽已注销,但保留集体成员权。退伍后,若未在村庄集体重新落户,且未在村庄集体生产生活,其集体成员权丧失。四是因政策性或自愿迁徙而流动的集体成员权界定。因政策性移民或自愿迁徙而来的人口,若符合前三个标准,即户籍在本村庄集体、以集体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在村庄有较固定的生产生活,应界定为集体成员。具体分享集体成员权益需依据村庄集体界定集体成员权具体标准。五是因其他原因而流动的集体成员权界定。如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应保留集体成员权;对于空挂户,即仅户口在本村庄集体,既不以集体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也不在村庄集体生产生活,不应界定为集体成员权;对于退休回原籍农村落户的城镇职工,因不以集体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不具有集体成员权。
六、结 论
本文根据事实、规范和目标三维分析框架,即国家和村庄集体界定集体成员权的现有标准、集体成员权应该界定给谁、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目标,对集体成员权的界定标准展开深入研究。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标准主要包括法律、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司法规范性文件。目前无专门法律界定集体成员权,集体成员权的界定较零散并分布于不同部门法中,且部门法间存在矛盾。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集体成员权的界定相对明确具体,但仍未定纷止争,界定标准较抽象。地方性司法文件对集体成员权的界定较详细,但制定地方性司法文件的司法机关较少。村庄集体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标准通常详细具体、可操作性较强,但标准庞杂,部分标准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集体成员权界定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公平问题。但不同公平正义观得出界定集体成员权标准不同甚至存在矛盾。如根据平等自由主义观点,集体成员权应配置给社会状况最差的农民,而根据目的论或本性论,应配置给最有利于村庄集体发展或对村庄集体发展贡献最大的人,但按自由至上主义观点,国家不应制定集体成员权界定基本标准,村庄集体以合法程序分配集体成员权即可。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主要目标为解决纷争、规范管理、保护权益和促进发展。具体目标,一是让已转移或愿意转移的农村人口真正实现集体成员权退出,实现新型城镇化,二是让愿意留在农村和只能留在农村的农村人口发展现代农业和实施乡村振兴。国家应制定集体成员权界定的基本标准,村庄集体在国家基本标准基础上制定具体标准。国家界定集体成员权的基本标准,一是户籍,二是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三是在村庄有较固定的生产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