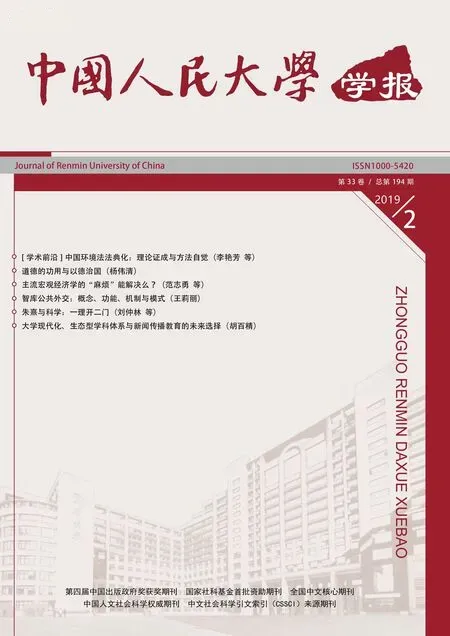世系和统系的构建及其意义
——《史记·太史公自序》相关内容解读
过常宝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追溯了自己史官家族的谱系,并将孔子撰《春秋》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统系联系起来,从而为《史记》的撰述建构了一个堂而皇之的职事话语传统。重新清理这些内容,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司马迁的职事观念、使命意识、撰史方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始祖重、黎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将自己家族追溯到遥远的五帝时代: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注]① 司马迁:《史记》,32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颛顼,是五帝之一。五帝在中国文化中都是半人半神的身份,体现了社会的最高价值和最终依据。《庄子·大宗师》云:“夫道……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注]② 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13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吕氏春秋·古乐》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注]③ 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228、6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五帝是中国文化的发端起义处,也被视为文化发展的目的,所以,将一个传统追溯到五帝,就说明了这个传统具有神圣的价值。《吕氏春秋·序意》载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乱存亡也,所以知寿殀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突。”[注]④ 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228、6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这一段话是说《吕氏春秋》“十二纪”乃效法黄帝、颛顼,体现的是鉴往知来、天人相应、趋吉避祸的理想和法则,这也体现了人们对颛顼神性品质的理解。
重、黎,从《自序》描述中可知为颛顼臣子。根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史墨语,重为少皞氏“四叔”之一,那么,重与司马迁无关。司马迁实际认为黎是自己的始祖。《国语·郑语》曰:“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韦昭《解》:“淳,大也。耀,明也。敦,厚也。言黎为火正,能治其职,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曰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历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时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则黎授民时,能够昌明天地之德,继承了颛顼沟通天人之职。
司马迁关于始祖重黎的追溯来自《国语·楚语下》: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注]⑤ 徐元诰撰,王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465、514-516、465-46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这段话是观射父答楚昭王问“重、黎使天地不通”之事。观射父所言,乃是一种职事传统的形成。上古职事传承与家族谱系有吻合之处,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但在这段话中,谱系不是重点,所以在说及人物时有些含混,如文中的“重”和“黎”是两人,若论氏族则需分开来谈,说清楚程伯休父究竟是重还是黎的后人。因这一段话述及“司马氏”,遂被司马迁转接上自己的族谱,并将家族的源头上溯到重黎。这一转接虽然含糊,却隐含着一项重要的文化转变。
周朝行宗法制度,血缘宗亲等级关系和代际传承成为社会组织的重要方式,因此,宗族谱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周人对自己的宗族谱系有个完善的过程。在西周刚刚成立的时期,所祭祀的主要是周文王、周武王。如《尚书·洛诰》云:“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216、217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这在《诗经》中也有显示,如《周颂》中最早的作品《大武》六章所祭祀的除了天地外,主要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后来,《天作》《思文》进一步上溯到太王乃至始祖后稷。周天子作为周民族之大宗,有祭祀始祖的责任,所以,要将宗族谱系追溯到始祖,并使谱系完整。但对于诸侯而言,他只能祭祀自己氏族之祖,也就是只需追溯到受封立国的那位祖先。
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下降,各种僭越行为常常发生,诸侯开始向往能有个半人半神始祖,而这原本是周王的特权。比如,楚国一直自称王,有与周王分庭抗礼之意。《国语·郑语》载史伯云:“夫其(楚)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后也……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注]③ 徐元诰撰,王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465、514-516、465-46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这实际上是代楚立言,也可以认为,史伯立于西周春秋之交,敏锐地感觉到诸侯在文化上的新追求,并代为言之。再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观乐,“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注]⑥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1503、1163、1087-10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周初,叔虞被封于唐地,建立晋国。陶唐氏实指尧。季札这句话将晋与尧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季札自己的创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注]⑦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1503、1163、1087-10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范宣子是晋国执政大臣,也是一个革新人物,他将自己的祖先追溯陶唐氏,也就是尧时。范宣子的话也反映了称霸多年的晋国的心态,并对季札产生了影响。
但是,大多数中原姬姓诸侯,他们与周天子共有一个祖先,无法像楚王那样别寻始祖,也不一定有晋国那样的文化资源,如何才能满足自己祭祀神性祖先的意愿呢?于是,一种新的文化制度应时而生,这就是分野说。我们来看《左传·昭公元年》这个记载: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知之。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晋为参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注]
子产这一段话,通过一个梦,为晋的开国之祖叔虞连接上另一个远古神灵石沈。石沈在分野理论中为十二星次之一,与二十八宿相配为觜、参两宿,分野主晋;台骀亦是远古神灵,为汾水神。由此,晋国国君可以依附两个神:实沈和台骀。这两个神的古老程度可以和周人祖先契相比,满足了晋人文化升级的精神需求。春秋时,分野制度发达,如《左传·昭公十年》“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注]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1217-1218、13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之类,差不多覆盖到所有主要诸侯国。分野制度,包括对所在地先祖神的祭祀义务,使得诸侯国能够拥有自己的神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周人的祖先神相抗衡。
分野制度,适应了春秋时期天子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现实,体现出割据状态下的政治文化的特点。到司马迁时代,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诸侯分封制大体消灭,大一统集权制度基本形成。汉初虽然还有诸侯国,但其地位大大下降,并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因此,分野制度的影响力也逐渐式微。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新一轮祖先追溯情况。从《史记》来看,新的祖先追溯有如下两方面的特点:
第一,始祖追溯扩展到在历史上和当代社会中各主要阶层。包括前代诸侯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注],“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注];蛮夷民族,“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注],“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注];历史人物,“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注],“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注]司马迁:《史记》,173、1689、2879、1739、338、26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此外,还有司马家族的“昔在颛顼”,等等。这些家世追溯在先秦是很少见到的,它说明社会的主体发生了变化,社会的政治文化结构也都发生了变化。在《史记》中,我们看到各类人的祖先追溯大多会被汇聚到五帝身上,并进一步汇聚到黄帝身上。韩兆琦说:“中国的远古传说中有所谓‘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司马迁认为他们都是一家人。它说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是黄帝的子孙,并在《五帝本纪》中给他们一一地排了世序……这种见解的产生,又有它当时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各诸侯国在互相融合、互相兼并中所造成的那种逐渐统一的政治趋势。”[注]韩兆琦:《司马迁的民族观》,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1983(2)。从新文化建设来说,新一轮祖先追溯,体现了新的社会主体和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合法性需求。
第二,始祖追溯主要是通过文献文本的相关性来进行的。如这篇《自序》,即以《国语》材料来推衍自己的家族。但司马迁与重黎的联系仅有“司马氏”三个字。《国语·楚语》说程伯休甫为“司马氏”,是说他的官职发生了变化,按当时姓氏命名规则,他的后人有可能以司马为姓氏。但司马一职并不始于周宣王时代的程伯休甫,殷商可能设司马[注]王贵民:《就殷墟甲骨文所见试说“司马”职名的起源》,载《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至迟到西周初期,《尚书·牧誓》为周武王伐殷誓词,《尚书·梓材》为周公册封康叔于卫的诰辞,两文中都提到司徒、司马、司空。金文中还有“司马共”“司马井伯”的记载,而共、井伯都是王朝卿士,与程伯休甫并非一族。此外,西周司马类别较多,《周礼》所载有大司马、小司马、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都司马等,诸侯国还设有“国司马”。如西周中期的《豆闭簋》所提到的“邦君司马”即为“国司马”。春秋时期,司马一职更为普遍。在这些司马职官中,会产生不止一个司马氏族。而且,根据《国语·郑语》史伯所云,黎为祝融,后有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大多已经灭国,当春秋时期,中原妘姓的邬、郐等,曹姓的邹、莒等尚存,但都已衰落,只有楚王族芈姓一家独盛。这里已经将黎之后的谱系梳理清楚了。但我们看到,司马迁在追溯黎为祖先时,完全未涉及八姓,说明了他的追溯方法有着相当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二、“世典周史”
在述及西周以降的家族史时,《太史公自序》云:
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注]
重、黎之后在周者为程伯休甫,也正是在程伯休甫手里,这一族“失其守而为司马氏”。所谓“守”即重、黎“司天”“司地”“序天地”之事,也就是沟通天人,这是宗教性职务,后世称为天官。重和黎各有侧重。重司天,应指祭祀、祷祝天神;黎司地,或指祭祀、祷告地祇,或指代民祷祝等。《索隐》:“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据《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颛顼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别……今总称程伯休甫是重黎之后者,凡言地即举天,称黎则兼重,自是相对之文,其实二官亦通职,然休甫则黎之后也。”[注]司马迁:《史记》,3285-3286、32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程伯休甫,《诗经》作程伯休父,袭程国君主。程是周畿内诸侯。南朝梁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洛阳“上程聚”云:“古程国,《史记》曰重黎之后,伯休甫之国也。”[注]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33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程伯休甫时任朝廷卿士。《诗经·大雅·常武》云:“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毛传》:“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为大司马。”[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576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这是说周宣王让尹氏任命程伯休父为大司马,随王征讨徐方,并且大获全胜。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此次任命是就这次军事行动而言,还是一个朝廷常设职务,在《诗经》中并不确切,但《国语》显然认为这是一个固定的职务。
《自序》云:“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这句话暗示程伯休甫为司马氏第一位史官。我们来梳理一下司马的职事。从《诗经·大雅·常武》来看,程伯休父之司马为军事官员无疑,但大司马在西周又不止于武事。《周礼·夏官·大司马》云:
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维邦国;制军诘禁,以纠邦国;施贡分职,以任邦国;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以九伐之法正邦国。[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834-835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
由此看来,大司马为周王重要佐官,几乎负责一切军国政务,地位十分重要,这些已被出土金文所证实[注]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12-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除此之外,在金文中还有司马在策命仪式中担任“右”的载录,如:
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王才周,格大室,即位。司马井伯右走,王乎作册尹□□走……(走簋)[注]
隹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才周师录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司马共右谏入门立中廷。王呼内史年册命谏曰……(谏簋)[注]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159、20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右”是引导受策命者接受策命的职事,在策命仪式中较为重要,一般由朝廷卿士担任,并非特定性宗教职务。也就是说,这位程伯休甫所任司马一职与史官无涉,“司马氏世典周史”不从程伯休甫开始。
有学者根据现存各类材料,认定西周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的异姓史官家族共有四家:辛氏、尹氏、程氏、微氏。其中辛氏,《左传·襄公四年》引魏绛的话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尹氏,《逸周书·世俘》载,武王克殷后返回宗周举行燎祭,“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此“史佚”即尹佚,为尹氏史官之代表。微氏,墙盘铭说:“青幽高祖,才(在)微灵处,雩武王既殷,微史(使)烈祖乃来见武王”。以上辛氏、尹氏、微氏都有多种文献可考,唯有“程氏”,除了司马迁根据《国语》记载,自云“世典周史”外,无任何材料可以佐证。[注]胡新生:《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载《历史研究》,1994(3)。
“惠襄之间”已经是春秋,若以周惠王和周襄王交替之年,则约在公元前651年,当时周王朝有废立之乱,司马氏“去周适晋”。晋国史官可知的有史苏、卜偃、董狐、史墨、史赵、史龟、周舍等[注]晋国春秋时期见诸文献的史官有:孙伯黡、辛有之二子、史苏、卜偃、董因、史援、董狐、董叔、董伯、史赵、史龟、史墨、董安于、屠黍、周舍。参见樊酉佑:《晋国史官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并无司马氏任史官者。三十年后,晋随会亦因晋国内部废立之乱,而逃至秦国。[注]随会与司马氏无关,司马迁只是以“随会奔秦”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提出来。参见张胜发:《“随会奔秦”与“司马氏入少梁”》,载《渭南师专学报》,1993(4)。当此之时,司马氏离开晋国入居少梁,此时少梁在秦治下。这一支包括司马错(为秦将)、司马靳(事武安君白起)、司马昌(主铁官)、司马无泽(汉市长)、司马喜(五大夫)、司马谈(太史公)、司马迁。司马错以下这个谱系应该是司马迁家族最为切实的家谱,司马错是司马迁能够追溯到的最远之祖先,所以特别述及。其他司马氏有:在卫国之司马喜(中山相);在赵国之司马凯(以剑术显)、司马蒯聩(可能是《刺客列传》中的盖聂)、司马卬(受项羽封)。由这个谱系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乃至汉初,司马氏无任史职者。司马谈所谓“后世中衰”,或即指春秋战国乃至汉初司马氏无任史职的事实。
由上可知,所谓“司马氏世典周史”,实际只是司马迁根据《国语》“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一句推断出来的,并无实据。司马迁之所以勉强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程伯休甫,追溯到重、黎,就是为了强调自己家族的天官或史官传统的原生性。
下面我们根据《自序》来看看司马迁对天官和史官的认识。从“失其守而为司马氏”这一句话来看,司马迁似乎认为司马氏的史官与重、黎的天官颇有不同。天官的主要职责是“世序天地”,也就是沟通天人,包括祭祀、灾异、祝告、敬授民时、礼乐等,为早期宗教性职务,亦即巫。上古巫史不分,史主要指巫职中承担载录、出使之人,从春秋文献看来,史仍有宗教祭祀之职责。司马迁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这个巫史一体的意识,而将自己的家谱追溯到重、黎和颛顼。那么,所谓“失其守而为司马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汉代的史官制度来看这个问题。有学者总结西汉太史的主要职责大致有九项:第一,掌天时、星历,议造历法,颁行望朔,奏时日禁忌;第二,主持并参与多种祭祀仪式;第三,礼乐损益,音律改易;第四,随从封禅,事鬼神;第五,掌管天下郡国计书;第六,掌术数算学与课试蒙童;第七,记录灾异;第八,掌灵台,候日月星气;第九,掌明堂、石室档案图籍。[注]以上参见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39-4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比较起来,其中天时星历、主持祭祀、记录灾异、候日月星气等,都是阴阳鬼神之事。也就是说,汉代史官亦有“序天地”之职,所区别者大约在两点:一是早期的“序天地”有着崇高的地位,《史记·天官书》所谓“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因其职事关系到人类的生存、规范和意义,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而到了后代,如《报任安书》所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注]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27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天官之职已完全衰落,为统治者所蔑视;二是后世太史与重、黎之“序天地”相比,多了文献载录和保存等事,而这个载录之事又为司马迁所特别留意。大约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司马迁才有“(程伯休甫)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这个奇怪的说法。这其中既有对巫史地位衰落的悲叹,也有对巫史职事的执着,体现了一种复杂的心态。
从这个家族谱系来看,司马谈是司马氏第一个史官。史官这一职事,在西周春秋时期达到高峰,文化地位十分突出。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甚至大臣也还设有史官,如秦昭王与赵惠文王渑池会盟时,有秦御史记录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注]⑥ 司马迁:《史记》,2442、26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赵王亦有史官跟随、记录。但秦一统天下,不但“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秦记》及其他撰述活动也都戛然而止,史官职事断绝。各类文献上所谓“史”,基本上都是“吏”。东汉卫宏的《汉旧仪》记载:“旧制尉皆居官署……更令吏曰令史,尉吏曰尉史,丞吏曰丞史。”[注]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其中令史一职,据秦简,除执掌文书、监督仓啬夫与代理官啬夫外,还有监督谷物刍稿出入仓、巡查府库、负责上计事务、参与司法程序和行庙等,显然是个事务性吏职。汉代从朝廷到各级衙门,都设有令史一职,参与礼仪和祭祀、护驾、宣诏、举谣言等,虽然承担了不少史官职事,但职位低下。[注]以上参见苑苑:《秦汉部分史职研究——以尹湾汉简为考察基点》,河北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此外,其他职务也代行史事,如《史记·张丞相列传》载:“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⑥。可见秦及汉初,史事分散,并无先秦意义上的专任史官。
唐初魏征所撰《隋书·经籍志序》曰:“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注]魏征等撰:《隋书》,9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太史的长官是太史令。《后汉书·百官志》曰:“太史令一人,六百石。”自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注]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35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由此看来,汉代太史的职责与春秋之前史官相仿,仍以沟通天人和文献职事为主,属天官。这可能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天命观及改正朔等建议有关。可以断定,司马谈是汉代第一位史官,也是司马家族的第一个史官。对于史官这个悠久的职业来说,尤其是当史官被当作是一种天职之时,传统是十分重要的,缺少一个深厚的传统会使得司马谈父子深感不安。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注]③④⑦ 司马迁:《史记》,3295、3296、3297、3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这句话不但要为自己追溯一个传统,还体现了延续这个传统的急切愿望。
三、《春秋》王道
司马迁对重、黎的追溯,一方面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之文化建设,但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职事寻找到一个悠久而神圣的传统,但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司马迁这个追溯其实是很勉强的,难以说服他人。所以,司马迁还有另一个谱系以支持自己的史官事业。《太史公自序》云: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③
在这段话里,司马迁将自己的《史记》著述看成是继承孔子的《春秋》事业,而不是归之于重、黎的传统。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孔子所撰《春秋》是年代史书的直接源头,而重、黎传统并没有这样的史书传世。其次,司马迁认为《春秋》涵盖了重、黎天官职事,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④所谓王道,在儒家看来也就是天道。再次,孔子《春秋》也在一个神圣谱系或传统之中。所谓“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实来自《孟子·尽心下》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注]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3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孟子在这里构建了一个既不同于宗法也不同于职事的王道传统[注]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修订本),241-24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它所谓“王”,并非指现实的帝王或诸侯王,而是文化缔造、道统传承之“王”。孔子在匡被围,却满怀信心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里的“文”就是自周公传承而来的以礼乐为标志的王道。孔子以“素王”身份传承这个统系,这个统系的标志就是捍卫礼乐王道的《春秋》。司马迁《自序》在论及《春秋》之功用时引用董仲舒的话云: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⑦
这一神圣的裁决权力和支持这一权力的统系,对司马迁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所谓“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所谓“意在斯乎”,就是对这一传统的自觉体认,这不是一般的精神认同,而是一种真切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司马迁确切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五百年一出的“王”。这一传统由于没有宗族血缘或职事传承的关系,对司马迁确认自己的事业,能有更为直接的激励,也能弥补渺茫难信的家族传统给自己带来的缺憾。
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统系,似乎也只能在战国时代说说,汉代皇帝以天子的名义一统天下,因此,他既是俗王,也是圣王,所以有壶遂之问:“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注]而对于这样的疑问,司马迁也只能“唯唯否否”,顾左右而言他。这说明,在集权政治背景下,这个天道统系是无法存在的,更何况去实践、延续它。司马迁的“唯唯否否”,也流露出对这个统系的犹疑。也许正是如此吧,司马迁才同时认同两个传统,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给人以更踏实的感觉。
司马迁出任史官以来,常要侍从汉武帝巡幸,参与多种祭祀活动,制定太初历,备皇帝咨询,等等。这些都是史官本职,司马迁似乎都不甚在意。因为,在汉代官员序列中,史官地位低下,话语权非常有限,这些从前的神圣事务,在汉武帝时代,只能等同于倡优之事。司马谈父子身处古代巫史传统的末端,悲哀盛时不再,而对曾经有过的辉煌满怀憧憬,他们不认可自己在朝廷序列中的地位,转而认同这个悠远的神圣传统,并期望从《春秋》那里寻求天道之担当。司马迁将自己的家世追溯到重、黎,这是强调自己的职事有一个神圣的传统,是天命的代言人,它是一个很高的起点,也是某种精神皈依;将自己的《史记》撰写追溯到孔子《春秋》,这是强调史官裁决天下的权力和责任,是一种左右社会发展的职事实践。家族世系和天道统系上的归属,能赋予司马迁某种神圣权利,使得他获得一份具有超越历史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具体而言,巫史传统赋予司马迁话语权的合法性,而孔子《春秋》则给予他独特的话语方式。
相对于改历、封禅、从巡等,司马迁特别在意《史记》编撰,他对壶遂说:“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注]。其实,传统史官虽然有载录之职,但并不撰史,撰史的只有孔子。而《史记》亦非只载录盛德和功业,它有着更为高远的理念和更为激烈的态度。《吕氏春秋》认为颛顼之道“所以纪乱存亡也,所以知寿殀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突”,这是自历史和天人两个层面,说明巫史的绝对权威和至上价值;而孔子作《春秋》所显示的价值审判之至上“王道”,以及其“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注]司马迁:《史记》,3299、3299、3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于孔子而言,可谓立言以不朽。这几个加起来,就是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注]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27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司马迁的《史记》在讽刺汉代皇帝这一点上可谓不遗余力。班固《典引序》记东汉明帝言:“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21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三国魏明帝在与王肃谈论《史记》时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注]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4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三国志·魏志·王肃传》)甚至到清代的王夫之说:“司马迁之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又说:“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注]王夫之:《船山全书·读通鉴论》,140、15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1。他们关于《史记》为谤书的判断是不错的,但说其“受刑之故”,则不够准确,实际上,司马迁理解孔子著《春秋》就是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其作史的姿态就是“当一王之法”,就是裁决当世,因此,司马迁作“谤书”与继承孔子统系有关,而与“受刑”无必然之关系。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将家族的历史追溯到程伯休甫和重、黎,又主动承接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道传统,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恢复史官的神圣性,重构史官的崇高地位;第二,从传统中为自己的史官职事寻觅合法性和权威性;第三,为自己的《史记》撰写理念和方法找到历史性样本。因此,司马迁的家族追溯和职事传统建构,对于他的史职认识和实践,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兼论葬仪之议中的刘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