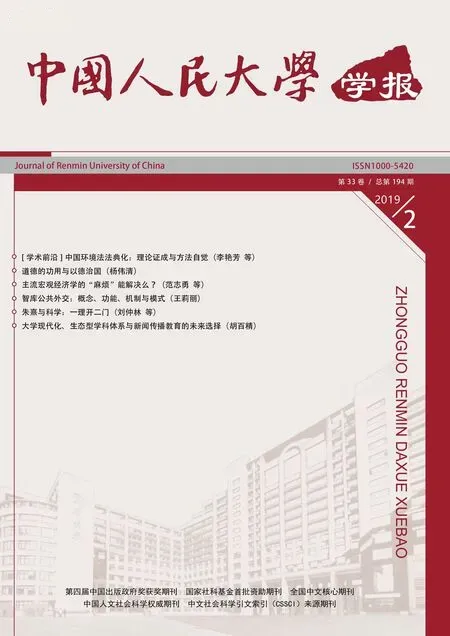朱熹与科学:一理开二门
——理学对科学的双重意蕴
刘仲林 周 丽
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一)中提出了广为人知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一,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0。
为什么中国与近代科学的产生失之交臂?有多种多样的回答,其中近代自然科学未能从传统哲学分化出来是一个重要因素。对这一问题,宋代朱熹(1131—1200)的理学思想具有代表性。朱熹既是中国传统哲学向近代科学转化的先驱者,也是转化途中又折回传统哲学的守护人。英国的李约瑟,日本的山田庆儿,中国的胡道静、马来平、乐爱国等许多学者都谈到朱熹思想中的近代科学萌芽。事实上,朱熹确实在这一方向上做了许多研究,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探路的先行者。但是,由于朱熹固守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定位,大自然之理未能冲破泛社会伦理框架,未能在研究自然之理方向上迈出独立的步伐,以致近代科学终未在理学中开花结果。至明初,朱熹理学被奉为正统哲学,把大批知识分子引入钻研儒家经典的死胡同,因而被视为阻碍近代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注]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332页,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2。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李约瑟把朱熹理学界定为一种有机自然主义,并视之为现代科学思想的来源。[注]乐爱国:《李约瑟评朱熹的科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载《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9(3)。
笔者将以“一理开二门”为主线对朱熹理学之“理”的范畴进行梳理,并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角度深入分析朱熹理学既孕育又遏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矛盾现象,揭示其理学思想对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双重意蕴。
一、 理不离气的本体论:自然之理与社会之理的共相
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通过对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思想的阐释、总结与吸收,使得理学的许多范畴与论点有了系统的深化和发展。冯友兰曾言:“朱子之学,系以周濂溪之《太极图书》为骨干,而以康节所讲之数,横渠所说之气,及程氏兄弟所说形上形下及理气之分融合之,可谓集其以前道学家之大成也。”[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25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朱熹集前辈学者思想之大成,建构了以形上之理为本体的理学体系,其理学体系的立论基础便是“理不离气”,从浑然一体而可分言的理气处,来论宇宙万物本体与人类道德本体的共相,也即自然之理与社会之理的共相。朱熹从理不离气这一观点,拓展至“理=太极=道”这一范畴等式,从本体论的视角,为近现代科学的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生长空间。
(一)理不离气
李约瑟曾写道:“对朱熹的自然主义哲学(理学)的探讨是要从其对气和理的概念的解释开始,因为这两个概念通常是自然主义的宇宙论中分别表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注]⑤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二,503、5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0。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便是理与气。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注]⑥ 朱熹:《朱子全书》,23册,2755、33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在天地之中,“理”是万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是看不见的本体,无形迹可循,为“形而上”之道;而“气”是构成事物的质料或用具,有形迹可循,为“形而下”之器。
朱熹虽分言形而上之“理”和形而下之“气”,但理气乃是浑然一体的,而非两体对立的。在朱熹看来,理气是并存的,就具体事物的存在而言,理气二者是不相分离的关系,具体的存有物是有生灭的,而形而上的理则无生灭,理是一切存有物的形上学根据,然而无具体的“气”的存有物又无从谈其超越的形上学之“理”的根据。《朱子语类》(卷一)曰:“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册,3页,北京, 中华书局, 2017。理气二者是不可混杂的,是不离不杂的关系,但从形上学的根源上讲,可以说是理先气后。这种理气的先后,类似于西方哲学中“逻辑先在性”的先后,而不是“时间先在性”的先后,但不只是逻辑上的先后,而且是形而上的先后。总的来说,朱熹认为有理方有气,理不直接创生万物,是通过气之存有物依傍理来创生万物,理气合则万物生。
诚如李约瑟所说:“朱熹以其中世纪的方式肯定理和气的普遍的互相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⑤当然,不同在于朱熹是在理气的关系中寻求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并行的共相之理,近代科学主旨方向则是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上寻求外在物质世界运动规律之理。
(二)自然之理与社会之理的共相:理=太极=道
朱熹虽然认为理气是浑然一体的,但理是气之存有物的形而上根据,也就是说理是第一性的,理气说的核心观点,可用朱熹一句话来概括:“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⑥(《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朱熹用普遍存在于宇宙自然中的最高概念“理”,替代了原始的朴素的“天理”也即理学家所说之“太极”以及不可言传、玄之又玄的“道”。在朱熹的诠释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有这样一范畴等式:“理”=“太极”=“道”。李泽厚在梳理中国古代思想史时总结道:“朱熹庞大体系的核心是建立‘应当’ (人世伦常)=‘必然’(宇宙规律)这一观念公式,万事万物之所以然(‘当然’)当即人们所必须(‘应当’)崇奉、遵循、服从的规律、法则、秩序,即是‘天理’,这个超越天、地、人、物、事而主宰之理(‘必然’)也就正是人世伦常之‘应当’,两者既相等同又可以互换,朱熹包罗万象的理世界就是为这个公式而设。”[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219-220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以理会通太极与道,以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的都包含“所以然”(外在超越)与“所当然”(内在超越)来论证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的共相、自然之理与社会之理的共相。
在朱熹看来,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理,但都是一个根本的、整体的理,这个根本的、整体的理就是“太极”。朱熹以太极即是理,使得理气关系得以厘清,并以此把儒学引入理学之路向。他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册,1页,北京,中华书局, 2017。此言可同他讲“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相参照。太极是世界万事万物之“所以然”的最初根源,是最根本的理,把极致之理的太极等同天理。这个宇宙本体的“天理—太极”既是社会性的也是伦理性的,朱熹所说的宇宙本体的太极即天理还类同道德本体,他的自然之理的“所当然”是等同社会伦理的“所应当”。
朱熹再顺着其分解的路线来把“道”作“理”来理解,朱熹常言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气,亦可换言形而上者为理,形而下者为器,也即可言道就理,故《朱子语类》有曰:“凡民生日用皆是一个道理,若只理会得民之故,却理会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极时,固只是一理。”[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五册,1927页,北京,中华书局, 2017。从他的分析中可知,天道与人道虽有不同,但终极来说是通道为一的,都是一个道理即天理,所以《朱子语类》中说:“一草一木。与他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君臣父子、礼乐器数,都是天理流行活泼泼地,哪一件不是从天理中出来。”[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三册,1049页,北京,中华书局, 2017。朱熹自然就把天道人道自然归结为天理,理自在天道人道中,理就是道,在道的范畴之中,天道与人道是互通的,道是太极也是理。
二、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心之理与物之理的共相
朱熹另一个与近现代科学密切相关的观点是“格物致知”,正是通过格物穷理,打开了通向近现代科学的大门。
“格物致知”源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给出了以格物为起点、平天下为终点、正心修身为中心的大学之道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其“格物致知”的独特提法尤其引人注目,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大学》没做任何解释,这给重视《大学》的理学家们留下了儒学理论新的发挥的空间,而其中发挥最系统的要数朱熹。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认为朱熹的理学思想中最独特最伟大之处便是讲格物致知。[注]钱穆:《朱子学提纲》,12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朱熹所言的格物主要是对所触之自然存有物的“即物穷理”。关于理,金永植在《朱熹的自然哲学》中认为最近的含义便是这一句:“止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以然之则,所谓理也。”[注]金永植:《朱熹的自然哲学》,23-2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故朱熹所释的穷理,自然就是不仅要穷自然指存有物的“所以然之故”之理,也要穷“所当然之故”之理。就“格物致知”的“格所以然之理”的指向而言,是和近代科学探寻的物之理的指向相同的,即都含有通过具体客观事物,探寻其存在和变化的规律。《朱子语类》有曰:
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四册,1496页,北京,中华书局, 2017。
这说明,朱熹所格之物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要认识万物之所以然之理,必须对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等自然万物都展开研究,通过格自然之存有物而知存有物之理,不能离自然物而探究物之理。朱熹非常赞同程颐的“一理万殊”的说法,在朱熹的诠释中也认为,物物各有理,但都是一个理,即是所当然之理与所以然之理的共相,把人伦日常之道德准则与天道流行之宇宙规律等同一理。他论证说道:“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第,此即所以然之故。”[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二册,414页,北京,中华书局, 2017。而就人伦日常而格“所当然之理”,朱熹说: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皆人所不能无者,但学者须要穷格得尽。事父母,则当尽其孝,处兄弟,则当尽其友。如此之类,须是要见得尽,若有一毫不尽,便是穷格不至也。格物,莫先于五品。格物,是穷得这事当如此,那事当如此。如为人君,便当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又更上一著,便要穷究得为人君如何要止于仁,为人臣如何要止于敬,乃是。[注]⑥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册,284、2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7。
朱熹认为格“孝”“友”之事,则会自觉践行“孝”“友”,朱熹探究物之理的路数便可清晰,就是穷物之理,而至豁然贯通之理,明心之理,也就是朱熹所谓“格物致知”的初衷。所以朱熹晚年为大学章句集注时就“格物致知”补了以下一段话: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注]朱熹:《朱子全书》,6册,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所谓的致知在格物就要知道万物的理,就必须就物而穷其中的理而至知,这是一段朱熹认识论的精华,实际是借补经文之机,舒己之意,返本开新,开出格物新天地。由此寥寥一百三十余字,可明显看出,朱熹讲格物致知是落实于即物穷理,但其所依据是“以心知理”。其格物致知思想的核心便是以明心之理而穷究物之理。对朱熹来讲,从心之理到物之理,实际是心之理与物之理的共相,他说:“物与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两无少欠,但要我应之尔。物心共此理。”⑥在朱熹看来,理在人心即是心之理,在具体事物即是物之理,通过格自然存有物之理就可以明白心之理,人之心已具备万理。
朱熹把物之理与心之理直接等同起来的,并且把落脚点放在心之理上。这样,朱熹的“格物致知”有对自然知识的探寻的指向,对中国近代科学有积极的启蒙意义,然而与近代科学在认识上的(主客)物我二分不同,其“格物致知”的起点和落脚点都是心物合一, 且以修身正心为本,无法形成主客二分的近代自然科学认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朱熹格自然之物、寻物之理,与格社会之人、寻心之理,虽有别但理同,是心之理与物之理的共相,也即“所以然之理”与“所当然之理”的共相。
三、 天理归仁的价值观:生生之理与仁爱之理的共相
宋代理学家们在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性命义理的基础上,对儒学传统的“仁义内在”的价值观进行了改造和复归,至朱熹,理学的综合体系得以形成,儒学的性命义理实现了自然宇宙观和道德形上学的合一,使得传统儒家的“仁义内在”的价值观得以挺立。朱熹以道心与人心来论天理,把其本来认识论中具有豁然贯通之理的认识主体之“心”范畴,拓展至有善恶的仁学价值论体系中,主张心统性情,以生生之理与仁爱之理的共相证成天理归仁的价值观,从中国哲学特有的存在和价值一体的角度分别与近现代科学的存在和价值有所交汇。
(一)从人心道心来论存性善之天理
“天理”作为哲学范畴出现在《礼记·乐记》的“穷天理,灭人欲”的论述中。《朱子语类》(卷十二)载:“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熹在此基础上综合其他儒家之说提出了自己的“明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从“人心”“道心”相即不离来论存性善之天理。
朱熹所谓人心、道心,并非是说人有两个心,而是指人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活动。[注]杨天佑:《朱熹及其哲学》,2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或问‘人心道心’之别。曰:‘只是这一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五册,20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7。所谓人心,指源于人的耳目之欲之心,是饮食饥渴之欲,是心之用,就是情,是指“恻隐”“善恶”“辞让”“是非”等观念情感,属于已发的现象世界,是人的气质之性。所谓道心,指以仁义礼智之义理为内容,是本体的心,是天理的体现,是未发的本体世界,也就是人的天命之性。在朱熹看来,人是性命与气质结合之物,心之性理是天命所赋予的,而心中有欲是受形气之影响。
在朱熹的论述中,人心道心是不离不杂的,二者是相互依存、相即不离的,道心与人心虽与天理人欲有关系,但不能把人心直接等同于人欲,人心向而为善时,则人心等同于道心。朱熹承认人人都有道心人心,但人心不都是向善的,它还有着不向善的可能,要保证性之善,必须使道心成为人心的主宰,人心必须服从于道心,把客观存在的人欲纳入天理的管辖之内,以道心节制人心。《朱子语类》有载:“道心是义理之心,可以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据以为准者也。”[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四册,148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7。因为道心即是性善之天理,人心虽可为善,但以可有私欲为恶,若不加以节制,则可危及天理,所以人心必须接受道心的指导,合于道心者为之,不合于道心者不能为,由此性善之天理才能得以恢复和保存。
(二)天理归仁的实现:生生之理与仁爱之理的共相
朱熹理学思想的枢纽点是在“心”。以人心道心而论性善之天理,保存了孔孟以降的传统儒家的道德本体论的主体思想,然朱熹之理学经北宋理学之熏陶,其性善之论不再拘于传统儒学之道德本体之传统,以心善论性善,而是把“人心”之善扩充至“天地生物之心”之仁,由“心”而言“生”,从道德本体和宇宙本体的合一来论天理归仁。
朱熹把“心”和“生”结合而言存在之本原,是承程颐之“天地生物之心”为万物本原这一观点,从本原上讲,天地有“心”,是以“生”为心,即所谓“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有载:“伊川言:‘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盖谓天地以生生为德。自‘元亨利贞’,乃生物之心也。”[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五册,179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7。元是指万物滋生、造化发育的开端,天地有了生物之心便有了自然万物,元、亨、利、贞便是天地变化、生生不已的天地生物过程。《仁说》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注]朱熹:《朱子全书》,23册,32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朱熹把心的内涵和外延扩大,不仅人有心,物亦有心,人物之心皆是以天地之心为本。蒙培元在《朱熹哲学十论》中指出:“朱子提出并讨论了‘天地之心’ 的问题,是为了说明天地自然界生命创造的深层意义。‘生’是其天人之学的核心,‘心’便是其‘生’的学说的核心。”[注]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17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在朱熹的诠释中,人心与天地之心是相贯通的,因为二者之间都贯穿着一个仁的脉络。他说:“盖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为心,则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尝不贯通也。虽其为天地、为人物各不同,然其实则有一条脉络相贯。”[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六册,242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7。《系辞》言:“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以其德生万物,其目的是“继善成性”,是仁心之体现,心德是以仁为统的仁义礼智,是性善之德,由“心”而说“生”把天地生物之仁德与人心之仁善以仁而贯通。
把人之仁心扩大至天地生物之德心,以天地“生生不已”之德来说明仁。朱熹用“心”字贯通天地,由“天地生物之心”来实现自然万物的“生生之理”之德。关于朱熹哲学之“生生之理”,除了蒙培元认为朱熹之理从“生”的角度论述,还有唐君毅把朱熹之理理解为“生生之理”。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指出: “然朱子所归宗之理,则又为一统体之理。此统体之理, 即一生生之理生生之道,而相当西方哲学所谓实现原则。”[注]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2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这里所说的西方哲学之实现原则实际是一种创生,中国哲学中的“生生”与“化育”“流行”皆有此创生意。“生生之理”是一种生命创造之理,是气化之生生不已之理,是自然界的“所以然之理”,由“天地生物之心”到“人之仁心”,人心是天地之心的实现,仁德是天地之德的实现,人心之仁德是自然界之生生不已的生命创造的关键,其气化之“生生之理”也蕴含着心之“生生不已”之“仁爱之理”,是“所以然之理”与“所当然之理”的统一。 朱熹说生之意思是仁,所论之“生生之理”是为实现儒家一贯所持“仁爱之理”之德,以“生生之理”与“仁爱之理”的共相证成天理归仁。
四、朱熹理学对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双重意蕴
我们以“一理开二门”为脉络,对与科学相关的朱熹理学的“自然之理与社会之理”“心之理与物之理”“生生之理与仁爱之理”分别进行了梳理与论证。下面我们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朱熹理学对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双重意蕴。
第一,自然万物有自然之理,社会人伦有社会之理,若分门别类探究,自然之理的科学目标就鲜明地呈现出来,再随探究深入,必假之以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近代科学的大道就会越走越宽广。然而,由朱熹“理=太极=道”范畴等式的确立可知,其理学之本体是宇宙本体与道德本体的合一,仍然是承先秦儒学的道德本体而来,没有打破原有的对“存在”之追问的范畴体系,而只是用高度概括的具有普遍性的、共相性的“理”来替代“太极”“道”等范畴,朱熹没有对物质世界进行分门别类具体深入研究,未能探索出不同物质层次、不同领域的“理”的各自不同表达。朱熹的“理”缺失了从传统的有机自然主义跨越至近代科学的机械自然主义的阶段。然而朱熹这种从自然和人文两个视角考察“理”的视角,对现代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科学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社会学、STS(科学·技术·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富有启发性。从时间的角度说,朱熹所处的时代是近代科学形成和学科分化初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区分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的不同,以拓展出自然科学独立发展的天地,但是朱熹的理学却反向操作,在近代自然科学处女地远未开垦之时,就匆忙做人文之理与自然之理的合一,结果把自然科学独立成长扼杀在摇篮中。当然,这和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长期聚焦“天人合一”有密切关系,不是朱熹一人的原因。
古人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近代科学而言,宋明时期是一个探索自然之理与社会之理分化的时代,而朱熹关注的重点是两“理”合一的问题,结果自然难以促进自然科学的独立和深化发展。所以,尽管朱熹的理学凸显了“理”的至高无上地位,指明了探索自然之理的方向,但并没有带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繁荣。令人进一步深思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文理会通、跨学科发展的时代,朱熹关注的自然之理与社会之理的共相,对正在走向 “分久必合” 新时代的现代科学可能有更深刻的启迪意义。这是本体论视角下的朱熹理学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双重意蕴。
第二,朱熹打出“格物致知”的大旗,大胆补充古籍缺乏解读的短板,打开了格物穷理的大门,是传统文化向近代科学转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如果沿此格物方向深入探索,追求自然之理的近代科学将光明正大地进入中华文化的主殿堂,而不再会被称为“奇技淫巧”。可惜,这一方向的客观深入研究并没有发生,因为在《大学》中“格物致知”只是“修齐治平”的起点,后边还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项,“格物致知”以修身为本,属心灵“内修”层面,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外治”目的层面。“格物致知”的目的在实现家庭社会的太平世界理想,由此,聚焦追求物质规律的分科——自然科学就无缘产生了。
但从现代科技发展来看,随着科技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关联越来越多,在许多研究领域,格物与正心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例如,随着生物学克隆科技发展,人类能不能克隆成为一个复杂问题,不仅有科技难题,更有社会伦理难题。又如,随着人工智能研究深化发展,人工智能和人类关系如何,会不会给人类带来危险和困境,这不仅是科技问题,也关系社会伦理等问题。由此可见,从未来发展考虑,朱熹主张的“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认识论共相观,对现代科学综合化、跨学科化发展有积极启迪意义。另一方面,从科学创造过程的角度说,朱熹提出的认识过程“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是科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创造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思维阶段。1926年美国心理学家沃勒斯提出了创造的四阶段说(准备、孕育、豁朗、验证),朱熹所言恰属豁朗(第三)阶段。朱熹揭示了科学发现不是一个线性思维方式,而是包括想象、直觉、顿悟的多种非线性思维方式。笔者之一曾提出科学创造中的意象思维和审美逻辑方法[注]刘仲林:《科学创造性思维中的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2)。,与朱熹的“豁然贯通”有密切的联系。从创造过程和思维方法的角度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确有共相,古人的修身为本对科技工作者创造心理和创造技法成熟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第三,在价值观方面,朱熹天理归仁的价值观是沿袭北宋理学之价值观而来,将《易传》生生日新的价值理念融入传统的“仁学”核心,使泛伦理化的儒家思想融入新的价值观念。朱熹天理归仁的价值观是对传统的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回归,仍然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价值导向。而近代科学的发端也是基于对传统自然主义价值观回归,不同之处在于,其主张的是人与自然相分的机械自然主义的价值导向。在近代西方世界关于人与自然二分的机械自然主义价值观下,人一是在自由主义思想下对自身塑造,二是在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下对自然改造,如此才有了近代民主与科学。然而这种人之存在与科学实证主义二分的价值观使得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出现严重分裂,进而导致近代哲学的人性危机与近代科学危机。现代科学的发端便是对这种实证主义有所缺失的科学概念和人之超自由的存在的批判而来,把缺失的形而上中的“最终问题”与宇宙论的“永恒问题”纳入理性的纯粹世界重新考虑,从价值与存在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朱熹以“生生之理”与“仁之理”的共相证成的天理归仁,从存在与价值统一角度而言,对现代综合科学的发展富有启迪意义。
朱熹诗云:“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春日偶作》)若问:朱熹本人对乾坤造化心有深入了解吗?回答是:似有而又似无。从本体论上对“理”范畴的形上提升,认识论上对“格物”的高度重视,价值论上对“天地大德曰生”的高度弘扬,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朱熹对“乾坤造化心”的倾注,这正是宋明新儒家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朱熹向近代科学大门迈进的体现。但是当朱熹把这一切都束缚在泛伦理化的“仁学”理论框架下的时候,他似乎没有深度理解“乾坤造化心”的真谛。这也正是朱熹理学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起止兼有的矛盾性。
五、结语
朱熹理学通过共相贯通的努力,把天地的“生”与人类的“仁”贯通为一,为传统儒学开拓了新视野,为孔孟“仁”注入了生气,为建构新儒学形而上体系奠定了基础,其意义颇为深远。儒家从孔子开始,“仁”这个范畴一直是儒家体系的核心。后来的儒家,从汉、隋唐到宋初,基本上是在孔子设定的这个圈子里谈论仁。朱熹理学突破儒家传统圈子,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角度加以论证,从而使仁的形而上学意义更为明确。
而天地的“生”与人类的“仁”如何共相贯通?这里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仁为纲,以仁统生;二是生为纲,以生统仁。判别两条路的重要标准是:既然天能造化,以显天生,那么人能否造化,以显人生?回答否定的,是第一条路;回答肯定的,是第二条路。
朱熹选的是第一条路,承认天的造化,回避人的造化。朱熹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册,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7。人是从天地间产生的,人应继承天地之大德,方是顺理成章,但朱熹却半路笔锋一转,言人心必仁,达到了仁就达到了天地之大德,给人明显的偷梁换柱之感,用仁代生,由此人的大德就变成仁义礼智信了。当然,朱熹否定一般人能造化,却没有否定圣人的造化。朱熹做了很有价值的共相贯通努力,但这种努力选择的是“仁为纲,以仁统生”的道路,即以仁学为核心,同化、消解生生哲学。通过这条道路,虽然使“仁”的视角扩大到天地宇宙,明确了仁的形而上意义,促进了新儒学诞生,但也明显束缚了生生哲学的生机勃勃活力,使其成为仁学的附庸,阻断了生生哲学创造力在人类身上普遍落实,终止了分门别类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深化发展。
“生”与“仁”的共相贯通,还有另一条“生为纲,以生统仁”的道路,宋明理学没有走,道家和佛家也没有走,今人能尝试走一下吗?这正是张岱年为代表的“综合创新学派”走的探索之路。张岱年解释《易传》生生日新观点时指出:“生就是创造,生生就是不断出现新事物。”[注]张岱年:《张岱年全集》,五卷,22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张岱年把“生”的观念提高到“创”的高度,突破以“仁”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框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崭新的天地与人类创造共相的“广义创造观”,从解放生生哲学蕴藏的强大创造力开始,以期实现中国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80多年来,以张岱年为代表的“综合创新”学派,正在这条大路上探索,初步形成了与“仁学”不同且互补的“创学”理论系统。
朱熹创建的恢宏理学体系是宋明时期哲学的高峰,足以成为近代科学发展的摇篮,但儒家传统的泛伦理学框架,又阻碍了近代科学萌芽成长壮大,朱熹的理学未能开出近代科学,固然令人扼腕,但对新时代下的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有深刻而丰富的启迪。在今天,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然进入一个大综合的时代,一些西方学者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综合整体思想”能契合现代科学新发展。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物理化学家伊利亚·普里高津说: “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 一个新的归纳, 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注]伊利亚·普里高津:《从存在到演化——自然科学中的时间及复杂性》,3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李约瑟认为朱熹是中国最高的综合思想家,并提出朱熹的哲学基本是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过程哲学),不曾经历牛顿和伽利略的阶段,靠洞见达到类似怀特海的立场。[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二,4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随着现代科学发展,特别是大批新兴文理交叉科学领域崛起,朱熹天人合一的广义理学观,重新呈现出积极而深远的现代交叉科学意义。现代综合科学的发展,中西会通哲学的深化,使得朱熹憧憬的自然之理与社会之理会通为一的“大理”研究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