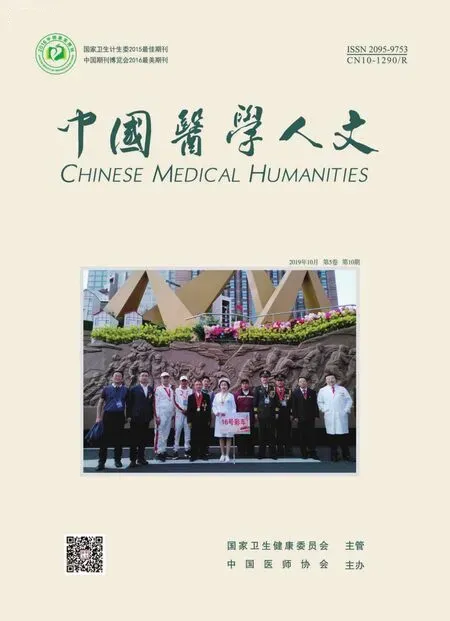二十一世纪医学面临的挑战
文/金观涛 凌 锋 鲍遇海 金观源
20 世纪下半叶,医学的基础研究有了巨大的进步。除了疾病检测手段的大飞跃外,最关键的是对病因的认识,其从人体器官、组织、细胞的功能和结构进入DNA 层面。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1991 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纳罗德(Steven Narod)及其同事确认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的易感基因,并进一步将该基因定位于17q12-23。可以说,整个1990 年代到世纪之交,随着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建立,以及一个又一个致病基因的发现,医学界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只要在基因层次确立各种疾病的原因,就能找到彻底治疗疾病的最基本方法。这将是医学界的一次大革命。
纵观现代医学兴起的过程,其主线是把科学的因果解释用于医学的历史。现代医学的每一次大进步,都与某一类病因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现代病因学开始于19 世纪下半叶巴斯德(Louis Pasteur)等人建立的病菌学说。该学说的核心观点是人类的许多疾病均由细菌引起,包括结核病、霍乱等,只要这些细菌被消灭,疾病便可痊愈。这个学说催生了消毒灭菌术的发展和抗生素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临床治疗学和外科手术的进步。到20 世纪上半叶,人们又发现缺乏某种营养素可引起疾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营养性疾病学说,该学说立即促成了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的发现,使得像坏血病及地方性甲状腺肿这一类的疾病得以治愈。这两个学说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使人们更加相信疾病是由单一病因引起,只要去除病因,疾病便可痊愈。疾病发生的直线因果关系是如此的有影响力,以至于今天医学院的老师给学生讲课时还时常教导他们,体内的多重病变最好能用一个病因来解释。
20 世纪50 年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研究使疾病发生的因果探讨进入到更深层面。人们发现,当免疫系统在保护人体免受外源性病原体侵犯时,如果反应不当则会攻击人体自身。这些病包括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风湿热和幼年型糖尿病等。这使医生想到对疾病的因果分析必须深入到身体内部,即从基因水平来寻找病因。人们相信:只要病因研究进入DNA层面,一百多年来对疾病原因的追寻将进入最后阶段。随着终极病因和相应治疗手段的发现,现代医学必将如历史上有过的革命那样再一次大飞跃。
但是从1990 年至今,已经过去20 多年了,我们要问:临床医学对疾病的治疗真的发生了革命吗?没有!究其根源,存在如下三个原先没有想到的问题。
第一是疾病谱的转变。早期各种各样的病毒性、细菌性传染病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包括肺结核、天花等。随着医药的进步,特别是疫苗的发明,人类基本控制住了这些传染性疾病,但疾病谱却发生了转变。对大部分国家来说,目前对人体健康威胁最大的,不再是传染病,而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代谢性疾病(如肥胖和糖尿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如老年痴呆)等。换言之,大多数现代疾病属于慢性病,或者说复杂性疾病,发病不是由单独因素导致,致病因素往往多到难以用因果分析。以高血压病为例,虽然科研人员对其发生机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与临床研究,但至今还找不到确定病因。以肾脏为中心的高血压发生机制及其模型已提出40 多年,许多降压药物都是根据这一机制开发出来的,新近受到质疑;另一个以脑为中心的高血压发病新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其是否正确无人知晓。
第二是检测仪器、治疗手段和病因确定方面的进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过度干预抵消。临床上外科手术属于直接去除病因的治疗手段,本来对于慢性疾病手术并非一定有效。而近三十年兴起的介入疗法是不同于传统手术的介于外科与内科之间的新疗法,它通过直接去除病因,在许多慢性疾病的防治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随着这一疗法的普及,其效果却被过度干预抵消。脑血管介入疗法(支架成形术)即是典型例证,SAMMPRIS研究中,颅内动脉严重狭窄的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受到严格的药物治疗,另一组除了严格的药物治疗外还加上颅内动脉支架植入。研究结果大出人们意料,单纯药物治疗组的结果优于支架植入组!这项发表于2011 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发现,对颅内动脉狭窄的患者,安置颅内动脉支架可能造成的伤害比益处大。因为安置支架引发二次中风的机会,比不安置支架更高。
第三个问题更发人深省。虽然发现了致病基因,但这些基因水平的病因和以前发现的病因却大不相同,它们很难与临床防治挂钩。例如,肿瘤被普遍视作多基因突变的后果。一项采用当前先进的DNA 序列测量技术来研究肺癌细胞基因组的结果显示,在一种肺癌细胞里就存在着两万多个碱基突变。再如高血压病,其候选基因至今虽然已报道150 种,有血管紧张素原基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基因、醛固酮合成酶基因、心钠素基因、内皮型一氧化氮合成酶基因等等,但它们中尚没有任何一个被确认为原发性高血压的决定基因。鉴于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英国《自然》杂志在2008 年6 月刊发的一篇文章提出:“由一种基因导致一类疾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一切向我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尝试用系统医学重新诠释医学的基础,新的生命哲学也将随系统医学的出现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