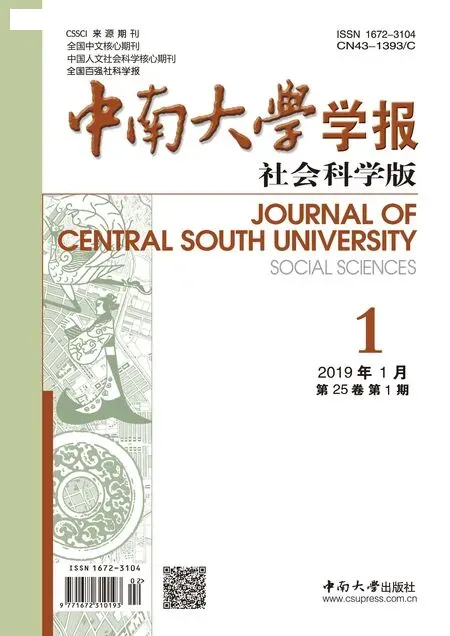徽宗朝丰亨豫大的政治理想与月令的文体新变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月令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经学、史学、文学研究的一大重点。前辈学者如顾颉刚、容肇祖、杨宽等先生,都对月令有所关注①,后代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早期月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受制于对徽宗的评价,以及月令的实用化功能被削弱的整体趋势等诸多因素,学界对于徽宗月令鲜有关注。事实上,作为上古礼仪之一,月令在徽宗朝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徽宗曾多次下诏颁布与月令相关的制度:从明堂的建设到月令颁朔官制的确立,再到对信息传递、信息示民的保障。徽宗试图依托国家制度来推行月令的实用化运转。除此之外,北宋末期的权臣如蔡京、蔡攸、王黼等人对月令布政的强调,亦可视为是对徽宗圣意的迎合②。本文在对月令这一文体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徽宗月令的文体形态,并结合相关史料,探讨月令如何体现徽宗朝丰亨豫大的政治理想。
一、徽宗前月令述略
上古时期,时令观念至关重要,对时令的掌握,有助于先民了解自然的发展规律,并将其运用于农事、渔猎等生产活动之中。上古先民对四季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两种观测方式上,即星象观测和物候观测。关于星象的观测,《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1]对物候的观测,如《诗经·七月》所记载的“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等[2],通过“俯察昆虫草木之化”的方式,达到“知天时,授民事”的目的。两种观测方式各有利弊,相互补充。月令作为较成熟的授时类文体,在二者的基础上做出规律性的总结,以此来依月推演相对应的祀事、农事、政事。
月令,顾名思义,有“月事安排政令”之义,属占候之学。月令通过星象、物候两种观测方式,使先民获取时令讯息,为生产生活提供一定的依据,并将此扩大到“以月系事”的政令上。“观象授时”本是朴素自然主义的体现,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月令能够反映“天时”,故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崇高感与神秘感。战国阴阳家在原有的授时观念中杂入五行阴阳等概念,使月令在指导具体政事活动时拥有了更周密、更全面的理论依据。
(一) 月令文体成熟的标志:《礼记·月令》
一种文体,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之中,往往会存在某一标志性的、为后世传承者奉为圭臬的作品。反映在月令文体上,这一作品便是成于先秦、并被纳入《小戴礼记》的《礼记·月令》。《礼记·月令》的文体体制与语言风格,标志着月令文体的成熟。后世的诸多月令受制于尊经观念的影响,虽在此基础上有所生发,却鲜有质的突破。
《礼记·月令》以月为基本单位,所含13篇月令结构基本相似。此处以其中的《孟春》篇为例,对月令的文体结构加以分析。根据《孟春》的内容,该篇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天象,包括本月的星象位置与太阳位置: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
第二部分为五行,包括本月对应的“帝、神、虫、音、数、味、臭、祀、脏”等诸多要素:
其帝大皞(帝)。其神句芒(神)。其虫鳞(虫)。其音角。律中大簇(音)。其数八(数)。其味酸(味)。其臭膻(臭)。其祀户(祀)。祭先脾(器)。
在这一部分之中,绝大多数要素如“帝、神、虫、音、味、臭、祀、器”是以季为周期而变化的,少部分要素如律、数则一月一变。
第三部分为物象,包括本月的自然物候: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第四部分为人象,包括本月应做之事,往往自天子始,至百姓诸业:
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天子行居)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祀事)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农事、政事、军事等)
第五部分为训诫,言不依照此令行事将会出现的灾害: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3]。
《礼记·月令》以季为单位,每三个月(孟月、仲月、季月)为一周期,构成同月祀事、政令相近的规律(如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均存在的荐庙活动)。除此之外,为了契合五行观,在夏秋之际另有《中央土》一篇,以此将五行的观念与四时观完全对应起来。
不同于战国时期纵横捭阖,富于逻辑,长于辩论,辞采绚然的其他文体,《礼记·月令》的语言风格显得十分古拙,它以平实的叙述语态为主,亦鲜有修饰性文辞。但同时,《礼记·月令》努力构建了一种兼具语义和格式的形式化叙述结构,借由“四时”循环的文义,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在平整的基础上呈现出节奏感与回环性的特征。
(二) 徽宗前其他月令略说
为使徽宗月令符合礼的规范,礼制局在徽宗月令颁布之前便对月令的源流加以考订,通过对比徽宗前历代月令的差异,梳理出月令文体的嬗变轨迹。
议修定时令:“臣谨按《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官》太师,颁告朔于邦国。盖听朔则每月听朔政于明堂,颁朔则以十二月朔政颁于诸侯。又按《周礼·月令》,天子居青阳、明堂、总章、玄堂,每月异礼。然《月令》之文,自颛帝改历术,帝尧正人时,《大戴》有《夏小正》,《周书》有《时训》,《吕氏春秋》有《十二纪》。《礼记·月令》虽本于吕氏,然其所载皆因帝王旧典,非吕氏所能自作也。唐开元中,删定《月令》,国朝亦载于《开宝通礼》,及以祠祭附为祠令。今肇建明堂,稽《月令》十二堂之制,其时令宜参酌修定,使百官有司奉而行之,以顺天时,和阴阳,诚王政之所先也。”[4](1184)
由此可知,前代月令的流变情况除未记为文本信息的“颛帝改历术,帝尧正人时”二者之外,大体依照《夏小正》→《周书·时训》→《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唐月令》→《开宝通礼》一脉承袭而下,但也到了须应时而变、“参酌修定”的时候了。
《夏小正》成书于《礼记·月令》之前,其内容相对完整,可视作月令文体的雏形。《礼记·月令》在《夏小正》的基础上,有三点突破:① 在物候上,加入四时观与五行观念,并生发出五行五色五虫五器等大量阴阳家概念,以此作为一年布政、祭祀等具体活动的理论依据。② 在原有单一授农时的基础之上加入对不同类型职业的指导。③ 物候的内容得以确定,形成了后世所谓的七十二物候。
《周书·时训》《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三者的关系。《周书》(后世称之为《逸周书》)的《时训》篇与其他月令文体差异巨大,考察其言论,此处所言当为《逸周书》的《月令》篇,而《吕氏春秋·十二纪》则具体指《十二纪》的首篇文章。《逸周书》《吕氏春秋》和《礼记》三者的月令之间的承袭关系,学界尚存有争议。就文辞而言,三者的文辞几乎完全相似,除《吕氏春秋·十二纪》缺少“中央土”的内容之外,仅有一些具体的词语存在差异。如在《孟春》中,《礼记·月令》所载为“鸿雁来”,在《逸周书》《吕氏春秋》中则载为“候雁北”。《逸周书·时训》虽与《礼记·月令》之间没有太过直接的关联,但是根据后世月令的特征,可以发现《逸周书·时训》对月令的表现形式确有一定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反映在物候的记载上,《礼记·月令》之中,每月的物候仅依先后次序加以记录,而《时训》之中则将每一种物候的出现时间固定在了该月的某一时刻,形成五日一候的特殊现象。五日一候使得物候与阴阳学的关系更加紧密,但也导致原有物候的授时作用被削弱。
《唐月令》载于《唐书·经籍志》,据《文献通考》所载,为“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注序”[5](5358)。《唐月令》的主体借鉴了《礼记·月令》,仅对其结构内容做了少许调整:一是依据天象将一月的信息按照月初和月中两个时段分别展开论述,并对物候、布政信息进行了相应的分割,使每个部分得以平均分配。二是对天象进行了重新修正,使得星象信息由推演所得改为观测所得。三是对具体条目进行稍许增补,在阴阳上增添了“性”“事”两个概念,在布政上增加了如“祭风师”之类的天子仪制。《唐月令》对天象信息的调整,使其在授时上更加准确。但是由于布政信息主要照搬《礼记·月令》,而周官制度又不复存在,《唐月令》的布政信息不可避免地走向象征化的道路。
《开宝通礼》成书于宋太祖开宝年间,由卢多逊等人依照唐《开元礼》制成,今不存。《朱子语录》曰:“《开宝礼》全体是《开元礼》,但略改动。”[6]《宋史· 礼制》同样有类似的记载:“《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7](2421)故而《开宝通礼》的《月令》篇因袭《唐月令》的可能性极大。《宋会要辑稿》记载:“景佑三年,诏贾昌朝与丁度、李淑采国朝律历、典礼日度昏晓中星、祠祀配侑岁时施行者,约《唐月令》,定为《时令》一卷,以备宣读。而淑定入合仪,异于《通礼》。”[4](2312-2312)可知《开宝通礼》的《月令》篇内容确与《唐月令》存在不同,然二者差距在何处,今已不得而知。
总的来说,徽宗月令之前的月令呈现出三个特征:① 《礼记·月令》在月令体系中具有绝对的影响力。② 布政信息与当朝制度呈现出分离趋势。③ 观测能力的提升使对天象的观测更加准确。与此相反,物候授时功用日渐衰退,物候逐步走向固化,成为象征化的表现方式。
除此之外,话语权的转变同样值得注意。在月令中,天象、物象、人象的顺序,反映了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依时行令的朴素逻辑,强调了对上天的绝对服从。作为早期巫祝文化与天官制度演化出的特定产物,月令的思想与先秦训诫政治及阴阳家理论息息相关,呈现出阴阳家对于诸侯的谏诫性质。“《月令》之‘令’,从文本上来看是阴阳家代天子所拟、对庶民所颁之令,从功能上来看又是阴阳家对君主的‘令’上之‘训’。”[8]这样的效用在秦汉之后随着阴阳家话语权的缺失而不复存在,月令的施行转而成为突出帝王地位,提升帝王天人感应式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完成了由“巫言”向“王言”的转变。
二、徽宗月令的因与变
徽宗月令现收录于《宋大诏令集》中,所涉时间从政和七年(1117)十月到宣和三年(1121)十二月,长达五十三个月(其中包含政和八年闰九月与宣和三年闰五月)。目前仅保留了宣和三年之前的月令,其后四年的月令已散佚不存。徽宗朝明堂持续以月令的方式布政,直到靖康元年钦宗诏罢颁朔布政乃止。徽宗月令在许多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将月令布政重新实用化。
(一) 徽宗月令的突破
徽宗月令针对月令实用化的目的,通过内容细化以及政令与阴阳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许多与前代月令不同的特质。
1.单篇月令的突破
参照《礼记·月令》的基本结构分类,可将徽宗月令分为七个部分,以政和八年四月月令为例。
第一部分为布政位置,包括该月天子布政的背景,包括时间、明堂位置等信息,作发语用途,如:
政和八年四月朔,皇帝御明堂,以是月天运政治布告于天下曰……
第二部分为天象与物象,包括该月的节气、朔日的星象、律,并有节气与物候所现时间,如:
孟夏之月,朔日癸丑,日在胃,昏张中,晓斗中。辛酉、立夏,斗建巳,日在昴,昏翼中,晓斗中,得孟夏之节,蝼蝈鸣,律中仲吕之正声。丙寅、蚯蚓出。辛未、王瓜生……
第三部分为传统五行的信息,与《礼记·月令》的五行部分类似,只不过这一部分并非每月都有,仅在每季孟月出现,如: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色赤,其音徵,其数七,盛德在火。
第四部分为新增的气论部分,包括性、德、政、令、人等。该月含气的转化,以及百姓的病与养,依月用律等讯息,如:
其性暑(性),其德彰显(德),其化蕃茂(化),其政明曜(政),其令热令(令)。其在人也,逆夏气(人)……
是月也,少阴火之位,客气阳明燥金,为清化,为收……(气的转化)。是月也,大凉复至,火气遂抑。民有气郁中满之疾(民病)……以酸补之(养)……
是月也,小满之后,属三气之初……(气的转化)
凡乐之声,仲吕为宫,黄钟为徵,林钟为商(依月用律)……
第五部分为人象,包括本月应做之事,自天子祀事、朝堂政令,至与百姓相关的刑法、农事、税收、诉状、人事等各个方面:
是月也,朔告于庙(祀事)……
是月也,天祺节,有罪毋决三日(刑)……颁时药于五门(医)……申伐木之禁(农)。军马听择官地系荫(军)……夏田应诉灾(诉)……诸州以秋税籍(税)……及吏皂之愿试刑法者(吏)……
第六部分为训诫,言若不依照此令行事将会出现的灾害:
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行春令,则蛙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第七部分为结语,敦促百官与民众共同为之:
於戏!五运之政,其犹权衡,髙抑下举,系之人事。朕奉若时令,以敷锡庶民,尔钦承其无怠[9](440)。
相比前代月令,绝大多数徽宗单篇月令的内容,存在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一月六令的传统不再是定式。由于徽宗月令采用依月颁行的原则,并严格践行五日一候和物候节气相关联的规则,使得徽宗月令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因闰月月令等因素导致物候无法均衡分布在每月之中。
第二,气论被重视并成为五行中的重要内容。前代月令之中,五行与四季的内容是固定对应的,即春与木,夏与火,秋与金,冬与水(中央祭祀与土),天子居行也以此为基础,并配以对应颜色的服饰与器具。而在徽宗月令之中,五行因素受该月阴阳主客之位变化的影响,出现了流动的现象,构成“气论”的主题。
第三,增加了依月用律的内容,并对每月的声律予以详尽的阐释。在月令中,一方面律体现在每月节气所对应的音律中,将前代月令之中律与月的关系调整为律与节气的对应,这一转变,使得律的内容更加细致,也使得律成为构建五行变化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民病”之后增加“凡乐之声”的内容,并详细标明该月所用音律。依月用律之说与大晟乐府所制之律相吻合,故可将其视为大晟乐府乐制在月令之中的体现。
第四,强调月令与民众的联系。在前代月令中,涉及民众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布政上,在五行环节很少,直到唐代月令增添了“性”“事”二义,五行内容与民众才具有了极小的关联。而在徽宗月令之中,不仅对民众诸事的指导更加具体,还不吝笔墨地将涉及民众的内容纳入五行部分,使其成为五行部分的主要元素。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政、令、化、人等五行意涵和民众病与养的内容之中,借由五行的演变,指导该月民众具体的衣食住行,以及该月出现易犯疾病时调理的方法,以达到“五行致中和”的效果。
第五,布政信息的具体化、实际化。《礼记·月令》确定了布政信息中周官的具体职能,这一定式在前代月令中得以固化,导致了月令布政信息与现实官制之间的脱节。徽宗月令一改前代月令承袭周代官制的状态,积极采用宋代官制,通过类似诏令的布政形式来直接指导枢密院、六部等国家机构,以及各地分支机构,为该月所应施行的具体政令提供实际的指导。
2.整体结构上的突破
在整体结构上,徽宗月令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前代月令往往是以一年为周期,故往往由春至冬便结束了。徽宗月令则不然,不算岁运,徽宗月令共计五十三篇,数量是前代月令的四倍多,因年代、撰写人的不同,其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徽宗朝探索月令文体的发展脉络。可将目前所存的徽宗月令划分为四个时期:尝试期(政和七年十月至政和八年元月)、成形期(政和八年二月至重和元年十二月)、极盛期(重和二年正月至宣和二年七月)、衰落期(宣和二年八月至宣和三年十二月)。
在尝试期,月令的具体形式尚未确定,故月令的调整与变动情况也相对较多。依照前文所述,徽宗在拟制月令之前曾召礼制局对月令加以考订,似乎早期月令当从模仿前代月令开始,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尝试阶段,原有月令之中除律之外的五行部分均未载,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气论的描述,如“其位金,其气厥,阴风木五之气,终木火交司,地气始闭”(政和七年十月月令)[9](435);“其位水其气少阴火居之”(政和七年十一月月令)[9](436)。这反映了徽宗月令的重要特征:徽宗月令在创立初期,便不再对《礼记·月令》做单纯的效仿,而是有意识地对自身要表达的内容进行积极探索。
政和八年二月,徽宗月令基本成形。重和二年正月,徽宗月令的内容进一步加强,进入成熟期,具体表现为:在第四部分气论上增加了神、天时的内容,并将其与八卦相关联,如“然其神三风,与司天君棋,同入震宫”[9](447)(重和二年二月月令),使得原有气论更加深奥。与此同时,布政信息更加细化,内容涉及朝野内外的各类日常措施,布政效用达到最大化。
随着江南方腊叛乱,以及徽宗个人关注点向联金灭辽、收复幽云转移,月令与明堂布政逐渐不再受到重视,走向边缘化。宣和二年七八月间,负责颁朔布政的官职被大幅缩减③,从宣和四年王黼所上奏章④可知,宣和三年十月之前的月令被编册上进,暗示月令布政工作的阶段性完成。这一现象,在月令内容的详实程度上同样有所体现:在成形期及成熟期,月令字数在800字左右,后期逐渐缩减到400字左右;除已固化的内容如天象、五行、物候等,月令的其他内容多被省略,特别是布政信息,仅保留了祭祀和少数有规律且无关紧要的政令。月令布政功用沦为模式化的存在。
除此之外,在徽宗月令中还有一些新变化。首先,为了保证月令依月布政的实际需求,徽宗月令在布政过程之中考虑到了闰月布政的问题,出现了闰月月令。闰月月令的结构与一般月令类似,只是在节气上得以顺延,致使物候与所在月之间的关联不再紧密。其次,依月布政的施行,使得一年之中的中央土祀被取消,四季与五行之间的关联开始松动。最后,气运的出现。在每年十月,明堂颁布次年的气运,气运的形式与月令的星象、五行部分相似,立足于来年阴阳之气的变化趋势,配合月令统筹安排信息。
在语言风格上,原有单一平实的叙述风格出现变化。在“於戏”之后,徽宗月令以诏令常见的四六骈化句收尾,骈散有针对性地结合,这使得月令的庄重性与功用性得以协调,也使得月令的文体属性由占候之书进一步转向诏令之书。
作为“王言”,诏令文体有威严与温厚相结合的特点[10],这一特点在徽宗月令的布政内容上同样有所体现。徽宗月令的布政内容往往具有宽严相济的特点,在祭事、政事上,月令语气偏重强硬,且话语具有总揽性,以示皇帝的威严。而在社会福利、宽待囚徒等方面,言语往往事无巨细,如“籍老疾孤幼不能自存,若非游堕而乞者名数,以待施惠”(政和八年十月月令)[9](443)、“颁药役兵以备疾疫”(政和七年十二月月令)[9](437)、“犴狱禁肉给火,假以襦袴”(政和七年十一月月令)[9](436)等内容,以示朝廷对百姓尤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
整体而言,徽宗月令的结构与内容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这使得徽宗月令无法像前代月令那样做到结集颁行,重复使用。这样的特性造成月令内容多样化的同时,也使得颁布月令的权力牢牢把握在中央手中,成为徽宗展示其个人及朝廷形象的一种手段。
(二) 丰亨豫大与徽宗月令中的形象构建
徽宗所构建的政治理想,可以用丰亨豫大一词予以概括。
丰亨豫大之说最早出于政和六年的诏书:
当丰亨豫大极盛之时,毋为五季变乱载损之计[11]。
该诏书被刻石立于端礼门附近,成为徽宗朝的执政纲领。“丰”“亨”二字出自《丰》卦辞,不仅有强调丰盛富足之意,还突出了王者之德、王者之治,并有教化之用。“豫”“大”二字出于《豫》卦,强调圣人顺理而动,在众人悦豫的局面下,警醒有为,化养天下[12],即形成一种圣人在上,大臣在下,天下人和悦安乐的理想成就。丰亨豫大之说,反映在月令之中,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皇权形象的强调。丰亨豫大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的首要前提是君臣各司其职,即所谓别君臣。这一点表现在月令之中,便是对皇权的强调:月令以“天子御……,以是月天运政治布告于天下曰”开头,强调天子在月令颁布中的权威性。同时,在结尾处,采取传统诏令常见的“於戏”作结,将月令的属性变成天子所下达的诏令之一。除此之外,月令中原有的约束天子的话语均被剔除,转而增添了许多如“播告庶邦,无替朕命”(《宣和二年八月月令》)等以帝王口吻敦促百官民众的话语[9](462)。
第二,是对徽宗勤政形象的刻画。徽宗月令通过布政信息,构建了自身勤政、仁厚、治国有方的明君形象。在布政信息中,徽宗诏令往往兼具总揽的视角与温厚的胸怀。对于朝政,其所言往往能总揽全局,针对行政、功绩、人事及具体工作提供纲领性的指导;对于军队,则关注粮草、所训兵役、兵器等与军队活动相关的方面,处处体现出徽宗勤政的形象。关于社会福利方面的布政,则呈现出其宽厚仁慈的贤明君王形象。在月令中常提到的泽漏园、居养院、安济坊,以及对于囚徒居住环境的关心,正是徽宗宽厚形象的直接反映。这样的布政信息,也塑造了祥和安逸的社会形象。对民众的体贴,对人才选拔的关注,以及在布政信息之中多次被强调的社会福利机制,确实体现了《礼运·大同》篇所倡导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政治理想。
虽然徽宗月令是布政官员以徽宗之名代书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徽宗月令在诸多方面呈现出重要的变化,包括对月令内容、表现形式的创新,甚至恢复明堂颁朔布政、推行月令这一行为本身,都无不体现了徽宗个人的意志。
三、徽宗月令的施行及其实际效果
因徽宗月令布政功能的实用化,在其施行过程之中,徽宗制定了大量相关的运行制度,并以诏令或御笔的形式加以宣告,形成了中央布政系统与地方传递系统两大部分。
(一) 中央布政系统
徽宗月令所采用的中央布政系统,即明堂制度。徽宗月令因明堂礼制而兴,也是明堂展示功用的具体表征之一。明堂在中国古代为天子祀天之所,明堂祀与南郊祀并称为两种日常大祀,在历代礼制之中都有延续。然而,除极少数帝王(如武瞾)之外,前代明堂实际上并无实物,明堂祀所往往会依照旧例,在所祀时节选择某一大殿临时行礼,如北宋前期明堂祀所为大庆殿,南宋明堂祀所为教场射殿(绍兴四年、绍兴三十一年、淳熙六年)、常御殿(绍兴十年)和大庆殿(其余时间)。这样虽并不完全符合周制,但是考虑到明堂的使用频率和建筑的用地面积,此法不失为一种折中之选。徽宗朝的明堂祀却并未因循旧例,而是依据周代礼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历经两年建设,在原秘书省旧址上新修明堂。徽宗依照周礼,欲“飨帝、严父、听朔、布政于一堂之上”[9](428),其中听朔布政的载体,正是徽宗月令。徽宗初建明堂,礼制局列上七议,制定明堂礼仪,有三条议论与月令体制存在直接的联系:
二曰:古者天子负扆南向以朝诸侯,听朔则各随其方。请自今御明堂正南向之位,布政则随月而御堂,其闰月则居门焉。
三曰:礼记月令,天子居青阳、总章,每月异礼。请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时令,使有司奉而行之。
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之日。请以每岁十月于明堂受新历,退而颁之郡国。月令记述[7](2771)。
这三条议论分别强调了月令三个不同的内容。第二条强调布政随月的制度,成为徽宗月令布政信息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三条突出月令的礼制要求,确立颁行礼制所在地及其相关礼制、时令分布等基本信息;第四条则阐明每年十月颁布来年诸月岁运情况,以此作为月令的补充。明堂礼仪的制定,为徽宗月令的具体颁行提供了基本指导。
在月令施行过程中,徽宗本人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为方便管理,徽宗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明堂月令的施行。在颁朔制度之中,确立了固定的布政人员:
议差官属“今肇建明堂,统和天人,凡宗祀、听朔、布政、朝会,远法成周之制,欲乞置明堂颁政一员为长,颁事二员为贰,颁朔每方二员,各掌远方之事,以备太平盛典焉。其提举、管勾官,亦令随事置员。”从之[4](1186)。
相关职官的设定,意味着明堂已不再是临时性的仪式场地,而转变为宋代政府发布信息的专门机构。依照宋代职官表,可知明堂布政官员的级别并不高,然而由于月令的内容是以徽宗之名发布,且其背后与蔡京、蔡攸等权臣存在着若干关联,故而月令的布政信息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除此之外,颁朔布政府还有其他办公地点。明堂颁朔布政府位于“宣德楼前,左南廊对左掖门”[13],并将原有其他宋廷机构如“太史局、天文院、崇文台、浑仪”[4](1186)等与月令内容相关的机构纳入其中。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固定机构,从其体系与人员安排来看,徽宗月令已具备了颁政所需的基本能力。
明堂的建立与明堂制度的施行,对于徽宗而言,政治意义巨大。首先,取法明堂礼,兴修明堂的意愿,在神哲二宗时就已出现,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故而可将兴修明堂一举视作绍述父兄之志的外化。其次,建设符合周代礼制的明堂,是对儒家正统地位的尊崇,更是对上古三代的直接继承,成为徽宗展示太平盛世的直接手段。
(二) 地方传递系统
除了中央布政系统之外,徽宗的月令制度尽可能采用既有信息传递系统,并通过惩戒的方式,为月令在全国各地的传递、地方官员的执行和民众的接受提供相应的保障。
徽宗在施行月令过程之中,通过御笔手诏的方式直接介入,以保障月令的传递与下达,以此来促进月令的实际布政功用。
二十一日,诏:“应颁朔布政诏书入急脚递,依赦降法。诸路监司、州县依此。应颁朔布政诏书付吏部,差人吏、工匠、纸札,限一日以事分下六曹,限一日下诸路监司,违者杖一百……施行不如令,加二等,不以赦降原减。”
诏:“颁月之朔,使民知寒暑燥湿之化,而万里之远,虽驿置日行五百里,已不及时。千里上可前期十日先进呈,取旨颁布,诸州长吏封掌,候月朔宣读。”[4](1186)
为了使月令的传递得到保障,徽宗选择了当时传递最重要公文时所用的急脚递。急脚递最快一日可达四百里[14],按照北宋地域大小来算,加上先十日投递的诏令,基本可以保证每一州县准时收到月令。除此之外,在月令颁布过程中,对每一个步骤的时限加以限制,尽可能保持高效。
为了监督和管理月令的颁行过程,徽宗还制定了相关的惩戒措施,如:
应承受颁朔布政诏书,监司随事检举下诸州,州下诸县。牓谕讫,具已施行申州,州申所属监司以闻。共不得过十日,违者杖一百。若检举不以时,施行不如令,加二等,不以赦降原减[4](1186)。
这一措施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惩罚:一是关于颁行不及时的惩罚。由于月令的时效性仅有一月,如果错过颁行时间,月令的布政效果也就不复存在,故而在月令的颁行过程中,及时性成为月令制度关注的重点。二是关于颁行不以令的处罚。月令之中已有不按照月令执行遭受灾难的预测,如果官员不按照月令内容施政便属于知而不为,故在处罚上较前者更加严重。
上文提到徽宗月令多涉及与民众相关的内容,而在布政过程中,为了彰显月令为民所用的目的,徽宗依从朝臣奏议,将月令榜示于民。
提举京西北路常平等事时君陈奏:“共惟皇帝陛下肇建合宫,诞布仁政,每月谷旦行月令以顺阴阳,德至渥也。内以诏书降付省部,外则委之监司、郡守,推而行之,孰敢不虔!然窃考成周之时,凡治教政刑之法,莫不垂于象魏,使万民可观。浃日以敛之,而又设官分职,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臣愚欲乞今后以颁朔布政诏书并昭示于魏阙之下,使民拭目而观,咸知陛下德意。诸路州县集民宣读,悉意奉行,印给黄牓,遍行晓谕。”[4](1186)
通过在都城张贴黄榜和地方集民宣读两种方式,普通百姓也得以有机会了解月令颁行的政策,达到真正意义上布政于民的效果,实现了丰亨豫大政治理想中化育民众的目标。这一举措,在月令发展历史之中可谓绝无仅有。
(三) 徽宗月令的具体实施情况
徽宗的构想,是通过月令的颁布,联结上天与皇权、朝廷与地方、百官与民众,起到顺天之道,化育民众的效用。然而,在实际的施政过程中,因月令布政的形式和政局状态等因素,月令的效果实难如其所愿。
首先,是月令本身存在的缺陷。月令布政的核心,在于依照时令信息,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作为理论根据,并将其细化到颁布各方的政令,以此达到顺天意的目的。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顺应自然的政令似乎确有一定的益处,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徽宗依照月令规律进行布政的构想却并无太大的可行性。
就地理区位而言,北宋所辖地域虽不及汉唐广博,但其面积亦有近320万平方公里,因地理、气候条件的差异,月令所指物候难以与各地尽相符合。假定以天子所居的东京开封府的气候为月令布施的主要依据,那么其与南方诸地的差别是比较大的,王安石即有咏梅诗“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红梅》)之叹。因此,即使将月令张贴于各地,其实际的指导效果却并不能完全契合当地的自然气候。
其次,是月令无法反映突发情况。政和八年闰九月,江、淮、荆、浙、广南、福建诸路发生重大洪灾⑥,粮食无法供应百姓生活已成事实,此时徽宗御笔手诏已多次颁行相关措施,如《江淮荆浙分三等截上供斛斗四十万赈济诏》(政和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监司督责江淮荆浙等路被水官吏劝民还业诏》(政和八年闰九月十一日)等,然而检视该月的月令《政和八年闰九月月令》《政和八年十月月令》⑦,其中非但未涉及救赈举措,连御笔手诏之中所言的缓税政策亦毫无体现,甚至出现了与御笔手诏相冲突的内容,如“圭租给前后官,以所附月为限,场务较租额亦如之”[4](443),要求各地按时纳税。可知月令在面对突发情况时,非但无法提供相应的政策指导,还会导致当地官员面临违御笔与违月令两难的局面。这也说明月令在布政过程中仅能够对具有规律性的、日常的政令加以指导。然而这些政令多为定例,因此对地方官员而言,月令的实际参考价值并不大。
再次,是信息传递系统亦未达到应有的效果。宋代建立了一套相对严密的信息投递系统,然而在徽宗时期,信息传递机构已多有废弛,递铺兵员极度短缺,部分地区不仅缺少应有的马递、急脚递,甚至还出现了因“无人交替铺分”而导致的“致积递角,留滞程限”⑧的现象,各类文书难以准时到达。靖康年间在福建路甚至出现了“有经半月二十日杳无京报”⑨的情况,可推知此时月令准时发往各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宣和元年针对偏远地区颁布月令的时间由提前十日放宽至提前二十日的诏令,亦暴露了月令难以按时送达的事实。
最后,至于前文提到榜示于民的政策,即使在徽宗的诏令之下,京畿官员与地方官员准时完成榜示、宣读等“遍行晓谕”的流程,实际的效果同样不理想。“自崇宁迄宣和,竟恤之诏岁一举之,宣之通衙而人不听,挂之墙壁而人不视,以其文具而实不至故也。”[15]所谓“文具而实不至”,指的是在表现形式上的完备与具体内容的缺失。而标榜模仿周礼明堂制度而产生的、包含大量与阴阳五行相关内容的月令,无疑正是其抨击的典型。民众的不闻不视,使得徽宗月令布政于民的设想成为空谈,其构建的美好愿景也在施行的过程中因种种困难而不得不再度转向原有的象征化道路之上。
四、结论
徽宗月令并非徽宗构建丰亨豫大形象的唯一产物,在徽宗朝大量的改革及具体的政治活动之中,均可或多或少地感受其在形象构建上的尝试。因丰亨豫大这一政治理想主要针对的是皇权、朝臣与民众三个部分,故而其构建的丰亨豫大政治理想往往包括三个主题。
第一,皇权与神权。徽宗朝利用神权的独特地位,大量采用以神明作为他者评论示现的方式,如“神降事件”[5](2219-2220)、“祥瑞事件”[4](2601-2608)等,对徽宗朝特别是徽宗自身的形象加以肯定。将皇权与神权相关联,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帝王执政和改革的权威性,促其摆脱宋代原有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制约,成就徽宗一人独大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神权的示现,本身即是对皇权正确性的嘉奖和肯定,这一点在徽宗降祥瑞的事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通过芝草、九茎、瑞鹤等世不常见的祥瑞作为太平盛世的象征,彪炳徽宗自身执政的贤明形象。
第二,当朝与上古。徽宗朝的改革内容,绝大多数都以上古三代之法作为其模仿和追溯的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上古三代特别是周代,被称为治世贤明的典范。徽宗朝的一系列措施具有象征意义,如铸九鼎、定八宝,官制上的三公三少,礼制上的元圭、政和五礼新仪,乐制上的大晟乐府等,这些制度方式均可以在先秦的经典典籍之中找到渊源。徽宗采取主动学习、模仿上古制度特别是周代制度的方式,试图将当朝与上古三代相联系,做到对上古三代社会的重塑和复现,以此构建太平盛世的美好风貌。
第三,天子与民众。民众虽然地位不高,却是徽宗丰亨豫大政治理想中的重要环节。由于民众是一个颇为广泛而在构建体系之中难见明显成效的群体,因此民众往往充当着目标受众的身份。体现在徽宗丰亨豫大的构建中,主要包含三种模式:① 天子知民疾苦。通过徽宗所设福利机构,解决民众的现实疾苦。② 制度化育,通过种种制度法令,敦促百姓得到教化。③ 天子与民同乐。通过皇帝与民同乐的方式,如中秋赏灯,创作《清明上河图》等行为,共同营造太平盛世下的同乐风貌。
在上文所提及的众多构建活动之中,绝大多数内容往往只涉及上述其中一两个部分,而徽宗月令则不然。月令顺天时的特征,使其具有了神权的特征;月令以及明堂制度所依照的,正是周礼的相关制度;而月令布政于民的政策,更使得月令具有化育百姓的功用。因此,丰亨豫大政治理想与徽宗月令的关系不仅是因果关系,还具有表里关系。丰亨豫大的政治理想,是促成徽宗月令对前代月令做出突破性尝试的内在动因。内容上,徽宗月令正是上述三种倾向中最能够反映丰亨豫大政治理想的作品,成为丰亨豫大政治理想外化的投影。
从宏观的学术视野上看,徽宗月令仍不失为一种将传统经典文体实用化的可贵尝试。徽宗月令不再单纯照搬上古月令的文体样式,而是积极地将现实情况与上古精神加以融合,因势利导地创建符合现实功用的文体形态。但是在月令的施行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月令的实际指导功用,使得月令质朴的哲理观与实际施政内容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徽宗月令最终不得不再度流于形式化。徽宗月令在创新过程中的成与败,对月令文体乃至所有经典文体的重塑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然而,徽宗月令既未被后世月令所继承,亦未引起后世的重视,仅仅活跃了五十三个月便被束之高阁。这样的结局,无疑是徽宗的遗憾,亦是历史的教训。
注释:
① 三位先生对于月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礼记·月令》源流的考订。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 2002年)认为《月令》全为王莽所作;容肇祖《月令的来源考》(《燕京学报》1935年18期)认为《月令》出自战国阴阳家邹衍之手;杨宽《月令考》(收录于《杨宽古史论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认为《月令》源自战国“晋学”。
② 蔡京,王黼事见于《宋会要辑稿》礼二四《明堂颁朔布政》,蔡攸事见于《靖康要录》卷六,七日圣旨条。
③ 宣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诏:“颁政事、颁朔,人主之事,不可以为官称。可减罢颁政一员不置;颁事二员改置司常一员,掌颁朔布政等事;颁朔四员改置司令二员,掌读月令等事。以上并隶明堂颁朔布政府。”八月十四日,诏明堂颁朔布政府详定官并罢。(《宋会要辑稿》,第2 册,第1186页)
④ 四年二月十四日,太宰王黼言:“今编类到明堂颁朔布政司政和七年十月止宣和三年十月颁朔布政诏书,及建府以来条例,并气令应验,《目录》一册,《编类》三册,《岁令》四册,《朔令》五十一册,《应验录》四册,总六十三册,谨随表上进以闻。”(《宋会要辑稿》,第2 册,第1186页)
⑤ 明堂共有十二堂,依照月份的不同,皇帝布政的地点也会转移,由此顺应天象,达到“十二堂以听十二朔”的目的(《宋会要辑稿》,第2 册,第1179页)。
⑥ 内容据《监司督责江淮荆浙等路被水官吏劝民还业诏》,《全宋文》165册,第302页。
⑦ 因月令布政于每月朔日,即每月月初,故其布政讯息往往与前月状况相关。
⑧ 宣和七年四月,翊卫大夫、安德军承宣史、直睿思殿李彦奏:“臣近被奉处分,前去京东路勾当公事,其沿路一带铺分营房并未曾修盖,虽有见管铺兵去处,往往不过两三人传承文字,亦有无人交替铺分,致积递角,留滞程限。”(《宋会要辑稿》,第15 册,第9483页)
⑨ 靖康元年(1126)七月,臣僚言:“窃见兵革未弥,羽檄交驰,凡有号令及四方供应文书,类多急递,今闻畿邑如尉氏、鄢陵等处及京西一带递铺,兵卒类多空阙,而州县恬视不以填补,至有东南急递文书委弃在邮舍厅庑之下数日无人传者,且如福建路有经半月二十日杳无京报。”(《宋会要辑稿》,第15 册,第9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