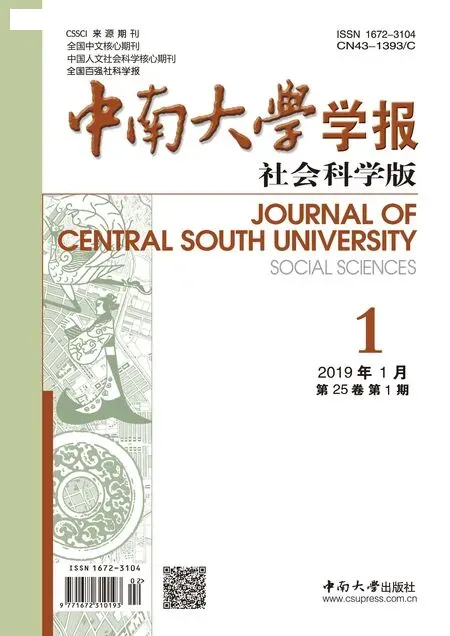论词之修择观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所谓词之修择观,即修订、斟酌填词初稿的观念与方法。“修择”一词出自宋末张炎,“修”即修订、修饰之意,“择”即斟酌、权衡与取舍之意。修择是提升词作质量并使作者能安心脱稿的基本前提。
张炎《词源》卷下云:
词既成……倘急于脱稿,倦事修择,岂能无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协音声。作诗者且犹旬锻月炼,况于词乎
张炎认为词乃美文,比诗歌更讲究锻炼的功夫。他希望词人在完成初稿之后,不要急于脱稿外传,而应悬“全美”为目标,立足通篇,“旬锻月炼”,对词之初稿在意趣、结构、句式、字词、音律等多方面进行反复、长时间的修订,从而全面提升词作的境界与格调。倦事修择者,或矜于一得一隅而忽略缺失与整体,或不明词之高境所在,不知修择路径,难免留下种种遗憾。由张炎之语,可知古人佳词之成,背后竟费如许心力,修择之功,岂能忽焉?
稍检词史与词学史,词在流传过程中的版本差异乃一突出现象,这其中当然有刻工误植错刻的问题,但更多的可能是作者修择其词时,先后有不同的文字版本流出,从而形成一词而多面的情况,由此而衍生出后世的词集校勘之学。这方面见诸词话、词集序跋的记载颇多,大致可见修择的过程及由修择过程所体现出来的修择方法与观念。词之修择与创作其实是一个完整而连续的过程,相关的词体创作论见诸论著的颇多,但对于修择观的研究尚多空白,此亦使得词体创作论欠缺重要一翼。本文因结合修择实践及修择观之发展,提炼其理论与方法,以丰富词学研究之格局,彰显出词之修择观在词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以修择通向经典:文学史上的一种基本事实
在文学创作中,只有极少数灵感突发、天才淋漓的优秀作品因为下笔天成、浑然一体,故往往一经落纸,便难移易一字,才可谓得之乎天、顺之乎心而应之乎手的自然佳作。但这样的创作情形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可遇不可求,无法复制。
昔陆机《文赋》分析创作的两种带有极端性的形态时说: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2](40-41)。
创作若遇天机骏利之时,一切便无施不可,水到渠成,笔下文字的神采可能也出乎作者想象之外;而一旦六情底滞,则理伏思障,文字也枯涩无神。陆机说这种应感通塞的玄机,“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现在我们当然明白前者其实就是灵感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灵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因此这种思维奔涌的创作状态无法长期保持。这意味着大量的文学创作在初稿时呈现出来的心理感觉基本上是“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而已。所以,大多数文学创作的过程除了早期的观察、体验生活,提炼思想和情感,聚焦故事场景和情节发展,构思文章结构和脉络,调动语言资源进行写作之外,还必然包含着初稿完成之后的修改甚至一改再改。这个过程因文体的不同,有时也各有不同,但修改贯穿在各体文学的创作实践之中,已然是文学史的一种基本事实,也是文学理论应予关注的话题。如左思《三都赋》出,洛阳为之纸贵,但那是左思构思十年的产物,其中的反复修订简直数不胜数。《红楼梦》也是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红楼梦》第一回)而成。换言之,其初稿的凌乱无序大概也是可以想象的。若无这样孜孜不倦的修改功夫,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学经典是否还能称之为“经典”,可能就是个疑问。我觉得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会消失在经典之外,还有一部分则要在经典的序列中被打折、被降级甚至被边缘化的。
当然,天赋灵感的好词也是毋庸修改或无法修改的。况周颐描述其从灵感突发到援笔成词,其间有不能自已者,亦如陆机“应感之会”“天机骏利”之时。类此之词,凌空而来,倏然而至,自难再有多少修改的空间了。其语云:
吾苍茫独立于寂寞无人之区,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霭中来,吾于是乎有词。洎吾词成,则于顷者之一念若相属若不相属也。而此一念,方绵邈引演于吾词之外,而吾词不能殚陈,斯为不尽之妙。非有意为是不尽,如书家所云无垂不缩,无往不复也[3](4412)。
如此顺心顺手而来的词,如果强作修改,恐也有“逆心逆手”之讥了。所以况周颐认为“佳词作成,便不可改”[3](4415),所谓“佳词”应该就是在上述情境中创作出来的作品。
一般来说,长篇作品因为关合人物、情感与场景过多,需要费力修改,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若诗词之修改,即便是篇幅稍长的慢词,也不过一二百字,当然无须动辄以数年之力营营于此。若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之类,应该是非常极端的例子了。但修改的事实也一直伴随着创作过程。参诸文学史,改词之例开卷可见,改词之形也多种多样。毕竟,词的产生还多是“构思”的产物,而一经构思,便往往难臻完美,所以改词乃是词人创作的常态。而从创作观念上而言,古人多重名句,一篇之成常因一二名句而起,但并非一篇之中杂有一二名句便足以振起全篇,所以有名句而无名篇的现象便比较普遍。词人当然能意识到这种全篇不平衡的现象,有此意识,自然也就有完善之心,修改之举因此也就成为一种自觉。胡仔说:
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如贺方回“淡黄杨柳带栖鸦”,秦处度“藕叶清香胜花气”二句,写景咏物,可谓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4](167)。
既然全篇皆好之例极为难得,所以修改之心简直贯穿在词人创作的全过程。词至宋末,创作盛极而下,富艳精工愈成风尚,词艺之讲究也日甚一日,故嘱咐或教人改词也为理论家所重视。张炎即说:
词既成,试思前后之意不相应,或有重叠句意,又恐字面粗疏,即为修改。改毕,净写一本,展之几案间,或贴之壁。少顷再观,必有未稳处,又须修改。至来日再观,恐又有未尽善者,如此改之又改,方成无瑕之玉。倘急于脱稿,倦事修择,岂能无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协音声。作诗者且犹旬锻月炼,况于词乎①
张炎在此并非就具体的修择来谈,而是就填词的一般情形来言说修择的必要性。按张炎此节意思,大致有四:其一,诗词都是需要深加锻炼的艺术,而词比诗更讲究修择;其二,填词的最大追求就是“全美”,使作品成为“无瑕之玉”,故修改是达成艺术精品的必经途径;其三,修改非一时一日之事,而是反复多日甚至经月之事,不能稍改即安,因为每一次关注的重点可能不同,所以相应的修改也各有笔墨;其四,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前后之意是否连贯、意思是否重叠、字面是否粗疏、音律是否和谐等方面。可见琢磨修改是词稿初成之后的常规工作,因为文学既悬格甚高,则必多遗憾之事,如此数四取改,也是尽力弥补缺憾之意。是否能因此臻至“全美”,自然难说,但追求“无瑕之玉”之心倒真是词人应该具有的。姜夔在《庆宫春》小序中言此词创作因缘,赋写初稿后“过旬涂稿乃定”,可见其用心耽意,真有不能自已者。
二、宋人改词之范式与类型
宋人改词之例甚多,有据音律改者,有据句法改者,有据语意改者。有的随作随改,有的事后再改,有的奉请词友修改。总之不惮修改,以求完善,此亦在在可见宋人尊体之心。据音律改者,张炎《词源》即曾数举其例。张炎言其先人晓畅音律,故其《寄闲集》一编缀以音谱,但这是定稿之后的情形。而在定稿之前,张炎先人“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张炎这样说是有证据的,他将其先人《瑞鹤仙》按之歌谱,声字皆协,但“粉蝶儿、扑定花心不去,闲了寻香两翅”二句中“扑”字稍有不协,故改为“守”字。虽然扑字可见动态,守字仅见静态,情境尚有不同。但词在当时以音律为先,音乐性的强调仍是第一位的,虽不免偏至,亦可见用心。又举其《惜花春》之“锁窗深”句,因为“深”字不协音,所以改为“幽”,“幽”字也不协,再改为“明”字,直至协音乃止[1](256)。细勘其改字之迹,以“幽”改“深”,大意尚存,而以“明”易“幽”,则一反其意。看来改词中的换意虽不一定出乎本心,但也是难以避免的。
宋词音律大概在北宋后期即多凌乱失序者,即便如曾任大晟府提举的周邦彦也被张炎认为“于音谱,且间有未谐”[1](255)。美成尚且如此,何况他人!而到了宋末,音律问题已经到了非自学而能,而需要专人指授的地步。张炎甚至说:“若词人方始作词,必欲合律,恐无是理……今词人才说音律,便以为难。”[1](265)沈义父说:“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5](281)这说明至少从北宋后期开始,不合音律的词作便较为常见,而音律之误正需要修改时一一勘察才能发现并逐一加以纠正。沈义父说:“初赋词,且先将熟腔易唱者填了,却逐一点勘,替去生硬及平侧不顺之字。久久自熟,便觉拗者少,全在推敲吟嚼之功也。”[5](284)正是侧重在音律问题的推敲修正上。所以据音律改词,应该是宋代比较普遍的现象。
宋末人对词之音律的感觉如此相似,说明对声律的蒙昧确实导致了不少词作不协音律,这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宋末词人周密曾填西湖十景词,其小序云:
西湖十景尚矣。张成子尝赋《应天长》十阕夸余曰:“是古今词家未能道者。”余时年少气锐,谓此人间景,余与子皆人间人,子能道,余顾不能道耶,冥搜六日而词成。成子惊赏敏妙,许放出一头地。异日霞翁见之曰:“语丽矣,如律未协何。”遂相与订正,阅数月而后定。是知词不难作,而难于改;语不难工,而难于协[6](3264)。
周密“冥搜六日”,词方成,可见构思之苦。即便如此,霞翁也一眼识出其多未协声律处,而订律用时数月,可见斟酌之难。周密因此而深悟“词不难作,而难于改”的道理。另有一种改字只是出于叶韵的考虑。如陈师道《浣溪沙》上、下阕末句分别为“安排云雨要新清”“晚窗谁念一愁新”。据王灼说,上阕末句原是“安排云雨要清新”,“以末后句‘新’字韵,遂倒作‘新清’”[7](93)。这是典型的据韵改字。
据语意修改者,多属自改。如苏轼《蝶恋花》“绿水人家绕”,有见真本者,“绕”原作“晓”,两者意思明显不同,或苏轼初稿写就后,再据意斟酌用字[8](31)。原本不传,而改本却广为人知了。自改句或句段之例,也颇常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
贺方回《石州慢》,予旧见其稿,“风色收寒,云影弄晴”改作“薄雨收寒,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箸,向午滴沥檐楹,泥融消尽墙阴雪”改作“烟横水际,映带几点归鸿,东风消尽龙沙雪”[7](90)。
这是王灼亲见贺铸稿本《石州慢》,再对勘流传本,发现了这一改句和句段的情形,很显然流传本用的是贺铸后来的改本。情景变化虽然不大,但在意象选择上,从“风色”到“薄雨”,从“云影”到“斜照”等,相关的变化还是明显的。尤其是后面句段的修改,把原本比较单一的对冰雪消融的描写转变为将冰雪置于更广阔、更灵动的背景之中,显然更具情感张力。
有的改词是因为原作描写对象过于宽泛,而在调整了咏写对象后,需将旧词作比较多的修订。如黄庭坚年轻时写过一阕茶词,乃泛咏茶与饮茶之事,调寄《满庭芳》,原词如下:
北苑龙团,江南鹰爪,万里名动京关。碾深罗细,琼芷冷生烟。一种风流气味,如甘露、不染尘烦。纤纤捧,冰瓷弄影,金缕鹧鸪斑。 相如方病酒,银瓶蟹眼,惊鹭涛翻。为扶起尊前,醉玉颓山。饮罢风生两腋,醒魂到、明月轮边。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9](141)。
但据说后来黄庭坚又增损其辞,专咏福建建瓯之贡茶,改成如下:
北苑研膏,方圭圆璧,万里名动天关。碎身粉骨,功合在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梦、开拓愁边。纤纤捧,香泉溅乳,金缕鹧鸪斑。 相如虽病渴,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便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妆残[9](141)。
两词相较,完整保留的仅有“碎身粉骨”“纤纤捧”“金缕鹧鸪斑”“醉玉颓山”“归来晚”等寥寥数词、数句,大段已是经过修改。吴曾说,经此修改,“词意益工”[9](141)。此当然是他个人感受。值得注意的是:今本《山谷词》所收《满庭芳》此词,字句又有差异,当是后来又加修订的了②。其中既有恢复稿本者,如末句“相对小窗前”,也有与此前两本均不同者。宋人词话中关于黄庭坚改词之例颇多,当是其勤于改词、精益求精而广为人知的缘故。如其当涂解印后所赋《木兰花令》便有两个版本,两本下阕基本相似,仅过片有一字之异,而上阕已是全然不同[9](147)。
在宋代改词之例中,还有因传唱节拍需要而由歌者擅加之词,此可不论[8](46)。另有一种改词乃是借他词以自用,因此必须稍加点窜,以切合情境,并非为求原作精进而修改。如北宋时有一妓易欧阳修《朝中措》数字为某相寿,将“文章太守”易为“文章宰相”,将“看取衰翁”易为“看取仙翁”[8](47-48)。凡此属于临时性、功用性改词,带有游戏性质,也可不论。
三、近代改词之风与况周颐等修择观之形成
近代改词之风亦如前代。如郑文焯改词便甚勤,一稿而有三四易者,更有初稿仅剩一二句,几乎通首另作者。朱祖谋也曾有一词作后数年又取改数字的情况[10](4594-4595)。陈蒙庵《我所认识的朱古微先生》一文提及朱祖谋生平最后一首词作《鹧鸪天》(忠孝何曾尽一分)手稿时说:“朱先生在他原稿上面的‘身后’‘水云身’‘词人’,几个字旁边,都加上一个三角的符号,意思是‘不妥帖’,‘字面重复’,要加以修改了,终于是在作词的几天以后,便与世长辞,来不及再改了。”[11](9)可见无论是初习填词者,还是一代词宗,改词几乎是通贯一生之事。此皆自改之例。也有敦请词友修订者,凡此皆求精粹其词而已。陈蒙庵曾回忆说:
他(按,指朱祖谋)自己填词,绝不肯轻易的下笔,一年做不到几首。当他填一首词成功,就跑到况先生那里,写了出来,先说:这个字不好,那一句不对,你看怎样?你替我改。于是况先生改了,推敲着,吟哦着,那读词的声音,很尖锐,使着长腔,抑扬顿挫,非常好听……过几天又来商量了,却添上了张孟劬(尔田)先生的改笔,仍是不满意,结果等定稿出来,全不曾采用。却是撷取众长,重加镕铸,自然他的词集里,没有一首不是绝妙好词[11](11)。
作为晚清四大家之一,朱祖谋填词饶有声名,犹且精谨如是,此在在可见修择之与创作的重要意义。修择之例既多,自然会引起词论家的注意,所以况周颐说:
佳词作成,便不可改。但可改便是未佳。改词之法,如一句之中有两字未协,试改两字,仍不惬意,便须换意,通改全句。牵连上下,常有改至四五句者。不可守住元来句意,愈改愈滞也[3](4415)。
这是从方法、结构上言明改词、改句、改多句的重要性,因为原词未佳,改词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从况周颐的叙述来看,以改字这种小改为最好,但完全契合的改字,料多困难,故改字若未稳,只有换掉原意,这就不是更改几个字能解决的了,很可能全句要重写。而一词之中的句子,往往彼此牵连,若一句整体改换,意思不同,若在通首词中意脉贯串,便须将其前后数句均作改易,如此方能使修改后的词不至于意脉阻断、旁逸甚至彼此矛盾。这就涉及意思的连贯和结构的平衡等问题,即如张炎所说:
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衬副得去,于好发挥笔力处,极要用功,不可轻易放过,读之使人击节可也[1](258)。
所谓“拍搭衬副”,其实就是强调在一阕之中“牵连上下”的重要性。如果说改字的初衷尚在守住原意的话,改句便开始动摇原意,至改动四五句,则基本上是新创意思了。所以从改字到换意,是况周颐改词理论的基本格局。
弟子赵尊岳深得乃师况周颐心意,其《填词丛话》云:
改一句或尚非难,独求一字之精当,实不易易。因之往往以改一字而改一句,或且连改数句者,求其理脉之顺,不当惮烦。理脉所系,实即在此一字。既不当犯前后凌杂之弊,又当使韵稳神洽,恰如分际,诚不易措手也[12](2768)。
将赵说与况说对勘,很明显,赵尊岳实际上把况周颐之说予以了理论提升。况周颐主张先改字,改字未惬再改句,再开展结构上的前后牵连,因此很可能一改就是四五句,因为改动甚大,故意思转换也就变得十分自然。赵尊岳则认为改字难于改句,因为通过一字之变化,仍要维系理脉自然、神韵自如,并非易事,而改句尤其是改多句则几乎重置理脉,自然受限少而发挥多,相对容易多了。赵尊岳从“理脉”的视角看待改字、改句问题,显然更具理论眼光。
改词看上去只是一种方法和实践,其实背后支撑改词的是词体与词学观念。王国维曾用“要眇宜修”作为词体的基本审美特征[13](211)。词体的意思精微与形式美赡,都意味着关于词的斟酌修饰是词体题中应有之义。况周颐曾引用王鹏运之语云:“恰到好处,恰够消息。毋不及,毋太过。”[3](4408)况周颐又以数则敷衍了这一理论,他反对词“过经意”,也反对“过不经意”,前者为的是避免斧琢痕,后者是为避免“褦襶”之讥,即草率、乏分寸感,不合体之意。故填词过程中的用心斟酌是况周颐要求的,并主张斟酌后的审美效果不见斟酌之痕。
但况周颐承王鹏运提出的填词要介于“过经意”与“过不经意”之间,并非只是一种中庸的做法,其实是主张在自然中有创新的。他曾明确说:“填词之难,造句要自然,又要未经前人说过。”[3](4410)这意味着这种看不出经意痕迹的修饰,不是为自然而自然,而是以创新为基本前提的。但况周颐也很清楚,自唐代以来,佳作如林,天然好语几乎用尽,哪里还有现成的供后人驱遣呢?为此,况周颐主张只有依托性灵和书卷,方能有创新出奇之处。而在性灵与书卷二者之间,则以“吾心为主,而书卷其辅也”[3](4411),书卷的作用主要是使词的语言更便捷、更精准、更有感染力。
如此讲究的填词高境,自然难以一笔而成,修改也因此成了填词完成的一个必经过程。况周颐主张修改,是因为在他看来填词境界高低不同,如何由低到高,自是可以通过努力和修改渐次提升的。在况周颐看来,凝重中有神韵是词中第一境,其次则虽神韵欠佳,但凝重中有气格,再次则轻倩中有神韵。其语云:
填词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所谓神韵,即事外远致也。即神韵未佳而过存之,其足为疵病者亦仅,盖气格较胜矣。若从轻倩入手,至于有神韵,亦自 成就,特降于出自凝重者一格。若并无神韵而过存之,则不为疵病者亦仅矣。或中年以后,读书多,学力日进,所作渐近凝重,犹不免时露轻倩本色,则凡轻倩处,即是伤格处,即为疵病矣。天分聪明人最宜学凝重一路,却最易趋轻倩一路。苦于不自知,又无师友指导之耳[3](4409)。
简单来说,况周颐反对作聪明人词,轻倩看上去悦目,其实往往格调不高。天分不够的人难以悟及于此,而天分高的人又往往对“轻倩”情有独钟。面对这种因作者不自知而误入歧途的情况,师友的指导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填词境界既有此高低不同,相应的学词程序也必须讲究章法。况周颐曾明确开示学词程序云:
词学程序,先求妥帖、停匀,再求和雅、深(此深字只是不浅之谓。)秀,乃至精稳、沉著。精稳则能品矣。沉著更进于能品矣。精稳之稳,与妥帖迥乎不同。沉著尤难于精稳。平昔求词词外,于性情得所养,于书卷观其通。优而游之,餍而饫之,积而流焉。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掷地作金石声矣。情真理足,笔力能包举之。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则沉著二字之诠释也[3](4409-4410)。
很显然,学词程序与填词境界级差是逆向而行、由易到难、渐趋深沉的。这层意思,用况周颐的话作另一番表述就是:只能道第一义——意不晦,语不琢——不求深而自深。其语云:
初学作词,只能道第一义,后渐深入。意不晦,语不琢,始称合作。至不求深而自深,信手拈来,令人神味俱厚。规模两宋,庶乎近焉[3](4410)。
所谓第一义,也就是浅表单一意义。职是之故,况周颐一反张炎③、王国维不主张联句、次韵等,而是主张“初学作词,最宜联句、和韵”[3](4415)。何以在他人郑重所言之填词之忌,况周颐要反之以谓“最宜”呢?这与况周颐立足“初习”填词这一阶段性有关。联句、和韵往往须承他意,作为练习,乃是操练文体感觉而已。况周颐也说选择联句与和韵,原因是“始作,取办而已,毋存藏拙嗜胜之见”[3](4415),这意思说得足够清晰。初习词,只是熟悉文体规律、培养语感、句感,即便承袭他意也无妨,毕竟是初习而已。
从况周颐对凝重、沉著、不求深而自深的追求来看,语意的丰富、潜隐、深刻是其对填词的最高要求。“词贵意多”[37]是他明确提出的主张,但他反对以重复来呈现虚假的“意多”。其语云:
词贵意多。一句之中,意亦忌复。如七字一句,上四是形容月,下三勿再说月。或另作推宕,或旁面衬托,或转进一层,皆可。若带写它景,仅免犯复,尤为易易[3](4415)。
当然况周颐也有退而求其次的要求。但这些不同要求为况周颐改词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因为进阶宛然,故改词的路径自然也是清晰的。其弟子赵尊岳深明乃师之意。其《填词丛话》卷四云:
改词之法,无论师友研讨,或自窜自订,首当求平贴易施,再进求精稳。其能于精稳之外,别立新意,而又不蹈纤佻者,更擅胜场[12](2768)。
赵尊岳的改词之法与况周颐的学词程序正相对应,可见改词正是一个不断提升填词境界的过程,不必斤斤于一字一词一句之义,而要立足整体词境。因此,在这样的观念中,改词其实也成为创作的重要一环,起着提升词境的重要作用。“规模两宋,庶乎近焉”,路径虽有差异,方向则在两宋之间,这是况周颐非常明确的填词方向。
在具体的改词方法上,况周颐提出了“挪移法”。他说:
改词须知挪移法。常有一两句语意未协,或嫌浅率,试将上下互易,便有韵致。或两意缩成一意,再添一意,更显厚。此等倚声浅诀,若名手意笔兼到,愈平易,愈浑成,无庸临时掉弄也[3](4415-4416)。
这显然是更进一步的改词之法了。除了两句前后互换,可能别出韵致,但此需要妙心体悟,且此上下互易,也必然存在格律字词的调整。至于压缩两意、更添一意,则是提高词境的改词之法了。陈匪石云:
炼句本于炼意……意贵深而不可转入翳障,意贵新而不可流于怪谲,意贵多而不可横生枝节,或两意并一意,或一意化两意,各相所宜以施之。以量言,须层出不穷;以质言,须鞭辟入里。而尤须含蓄蕴藉,使人读之不止一层,不止一种意味,且言尽意不尽,而处处皆紧凑、显豁、精湛,则句意交炼之功、情景交炼之境矣[14](218)。
陈匪石此论本于其师瞻园,并作了点化,虽然未必是从改词角度来说的,但将创作构思中的斟酌之方包蕴其中,其实也有斟酌乎词前的意味。陈匪石在这里提到的“句意交炼”其实是改词的不二法门,而“情景交炼”只是随之而成而已。而意贵深、新、多之论,与况周颐所论如出一辙。陈匪石要求的意思紧凑、层进层深,也与况周颐的词学观念彼此呼应。
炼意涉及意境,而情景交炼有关结构。这当然是改词的高境,蔡嵩云笺证《词源》论改词一节云:
词之修改,不宜专重字句,尤须兼顾意境与结构。孙月坡《词迳》云:“词成,录出黏于壁,隔一二日读之,不妥处自见,改去。仍录出黏于壁,隔一二日再读之,不妥处又见,又改之。如是数次,浅者深之,直者曲之,松者炼之,实者空之。然后录呈精于此者,求其评定,审其弃取之所由,便知五百年后此作之传不传矣。”此论改词,较玉田又进一层说。“浅者深之”四语,极修改之能事。惟浅、直、松、实四病,犯者每不自觉,且其病在骨,又甚于字面粗疏、句意重叠或前后意不相应者,故既改之后,犹恐或有未妥,必更求精于此者评定。倚声小道,其难如此[15](162)。
可能需要说明一下,蔡嵩云引述孙月坡改词之论,并非针对常规填词情形,而是悬词作五百年后是否能流传这一创作高境和理想而言的,故才反复黏壁、审读、修改,再请高手评定,以精益求精。若每词如此,恐也不胜其烦矣。在孙月坡之论的基础上,蔡嵩云提出词之修改首重意境与结构,其次才是字句斟酌的问题。字句方面表意粗疏、意思重复、前后意错位甚至矛盾等,属于很基础的问题,如沈义父《乐府指迷》特别提及的情形:
甚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秋,如《花心动》一词,人目之为一年景。又一词之中,颠倒重复,如《曲游春》云:“脸薄难藏泪。”过云:“哭得浑无气力。”结又云:“满袖啼红。”如此甚多,乃大病也[5](281)。
蔡嵩云当然部分认同沈义父的观点,也认为《花心动》“病在前后意不相应”,《曲游春》“病在前后句意重复”[15](70)。关于词意忌复问题,况周颐也曾再三强调。他说:
词贵意多。一句之中,意亦忌复。如七字一句,上四是形容月,下三勿再说月;或另作推宕,或旁面衬托,或转进一层,皆可。若带写它景,仅免犯复,尤为易易[3](4415)。
况周颐开示了多种避复之方,或推宕,或衬托,或转进,目的当然是厚其意蕴,灵动其词,但如果为避而避,带写它景,犯复之弊虽免,而枝蔓之意又起,殊非填词正道。此类问题当然不独词体所有,文学之事大抵如此。所以蔡嵩云同时认为,这些问题只是相对而言的。他说:
其实月与雨,春与秋,虽非同时所应有,然作追溯已往或预想将来语气,则咏月说雨,咏春说秋,有何妨碍?至同一事物,在一词中固不宜颠倒重复,使作者工于换意,一说再说,未尝不可。如美成《瑞龙吟》起句“章台路”,已暗伏“柳”字,中间“官柳低金缕”,则明点“柳”字,结句“一帘风絮”,仍收到“柳”字,何以不见其重复?但觉脉络井然,极情文相生之妙。即由工于运意所致。名家词中,此例甚多,难以枚举[15](70)。
蔡嵩云真是别有巨眼者,在他看来,前后句意思是否彼此相应或者重复,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关键是这种现象背后是否有脉络支撑。如果作者善于换意,则咏月说雨、咏春说秋,完全是可以的,何况在时间上既可以追溯过往,也可以预想未来,则在这种时空转换中表达自己的独特之意,即便在现象上存在矛盾,也不妨碍作品的魅力。至于重复,就更要视结构脉络、情文关系而论,他以周邦彦《瑞龙吟》一词为例,说明名家名作,一阕之中数度重复,但因为工于运意,所以不见其重复。所以是否相应与重复并非裁断词高低的充分依据,关键在作者换意、运意水平的高低。应该说,蔡嵩云所论确实更见理论魄力和眼力。
修改词的目的在于提升作品的整体质量,所以蔡嵩云提出的“意境与结构”便是着眼于词的整体目标而提出的改词方向。具体路径则是浅者深之,直者曲之,松者炼之,实者空之,形成整体上含蕴深厚、婉转凝练、脉络有致、清空有神的境界。蔡嵩云认为孙月坡论改词较张炎更进一层,确实如此。其实,况周颐所论似也未及于此。当然这也可能与况周颐无意多论改词理论有一定关系。
由以上对况周颐、赵尊岳、蔡嵩云等人修择理论与修择方法的勾勒来看,在长期词之修择实践的基础上,晚清民国的一些词论家开始提炼归纳出颇为完整的词体修择观,他们不仅在字词句篇等方面提出了不少修择的方法,更因为有借助修择以提升填词之意境、结构与格调之目的,而将修择与经典的关系予以全面衡量,故这一时期的修择观其实已经成为创作论的一部分。尤其是民国时期,私相传授填词之法,成为一时风尚,如况周颐等填词名家,便多因倾慕而师事者,其弟子如赵尊岳、陈蒙庵更成为此后词坛有影响力的人物。故况周颐之修择观不仅具成体系的理论形态,也当有丰富的修择实践作为基础,并由此演绎其理论。中华书局2016年影印、梁基永辑录之《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一种(与《陈蒙庵批校白石道人歌曲》并《纫芳簃词》《纫芳簃琐记》《纫芳簃日记》三种合为一册影印),况周颐对陈蒙庵填词月课的批点痕迹便昭昭在焉。结合词学修择观的发展,以及况周颐在《蕙风词话》等著作中表述过的修择理论与方法,再对勘况周颐所批点之月课,正可由此揭示久被词学史冷落的关乎修择理论与实践的话题。
注释:
① 关于改词情形,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也有类似表述:“一词作成,当前不知其何者须改,粘之壁上,明日再看,便觉有未惬者。取而改之,仍粘壁上。明日再看。觉仍有未惬,再取而改之,如此者数四。”见《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594页。
② 今本《山谷词》之《满庭芳》云:“北苑春风,方圭圆璧,万里名动京关。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捧,研膏浅乳,金缕鹧鸪斑。 相如,虽病渴,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为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全宋词》第一册,第386页。
③ 按,张炎只是反对强和人韵,如原韵较宽,则赓歌无妨,若韵险则以不和为好。参见张炎《词源》卷一,《词话丛编》第一册,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