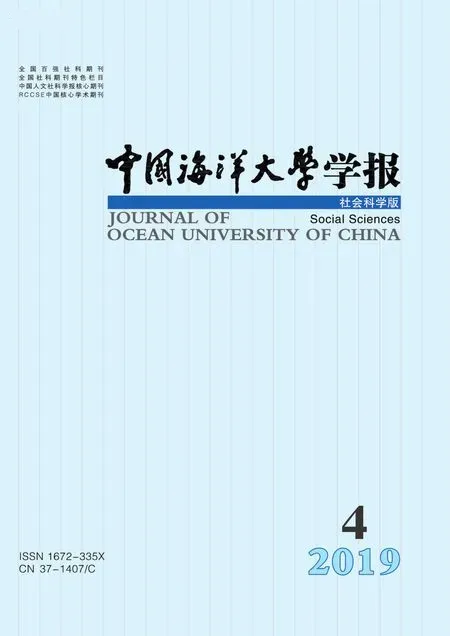《米格尔街》的记忆与身份认同
刘 爽 庄 静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2001年,V.S.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印度裔的奈保尔生于英国殖民时期的特立尼达,后留学英国,又广泛游历中东、非洲等地,多元的身份背景和开阔的视野使他的作品犹如万花筒般繁复。奈保尔的许多小说都带有“伪自传”的性质,但文中的“我”作为叙述者,并不与现实中的作者完全重合。他只是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投射到自己的作品中,想象出一个全新的人物,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正如弗南德兹所说:“一个人讲自己的经历,那是自传;一个人想象出一个人物来向我们讲他的经历,那就是小说。”[1](P20)
奈保尔的成名作《米格尔街》由17个短篇故事构成,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讲述了处在英国殖民和二战期间美国入侵的双重背景下,殖民地人民疯癫狂热又乏味沉沦的生活。文中有贯穿全篇的人物“哈特”“埃多斯”和“我”等,但每个独立的篇章又有单独的人物。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是殖民背景下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米格尔街”在外人看来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们宗主国所处的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2](P18)比本土文明有着更先进的知识。“知识意味着超越一时一地,超越自身的局限,向遥远的、陌生的领地推进”,[2](P40)面对高级知识的推进,特立尼达的原住民们有的自我放逐、自暴自弃,让自己彻底“失语”;有些人积极改变自己的处境,具有独立的理想和行动力,但身份重构的过程却归于失败。这些人物的命运互相交织,使得《米格尔街》的记忆既诙谐生动又充满虚无。由此,奈保尔在重返童年记忆空间的写作中,构建起后殖民文学“自我-他者”的叙事再现。
一、臣服:自我认同的消解
《米格尔街》的生活记忆展现了两方面的文化“消解”:其一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丧失对本土文化的认知,使得民族文化消解,完全沦为西方文明的奴隶,在西方文明中迷失了自我;其二是当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正面冲击时,不知如何抉择,“臣属民族自身没有能力认识对他们来说什么是好的”,[2](P46)左右摇摆以致失掉两手文化,最后彻底失语。这两方面的文化“消解”都使得文化夹缝中的主体丧失对自我身份的认知。《鲍嘉》中的主人公鲍嘉、《直到来了大兵》的爱德华均属于前者,《谨慎》中的博勒便属于后者。
姓名往往是确定一个人主体身份的符号。起初《鲍嘉》的主人公无人在意,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米格尔街上的人对他的称呼是因为电影和纸牌,他的身份和精神状态表现出离散和虚无。这个被“我”视为“最百无聊赖”的人,却以走私和开妓院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然而,在以先进文明为代表的警察、法官、医生和市政要员眼里,生意红火的妓院老板鲍嘉只不过是跳梁小丑。鲍嘉被接受自己贿赂的警察罗织罪名,抓了又放出,他在米格尔街上来了又走,走了又回,沉浮不定。人物身份姓名的神秘、结局的未知,使《鲍嘉》这个故事充满神秘和不确定感。面对各方面比特立尼达更发达的美国,文化水平低下的鲍嘉接受的都是西方负面消极的感官文化,说话行为粗鲁野蛮,口音彻底美国化,竭尽酗酒、打牌、赌博之能事。以前的鲍嘉是安静的让人感到乏味的性格,如今的鲍嘉完全丧失本性,成为米格尔街上最让人害怕的人。原本无名无姓,来源结局都成谜的鲍嘉,代表一种文化身份无根基的存在形态,在向西方文明趋近的过程中自我消解往往是最迅速的。
二战期间,英国殖民特立尼达的同时,美国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上建立了二百多个军事基地,直到1970年才撤除。《直到来了大兵》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主人公爱德华是被先进的美国文明彻底同化的代表,他比鲍嘉更进一步臣服于西方,同时也是被西方文明愚弄的对象。“政治上的困境导致了美学的困境和表达的危机:找到操另一种语言和干着明显殖民主义勾当的敌人很容易,但当自己方面的人代替敌人干了这些勾当,他们同外界操控势力的联系就十分的难以表述了。”[3](P442)过去的爱德华沉稳乐观,热爱绘画,和街上的同伴一起挖蟹,虽然没有什么大志向,但多才多艺充满童真。直到美国入侵特立尼达,用丰厚的报酬诱惑这些“未开化”的人,爱德华就是其中之一。从此在他心里对特立尼达的文化和人民只有否定,甚至将自己在特立尼达的失败都归咎于它的落后和野蛮。他完全沉浸在美国文化中寻找自己,进行自我重塑,迷恋又疯狂,他急于摆脱落后贫困的出身,梦想完全成为纯正的美国人。“他们在现代世界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价值仅仅因为那些强大的、现代化的帝国有效地使他们摆脱了衰落的悲惨境地,并且将他们转变为重新焕发出生机的、具有创造力的殖民地。”[2](P43)在完全接受美国文明的爱德华眼里,米格尔街是衰败之地,并会继续衰落下去,充满着牛臊味儿,这里没有可以理解他艺术境界的人,甚至连这里的女人也没有美国女人那么时髦、高级。在美国人那里工作的爱德华,找到了新的、刺激的生活乐子。他夸赞美国电影院的巨大屏幕、用朗姆酒去讨好美国人,甚至娶了一个美国妻子。而在他眼里高级、时髦的美国女人,实则与西方消极文化同样具有欺骗性。曾立志不碰女人的爱德华被自己臆想中的完美女性抛弃之后,选择离开家乡,自我放逐。先进的美国文明与衰败的米格尔街文化,都没有使爱德华获得身份认同感,自我放逐意味着文化归属走向虚无。
博勒在《米格尔街》中,是另一类悲剧性人物的代表。他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渗透,也没有在本民族文化中找到依托,一个原本可凭手艺安然度日的理发师,不断在现实的漩涡中挣扎,直至精神崩溃瓦解。博勒是现实和自我无法契合的悲剧。不相信战争的结束,“失踪的球”从来没有中奖,“建房互助计划”的泡汤,想去委内瑞拉却被自己的同胞欺骗,生活的种种愚弄使得博勒日渐疯癫。起初,他是个怀有单纯梦想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单纯也意味着软弱,他将自己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寄托在投机性的事件上。生活中经常性的失望和欺骗,一步步逼迫他与现实世界分离,变得疯疯癫癫,他开始挑剔地选择亲自动手理发的人——“必须是自己喜欢的”,即使中了彩票也不再去相信,甚至将自己谋生的小推车砍得稀烂,最后自我封闭,待在小屋里每月只出门一次。一个原本具有清晰身份感的理发师,在反复的自我否定和被否定中,走向了身份认同的虚无。
“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利,正如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葛兰西将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称为文化霸权。”[2](P9)殖民者为满足自身经济、文化利益的要求,既强迫本土人民付出自己的体力劳动,也将自己的文化推而广之,在意识形态上加强控制,实现文化霸权。在二十世纪前期,特立尼达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是非集权社会的典型,社会文化作为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点是破碎的,生活在“无根文化社会”里的人们就无法找到自我身份的基点。米格尔街就是这样一个“无根文化”的社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如爱德华、博勒、鲍嘉,都是无法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牺牲品,他们不仅在地缘政治上处于边缘,还在精神上从边缘跌落,成为没有文化根基的边缘人。
二、反抗:身份重构的无望
“东方将极大地扩展至伊斯兰教地域之外。这一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在世界其他部分不断进行探索和扩张的结果。”[2](P151)和早期英国殖民地埃及、印度一样,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特立尼达也被纳入“想象的东方”之中。米格尔街的居民在“被想象中”重构自己的身份是艰难的,在重构的过程中障碍重重,甚至得不到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国家承认,失败仿佛是注定的归途。米格尔街故事里的人物,除了“我”依靠行贿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其他一起成长的同伴反抗西方文明的自我斗争均以无果告终。
《乔治和他的粉红房子》中的伊莱亚斯,他是摆脱原生家庭寻求身份重构的底层人物的代表。伊莱亚斯和米格尔街上大部分的孩子们一样善良纯洁,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没有理想可言的特立尼达他有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医生。伊莱亚斯的原生家庭是西方文明社会人眼中落后贫穷的代表,而所谓先进与落后显然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的。《只是为了,爱,爱,爱》这篇故事的结尾提到上流社会白人女性的生活:“克里斯蒂安尼夫人,或者说赫瑞拉太太,穿着短裤短衫,正坐在花园里的一把安乐椅上看报。透过敞着的门,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仆人正在准备午餐。车库里有一辆黑色轿车,新的,很大。”[4](P130)反观伊莱亚斯的母亲,“乔治的妻子几乎总在牛棚里面。……儿子伊莱亚斯长大后,乔治就更多地打女儿和妻子。”[4](P18)在充满暴力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伊莱亚斯想要拿到出色的成绩,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渴望从殖民地一文不名的底层人物一跃成为上流社会的医生,为自己构建一个新的身份,摆脱西方文明定义中殖民地人愚蠢、无知和缺乏理想的偏见。但寻求新生活的必经之路仍然要靠英国人的一纸文凭,一次次考试碰壁使得伊莱亚斯被迫面对现实,驾起了清洁马车。与伊莱亚斯试图凭借知识改变命运不同,《懦夫》中的“大脚”比佛希望依靠力量寻找出路。在成为拳击手后,比佛受到了一个英国人的挑战,这个英国人自称是皇家空军拳击赛的冠军。他接受挑战却遭遇惨败,更令他悲哀的是,他输给的不过是一个在拳击领域名不见经传的英国人。比佛无法通过体力成为一名真正的拳击手,在力量强大的宗主国面前,米格尔街的比佛重构身份的梦想不堪一击。
伊莱亚斯依靠知识、比佛依靠力量,二者寻找出路均未果,而华兹华斯则想要成为一名诗人,从诗歌中获得表达自我的权利。《B·华兹华斯》中的诗人华兹华斯准备用27年的时间做一首能够唱到全人类心里的诗,他出场的身份是个乞丐,自己构建的理想身份是一位诗人。为了遇到一位知音,华兹华斯到处兜售写有自己诗歌的纸片,但是没有人与他产生精神的共鸣。米格尔街上也只有“我”这个单纯、未经世事的小孩,才会跟着华兹华斯这样的乞丐领略所谓“诗”的美好。在故事最后,诗人园子中的灌木都被砍去,只剩下水泥和砖块,“就好像B·华兹华斯先生从未出现过。”[4](P54)这个故事充满了魔幻的色彩,可以为一切事物哭泣、做任何事都像第一次的诗人,带着没有完成的诗歌同生命一道逝去。华兹华斯的故事表达了殖民地人民的理想和重构身份的困局不会受到任何关注的可悲境地,恰如伊莱亚斯无法通过英国人的考试成为医生,华兹华斯也无法通过写诗成为一名诗人。
伊莱亚斯、比佛、华兹华斯的生活图景都是米格尔街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身份重构不仅依靠社会群体的支撑,还要从组成社会整体的个体——家庭来寻找出路。传统意义上,家庭对个人的成长除了最基本的性别定义和经济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家庭会塑造一个人的社会行为、观念并构建其身份。《母性的本能》中的女人劳拉,生活没有正经的经济来源,与七个不同的男人生了八个孩子,她不仅尽力喂饱她的孩子们,还让大女儿罗娜跟着塞克维尔街的一个男人学习打字。“世上没有什么比教育更重要,我可不想让孩子像我这样生活”。[4](P100)劳拉将重构罗娜身份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试图打破殖民地女性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的困境。然而罗娜是在母亲不停地与其他男人生孩子的环境中成长的,后天教育的力量没有抵抗住来自家庭环境根深蒂固的影响,罗娜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母亲曾走过的道路,最终在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中投海自尽。孩子们通过家庭得来的基础认知是落后的,劳拉通过教育改变孩子卑微身份的幻想破灭了。“相对于第三世界男性而言,妇女更是遭受殖民文化的压抑。妇女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她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力,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大的反证”,[5](P498)在殖民环境中,劳拉只有通过不停地生孩子实现自我认同,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母亲。劳拉的情人纳撒尼尔总是说:“女人就像母牛,她们和母牛一模一样。”由此可见,女人在第三世界的殖民国家中只不过是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眼里的生育工具,在这种社会文化和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女性最终也无法重构自己的身份。
三、出走:冲出困境的曲折
西方文明的入侵使得第三世界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界限日益模糊,生活在殖民地的人们失去了文化依托。殖民地的人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无法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也不知该如何选择以何种身份重构自身,他们既不能完全投入西方先进文明的怀抱,又不能完全回归殖民地的野蛮文明。对于宗主国来说,他们是落后的殖民地,应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爱德华就陷入了西方文明的漩涡,最终被外来文明吞噬;对于自身来说,在抗拒西方文化入侵并勇于接受外来文明的挑战时,又悲哀地发现外来文明已无法挽回地渗透到落后殖民地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有人想冲破西方文化的藩篱,对自己身份进行重构时,同族人给与的不是掌声,而是嘲笑与漫骂。“大脚”比佛就是同族人无知嘲笑的牺牲品,乞丐华兹华斯向“我”兜售他写的诗歌,同样遭到“我”母亲的痛骂。他们既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社会,也无法在这片文化类型多元、种族成分复杂的土地上实现自我认同和身份重构,殖民地重建文化话语的道路注定是曲折漫长的。
国家阶级结构的稳定、把握政治的主动权是文化独立的前提,“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6](P216)只有在稳定的社会文化群体中,人们才能在获得外界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西方先进文明向世界各地的推进,背后有强大稳定的帝国政府的支持,政治困境导致了殖民地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困难,以致无法把自己的个体身份与当时混乱的社会阶级自洽。不稳定的政局环境导致西方文明不可遏制地控制了殖民地的文化表达权,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宗教文明,米格尔街的人们在辨识西方文明时也表现出无知盲从,无法用个体的独立意识做出选择。
《曼曼》中主人公曼曼是米格尔街上公认的疯子,大家都不敢靠近他,喜欢参加政治选举是他的怪癖,“每逢选举,不论是市镇议会选举还是立法机构选举,他都要参加,而且总要在选区各处贴上宣传海报,海报印刷得很考究,上方总是那句‘投票’,下方则贴着他的照片。”[4](P37)每次选举结束,曼曼固定得到三张选票。“我”的朋友哈特推断,投票给曼曼的都是和曼曼一样的疯子。曼曼不仅戏谑政治选举制度,还公然挑战宗教,他手持《圣经》用纯正的英国口音给大家布道,“他越是吓唬大家,大家越是愿意去听。”最后,曼曼决定要上十字架,像《圣经》中的耶稣为人类牺牲一样,让人们用石头砸他。就在大家都认为曼曼不仅已经成为了一个好人,甚至要成为一名圣人的时候,曼曼对着所有朝他扔石头的人破口大骂,原来这一切都是曼曼自导自演的一出玩笑,米格尔街上的人都成了他愚弄的对象。当局把这个愚弄大众,亵渎宗教权威的疯子永远监禁了起来。曼曼导演的这两场闹剧,透视出特立尼达社会人们对政治的戏谑和对宗教信仰的盲从。人们眼里的“疯子”曼曼,反而是政治与宗教“觉醒”的第一人,懂得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明白宗教给予的教育力量。永久地被囚禁,成为一个隐喻:无论是政治氛围还是文化信仰,都难以让夹在西方文明和本土文化中摇摇欲坠的米格尔街人走出身份认同的困境。
《米格尔街》是以“我”长大后的视角,根据“我”对米格尔街的回忆创作的小说。“我”的身份背景是复杂的,血统为印裔,生于特立尼达,有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背景,后来得到奖学金去英国留学深造,离开了米格尔街,在西方接受先进文明的熏陶。米格尔街在“我”童年的回忆中充满了新奇和冒险,“我”整日和哈特等伙伴一起厮混,听过形形色色的故事,见过脾性迥异的人,成人之后,见到了更大的世界,“米格尔街”这个色彩斑斓的万花筒逐渐褪色了,“开始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人。我不再希望今后成为埃多斯那样的人了。他太瘦弱,……泰特斯·霍伊特也是又笨又乏味,没有一点意思。一切都变了。”[4](P192)从前米格尔街上发生的充满噱头风趣的故事、有话题的人在“我”眼里都变得鄙俗不堪。
通过母亲的贿赂与父亲的关系,“我”永远地告别了米格尔街。“我”对米格尔街的童年回忆,不仅是“我”生活过的足迹,同时也是“我”的故土受到殖民侵略的历史记忆。通过“我”的视角,回溯生活在米格尔街上的人们经历的种种遭际,那些戏谑、冷静甚至带有童真的叙述,却将米格尔街居民的精神破碎、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迷惘和身份重构的挫败一一展现了出来。“我”,这个在“贫民窟”米格尔街上长大的“野孩子”,凭借去西方学习药剂学的机会,完成了社会身份的重构。在离开故乡时,“我”始终没有再回望过它。空间的断裂意味着一种决绝,预示着殖民地人民走出自我身份认同、进行身份重构困境的最终归途。但文学叙事本身又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换言之,后殖民时代的文学记忆,不仅仅拘囿于辨识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情状,更重要的社会命题在于如何解决自我与他者的冲突,实现自我身份认同,走出身份重构的困境。
《米格尔街》的故事用简单的笔触描绘了殖民地人民千姿百态的生活。每个简洁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米格尔街被殖民后文化的破碎,人们寻求身份认同、进行身份重构的渴望。这些生活在殖民地底层的人们面对西方文明的压迫,或与之搏斗抵抗、两手空空成为精神的无根者,从而丧失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无法重构新的身份;或全盘接受、彻底洋化,在西方文明里迷失自我。在精神创伤如此深重的社会里,进行自我身份认同和身份重新建构固然困难重重,但他们必须前进,用法侬的话说:他必须继续前行,直至找到未来知识出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