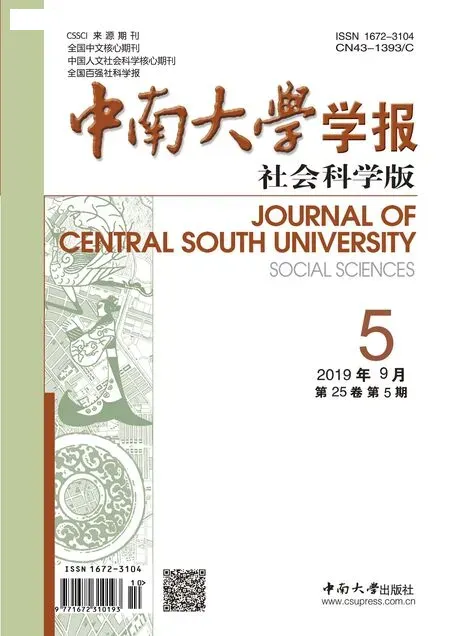《燃脂余韵》与民国的女性词批评
习婷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燃脂余韵》①共六卷,以清代女性诗批评为主,而涉及清代女性词的材料约五十七则。数量虽不及诗评多,却足以从中窥见民国女性词批评的部分特征。《燃脂余韵》(1914)成书早于雷瑨、雷瑊的《闺秀词话》(1916)、况周颐的《玉栖述雅》(1932)等专门的女性词话,手眼亦高于杨芬若的《绾春楼词话》(1912)、无名氏的《闺秀词话》(《时事汇报》本,1913),可谓是民国女性词批评的奠基之作。《燃脂余韵》先后发表于民国时期两本重要的杂志——《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作者王蕴章同时又是两本杂志的主编。新的传播载体与作者的新身份都使得《燃脂余韵》成为考察民国女性词批评新变的重要切入点。
一、《燃脂余韵》以前清代女性词的批评
清代郭麐的《灵芬馆词话》、丁绍仪的《听秋声馆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以及谭献的《箧中词》都有诸多摘录及评点清代女性词人词作的内容。此时的女性词批评既有历代女性词选、词评中存人存词、以德评词的传统,也有在词派理论渗透下,对女性词审美特质的提炼与规制。
《灵芬馆词话》是清人词话中较早关注同时代女性词人的著作。郭麐论及女性词人十余位,其中李纫兰、杨芸、孙云凤、孙秀芬被视为清代中期女性词坛的翘楚。丁绍仪在《国朝词综》所录五十余家闺秀词外,增补一百七十余人。在此基础上,还列二十八家“尤隽峭者”于《听秋声馆词话》中,为之张目,更推杨芸、李纫兰为“闺词之冠”[1](2710)。相较之下,陈廷焯、谭献二人的笔墨则精简得多,他们的评点主要集中在徐灿、贺双卿、吴藻三家。陈廷焯《词则》中则涉及对赵我佩、李纫兰、孙云凤、张玉珍等几位闺秀词的批点。至于女性词人的高下次序,陈廷焯云:“国朝闺秀工词者,自以徐湘蘋为第一。李纫兰、吴蘋香等相去甚远。”又云:“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蘋。明末叶小鸾,较胜于朱淑真,可谓李、徐之亚。”[1](3895)陈廷焯心目中的女性词史轮廓可见一斑。
郭麐、丁绍仪、陈廷焯、谭献等人拣选载入词史的女性词人不但名单不一,而且对她们的词史定位分歧也较大。此皆因各人所持评判标准不同。被推为浙中之首的孙云凤词,郭麐云其“清新婉美,在梦窗、竹屋之间”[2](708),梦窗、竹屋乃姜、张之羽翼,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1](255)。郭麐旨在称赞孙云凤词炼字炼句、能去俗去靡,臻于清雅。除孙云凤之外,孙秀芬、李纫兰以及杨芸词都擅长描摹景物,能做到细致入微、出语新隽而有清气。郭麐对于清丽的写景之作情有独钟,并从情感的角度区分四人词作的高下。其评孙云凤词“清丽芊绵,而寄意杳微,含情幽眇,置之《花间集》中亦当在飞卿、延巳之间”[3],评价最高。“《生香》一集与《琴清》相伯仲,而幽抑缠绵,似复过之,漱玉未能专美于前也”[1](1522),他认为李纫兰稍胜杨芸。孙、李的略胜一筹皆因含幽抑之情的缘故。但“飞卿、延巳”之比,恰说明郭麐对于词作情感的理解是就词体本色而言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幽婉悱恻之情。郭麐的评判标准是缀情入景,使景物的描绘有实在之意义,从而摆脱纤巧轻浮。但情感仅点缀于景物中,其力度与表现不能破坏“清丽”的整体风貌。因此,感情深挚的贺双卿词,郭麐评之“哀艳动人”,却并未推为审美范式。郭麐赞孙云凤词“清丽”、沈榛、蒋纫兰词“清绝”,丁绍仪谓杨芸、杨琬词“轻清婉约”,都表明浙派审美的焦点在于女性词的“清”美特征。
以陈廷焯为代表的常州词人抛出了一份与浙派截然不同的女性词坛点将录,列徐灿为榜首。陈廷焯谓徐灿词“神味渊永”“感慨苍凉”(《词则》),谭献云徐灿的《踏莎行》“芳草才芽”词“兴亡之感,相国愧之”[4](2959)。可见,陈廷焯、谭献等人都认为徐灿词跳脱了闺房儿女的爱恨情愁,抒写着更为深广的现实生活,有着如男性词一般的深稳沉著、格老气苍。又如《永遇乐》“无恙桃花”词“外似悲壮,中实悲咽,欲言未言”[4](2960),潜气内转、吞吐有致的笔法带来了沉著持重之气格,“有唱叹之神,无堆垛之迹”[4](2310),因此陈廷焯反复强调徐灿词“笔意在五代北宋之间”(《词则》)。再反观孙云凤词,陈廷焯云其“似马浩澜一派,然语却聪明”[4](2557),认为孙云凤不过似马浩澜“多丽辞”(《词品》语),构思虽新颖巧妙,但缺乏骨力与根基。即使孙云凤被郭麐誉为“梦窗、竹屋之间”“飞卿、延巳之间”,但南宋之丽、花间之艳仍然不及北宋浑然天成的自然与厚重和雅的气貌。质言之,陈廷焯既从格调、气貌、笔法等方面肯定了徐灿词的成就,也树立了女性词厚重典雅之轨范。
厚重来自浓郁情感的积淀。陈廷焯评吴藻的《浪淘沙》“莲漏正迢迢”云:“此亦郭频伽、杨荔裳流亚。韵味浅薄,语句轻圆。所谓隔壁听之,铿锵鼓舞者也。”“韵味浅薄,语句轻圆”都直接指向浙派“清空”之旨所引起的词情不足的弊病。陈廷焯认为:“蘋香词可取者如《河传》……自写愁怨之作,宛转合拍,意味甚长。”[1](3898)陈廷焯认为词首先必须有情,但陈廷焯、谭献所云之情不同于郭麐所谓的本色之情,而是指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情。谭献云双卿词“忠厚之旨出于《风》《雅》”[4](2960),较之郭麐的“哀艳动人”指涉已经十分明显了。其次,女性词情感抒发应以“一唱三叹,极其缱绻”(《词则》)的纡折吞咽法出之。陈廷焯云:“双卿词怨而不怒,可感可泣。吴蘋香则怨而怒矣,词不逮双卿。其情可悯则一也。”[1](3944)同样是可悯之情,“怨而不怒”方是正途,这样才能做到“悲怨而忠厚”。“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才是常派衡量女性词的准绳。
在《燃脂余韵》以前,清人词话中的女性词批评对清代女性词人的词史地位做了基本的勾勒,也以浙、常两派的词学观念为透视点,形成了“以清为美”与“悲怨忠厚”两种审美主张与论词取向。但郭麐、丁绍仪、陈廷焯、谭献等人对于清女性词的批评仅限于其词论、词评中的极小的部分,所见不广,所论不多。到了清末民初,在女性词人持续增多的情况下,女性词集也得到了整理。比如,1896年徐乃昌校定梓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这不仅使百家闺秀词的完整别集得以浮出历史地表,也有数家零散词作被另辑于《闺秀词钞》。这意味着,此前受资料的限制,词评家偶尔为之的女性词批评即将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建立在丰富的文献基础上的全面观照与评价,这无疑是推动女性词批评的重要一步。另一重要的变化则是,民国女性词批评不再依托个别词评家的个人著作,而有了报刊、杂志这样传播甚广、互动频繁的新载体,这使得女性词批评被置于一个更为开放的场域,被赋予除文学批评之外的更多功能。
二、《小说月报》的旧文化立场与《燃脂余韵》的尊体之道
1910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小说月报》,由王蕴章出任主编。或出于网罗更多读者的考虑,栏目设置略显驳杂,有“小说”“笔记”“文苑”“改良新剧”“新智识”“译丛”等。然而登载古体诗词的“文苑”在《小说月报》中还是显得突兀。恽铁樵②从主编的角度对此作出了解释:“文苑中之诗词,虽非小说,然小说与文学为近,敝报诗文,又太半出自闻(文)人,于此文敝之世,广为传布,俾青年知国文之高者如此。虽敝报不足言兴废继绝,抑亦保存国粹之一道也。”[5]恽铁樵一语道破了《小说月报》保存旧文学、旧文化的用心③。旧体诗词成为需要存续的国粹,其中也包括女性的旧体诗词。王蕴章说:“风雅道衰,至今而极。矧在闺帏,尤如星凤。”[6]为了重现风雅、接继道统,对女性旧体诗词也要“阐扬幽隐”,广为流布。民国初年女性诗话、词话频见于报刊,或亦受这一风气的影响④。
《燃脂余韵》就是在这一背景中诞生的。或者说,《燃脂余韵》同样有保存国粹与继承风雅的目的。1914年《小说月报》开辟“诗话”栏目,连载《燃脂余韵》。《小说月报》的宗旨是“移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7]。《燃脂余韵》当属“缀述旧闻”的部分。从发表在《小说月报》的两卷多内容来看,王蕴章并没有把这部清代女性诗话写成纯理论性的著作,而是注重故事性。他或写一门风雅,或写伉俪深情,或写红袖添香,或写闺中题画酬唱,或写名家奖掖推许。他笔下的女性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家庭、家族、文学群体乃至社会的成员而存在。丰富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多种人物之间的互动展现了女性作家鲜活的生活画卷。在王蕴章看来,填词赋诗的贤妻、良母、淑媛、红颜是文人生活的增色剂,伉俪唱和、闺秀酬唱、姑嫂谈诗都是风雅韵事。他的钦羡与向往之情是在在可感的。《燃脂余韵》所记录的文坛掌故都是旧文化生活的缩影,而“断自清初,以迄近祀”的取材既反映了王蕴章对旧时代的缅怀,也传递出时势或易而“风流未歇”的讯息。
女性旧体诗词在民国初年的地位得益于保存旧文化与旧文学意识的高涨,但并不意味着其被接受也是顺理成章的。由才德之争引发的女性写作诗词的正当性问题始终是古代女性文学批评史上的焦点。1915年,湖南浏阳含章女子初高等小学校长李素筠说:“闺阁之英,操觚弄翰,徒以吟风弄月为事,无暇及此(文字之学),更可想而知矣。此一女界之大厄也。”[8]康同薇则说:“夫海内淑秀,知书识字者非无其人也,然其上者,则沉溺于词赋,研阅于笔札,叹老嗟悲之字,充斥乎闺房,春花秋月之辞,缤纷于楮墨。其尤下者,且以小说弹词之事,陆沉于其间。”[9]同时期还有刘纫兰的《劝兴女学启》曰:“当世女子……其上者,批风抹月,弄草吟花,写妖艳之词,发言情之句,拾李易安之唾余,采朱淑真之遗沉,自以为椒花柳絮,绝擅高才,向不知其流于淫佚之道,娼妓之流,濮上桑间,何以异此。”[10]女性写作诗词第一次受到来自同性的公开质疑,甚至否定。当然,诗界革命与先觉女性以书写现实、抒发政治革命热情的诗暂时回应了来自同性的拷问。但是,标举旧文学的王蕴章如何化解女性词所面临的“淫佚之道,娼妓之流”的指责,则是他的《燃脂余韵》要考虑的。王蕴章的写作策略是接续浙、常两派“清”“悲”两大传统女性词学观来推尊女性词体。
王蕴章在《历代两浙词人祠堂碑记》中描述了他对“词境”的理解,他对“寥廓”“萧简”词境的具体描绘与抽象体悟都明显带有浙派“清空”词旨的痕迹。他曾言:“浙派词滥觞于竹垞,极盛于樊榭,再传而为枚庵、频伽,南宋风流,稍稍衰矣。而婉约清空,不失为词坛健者。”?论及周济的《宋四家词选》时,他也说“以白石附庸稼轩,论者不无微憾”[11](791)。由此足见“清空”在王蕴章心目中的分量。王蕴章论女性词“清”的词学语境是十分鲜明的,他明确女性词人与浙西词派的师承、家学渊源,如言《梦影词》“渊源浙派,刻意清新”,赵我佩“秋舲先生之淑女也。世其家学,所作以清圆流丽见长”,《衍波词》“清圆流转,出入于频伽、忆云二家,附庸浙派,当之无愧”[12]。他更将郭麐、丁绍仪提出的女性词之“清”美内涵进一步具体化。
“清”是以清雅的意象营造清空之境。清疏淡宕的山水之景与“清”之词境自然相宜相称,但女性词多写闺情闺致,生活所及、视野所限多为闺阃、庭院,意象绮巧软媚,词亦容易流于浓腻纤弱。因此王蕴章尤为强调女性词应有“吹气如兰”的清丽,而非“揉脂弄粉”的浓艳,“绮丽之思”要“以清隽出之”[11](649)。女性词避腻趋清,除了有意甄选雅致的意象、避免堆砌外,更应使词意清晰明畅,以此来增强词的骨力。
闺秀作词,多工小令。小令篇幅短小,蕴意精微,故易做到清婉。但长调合谋篇、用笔、运气于一炉,还需以典故来充实词意,闺人往往才学不足,难成长篇,遑论清空。然也有如何桂珍《莺啼序·和梦窗〈荷花均〉》被王蕴章评为“感事伤时,清空如拭,出自闺帏,允称难得”[13]。何女史的《莺啼序》之所以“清空如拭”,得益于典故的恰当运用。何词皆用熟典,密集的典故不仅没有遮蔽词意,反而创造了更为深广的意蕴空间,留下驰骋想象的余地,做到“空诸所有”,以虚写实,借故实隐射时事。何词亦出语古雅,以健笔直书之。情、事线索分明,夹叙夹议,脉络井井,气韵贯通。熟典、雅语及直笔共同成就了其词的“清空”之貌。
王蕴章对“清”的认识还在于音律的清圆流丽。他自称“最爱”吴藻的《浣溪沙》:“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几秋声。”重复的双音节词汇,将词意贯穿一气的同时,增强了律动,从而呈现出清脆爽朗、畅达流利的乐感。这应该是王蕴章尤为称赏的原因之一。又如赵我佩词《鬓云松》:“钏金松,钗玉溜。新月如眉斗。数尽迢迢良夜漏。梦也难成,梦也难成就。绿荫肥,红雨瘦。春去天涯,人去天涯久。客里伤春兼病酒。花似当时,人似当时否。”这首词韵脚密集,再加上反复的叠句,使得词声如贯珠,是以被王蕴章选录。其他摘录的词作也透露出此中消息。
清空之论原是浙派借以纠正明词绮艳之弊的尊体之途。王蕴章藉清雅之意象、清晰之命意、清空之词境及清丽之词韵涤荡女性词绮艳、浅俗、轻浮、浓郁的脂粉气,可谓是对症下药。而与朱祖谋等人的交往,又使得王蕴章汲取了常州词论的养分。王蕴章强调:“诗词之作,本乎性情。”[14]“本乎性情”,一谓切己,二谓真实。王蕴章更为关注的是女性诗词中所表达的凄切悲怆的身世之感。姚栖霞十七而夭,弥留之际写下的诗句,王蕴章谓“读之殊堪肠断”。丁月邻、许孟珠两母女“两世才媛,一则茹荼尝胆,霜辛苦酸;一则白发青裙,笔耕烟耨。亦可伤也。”[15]从中皆可见王蕴章对女性生命之脆弱、生活之艰辛的同情与痛惜。而其所评如:叶慧儿《珍珠帘·咏孤雁》“凄楚之音,令人酸鼻。嫁数年而寡,此词若为之忏矣”;顾贞立《浣溪沙》“皆幽咽哀断,令人不忍卒读”;吴香轮《青玉案》“抑何凄戾乃尔”;陆芝仙《乳飞燕》“声情激越,抑何其言之悲也”;浦合仙《临江仙》“凄艳动人”[15]。这些评价或写女词人身体之病痛,或写精神之孤独。王蕴章通过评点女性词,表达了对种种关于个人命运的省思与喟叹的关切。
王蕴章着意彰显凄悲之作,并不是因性情之故。性情分正邪,情绪有悲喜。闺人之作稍涉情事,极易流于轻佻、冶荡,甚至淫亵,连乐府之清新自然也难以做到。王蕴章自言不录“吟风弄月”的“浮靡艳荡”之作,就是有意摈弃了因感情欢娱而容易被误解为轻浮孟浪的作品。厚重沉痛的情绪于增加女性词的情感分量有益,故而,王蕴章鼓吹悲音悲情,旨在帮助女性词摆脱香艳纤弱的习气。
而感情之重只能重词之貌,若无骨力振起,则或板滞,或凄厉。因此,王蕴章为女性词的悲情注入了更为深厚的内涵。“诗词皆切戒无谓而作。弄月吟风,言之无物,虽不作可也。诗有诗史,……词亦有词史,词至于史,而其道始尊。”[16]词可以反映社会现实,女性词也是如此。女性词不仅可以容纳“己饥己溺”之悲,也可以承载女性的家国之叹、盛衰之感。“宗周嫠纬之思,未必便有此事,却不可不有此志。”[11](657)女性词中忧时念乱的现实关怀不仅是从一己之身的安稳与哀乐出发,也有着家国一体、由己而家、由家而国的眼界与胸怀。如评武兰仪“殉庚申之变,故所作诗词,类多凄恻云”[11](695)。又如评关锳的《蝶恋花》曰:“三事大夫,忧生念乱,其作于粤氛渐逼时乎?”[11](752)王蕴章的评点显然也乐于去点明女性词中的家国意识与现实情怀。
“清”与“悲”是女性词的两大显著特征,经浙、常两派的提炼与恢张,尤为泾渭分明。王蕴章论女性词的清美宗尚是受浙派宗风的浸润,而悲情寄托则带有明显的常派印迹。但他将风貌之“清”与音情之“悲”并举,并不强分轩轾。调和浙、常两派,或者说以浙、常两家词论核心主张施诸女性词,更深层的目的则在于从风格与内容两方面将女性词纳入正统词学,从而推尊女性词体。这是王蕴章在坚持旧文化立场的《小说月报》里所坦露的文学选择与姿态。
三、《妇女杂志》的妇德观与“温柔敦厚”之词旨
如果说《小说月报》的旧文化立场与王蕴章的旧词学尊体之举解决了女性词在文学领域存在的合理性问题,那么《妇女杂志》时期的《燃脂余韵》则需要回应其在新时期面对现实的必要性问题。
1915年,王蕴章应商务印书馆之请,创办《妇女杂志》,其发刊辞阐明了杂志的宗旨,即培植女学。王蕴章认为“女学”的内涵应该是“淑慎虔恭”的中馈之德与“明诗通书”的文艺之才,德为体,才为用。贤妻良母品质是妇德之核心,因此,他在“论说”栏目中刊登阐明贤妻良母教育的言论。第一期的“发刊辞”中题为《敬述吾家旧德为妇女杂志祝》的文章,作者梁令娴是出身名门、深受旧文化浸润、谨守旧道德的名媛。“小说”栏目曾发表王蕴章所撰的劝导妇女认清革命现实、回归家庭的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希冀“有功于世道人心”。“传记”则多宣扬孝女、烈妇、贤母事迹,望收“移风易俗”的功效。这些或标榜、或劝诫的方式都旨在规劝妇女以贤妻良母为立身之则与修身之准。
如何才能成为贞婉娴静的贤妻良母?王蕴章也在《妇女杂志》中作了正面回答,那就是培养新式女子的才与德。王蕴章并不排斥西方的科学知识,他也认为新时代的女性应该具备科学知识来提高生活质量,更好地为家庭服务、为社会效力。这些生活技能与常识是“术”。而王蕴章更注重的是传统的“艺”。王蕴章坚信文艺之才是涵养妇德之器。他在《玉台艺乘·序》中说道:“余尝谓女子之于学也,静一而恒久,一则锐,恒则精。……晚近以还,莘莘学子或舍其旧而新是谋,卒之纷驰旁骛。新者未必遂有成效,而旧有之国粹且日即于退化。宁非女界之大忧欤。”连载于《妇女杂志》的《玉台艺乘》专门介绍女性之书画、琴谱、篆刻、杂技等传统艺术。“区区此心,盖犹是保存国粹,促进女学之意。”[17]王蕴章挽救颓风、重振妇德的思路是以旧文艺来恢复培育妇德的旧文化环境,从而实现妇德的重建。因此,女性旧文学修习的目的最终是指向妇德建构的。这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中才德之争的命题已经完全不同了。
带有女校学生课余读物性质的《妇女杂志》践行着政府所倡导的援引古今名人及良媛淑女嘉言嘉行以示劝诫的修身教育之法。自1914年起,袁世凯开始大肆表彰贞女、烈女、节妇。这一倒行逆施的风气在王蕴章的《燃脂余韵》中得到了直接的响应。1915年《妇女杂志》第5期“杂俎”栏目重新刊登的《燃脂余韵》,除延续《小说月报》时期的基本特点与风格外,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对贞节、孝道等内容的书写比重增加。1918年王蕴章在《燃脂余韵·凡例》中说道:“惟节烈之作,广为甄采,匪云有裨阴教,庶几少挽颓风。”[11](1)《燃脂余韵》所记录的贞妇烈女,都是王蕴章为女性树立的妇德模范,而并非因诗词而入选。
贞女节妇是直指道德的行为典范,而诗词对德性的涵养则借助诗教的传统来实现。向诗教靠拢的常州词学中,陈廷焯的“温厚和平”、谭献的“柔厚”都落实在词的内容、写作技巧及风格上。王蕴章借常州词学论女性词,也强调情感的厚重与表达的含蓄。王蕴章以林下风评黄媛介,并言其诗“既足观其性情,且可以考事实”,说明其诗并不限于闺阁之间的女儿家情愫,而有着更为深广的现实内容。“性情”与“事实”共同铸就了“流离悲戚之辞”,但黄媛介对现实的认知与表述都在“温柔敦厚,怒而不怨”的范围内。旧词笺中《卖花声》词,王蕴章云:“味其词意,愁苦中温厚不迫,是女子中才而贤者。”[11](793)又如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的妻子沈鹊应,以死殉夫,王蕴章录其绝笔词,是从悲伤中体味其贞烈。还有三十寡居的左锡璇,身世飘零,词亦悲切,却“能从大处落笔,不作小红低唱”[11](789),王蕴章表彰的是她不耽于儿女情长,而有贤母风范。王蕴章以贞洁、贤惠之妇德为底蕴,将女性词中的悲情解读为厚重而端庄,凄哀而蕴藉的情感。
王蕴章更侧重诗教本义。在读到《题海沤女士诗集》“独立平权并自由,放言高论震神州。温柔敦厚风人旨,今见闺中第一流”时,他说:“晚近女教日媮,跅弛不羁者,率以欧化为借口,读此诗,可谓先得我心。”[11](707)王蕴章认为承载着旧文化、旧道德内核的旧文学才是女性表达情绪、涵养性情的正途。不可否认,妇女觉醒的自我意识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而王蕴章将这股热潮与冲动,置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框架中加以冷却,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学来重塑和涵养人物性格,最终引导社会风气。民国时期,词的“私人化色彩加重,关注社会、干预社会的功能已经退化”,“作词在当时或是一种个体化的情感寄托方式,或是一种文人雅士的文化休闲方式,或是一种以文人雅集为形式的群体化鉴赏与交流活动”[18]。这种私人化、个体化、高雅化的文学活动不失为瓦解女性集体意识与政治集会的良方。词相较于诗而言,与社会现实更疏离。常州词学主旨由“寄托”到“浑成”的转变,已经预示了诗教对词学输出的内涵转变——由干预现实变为温柔敦厚。而王蕴章在女性词批评领域又进一步退回到“温柔敦厚”诗教的本初功能。贺双卿可谓丰才啬遇的典型,王蕴章对其悲惨的命运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怜悯,以“一副痛泪”哭此“沦落不遇佳人”。关于双卿诗词,王蕴章却说:“‘诗意温柔敦厚,诵之者逐臣可不怨君,放子可不怨亲,弃妇可不怨夫。’读双卿词,亦当作如是观。”[11](755)王蕴章赋予双卿词现实的教育意义,这与“和平中正”(陈廷焯评贺双卿语)、“忠厚之旨,出于风雅”(谭献评贺双卿语)等常州词人的评价在本质上已然不同了。王蕴章的解读已经不限于“温柔敦厚”的“寄托”词论,而是以此回应重建贞婉、贤淑、隐忍妇德的现实问题。
《燃脂余韵》的写作与连载或许出于王蕴章用传统文艺来重建妇德、女学的目的,但诸多女性作家作品却得以在此集中亮相,女性文学的版图也在迅速地形成。有学者指出,发表了《燃脂余韵》等众多女性诗话、词话的《妇女杂志》实则有王蕴章等人以“拼补缀贴的方式,为文艺女性立传”[19]的用心,可视作女性文学史的滥觞。只不过,因为杂志的立场——“文苑、杂俎两栏,皆载有关女德及涉于女学之文字”[20],“杂俎”栏目中带有道德评价内容的女性诗话、词话终究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女性文学研究中妇德观念的修正与纯文学的回归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学者的著作中才得以实现,但《燃脂余韵》的奠基之功也不容抹灭。
四、民国的女性词批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文学进入现代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早期女性文学史成果有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1916)、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1927)、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1930)。而女性词史自然是这些著作的构成部分。谭正璧的《女性词话》(1934)、曾乃敦的《中国女词人》(1935)则可视为这一时期女性词专题史的雏形。叙述方式与思路由女性词话向女性词史、女性文学史的改变,意味着女性词批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王蕴章的《燃脂余韵》则是实现转型的桥梁。除谢无量的著作外,无论通史还是专题史的参考书目中,《燃脂余韵》都赫然在列。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从《燃脂余韵》中抽绎出清代中期女性词史的基本架构。而谭正璧的《女性词话》与曾乃敦的《中国女词人》则从《燃脂余韵》中选取了诸多史料。
作为第一部女性文学史著作,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叙述至明末而止,梁乙真有意赓续谢作,故而编写了《清代妇女文学史》。梁著全书分为五编,前四编按清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阶段,分“明清蝉蜕期”、“清代极盛期”(两编)与“清代衰落期”,第五编为“杂述”。在“衰落期”中有一章为《清代妇女词学之盛》,下设“常州词派之女作家”与“浙西词派之女作家”两小节,又以“庄盘珠”与“赵我佩”分别作为常派与浙派女词人的开篇。浙、常两派分野的批评观不仅与王蕴章如出一辙,其代表人物的名单及词作评述的文字也基本是出自王蕴章的《燃脂余韵》。梁乙真以庄盘珠为常派女词人之首,又将《燃脂余韵》中“瓣香秋水”的武兰仪紧置其后,吕采芝、杨芬若、徐元端、顾贞立、王朗、苏穆诸家归常州一派。此节中仅有胡淑慧、刘琬怀、浦映绿、周络隐四人是梁乙真的补充。在“浙西词派”一节中,开篇先叙述了浙西词派的发展脉络与词学主张,继而照搬了王蕴章《燃脂余韵》中“赵我佩”一条的全部内容,甚至包括对其父赵秋舲的评价。当然,《燃脂余韵》中提到的渊源浙派的孙秀芬、关锳、李婉等女性词人都被置于此节,且表述文字都来自《燃脂余韵》。
梁乙真“清代妇女词学”的写作思路可以说是在王蕴章以浙、常词学观观照女性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激昂善变与清圆流丽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重新排列王蕴章的批评材料,明确划分词派归属,将清代中期的女词人归类论之。王蕴章在《清代妇女文学史》的序文中称之为“以科学家之方法,爬梳而解剖”妇女文学,“足补《燃脂余韵》之缺憾”[21](1)。“科学家之方法”既有赞其析缕分条的意识与魄力之意,也不限于其女性词批评而言。只是,梁乙真在书中的分类标准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衰落期”“极盛期”都将女性作家分类而言之,有的以内容风格为一类,如贺双卿、阚玉归于“血泪文学”类,有的以身份为一类,如柳如是、顾横波为“风尘三隐”。这样简单的分类在女性总集中早已有之,而以男性对女性文学的介入与影响来作为划分女性作家群体的标准,则是梁著的一大特色。在“极盛期”中,梁乙真将清代前中期女性文学划分为“王渔洋与妇女文学”“袁枚与妇女文学”“陈文述与妇女文学”三个部分,揭示了女性文学演进的外在因素及主流文坛对其的接受情况。这种思路也明显受到了王蕴章的影响。王蕴章在《燃脂余韵》中尤为注重从师承、家学、交游等方面来突出女性诗词与主流文坛的关系,梁乙真将此提炼为女性文学史的骨架。目录标题所展现的条理性正弥补了王蕴章叙述零散与杂冗的“缺憾”,这是王蕴章所谓的“科学家之方法”。
女性文学的研究者或从断代入手,再打通全史,比如梁乙真在《清代妇女文学史》之后又有《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之辑;或由通史肇始,再衍生为分体文学,比如谭正璧先著《中国女性文学史》,再续《女性词话》。谭著《中国女性文学史》以时代文学为纲,词史部分仅论及宋代女词人。或许是有感于时代典型文体不足以反映女性文学的全貌,谭正璧于1934年又撰写了《女性词话》。之所以不以“女性词史”命名,是因为这部书确实更符合“词话”的性质。全书记女性词人共五十六位,以出生年时间为序,逐一贯列,用白话文介绍了女性作者的生平,并赏析其代表词作。此书将《燃脂余韵》等传统词话中录逸闻掌故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却脱去了传统词话中或猎奇或卫道的外衣,而是重在揭示女性的家庭关系与生存境遇,以此作为理解词作的背景知识。谭正璧的《女性词话》传递着这样一个讯息:女性词人在用词抒写着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内心世界的点点滴滴,而这些现实与情绪又都与他们所依附的男性尤其是丈夫、情人息息相关。这种赏析式的书写,也将传统词话中的掌故挖掘出其应有的价值,从而为理论研究增添了些许柔性与温度。
如果说《女性词话》无论是书名还是内容都还带有传统词话批评散漫与随意的缺憾,那么曾乃敦的《中国女词人》则算是第一部专门的女性词史。曾著中的女性词人不再简单地按时代顺序罗列,而是以时代结合女性词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经,再纬之以各时期女性词人的身份,以此构成女性词史的基本格局。这既厘清了女性词“胚胎”“繁荣”“衰落”“极盛”的发展动态,又呈现了每个阶段中各阶层、各群体女性词的立体风貌。这一理路显然是从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借鉴而来,尤其是其清代部分。曾乃敦进一步剔除了梁著中所引《燃脂余韵》的赘述,以“王派女词人”“袁派女词人”“陈派女词人”归纳清代女词人流派,更为简明扼要。在《中国女词人》一书中,也唯有清代部分有着清晰的群体与流派脉络,这应得益于王蕴章、梁乙真二人的前期勾勒。《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国女词人》都是女性词批评在体系化道路上的探索。
具有现代性的女性词研究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传统女性词批评的或删或汰,或承或继。出现在新旧交锋之际的《燃脂余韵》,既积累了深厚的词学理论与材料,也加强了词的现实功能。带着这两重特征接受现代词学科学精神的洗礼,女性词批评披沙拣金,才蜕变成越来越成熟的模样。
注释:
① 关于《燃脂余韵》的版本信息,参见史化《王蕴章〈燃脂余韵〉》,《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黄晋卿《交融与冲突中传统女性形象的写照——民国视野中的〈燃脂余韵〉》,《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年第2期。本文所引《燃脂余韵》主要采用在《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上发表的版本,不见于报刊者则用《清代闺秀诗话丛刊》本。
② 恽铁樵于1912年取代王蕴章成为《小说月报》的主编,直至1918年。
③ 参见张晖:《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晖在文中指出了《小说月报》政治、文化双重遗民的立场。而王蕴章在《小说月报》开辟诗词专栏,更是出于保存旧文化的目的。④ 潘静如《近代杂志所载闺秀诗话考论》共统计了1911年至1941年在杂志上发表的27种闺秀诗话,如:1911年《妇女时报》刊《绿蘼芜馆诗话》,1912年刊《绾春楼诗词话》;1913年《时事汇报》刊《闺秀词话》;1915年《女子杂志》刊《镜台词话》;1916年《妇女杂志》刊《闺秀诗话》。见《汉语言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傅宇斌《现代词学的建立——〈词学季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统计了女性诗词发表于《小说月报》《中华妇女界》《女子世界》《妇女杂志》等多种刊物的情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0-33页。
——燃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