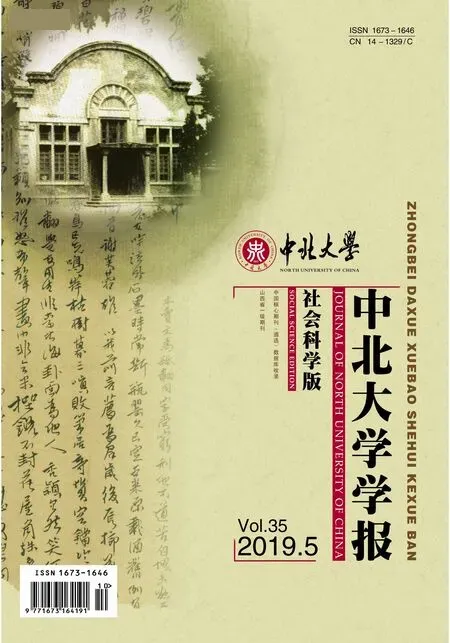“非遗旅游”与企业参与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的人类学研究
黄孝东, 徐业鑫
(1.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2.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山西 太谷 030801)
旅游和遗产是近年来出现的研究热点和公共话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 “遗产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吸引游客的手段和卖点。[1]212-225一般而言, 旅游资源开发主体可划分为完全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 政府与企业进行垄断性开发、 完全由政府为主体开发三种模式。 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开发模式中, 企业往往以一种纯粹市场化的原则进入东道主社会, 由此产生许多问题。 本文以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为例, 深入探讨企业参与“非遗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引发的各方社会行动者对遗产资源的争夺与博弈, 并对阻碍企业开发“非遗旅游”资源的因素进行分析。
1 研究背景
1.1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及其旅游开发概况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是以娥皇、 女英(当地人称“姑姑”)信仰为核心的大规模走亲祭祖活动。 相传山西洪洞县周村[注]本文对涉及的村落名称、 企业名称以及报道人姓名均进行了技术化处理。是尧的故乡, 尧王历山访贤遇舜, 禅让王位并把两个女儿(娥皇、 女英)嫁给舜, 周村和历山从此成为娥皇女英的娘家和婆家。 娥皇女英造福一方、 庇护百姓, 逐渐被后人尊奉为祖先神。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 周村人郑重地举行仪式到历山神立庙将二位“姑姑”接回娘家。 农历四月二十八, 历山人以给尧王拜寿为契机到周村再把二位“娘娘”接回去。 整个走亲仪式耗时三天, 往返150里, 途径二十几个村落, 跨越五个乡镇, 波及人口近五万人。 2006年和2008年,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被分别纳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申遗成功后, 周村-历山庙宇修复委员曾组织人员收集大量材料论证舜耕历山、 尧舜联姻的真实性, 计划打造“中国第一历山”, 而后交由企业经营。 计划提出后, 大部分历山村民和部分“社”[注]“社”是周村-历山地区管理庙事的民间组织, 成员由村民组成, 分为社首和普通社员。 周村村庙由南周村和北周村基础上形成的“南社” “北社”轮流管理。 2005年, 周村成立“总社”统领南北“社”。 原则上, 村委会与“社”互不干涉, 但二者时有交集, 例如每年“三月三”走亲习俗的启动仪式上和四月二十八的祭尧大典上, 都有村干部代表讲话, 村里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也会请庙上的人协助处理。 “社”在庙事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也对“非遗旅游”资源开发起到一定阻碍作用。成员极力反对, 导致计划夭折。 2012年, 山西W企业将周村“姑姑”庙(唐尧故园)纳入旅游开发计划。 计划包括: 流转/征用以唐尧故园为中心的六个沿河村落; 六村沿线挖一条龙形河道; 以唐尧故园为中心打造“皇英小镇”; 以采摘园、 绿植培育等项目为依托, 打造文化旅游度假区。 2014年, W企业草拟了一份《唐尧故园开发与保护合作协议》, 协议内容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
1) W企业出资设立唐尧故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唐尧故园的管理权归甲方, 涉及唐尧故园的一切资源都归甲方支配, 乙方委派代表积极配合和监督。 乙方在公司收回投资后, 按50%的比例分取利润。
2) W企业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投资建设、 开发、 宣传、 管理、 保护; 所有收入归甲方支配; 制定相关的管理规定; 聘用管理和工作人员; 有权转让权利与义务给第三方; 委托第三方进行策划、 宣传、 管理。
3) 村干部和村庙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支持配合甲方管理; 排除村民干扰; 提供涉及的所有资料、 照片、 证书、 文物等; 召开村民大会表决通过合作协议。
这份协议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村干部中只有极少数赞成签订协议, 虽然部分百姓愿意搬到新建小区居住, 但一致反对将“姑姑”庙交给W企业管理, 唐尧故园“总社”和南北周村“分社”成员绝大多数也都对这份协议持否定态度。 由于存在多重阻力, W企业之后的发展也不景气, 所以此事被搁置无人再提。
1.2 理论背景: 市场逻辑与乡土逻辑
企业参与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旅游开发过程遇到了许多阻力, 其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结为市场逻辑与乡土逻辑之间的博弈。 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人类学有关市场和乡土逻辑的相关理论做一个梳理。
市场逻辑是以个体或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对生产和交易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这一逻辑否定其他任何力量对其加以干涉, 更加排斥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马克思·韦伯把市场逻辑抽象为非人格性, 原因在于它的就事论事、 它的以商品为取向且仅仅以商品为取向。 只要允许市场按照自发趋势推进, 那么市场参与者的目光就会只对物、 不对人; 这里既没有仁爱的义务、 也不存在敬畏的义务, 更不存在由私人结盟支持的天然人际关系, 它与所有始终以私人亲善甚或血亲关系为前提的群体形成了截然对立。[2]777-778乡土逻辑是维持和支撑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 在以血缘关系、 历史记忆为联结纽带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 伦理、 家族、 习惯、 风俗等要素是人们的基本思维规则和行为规范。
市场逻辑和乡土逻辑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冲突, 正如费孝通所说,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 商人是敲竹杠的, 是寡情无义之徒。 他们斤斤计较, 重钱不重情。[3]105-122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转型,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 市场逻辑与乡土逻辑不再水火不容, 以“情”为核心的传统乡村秩序正逐步向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新型乡村秩序转向。 折晓叶在《村庄的再造》一书中提出“利、 权、 情”秩序, 旨在说明乡土逻辑的人情基础已经杂糅进了权力和经济利益要素。[4]70-71贺雪峰进而认为, 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结构正逐步走向解体, 人们开始依照自己的理性计算选择关系和做出行为, 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了钩, 农民越来越看重实际的有时是即时的好处, 越来越忽视交往中的感情。 中国农村社会越来越陌生化和疏离化, 依托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解体, 市场伦理和市场逻辑正在替代传统的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5]40-50然而, 社会结构的转型并不意味着乡土性和乡土逻辑的消失。 相反, 在某些特殊情境下, 乡土逻辑在市场化的冲击下会得到重塑和强化。 只要人们还未完全从乡土社会网络中“脱嵌”, 他的行为动机就不仅仅是维护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 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声望、 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 只有当物质财富能服务于这些目的时, 他才会去珍视或妥协。[6]121-129
2 多方社会行动者的利益表达与诉求
2.1 普通百姓: 把庙给我们留下就行
周村普通村民对W企业开发村庙的态度较为矛盾, 一方面, 他们认为这是一次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 另一方面, 他们又不愿让W企业完全接手村庙, 认为这是亵渎神灵, 是忘本的表现。
上文提到, W企业计划征用包括南北周村在内的六个村落, 围绕村庙进行旅游开发。 得知此消息后, 很多村民纷纷建房和扩建, 后被县政府禁止。 当再提及搬迁时, 很多人不愿意搬走。 在笔者访谈过的村民中, 大多数都表示不愿意搬走的原因是住不惯楼房, 而且到庙上也不方便, 和以前不一样了。 谢鹏[注]谢鹏, 周村村民, 45岁, 2017年当选周村村庙“北社”社首。 访谈时间: 2017年6月25日上午; 访谈地点: 谢鹏家。的一段话能够代表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想法:
很多人都打工去了, 自己种地的收入还没有流转费高。 其实我们也想有人把这个地方开发一下, 希望有更多人为我们宣传, 但我们不主张经营, 不能搞卖门票的形式, 游客纯粹是观光的。 我们希望游客能自发过来, 和我们一样是“姑姑”的信徒。 来到庙上烧香磕头, 布施上五毛也行一块也行。 我们更希望有人投资在庙外面搞建设, 吸引外面的人来我们这儿, 而不是在庙里面。
可见, 村民信仰的坚定性较之从前有所松动, 他们既想成为“非遗旅游”开发的受益者, 又不愿看到自己的信仰成为获取利益的工具, 这种矛盾的心理折射出了东道主社会特征的变化, 从深层次上讲, 是特殊的信仰与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相碰撞而产生的。
2.2 村庙管理者: “刺插的门不是门”
“刺插的门不是门”是当地人形容一件事失去本意的俗语, “社员”们在谈到W企业的开发计划时一致认为, 如果让企业完全接手“姑姑”庙, 当地人的信仰就变味儿了。 首先, 平时在庙上值班的妇女以及仪式上帮忙的当地人都是自愿的且没有任何报酬, 人们认为这是为“姑姑”尽孝心。 如果企业接管, 就会安排专门人员值班和管理, 并且按月发工资, 这与几千年来当地人坚守的习俗准则相悖; 其次, 每年“三月三”走亲仪式都由“社首”带领和组织, 当地人之所以听从安排是因为熟人之间的信任, 村际走亲仪式之所以能够有序进行, 原因在于每年的走动, 即使彼此之间不熟悉, 用家乡话说上一句: 我是周村“亲戚”, 双方马上就会熟悉起来。 此外, 仪式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并非一成不变, 需要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处理, 而且大多交接仪式具有神圣性且不可言传, 这一点是企业难以掌控的; 最后, 村庙管理者认为以“姑姑”信仰为核心的“三月三”走亲习俗应当是自发性的, 而非表演性的, 仪式过程是亲情交流和历史展演的双重体现, 绝不能拿这个去卖钱。
2.3 村干部: 庙上和老百姓不同意, 我们没办法
在《唐尧故园开发与保护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中, 法人代表是周村村委会, 协议最后的签字代表分别是: 南周村村委会、 北周村村委会、 唐尧故园主管单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单位, “社”没有任何发言权。 如果村委会干部一致同意协议内容并做通百姓的工作, 那么“三月三”走亲习俗很可能会以政府与企业合作的形式进行垄断性开发。 然而, 笔者在田野中发现, 大多数村干部的态度都较为模糊, 他们认为企业开发是好事, 但是工作很不好开展。 村干部闻立业[注]闻立业, 56岁, 周村党支部副书记。 访谈时间: 2017年6月20日下午; 访谈地点: 周村村庙办公室。说出了问题的关键:
“W企业想收了庙, 所有权归人家, 但是使用权是庙上的。 五洲在庙前征用了60亩地准备建个广场, 出资几千万或几个亿就闹成了, 老百姓行吗?老百姓愿意出让土地, 有钱花他还不乐意吗?但是要把庙给了W, 庙上的人首先就不同意, 本身庙上的事就归他们管, 村里一般不管。 他们又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 还有那么多亲戚朋友, 庙上和老百姓不同意, 村里也没办法……”
可见, 在各方社会行动者对“非遗旅游”资源博弈与争夺的过程中, 村干部平衡着各方的利益, 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在由南北周村构成的人口上万的“半熟人社会中”, 这种角色更难以凭借单纯的行政力量或关系人情做出决策。
2.4 县镇文化精英: 视野狭窄注定无法成事
洪洞县原文化馆馆长闻存良认为, “三月三”走亲习俗难以开发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 “三月三”走亲习俗牵涉二十多个村落, “非遗”项目的归属权和经费分配是个大问题。 此外, 如何选定传承人更是难以定夺。 其次, “姑姑”信仰发生了质的变化, 已从原来的自发性、 自愿性转变为号召性、 强制性, 成了一种摊派, 仪式也从参与性转变为观赏性, 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化发展。 老百姓希望W企业开发村庙, 因为他们能得到切实的利益, 而“社”里的人就成了W企业的员工, 要给人家打工。 现在企业都要25~45岁的人, 庙上那些老头给人家看大门人家都不要, 他们担心自己失去对庙的控制权。”
3 企业参与“非遗旅游”资源开发的困境分析
3.1 “民俗宗教”的不可让渡性与不可剥离性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属于民俗类, 较为特殊的是, “三月三”走亲习俗是信仰型民俗, 是一种“民俗宗教”。 一般来说, 这种“民俗宗教”是自发地经由历史性传承在地方社群中逐渐形成的信仰现象, 它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与地方社会人们的生老病死、 人生观、 生死观、 命运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在“三月三”走亲习俗仪式中, 当地人作为“遗产”继承者的东道主身份得到了认同和强化, 当信仰以重演的方式再现时, 人们获得了承载着历史意义的“尧裔后人”的荣耀感和使命感。 正如杨庆堃所说, 这种弥漫性的宗教渗透进了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地百姓在遇到困难时会向“姑姑”祈祷, 疾病久治不愈会找“姑姑”的“弟子”帮助治疗。 不仅如此, “姑姑”信仰在当地社会还承载着教育功能。 “姑姑”庙作为村落公共空间让孩子们耳濡目染着尧舜和“姑姑”的故事, “三月三”仪式过程中, 许多村落都有小学生组成的威风锣鼓方队, 迎亲队伍返回周村时, 孩子们会争抢仪式中所使用的器具, 认为这种神圣是可以保平安的。 这种特殊的“民俗宗教”不断地型塑着当地人的价值观念, 这种内化的信仰和生活交织在一起, 具有一种不可剥离性。
企业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三月三”走亲习俗去宗教化, 激活并强化了蕴含其中的乡土逻辑。 在《协议》中, 企业的非人格性体现的较为明显, 门票、 摊位费、 捐赠、 政府拨款等内容完全是商品化和利益化取向的, 缺失了对当地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仁爱和敬畏。 虽然《协议》中也提及了“保护”, 但仅限于物质层面, 即对庙宇、 神像和与之相关的神圣物品的保护。 由此可见, 企业奉行的市场逻辑与“三月三”走亲习俗特殊属性是相背离的, 所以才会遭遇部分村民和村庙管理者的强烈反对。 作为“非遗”资源的器具或技艺则不同, 物品本身就具有商品属性, 技艺则携带着天然的表演特质。 器具和技艺不仅更容易确权, 而且与市场逻辑不相容的文化禁忌也相对较少。 更重要的是, 器具和技艺之所以成为“非遗”资源,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稀缺性、 独有性和濒危性, 特殊的器具和独特的技艺只对少数“遗产”继承者有意义, 并不具备日常化和生活化属性, 对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也基本不具指导意义, 如阿多诺和英格尔德所言, 器物是去语境化的, 它被从生活的语境中抽离了出来, 应当将之重新嵌入于制造自我的物质过程中。[7]67-87企业在这个重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器物商品化过程是重新回归“活生生的语境”的过程, 也是器物向观念的流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器物中蕴含的文化意义被激活。 可以说, 开发此类“非遗”资源企业既能获得市场效益, 又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这对企业和地方社会来说是双赢的。
3.2 外来者引发的权力角逐和利益博弈
“三月三”走亲习俗作为一种“地方实践”, 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构造, 既包含可视的、 可计量的物质关系结构, 又包含诸如社会认同、 社会关系、 权利话语等隐性社会文化关系结构。 旅游是一种明显的“权力化社会活动”, 旅游开发主体和地方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关系, 企业参与“非遗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正是各种权力角逐和博弈的过程, 在本文实例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企业经济话语权力的失灵。 话语权不单是一种表述方式, 同时也具有强大的操控能力。 W企业参与开发当地“非遗旅游”资源过程中, 金钱成为其话语权的替身, 包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当地的土地流转与征用, 计划投入100万来开发村庙, 但条件是村庙的归属权为企业所有, 同时, 在企业收回成本后才能与村里进行利益分配, 所有庙事活动均由企业管理, 村庙管理者只能配合, 企业话语权力的形成是以当地人让渡或牺牲自我权利为前提的。 然而, 村庙作为“姑姑”信仰中最重要的物化载体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 当地人对企业的经济话语权力渗透形成了一种本能性的排斥和对抗。 正如部分报道人所说: “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 “要是把庙卖了, 我们就对不起‘姑姑’, 就是罪人!”说到底, 这种排斥和对抗是由企业和当地人之间不对等的、 不平衡的话语权所导致的。 当然, 有少数当地人的态度较为模糊, 因为他们对企业开发旅游能带来经济上的改善抱有很大期望, 而且企业也未对他们的信仰造成实质性破坏。
第二, 村落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进一步弱化企业话语权。 一般而言, 村落权力由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构成, 正式权力以象征国家行政力量的村委会为代表, 非正式权力则包括地方性社会组织以及具有知识、 经济资本、 声望或特殊品质的个体。 无论何种权力, “差序格局”都是其权力行使的重要参照标准。 但随着“超级村庄”的出现以及市场经济的渗透, 村落权力出现了“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局面, 形成了贺雪峰所谓的“权力的利益网络”。 在周村, 虽然村委会和“社”作为两条偶有交集的村落管理主体已成为一种“地方性共识”, 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权力的争斗与博弈。 一方面, 当南北周村需要作为一个村落共同体共同面对外部事务时, 谁更具发言权和决策权?在《协议》中, 虽然乙方是北周村和南周村, 但两村的村干部并不能达成意见的统一, 原因在于他们会站在各自所在的村落考虑和庙上的关系并计算利益得失; 另一方面, 村庙由南北两“社”轮流管理, 在庙宇修葺与建设、 仪式中的经费划拨与收入等方面时有矛盾, “南社”和“北社”也时常因各自村落在“总社”中所占的人员比例等问题而争论。 虽然在W企业的事情上“总社”及“分社”基本达成了一致, 但除了信仰因素外, 既得权力的维持也成为决策制定的参照系。 面对这两个方面的权力博弈, 企业成为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使其原本就难以行使的经济话语权力被进一步削弱。
3.3 汲取性市场介入与包容性市场介入
既然“三月三”走亲习俗很难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商品化生产, 企业在参与其“非遗旅游”开发过程中又受到了多重阻力, 那么是否意味着企业无法介入“民俗宗教”类的“非遗”项目中呢?笔者认为, 如果企业能够将介入路径由单向性转变为对话性、 由企业独揽转变为社区参与, 那么企业不仅可以介入“民俗宗教”类的“非遗”项目, 而且可以更好地进行生产性保护, 从而使当地文化得到传承和再生。 受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对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研究[8]51-67的启发, 笔者提出汲取性市场介入和包容性市场介入这对概念来对企业参与“非遗旅游”资源开发问题做进一步阐释。
企业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利用货币资本、 契约等方式对生产要素进行更加有效地整合, 从而使生产交换过程简单化、 清晰化。 原则上, 市场规则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 即交易双方以互惠和自愿为前提达成协议。 然而在本文实例中, 企业和“遗产”继承者之间却存在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企业牢牢占据着话语权, 如果以这种强势的态度介入“非遗旅游”资源开发, 将使“遗产”被剥离出东道主社会的日常生活, 成为一种买卖品和观赏品, 有选择地展示游客可以理解的部分, 当地人则彻底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真实表述, 笔者将这个过程称为企业的汲取性市场介入。 从短期效应来看, 企业的汲取性介入会使企业和当地人都成为受益者, 但从深层次和长期效应来看, 会造成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 W企业的开发计划之所以受到重重阻力, 其核心问题在于村庙的归属权, 当地人担心如果把村庙交由企业管理, 那么企业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破坏了他们的信仰。 “姑姑”信仰具有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双重属性, 对当地人来说, 这种信仰及其含括的器物和仪式的重要性在于维系亲缘关系和历史文化的传承性, 无法用金钱计量。 “姑姑”信仰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精神领域, 而且对周村-历山地区二十几个村落起到了一种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功能, 切实发挥着规范行为、 消解冲突、 强化协作等社会功能。 如果周村人把村庙所有权转让给W企业, 他们除了丢失信仰外, 还会受到仪式圈中其他村落的排斥和孤立。 经济行为嵌合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 相对于物质利益的受损, 当地人更畏惧的是情感道义的背叛和社会关系的断绝。
包容性市场介入则是企业以对话和协商这种相对平等的方式开发“非遗旅游”资源, 以不违背当地人的文化禁忌为底线。 这种介入方式不单纯是利益取向的, 而是将地方性文化与企业文化相融合, 打造企业+当地人的社区参与型“非遗旅游”开发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企业和东道主社会将形成正向反馈和良性的互动关系。 当地人既不丧失尊严, 又可以依托强大的企业资源维护和传承信仰, 企业则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当地人返乡就业, 进而保障遗产继承者的延续性。 不得不承认的是, “三月三”走亲习俗近些年出现了衰退的趋势, 随着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 返乡参加仪式的年轻人渐少, 有的村落甚至开始雇用他村人帮忙, 妇女们开始更多地参与仪式并提出更多要求, 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 要使企业做到包容性市场介入也需要当地人做出改变和努力, 例如, 村庙管理者在拥有归属权的同时可以学习企业的管理模式, 将村庙管理制度化、 规范化。 如果企业在村庙周边打造好了相关旅游景点, 村干部和村庙管理者可以请企业来做培训, 引导和强化当地人的市场意识, 建立和完善配套设施。
4 结 语
本文以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为例, 深入分析了企业参与“非遗旅游”开发时, 多方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过程。 究其根本,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这种民俗类“非遗”的特殊属性和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失衡是导致开发计划失败的主要因素。 笔者的核心观点是, 当我们将“非遗”视为一种旅游资源时, 应当充分考虑这种资源的文化属性和东道主社会复杂的社会结构。 在开发过程中, 开发主体应将“非遗”资源置于政府—市场—社会这一结构性框架中, 平衡各方之间的关系, 以更加包容性的方式介入, 从而实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