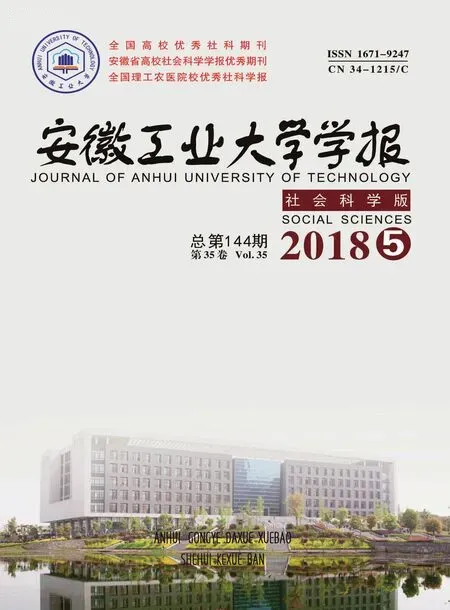弗洛伊德人格动力学视域下的海斯特
姚 成
(安徽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伊丽莎白·乔利被誉为“澳大利亚的一流作家”[1],她擅长融合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手法,塑造那些生存错位、心理失衡的“另类”人物。乔利的创作主题与她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因乔利的父母都是移民者,她认为自己是被主流社会框架所排斥的局外者,因而一直致力于描写那些郁郁寡欢、行为古怪的边缘人物。乔利在《井》中细腻地刻画了海斯特这一边缘人物形象。国内外对《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叙事手法、女性哥特小说的视角,鉴于此,本文运用弗氏的人格动力学研究《井》中海斯特这一边缘人物,通过分析海斯特的焦虑:现实性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以及为此采取的人格动力机制:求同机制和防御机制,展现海斯特内心世界的纠结与挣扎,揭示边缘人物的生存窘境,由此引起公众对边缘人物的关怀。
一、 海斯特由于人格系统冲突引发的焦虑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的发展是人的自我对本我和超我的调控,是人的本能与社会规约相互斗争、相互协调的产物。本我追求本能冲动和欲望发泄,遵守快乐原则。自我是受外在环境影响而改变的本我,是本我与超我斗争的结果,遵循现实原则。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它代表着良心和道德准则。若自我能合理协调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人格则处于健全状态,否则,就会导致精神失常。海斯特正是由于未能将本我、自我与超我协调统一,因而造成其心态失衡、性格怪异。
当人格系统发生冲突,即自我不能合理调节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时,焦虑便随之产生。焦虑据其具体原因被分为现实性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现实性焦虑是对来自外部现实的可预料到的危险的反应,是对外部危险的知觉情感。”[2]58希尔德·赫兹菲尔德初次见到海斯特,便称赞海斯特美丽的双眸。“眼睫毛这么长,眉毛也生得很好,很帅气!”[3]143希尔德刻意忽视海斯特生理缺陷和笨拙的动作,给予海斯特满满的肯定与赞许,让海斯特对未来充满希冀。缺乏母爱的海斯特将希尔德当作自己的母亲兼好友,形影不离地尾随希尔德,并谨遵她的教诲坚持用冷水冲洗脖颈,以期将来某个爱恋自己的男人用首饰装扮自己时,自己的脖颈仍能紧致如初。因此即便是最寒冷的早晨,海斯特也坚持用冷水冲洗脖颈,这体现了海斯特本我的欲望。少女时代的海斯特在希尔德爱的沐浴下渐渐忽视自身的残疾,自信活泼的她对爱情充满幻想与期待。然而,随着自己渐渐长大,海斯特愈加清楚跛足带来的无法改变的身体缺陷。因此,她默默地将儿时后期修整完美的照片从墙壁上取下,私自收藏。即便是从外国购买的精致手杖,海斯特觉得配上自己的跛足,拐杖也变得丑陋起来。海斯特始终无法正视自己的残疾。父亲逝世后,她继承了大农场,成为富有的农场主。但她认为自己根本没有结婚的希望。即便真有男子愿意与她结婚,也绝非是爱上残疾又丑陋的自己,而是想不劳而获地通过婚姻得到土地和财产。她明白自己的生理缺陷无法带来令人艳羡的爱情,一想到自己极有可能孤独终老,海斯特便抑制不住苦涩的泪水默默流淌。由于无法直面自己的身体缺陷,海斯特的自我不能合理协调源自本我的欲望,焦虑便随之而来。
“神经性焦虑则是主要起源于里比多的未被充分利用。它是自我在无法阻止本能的对象性发泄作用的冲动时所感到的恐惧感”[2]58,“它是自我的反宣泄不能控制本能的对象性发泄,而任其通过某种冲动性行为爆发时产生的。”[2]59海斯特从小被父亲和祖母忽视,是家庭可有可无的成员。在缺爱的环境中成长,海斯特已然忘记被爱的滋味。初次将凯瑟琳领回家时,凯瑟琳给予海斯特一个猝不及防的亲吻。这亲昵的动作出乎海斯特的意料,海斯特不断抚摸被亲吻的脸颊,“那里有种令人愉悦的感觉经久不去。”[3]12凯瑟琳的吻让长期缺爱的海斯特体验到被爱的温暖。海斯特甘愿倾其一切来满足凯瑟琳的愿望。两人如影随形,一起烹饪美食、缝制衣服、欣赏音乐。尽管对电影不甚欣赏,海斯特也开始期盼两周一次的电影。她发现自己期盼与凯瑟琳夜夜笙歌、尽兴狂欢,她并没有将自己视为凯瑟琳的母亲或姨母,也从不界定她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凯瑟琳的舞姿对海斯特有种不可言说的魅力,观看凯瑟琳热情洋溢的舞蹈,海斯特便会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在衣物的掩饰下,海斯特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怦然心动的爱情”。凯瑟琳的舞蹈对海斯特来说“是唯一一种用身体表达肉体之爱的方式”[3]114。她难以接受凯瑟琳与男人共结连理,一想到男人会霸占凯瑟琳纯洁无瑕的身体,她便觉得恶心难受。她为凯瑟琳而活,企图将凯瑟琳与世隔绝,以此独占凯瑟琳。这是海斯特本能的对象性发泄。但身处男权社会,“父权制把生理差别作为依据,在男女两性的角色、气质、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4]使其标准化、合理化。莫尼克·威帝格表示“生理性别范畴是政治范畴,它将社会创建成异性恋的社会”[5]。父权制规定异性恋是准则,同性恋则是禁令。海斯特深受父权制的迫害,认同这一观念,因此竭力压制自己的真实情感,但发现自我难以抑制本能的欲望,由此产生恐惧心理,进而焦躁不安。
“道德性焦虑则是源于自我对超我的服从关系,是自我由于对超我惩罚的惧怕所产生的情感。”[2]58道德焦虑产生于人格内部,常伴随着一种愧疚的痛苦感受。深受父权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浸染,海斯特的父亲一直想拥有一个可以继承家产的儿子,考虑到海斯特的生理缺陷也不利于农场管理,因此父亲对女儿漠不关心,甚至连父亲豢养的宠物狗都比海斯特得宠。海斯特向伯德先生抱怨“他的狗每天都要吃肉排的,而对父亲来说,我们其他人只要能吃上水煮面粉就行了”[3]41,祖母也从不关心海斯特内心的孤寂。希尔德的出现给海斯特灰暗的世界撒上一道明光。希尔德不仅是海斯特的家庭教师,更是她的闺蜜,是唯一给予海斯特真切关爱的人。她们一起绘画、欣赏音乐、出国旅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希尔德在一起的时光是海斯特最为珍藏、最为怀念的日子。但儿时的海斯特很快就意识到父亲求子心切,希尔德晚上的时间全被父亲霸占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海斯特碰巧看见倒在血泊中的希尔德,当希尔德发现海斯特时,第一反应便是让海斯特赶紧离开,以免满身血渍的自己吓到年幼的海斯特,给海斯特的童年蒙上恐怖的阴影。但转而考虑到自己胎儿的生命安全,因此恳请海斯特立刻通知她父亲。然而,海斯特看着这个浸染在鲜血中的挚友,出于对父权的畏惧——她内心十分了解父亲的品性,如果转告父亲必会遭到父亲的严惩,因而她选择自保,弃朋友安危于不顾,她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房间,爬上床用毯子蒙住头,假装对事情全然不知。直到天快亮时才听见父亲启动车子的声音。早晨从祖母口中得知希尔德小姐提前离开并且不会再回来了。晚上外出归来的父亲告诉海斯特她将去寄宿学校上学,并叮嘱海斯特一开始感到孤独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其他的女孩子在学校已有了各自的朋友。海斯特心里明白,父亲绝不会考虑得如此细致,一定是希尔德小姐在车上再三叮嘱父亲转告自己的。当时的希尔德即便已经自身难保,身处险境,仍一如既往地关心自己,用真诚的爱温暖自己幼小脆弱的心灵,而反观自己,因一己私欲,背弃朋友以保全自身。想到这,海斯特便觉得愧疚不安。每每想到自己当初的冷漠与自私,海斯特的自我会畏惧超我(良心与道德准则)的惩罚,因而恐惧不安。此外,遭遇车祸时,海斯特不假思索地以为被撞男子已死,为销毁罪证保护凯瑟琳,海斯特费九牛二虎之力将男子丢进废弃的枯井,但事后凯瑟琳坚信井中男子仍活着,请求海斯特用绳索救出男子,并表示是海斯特将男子扔进枯井,海斯特才是杀人凶手。海斯特才猛然意识到如果井中男子还活着,那么自己将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丢进深不见底的枯井,则成为了谋害生命的元凶。因此当凯瑟琳邀请海斯特前往枯井同井底男子谈话时,海斯特变得焦躁又恐惧。一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地成为残害生命的罪魁祸首,海斯特的头疼症便发作了,除了头痛,她还感到阵阵恶心。虽然她知道不应该诅咒别人死掉,但她还是在心中默默祈祷“彻底断气吧,就像那个晚上一样,不要再活过来了。”[3]153海斯特惧怕自己被动地沦为杀人真凶,她时常幻听到井中男子的叫喊声。海斯特的自我由于对超我(良心和道德准则)惩罚的惧怕而焦虑不安。
二、海斯特采取的应对措施:求同机制和防御机制
弗洛伊德认为,为了应对人格系统内部冲突而产生的不良情绪,人必须掌握有益于人格发展的各种动力机制,如:求同机制、移植机制、防御机制等,以推动个体人格的发展。
(一)求同机制
“求同机制是自我力求模仿或按照另一个人的某些方面去行动。”[2]60它包括自恋性求同机制、目标定向性求同机制、对象丧失性求同机制和强制性求同机制。
海斯特首先采取的是用目标定向性求同机制来缓解焦虑。目标定向性求同机制指的是个体会寻求合适的榜样,这个榜样会具有他所渴求的目标,并模仿榜样的独特性。海斯特自幼在单亲家庭长大,父亲拥有绝对的权威。正因为父亲拥有男权和经济大权才使他能够把希尔德从海斯特身边夺走,并据为己有。因此海斯特渴求男权和经济大权,将父亲作为自己的榜样,模仿父亲的特点。她穿着朴素,说话直截了当,从不拐弯抹角,男性气质较为凸显。当父亲询问海斯特从商店带回什么礼物时,她强调“我带来了凯瑟琳,不过她是我的”[3]11。海斯特像男性一样敢于公开表明自己的主权,宣称对凯瑟琳的占有权,正如当年父亲占有希尔德一样,这样凯瑟琳就不会被父亲抢走,海斯特也不会再次经历悲痛的折磨。车祸发生后,海斯特冷静的处事风格与凯瑟琳的胆怯形成鲜明对比,海斯特虽然忐忑不安,但仍保持清醒头脑,遇事沉着冷静,海斯特的男性气质愈加明显。父亲死后,尽管海斯特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她深知经济大权的重要性,仍坚持掌管财产,她效仿父亲,用一条金链子串起所有的钥匙,并悬挂于脖子上。除了钥匙,她从不佩戴其他首饰。金链上的钥匙作为权力的象征,给予海斯特的是一种安全感。为缓解焦虑,海斯特采取了目标定向性求同机制,与父亲认同,吸取其特点,使海斯特的性格和行为渐趋男性化。
其次,海斯特掌握了用强制性求同机制来消除自身焦虑。“强制性求同机制是指竭力同权威的禁令或戒律保持一致,其目的是通过顺从潜在敌人的要求以避免惩罚。这主要是指超我形成过程中的自我的求同过程。”[2]61凯瑟琳的到来给海斯特沉寂的生活注入了活力,观看凯瑟琳奔放的舞蹈会给她带来一种性爱的体验,她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凯瑟琳。但迫于父权制对异性恋的认同和对同性恋的打压,她不敢公开表达“异样”的爱,而是竭力压制自己的真实情感,以避免道德舆论和社会严惩。海斯特选择在脑海中默默回忆凯瑟琳的舞蹈,享受这独特的肉体之欢。她尽力与男权社会的禁令保持一致(自我),以避免道德舆论(超我)对同性恋(本我)的惩罚,运用强制性求同机制来消解焦虑。
此外,海斯特运用了对象丧失性求同机制。“对象丧失性求同机制是指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象或不得不放弃他,他就会力求在他的自我中建立该对象,把该对象的特点吸收到自身中来,以补偿他的损失。”[2]61希尔德对海斯特的童年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年幼的海斯特体验到朋友的关切和母亲的爱意,感受到世界的温暖。希尔德赞美的话语使海斯特忘却自身的生理缺陷,丢弃自卑,愈加活泼开朗。然而由于父权的介入,希尔德不得不永远消失在海斯特的世界。海斯特失去了她最为珍贵的朋友,因此,她采取对象丧失性求同机制,汲取希尔德的特点,使希尔德的特点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在自我中建立希尔德的形象。初次见到凯瑟琳,海斯特联想起年幼时的自己。因此与凯瑟琳相处时,海斯特模仿希尔德的教育方式教导凯瑟琳。如海斯特效仿希尔德,时常纠正凯瑟琳的错误发音。由于希尔德曾带着海斯特去欧洲旅行,欣赏音乐会和歌剧表演,海斯特也计划带着凯瑟琳一起去体验欧洲文化。与凯瑟琳在一起时,海斯特会有意模仿希尔德的特点,以此弥补失去希尔德的损失来缓解自我的焦虑。
(二)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是自我为了缓解焦虑进而采取的否定事实的策略。自我的防御机制主要包括投射、压抑、反向作用。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海斯特采用了投射来进行自我防御。“投射是自我否认神经性焦虑的根源(本我)和道德性焦虑的根源(超我)的方法。”[2]64它是为了把由于人格系统内部冲突产生的危险扭曲为外在危险,为自我做那些超我所禁止的事情寻求借口以达到自我安慰的目的。海斯特视凯瑟琳为自己生活的全部,而凯瑟琳除海斯特外还有自己的密友乔安娜。乔安娜与凯瑟琳从小一块长大,感情深厚,信件交往愈加频繁。海斯特满脑子都幻想着凯瑟琳躲在自己的卧室偷偷给乔安娜写信的场景,并臆想凯瑟琳在信中添油加醋丑化自己。海斯特愈发心神不宁,害怕长此以往凯瑟琳会被乔安娜诱拐,抛弃自己。凯瑟琳和乔安娜的友谊给海斯特带来了威胁,她甚至怨恨乔安娜为什么没有试图越狱,这样就会被处以两倍的刑期。一提及乔安娜,海斯特的头痛症便会发作,她感到焦虑不安,因此采取投射的防御机制,把来自本我的妒忌归结于乔安娜。她内心认定乔安娜是个垃圾伴侣,只会给凯瑟琳带来伤害,海斯特暗想“这肮脏的、满是病菌的丫头,应该被远远地隔离在她们鲜活纯净的生活以外”[3]51。闻到乔安娜的来信中有股浓烈的甜香味,海斯特觉得凯瑟琳的身上也带有这种味道,她甚至联想起毒品,臆造乔安娜有吸毒的恶习,并可能传染给凯瑟琳。海斯特因强烈的占有欲不愿乔安娜接近凯瑟琳,但是由于超我的道德约束——不能将凯瑟琳与世隔绝,因此便认定乔安娜是个只会给凯瑟琳带来伤害的危险人物,而自己是出于保护凯瑟琳的心态才讨厌乔安娜,把本我的嫉妒归结于乔安娜可能带来的危险。
凯瑟琳春心萌动,对异性充满好奇,一直期待真命天子的出现。她将电影明星约翰·屈伏塔视为自己的偶像,一边跳舞一边幻想自己就是他选择的终身伴侣。而出于对凯瑟琳强烈的占有欲,海斯特不愿凯瑟琳与男性发生亲密关系。她决不允许纯真无邪的凯瑟琳去做“那种在牲口棚或牧场的角落才会发生的肮脏的事情”[3]183,让男人玷污凯瑟琳纯洁的身体简直就是对凯瑟琳的糟蹋。对于结婚和生孩子,海斯特认为“那些被困在婚姻围城里的女人总是不遗余力地要让别的女人陷入类似的陷阱”[3]129。海斯特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将凯瑟琳与世隔绝是为了保持她的纯真优雅,避免她变得世俗和粗鄙。当凯瑟琳告诉海斯特自己爱上井中男子雅各布,并要与他结婚时,海斯特想到凯瑟琳会怀上雅各布的孩子,与他相亲相爱,她甚至幻想凯瑟琳、雅各布和乔安娜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那时候凯瑟琳会抛弃年老体弱的自己,并说道“我们在镇上为你找了一处最可爱的休养所,没错,我们会去看望你的”[3]185,面对余生的凄凉孤寂,海斯特恐惧不安。因此当凯瑟琳要求用绳索救出井中男子时,海斯特劝诫凯瑟琳如果救出雅各布,他必定一出来就会想方设法地杀人灭口,因为是她们将他推至枯井,险些丧命。海斯特出于阴暗心理不愿伸手救助井中男子,并为她的自私寻找借口,自欺欺人地认为袖手旁观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凯瑟琳的生命安全,将焦虑归结于井中男子的残暴本性。乔安娜和井中男子对海斯特构成了威胁,因此海斯特采取了投射的防御机制,将来自本我的敌意归结于乔安娜和井中男人给她们带来的生命危险,然而文过饰非,过度使用投射方式,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
三、 结语
乔利深知边缘人物的精神困境,因此决心以细腻的笔锋揭示边缘群体遭受的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井》中海斯特即是这一类型的典范。海斯特由于人格系统内部发生冲突,即自我不能协调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产生了焦虑心理:无法协调本能性欲与生理缺陷的矛盾产生的现实性焦虑,同性恋的本我与异性恋的超我相冲突引发的神经性焦虑,以及徘徊于人性冷漠与道德准则间的挣扎带来的道德性焦虑。为了消解焦虑,她采取相应的人格动力机制:运用目标定向性求同机制,模仿父亲,使自身男性气质日趋凸显;采取强制性求同机制,竭力抑制同性恋的本我以避免男权社会的舆论压力和道德惩罚;掌握对象丧失性求同机制,在自我中建立希尔德的形象。另外,海斯特采取了投射的防御机制,自欺欺人地将本我对乔安娜和雅各布的妒忌归结于他们二人给凯瑟琳带来的危险,以此逃避超我的责罚,满足本我的欲望发泄。乔利对海斯特这样“另类”的边缘人物抱以同情,努力唤起公众对边缘人物的关怀,期盼人们以更宽容的心态接纳那些脱离传统生活方式的边缘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