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柳百成 四十年前,我们52人赴美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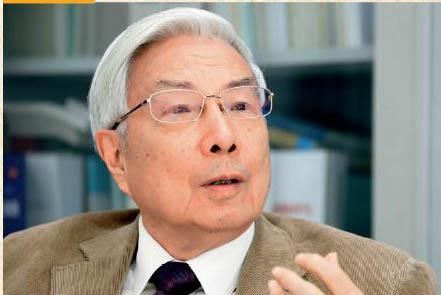
柳百成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材料加工工程系、机械工程系教授。1978年首批赴美的52位访问学者之一,并担任总领队。
自從1951年考进清华大学,至今我已经在清华生活了67年,工作了63年。回忆起1978年时作为首批52名访问学者之一留学美国,虽然时隔40年,但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出国留学是我学术人生的里程碑。回国后,不仅原来的铸造研究工作大大前进了,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用多尺度建模与仿真技术提升传统铸造行业的技术水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1999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也是因为在国内较早开辟了这方面的研究。
52个人带着50美元赴美留学
1978年,我45岁,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当老师。当年8月份左右,我接到通知称,中国要选派留学生赴美学习。当时清华大学可以派10人,机械工程系分得一个名额参加选拔。
我觉得喜从天降,因为知识分子经过“文化大革命”时的挨批挨斗,觉得国家选派知识分子出国留学,为我们带来了春天。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担忧,自己能不能选上呢?
要出国两年学习科学知识,英文不行肯定是不能过关的。所以在政治审查的基础上,要选拔外语比较好的人。系主任亲自口试,我得了第一名。接着清华大学、教育部也组织了考试,我很幸运,连过三关最终入选。
有人问我,为什么当时你能连过三关?这里有两个背景:第一,我一直坚信知识就是力量。“文革”期间,我被发配到清华校办工厂铸工车间,扛沙子抬铁水浇铸件,劳动强度很大。但我每晚仍然阅读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英文刊物《美国铸造学会会刊》,它是我的专业最重要的一本刊物,我的笔记本大概记了一尺之厚。第二,我生在上海,家庭并不富裕,但是非常重视子女教育,甚至借钱为我们交学费。我的小学和中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学习英文,经过严格的英文训练。因此,由于我本人有长期积累,又赶上改革开放的春风,才得到了出国进修学习的机会。
选拔结束后,我们到语言学院进行出国前学习,专门讲出国注意事项。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堂课上老师就告诫我们,不要以为选上了就等于出国,外交一旦有风波,你们随时可能走不成。
我也写信告诉我父亲,叫他先不要声张。当时我的弟弟在“文革”中受到牵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也担心会受影响。一直到1978年12月26日,我们启程赴美,报纸上刊登了消息,我父亲心里的石头才落地,才跟邻居朋友们说,“我儿子到美国去进修了。”
我们52个人分成5个小分队启程,当时中美没有通航,我们经巴黎到纽约,再到华盛顿,旅途将近20个小时。
我是清华小分队队长。同时,由于我年纪比较大,外语比较好,所以教育部指定我做总领队,帮助处理一些事情。教育部有关申请签证的信件由我携带。此外,还有一笔50美元的费用也由我带在身上,现在听起来觉得好笑,50美元,人均不到1美元。但这其实反映了当时国内的经济情况,我当时在清华当老师,月工资是79元。
这50美元在路上没有花,到了美国,我打算交给中国驻美联络处,也就是后来的中国驻美大使馆,他们也不接收。后来我和其他小分队队长商量,将这笔钱分给了5个小分队,买了几卷胶卷,让大家在华盛顿拍照留念。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出国,我也是。因此,尽管在国内进行了选拔考试,但到美国后,我们还是分别在美利坚大学和乔治城大学进行了三个月的强化英语学习。之后就分赴各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紧张学习。
见证中美建交、小平访美
1978年12月26日,我们启程赴美。12月26日是美国的圣诞节假期,为何要选择此时出发?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
首批赴美访问学者团队原定1979年年初出发,行程提前是因为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将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我们要赶在中美正式建交及小平同志访美前到达美国,为中美建交及小平同志访美做准备,营造气氛。
我觉得我们第一批访问学者,和第二批、第三批以及以后的访问学者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我们更幸运,或者说更幸福。因为我们不仅是在美国学习了两年,更重要的是见证了中美建交,特别是在华盛顿期间,参与了小平同志访美的主要活动,非常激动人心。
1978年12月26日早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现在回忆,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欢送出国留学人员,这是唯一一次。当天晚上我们登上飞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亲自到机场欢送。后来伍德·科克成为首任美国驻华大使。
1979年1月1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正式挂牌,升国旗。我们52人和大使馆工作人员一道,站在大门口高唱国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心情可以说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这段历史虽然时隔40年,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时任美国总统卡特邀请,踏上了访问美国的行程。
我们52人分成两拨,分别于1月28日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和1月29日上午在白宫迎接小平同志及卓琳女士。我有幸在白宫南草坪欢迎小平同志。欢迎仪式非常隆重、规格很高,先是鸣19响礼炮,之后卡特陪同邓小平检阅美国六军仪仗队(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国民警卫队、海岸警卫队)。我们就站在白宫草坪上,近距离听了卡特和邓小平历史性的发言。
紧接着卡特总统的夫人为卓琳女士举行招待会。招待会规模很小,我们52名访问学者全体出席。卓琳女士代表小平同志语重心长跟我们讲了好多话,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后来,我们第一批52人都按期回国了,在各自领域做贡献,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我们的重托。
40多岁时和大学生一起学习计算机
随后,紧张的学习开始了。因为与世隔绝多年,我们当中许多人对于去什么学校、学什么,不是很清楚,大部分都依靠美籍华人等的帮助介绍。我独自一人去了威斯康星大学,这源于“文革”期间我在清华校办工厂劳动时读到的《美国铸造学会会刊》中的介绍,当时威斯康星大学的铸造学科是美国最强的。
2012年威斯康星大学校领导来到北京,还专门给我颁发过一份证书:柳百成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到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的人士,也是中国第一批到美国的访问学者之一。
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了一年半,最后一个学期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材料与工程学系学习。总结起来,我在美国留学有三点收获:
第一,掌握了一批世界最先进的材料分析仪器,比如电子显微探针。这些仪器对于深入研究材料的微观世界十分有帮助,使我的研究工作大大提高了一步。学习期间我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其中一篇获美国铸造学会优秀论文奖。
第二,开辟了信息化与传统铸造业相结合的新领域。在房东太太家,我看到她八九岁的儿子在玩苹果电脑。在国内我没见过电脑,也不知道电脑是什么,但当时我敏锐地觉察到,电脑可能会改变人类社会。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学计算机,当时我已经40多岁了,跟20岁左右的大学生一起学计算机高级语言,这门课对我来讲很吃力。学习计算机语言跟学游泳一样,光看书不行,还要下水。好在美国的学习条件很好,机房24小时开放,我几乎每晚8点带一杯咖啡到机房,编程序到夜里两三点。
这一段学习经历对我回国后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开辟了计算机技术和传统铸造行业相结合的新领域。我和我的团队发明了国内第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模拟仿真软件“铸造之星”,把传统的铸造行业提升到了高端技术的科技水平。我于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第三,扩大了眼界,与国际学术界建立起长远的联系。我不仅在威斯康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还访问了密歇根大学、凯斯西储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世界各国的同领域专家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此外,铸造要和工程结合并进行产业化,因此要到先进的铸造厂去。我访问了通用汽车公司技术中心、福特汽车公司技术中心,还访问了工程机械巨头卡特彼勒公司。回国后,我仍和这些朋友及单位保持联系,为后面国际学术合作交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也是学习之外的重要收获。
从出国学习到出国分享自主技术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美正式建交,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
记得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的前三个月,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不用开伙,总有朋友打电话来请我吃饭。很多人想了解中国,而当时威斯康星大学只有我一人来自中国大陆。我也“来者不拒”,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正好借此机会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他们。
作为访问学者,我还多次被邀请去演讲、接受媒体采访。在麦迪逊一所中学的一次演讲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在互动交流时,有中学生问了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学生毕业后有没有失业问题?我理直气壮地说,No problem(不存在)。因为当时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全部是分配工作的嘛。
第二个问题,问我对美国印象如何?我想我总要说点好话吧,我说我在美国学到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三个问题接踵而至,问我想不想留在美国?我毫无犹豫,用了一首歌曲中的一句歌词来回答,这首歌是我小学时学的,歌名是Home,Sweet Home(《家,甜蜜的家》),“Home, home, sweet, sweet home. 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家,甜蜜的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比不上我的家。)全场响起掌声。美国学生也佩服中国人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那个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在国外,时刻想着维护中国人的形象。记得我在乔治城大学进修英文时,哥伦比亚电视台采访我时问,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中午吃饭都喜欢买鸡肉?事实上,我们留学期间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400美元,鸡肉是最便宜的,但我不能这样说,只能告诉他,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吃鸡肉。
哥伦比亚电视台播出采访后,又引出来一个故事。我有个中学同学在“文革”期间到美国纽约定居,他在电视上看到了我,马上飞到华盛顿,来乔治城大学找我。他问我,“文革”期间有没有受苦,要不要留在美国?当时很多人想,你们经历了“文革”,好不容易出了国,是不是要想办法留下来?我坚定地说不,我是要回国的,他听了也很受鼓舞。我在美国两年,他经常来看我,冬天还会寄些厚衣服给我,至今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
1981年1月2日,我如期回国,心想还不知哪年能够再出去。当时没想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越走越宽广。仅仅3年后的1984年,我就再一次出国,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出国接近100次,其中三分之一是到美国。我们从最初去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到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比如浇铸核电站使用的一个特大型钢锭,重400到500吨,全世界除了日本就只有中国才能铸造,我到欧洲去作报告,人家也很钦佩。除了学术交流,近年来我也积极地在国际上奔走宣传和解读中国的制造强国发展战略。
当年52名访问学者,有7人当选院士,其中3人来自北大,3人来自清华,还有1人来自北京邮电大学。我们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为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我们看到海外留学人员大批回国已经成为常态。
52 名" 首航學者" 名单

注:*为部分学者的某个信息不祥资料来源:根据受访者提供的资料及公开信息整理 资料整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姚冬琴 制表:《中国经济周刊》采制中心
(口述:柳百成;撰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姚冬琴)
责编:陈惟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