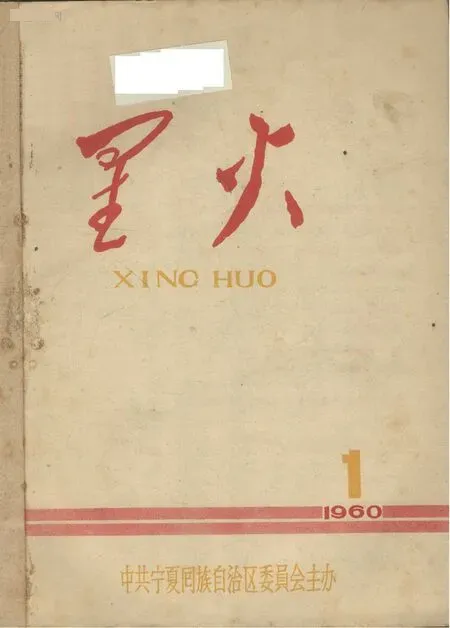理论:幽灵or烈日
○聂 梦
理论:幽灵or烈日
○聂 梦
得知丛子钰也在偷偷写小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然后是疑虑。
之所以“惊讶”,是因为通常读到他的文字,都是在那家与共和国同龄的重要文学报刊上,那样的思路和语调,似乎和文学创作相去甚远;之所以“疑虑”,是因为我固守成见——这成见一方面源于自身的悲惨经历,一方面也融合了周围的一些实例——一个终日与哲思为伍的人,又能把小说写得多漂亮呢。
这似乎又要扯到文艺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上了。在各自的领域里,两者通常都能够自得其乐,一旦衔接在一起,却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人说,这证明了理论之灰与文学之树之绿。话很有道理,但也仅仅是就不成功的文学评论而言,道出的是两者别扭关系的一个侧面。事实上,具体到写作中,倘若对形而上的理论光环念念不忘,又何尝不是要陷入另一种尴尬的境地呢。这就好比一个人,既不是萨特也不是加缪,却非要将一团空虚却厚重的迷雾,与不断拔节生长的情节、人物嫁接起来,其操作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文艺学爱好者来说,思辨的热情越高,创作的灵感也就越微茫(是的,我便是如此)。但丛子钰却并不这样。
在这篇名为《轮胎》的小说里,他明晃晃地展示了一种建构的雄心,一种对沉默不语和滔滔不绝的双重热望,以及一种让理念入侵灵韵的执念和能力。
这些雄心和能力集中体现在一表一里两个层面上。表层逻辑探讨的是在与世界的竞赛中,人类如何积极反抗外在的强制,并时刻提防内在的崩溃。深层逻辑关注的则是,庞大的体积如何在短暂的叙述时间中得到集中表现,同时又不会因为过度集中而失去对整体的暗示和对细节的铺陈。前一种逻辑对故事的完整性负责,后一种逻辑对小说的完成度负责。
运行在上述逻辑之下的,是一个发生在远东的“老人与海”的故事(这是一种偷懒的表述,仅就小说意图而言,《轮胎》比《老人与海》更为复杂)。事实上,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些意料之外的经验从何而来——通常年轻的小说家似乎更擅长描写流浪和爱情,又是如何令人信服地安置在小说里——丛子钰表示,从他父亲那里听到的零碎内容占据了事件的主体。虽然文中不时闪现的精彩表述一直试图提醒我们,眼前这位写作者经受过良好的文学训练,深谙文学的常识与非常识,懂得如何向各位大师致敬的同时彰显自我,但毕竟这些老道的可实践的知识储备,并不能解决双重逻辑与“老人与海”接洽的全部问题。
丛子钰的选择是写瞬间。
可以说,这一选择,实现了写作者小说智慧的集中彰显。所谓瞬间,并非地铁花瓣的瞬间,而是人性中忽明忽暗的某个瞬间,它们可以是眼波的一次流转、思绪的一轮滚翻,也可以是一个具体的点,或者撑起回忆乃至虚构里一切最富实感的时间。针对老徐“摆手”和“大笑”的问题,我们曾经展开过讨论。丛子钰的回答是,人与自然的抗争是多重的,它既成为老徐与章鱼搏斗时所需要的勇气和耐心,又成为获得失望结果时人们不得不去努力拒绝的失望情绪。大笑,究其本质,是人与自身茫然胜(shi)利(bai)的角逐,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这显然是一种新鲜的融洽,理念与异质经验,庞大与瞬间。
不论它们接下来在不同的读者那里究竟会走多远,眼下可以肯定的是,理论的介入,并没有在经验的转化过程中捉襟见肘,或者用力过猛,而是收到了颇为理想的效果:它让小说于叙事节奏之外的每一处停顿和冥想,都摆脱了花腔的嫌疑,而充满了结实的密度和质感。与此同时,理论强大的清洁功能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它将作者的表述,与时下流行的略带痞气的叙事,以及某些书卷气过分浓厚的知识分子写作区分开来,一种热情的、跃跃欲试的文明感提升了小说的辨识度。
本雅明说,眼镜在鼻子上,秋天在心中。对于从子钰而言,理论并非幽灵,而是烈日——所有萎靡的晦暗的经受不住考验的东西都要退到暗影里去,一切必须明朗,必须在思考中嗞嗞作响。在他的语境里,永远过着炽烈阳光炙烤万物的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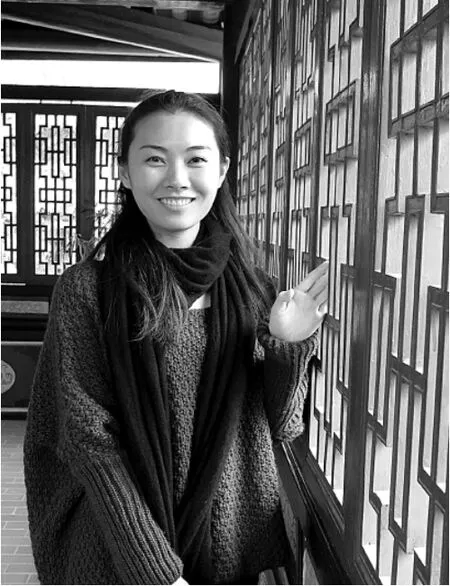
聂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85后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