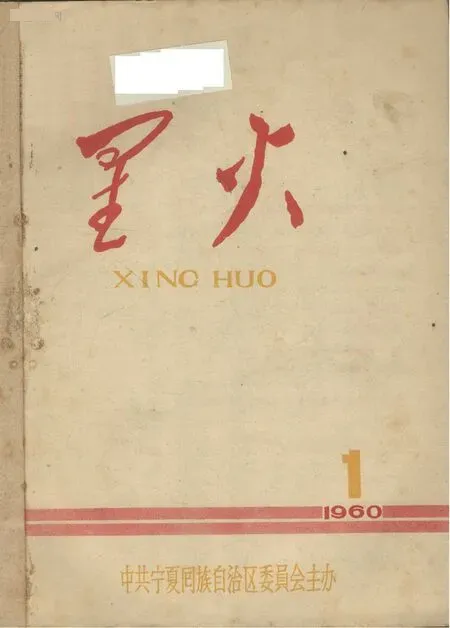像电影那样
○章 元
像电影那样
○章 元
“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姑娘!就算再过一万年,我也还是这样的姑娘!”
我给这段话配了一张会议室开会的现场照片发到朋友圈——逆光,会议桌上有七个杯子,我的杯子不在其中。他第一时间用我们的“恋爱专号”发来微信:“白雪公主在哪里?”我没忍住,扑哧一下笑了,还笑出了声。主任瞪了我一眼,我故意低下头,中午才做过的长直发哗地一下倾泻下来,恰好把主任的目光挡住。Perfect!耶!现在可以美美地抽上一支烟了。
刚把烟点上,对面那个怀了孕的年轻寡妇,就立刻掏出斯塔斯牌防霾口罩戴上了,还顺便用眼睛恶狠狠地朝我开了一枪。我也没客气,直接朝她的肚子回敬了一枪。是呀,我就这样,怎么了?难道在座的其他人不想知道,她肚子里那个传说中的遗腹子,为什么直到亡夫的周年忌日还没有出生吗?我们可是都看见了,她亡夫住院那会儿,本市首富王秃子的豪车可没少把她从医院接出送进。现在倒好,天天说预产期到了,预产期到了。这话说了两个多月,陪着听众度过了情人节和清明节,眼看就要连儿童节也一起过了。到底生还是不生,想好了没啊!
看我做出了示范,主任也华丽地掏出烟准备点上。无奈,伴着妩媚寡妇颇为夸张的干咳声,主任只好又把烟塞回烟盒。
“待会儿谁去采访清扫队的林大姐?”主任问。
寡妇咳嗽得更剧烈了,她索性举着肚子站起来,悠然地走到身后的窗前,打开窗子,朝着左前方市委大楼的方向卖力地咳嗽,好像那里有人能帮她申冤似的。我真担心她这么咳下去会早产……嗯,这么看来,她是肯定不会去了,其他人呢?唉,那还用问么!肯定和我一样,都在低头玩手机呗!报道这种普通清扫工拾金不昧的事,既感动不了中国,又没什么好处,谁愿意去啊?
“林大姐在半个月前,也就是这个月的三号,晚上八点多当班的时候,就在咱们脚下的这条人民路上,捡到了一个旅行袋……”主任敲了敲桌子,妄图赶走大家的瞌睡,看到有人抬起头,他继续抑扬顿挫地说道,“发现里面装着——现金——五十万!”
五十万现金呀!有人吹响了口哨,大家都笑了。
“五十万,在咱槐七市——人民路上的房子算最贵的了吧?那也足够买一套两居室了吧……”
“人民路上的金帝豪府,一套两居室可要六十七万呢!”寡妇头也没回地说。
我望着寡妇的背影,从心底为她这种努力成为众矢之的的勇气点赞。我们都知道她刚在本市最贵的金帝豪府买了房,还是一次性付了全款。而之前,为了给她的亡夫治病,看在她已经卖掉现有住房还不够医疗费的份儿上,在座的每个人都给她捐了钱。人的变化可真大,想开了就行。
主任被打断了,却依旧面不改色地接着说:“可人家林大姐呢?一个从农村来的合同工,就愣能不动心,还主动交公,积极寻找失主,这是什么样的情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样的事,不值得我们激动吗?不值得我们好好采访报道吗?——待会儿谁去?”
我继续玩我的微信。看来他今天不忙,居然能用“恋爱专号”聊这么久——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晚上就吃红烧带鱼吧,你早点回来做给我吃呗,你做的最好吃啦!——红烧带鱼有什么好吃的?我这儿有更好吃的!宝贝,你想我了吗?不过我最快也得十点才能到你那。省里突然来人了,一会儿做完工作报告,我得接待他们一下。
“我去!”我一时没控制住,对着手机脱口而出。去,不是动词。
我们已经半个月没见过面了!对,就是从三号到现在,整整半个月没见面了!今天中午我还特意去做了头发,结果……我去!省里来的什么人这么讨厌?竟然要被“接待”到十点,还是“最快”?!我去!我去!我去!!!
当“去”不是动词的时候,“我去”就成了一个特别能表达强烈愤慨的词,可比微信里那个愤怒的表情符号有力多了。给他发完,我把手机扔到会议桌上,盯着寡妇的背影,气冲冲地点燃我的第二支烟。从她站的位置望过去,市委大楼五层左起第三个窗户,就是他的办公室。我真恨不得用眼睛在这两个窗户之间架起一条索道,像动作片里演的那样,轻盈地滑过去,一脚踹碎他的玻璃窗,跳到他的办公桌前,冲他大喊:“我去!以后你再也别来找我了!老娘不稀罕!”
“好,就让乔诺去!散会!”主任笑眯眯地朝我点着头说,边说边往外走,一边走还一边嘀咕,“管你是不是动词。”
我——去!
也许就是这种浑不吝的二百五性格,才成就了我和他的奸情吧。
七年前,他是环卫局的二把手,我是刚到报社的实习记者。我们这对本来不会有太多交集的奸夫淫妇,因为夜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便朝着成为狗男女的方向迈出了坚定而扎实的一步。那晚的雪让他无法抽身回老家探望病重的父亲,他选择身先士卒,和一线职工一起,半夜出门扫雪,只为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就这样,他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只能在父亲的遗像前长跪不起……人民好公仆的形象新鲜出炉,只差一篇可以用于昭告天下的文章了。
像这种报道领导事迹的美差,为了实现真正的公平公正,一般都是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由谁去。也许是为了安慰初恋失败的我吧,那个阄竟被我抓到了。但我显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去投资未来的人脉,我只是分外真诚地盯着他的双眼,深情地问:“雪,谁都可以扫,可父亲只有一个,明知父亲病重,您还不赶回去看他,还去扫雪,您觉得您这么做合适吗?”
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足以证明那次失恋对我的打击有多大。没办法,谁让我就是这样的姑娘呢?初恋男友不就是因为他妈不同意,才决绝地与我分手了么?男人为了父母,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他当时被我问得愣住了。
后来,当然还要有“后来”。我和他坐在路边的烧烤摊前,频频举起劣质白酒干杯,以示宴会气氛热烈。他再次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小孩被美国大片毒害得太深了,那些电影中宣扬的“家庭至上”的价值观,被你们当成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像《拯救大兵瑞恩》那种,为了一个人,牺牲了那么多人,值得吗?那些人的父母又该怎么办?《2012》里,为了一条狗,差点耽误了开船,让一船人跟着陪葬,那就是尊重生命吗?你们这些小孩就会跟着瞎感动,被洗脑了都不知道。那是自私!懂不懂?是自私!整天玩个性,强调自我,你们就不想想,没有国家,哪来你们的“自我”?!那些电影你们算是白看了,都没想过人家是怎么通过电影进行文化洗脑创造GDP的……
他吧啦吧啦地说个不停,脸上现出不知是因为喝酒还是因为激动才有的红晕。我使劲睁着醉蒙蒙的双眼看着他,觉得他好可爱。事实上,那天当我问完他“您觉得您这么做合适吗”,他本能地愣了一下,然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是父亲的儿子,也是人民的儿子……那时,我真觉得他好可爱。真的好可爱。我一点都没有想吐的意思。真的。他是真诚的。特别真诚。我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我没办法不被他的真诚打动,没办法不尊重他的真诚。他是那么地相信他所说的话。
“我娘就是在雪天里跌了一跤,再也没起来……”采访结束时,他说。
可是,我今天还是吃不到他做的红烧带鱼啊!我不高兴了。我去,我去!
“乔诺,林大姐和小李还在接待室等着呢,你去把他们领到会议室聊聊吧。”
主任在楼道里把我叫住。我一边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一边听他啰嗦。
“不要写成千篇一律的好人好事,要深刻,要挖出人性中最闪光的那面,不是每个人都能对着五十万现金不动心,咱们槐七市能不能出个最美清洁工,可就看你的了。那可是五十万现金呐!”
我去!看来就算我没骂出那句“我去”,这件事也会落到我头上喽?
“主任,您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要让我去呀?”
主任倒是也没客气,嘿嘿一笑。
“你是环卫工专业户嘛,交给你,我放心!当年采访市长那篇,写得多好!多有新意!多感人!让人过目难忘!我相信你的实力,争取再抱个奖回来!”
自从两年前我们槐七市的一把手被“双规”后,每个人在提起他这个代理市长时,都自觉地把“代理”去掉,好像他已经被正式加冕了似的。拍马屁也好,民心所向也罢,反正他刚当上“常务副”,就力排众议,在西边那片荒地上建了一个“一定要超越横店”的影视拍摄基地。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金门大桥到尼加拉瓜大瀑布,从艾菲尔铁塔到英国大笨钟……既有按一下按钮就能被洪水淹没了的美国小城,又有随时可以炸掉的迪拜帆船酒店模型,四季常绿的假竹林,爱怎么烧就怎么烧的土坯茅舍……那真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别说穿越三生三世了,就是想穿越到其他次元,拍一部集魔幻、灾难、历史、动作、爱情、恐怖、战争于一体的电影都不是问题。保证足不出国,拍尽全球!
他提出这个构想时,我们还是清白如水的好朋友。整个槐七县——彼时还是县——的大街小巷,无数烧烤摊前,都留下了我们喝多后蹒跚离去的身影。那时他没少为我的价值观操心,我则永远一副不屑一顾玩世不恭的神情,唯一能让我们之间不那么剑拔弩张的话题,就只剩下对这个影视拍摄基地的构想了。也许是因为实现起来实在太过遥远了吧,所以我们才幻想得格外卖力。西边的那块荒地,在A4纸上被我们描绘得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美轮美奂。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知道,我们都是那么地爱看电影,只是他的电影梦做得更宏大一些罢了——我爱那个时候的他,真爱。
那时,他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把握十足地向我预言,在经济整体低迷的时候,文化产业必将异军突起领跑全国经济。我们这种小县城如果继续把钱扔在房地产开发上,肯定是死路一条。然而土地又是人类不可再造的资源——没有之一,这决定人们不可能将目光从土地上挪开。槐七县作为一个人口不多,没有矿产,没有支柱产业,没有名人,既不靠海也不靠河没有地理交通优势,要什么没什么的小县城,手里有的恰恰是大把大把的土地。该如何利用?太值得深思啦!毫无疑问,建造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吸引全国的剧组到这里拍摄,带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增加居民收入,解决就业问题,打造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才是最好的选择。
你得承认,当你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参加工作的小姑娘时,这些高屋建瓴的宏伟构想,基本上只能起到催情的作用。他说得激情澎湃,我的眼前却没有浮现本该浮现的美好前景。我只是问他,你爱我吗?他说爱。但是他不能和我在一起,因为他是有家庭的,这么做是伤害我……family!又是他妈的family!去他妈的family!美国电影中的“家庭至上”到底毒害了谁?!
那个晚上,他把几乎半裸的我重新用衣服包裹好,深深地吻着我的额头,然后说:“我不能伤害你。”
他是真诚的,我相信他。我永远相信他对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诚的。但他也应该想到,像我这样的姑娘在遇到这种事后,会干出什么事来——我和报社里的同事闪婚了,完全忽略了他从环卫局一把手变成副县长的新闻。我给他送婚礼请柬时,本以为他会黯然神伤,甚至上演个私奔什么的也不错——我们不是都爱看电影么!我一生都在等待如电影一般轰轰烈烈的场景啊!可没想到他竟然又一次一本正经地恭喜了我,还送了我一套《史记》,书页里甚至没夹带只言片语。恭喜你妹呀恭喜!从此,我和他没有半分交集。直到一个月后,街头巷尾议论起新副县长劳民伤财大兴土木想要建影视拍摄基地,我才意识到,他不能伤害我,没有和我私奔,也许是因为他心里有着更大的梦想。我轻而易举地原谅了他,于是也就跌进了更深的思念。
建造影视拍摄基地的项目规划,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上马了。从奠基仪式举行的那天起,就不断有剧组涌到这里,真正实现了项目还未竣工,投资已基本回笼。原因显而易见,凡是那些实景不让拍的,或者实景拍起来成本很高的地方,这里都有以假乱真的复制品,可以随便拍,剧组为什么不来?顺理成章地,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槐七县,靠着影视基地的名声也变成了槐七市,县政府的招牌换成了市政府,原本就是作为形象工程展示出来的人民路,这下子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市政府、写字楼、高档社区、商场、银行、饭店、KTV、超市、洗浴中心、市民广场、纪念碑、医院、学校、报社、电台、电视台、通讯公司、邮政局、影剧院、装饰城、博物馆、图书馆、公安局、法院、民政局、国税局、教育局、卫生局、房管局、文化旅游局……这座小城市里所有稍微有点用的机关部门,几乎都在这条路上,而完成这一切不过用了短短四年光景。
槐七市的每个人都在干着和电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事,人均收入打着滚儿地往上翻,传统媒体如此不景气的今天,我们报社依旧没有裁员。王秃子竞标成功,成了影视拍摄基地二期工程的施工方,正式跃为本市首富。三期工程也在积极规划中,当初那些激烈反对的声音,如今同样激烈地支持着这个项目。就在市民们畅想着自己的城市将像戛纳、柏林、威尼斯、蒙特利尔、卡罗维发利一样,在电影史上永垂不朽的时候,市里的一把手被“双规”了。
所有人都认为一把手的落马一定和影视拍摄基地有关,并暗自揣测,身为常务副市长主抓这个项目的他,用不了多久就会身穿橘色马甲站在被告席上,而拍摄基地的规划将会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王秃子和王秃子们会赔得连肝都吐出来。现在随便什么项目不都可以成就一批奸商和贪官么!槐七市完了!可是,没有。他还在。他还能隔三差五地临幸我一下,当然是以代理市长的身份。
那会儿我真的是担心坏了,只要他不在我身边,我就要刷屏看看有没有他被“带走”的消息。他知道后还是一本正经地问我:“我有没有给过你一分钱?我有没有给你调动工作,让你升职?我有没有带你出国旅游购物?我有没有给你买房买车买表买包?你是我最心爱的女人,我都没用我手里的权利为你做一丁点儿事,我还会去做别的吗?”
他的这段廉政表白,因着那句“你是我最心爱的女人”,把我听得心花怒放。可我转念一想,我都是你最心爱的女人了,你凭什么不为我做点什么,不对我好点呀?张爱玲还要胡兰成给她买衣服呢!
“我对你好也得用我自己的东西对你好才行呀!”
他的话,被我成功地引向了淫荡的范畴。我的心,也彻底踏实下来。我相信他,一如既往。
就像是为了证明他不能陪我吃饭确实事出有因似的,环卫局里负责宣传的小李一进会议室的门就告诉我,他们很快就得走,省里来人了——省里来的人没开公务车,但高速公路收费口的工作人员还是认出了其中几个,于是迅速向领导做了汇报——林大姐负责清扫的区域,正好是市政府所在的人民路,她得待命。
“和市长当年负责清扫的区域一样,他扫了八年呢。”我说。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几年受他的影响,我也“谨慎”了许多,人前绝不提他,生怕流露出一点“不正常”。今天这是怎么了?难道是为了让采访对象放松,才故意这么说,以便拉近距离?
“这么巧?我刚到局里不久,都不知道这事。林大姐,看来你也要当市长啦!”
小李打趣地说,却把我听得浑身不舒服。他扫过的又怎么了?就被他开过光,沾上仙气啦?
“我们林大姐可不想当市长,只要这次局里转正的名额里能有她,把城市户口落实下来,儿子明年高考能占点便宜就行!从农村考出来多难啊!是吧,林大姐?”小李笑着说。
林大姐赔着笑,没有说话,一双手不知放在哪里才合适。我拿了两瓶矿泉水放到小李和林大姐面前。这个和成龙的妻子同名的林大姐,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弹起来向我表示感谢,我怀疑她的屁股可能一直是悬在椅子上的。她实在太黑太瘦了,戴着帽子罩在工作服里的她,身上看不出一丁点儿女性特征,满脸褶子,保养得还不如我奶奶好呢!可资料上分明清清楚楚地写着她跟他同岁,才42岁啊!他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一丝一毫当过清扫工的痕迹了,可她呢?仿佛天生具备清扫工的DNA似的,从头到脚都写着“清扫工”三个字。命运啊,太可怕了。
“俺早晨扫地的时候,经常看见市长!他还送过俺一个口罩,让俺注意身体。”
林大姐看起来不那么紧张了,脸上也有了笑容,说着还从工作服的口袋里把口罩掏出来给我看。斯塔斯。和他平时戴的是一个牌子。他曾试图说服我也戴上这种号称可以防霾防SARS的口罩,结果只是被我无情地羞辱了一顿。这不是明摆着的么?我那么讨厌那个年轻妩媚现在还怀了孕的寡妇,怎么会堕落到和她戴同一个牌子口罩的地步?我不怕雾霾,雾霾越严重,我越可以少活几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不是啊,亲?”我嘻嘻笑地调戏他。他却戴上口罩,从猫眼儿使劲窥探一番,然后才蹑手蹑脚地打开大门,走出房间,走出楼道,走到大街上,走在阳光下。感谢雾霾吧,没有它,他怎么能够堂而皇之地戴着避人耳目的口罩从我的大门走出去?等等,这种只在网络上销售的口罩,他怎么也有?他有空网购么?
“为了节省公务开支,市长经常走路上班,有老百姓把他认出来,他就停下来,和大家打招呼,一点架子都没有,特亲民。咱们真是遇到好市长了!”小李热情洋溢地说着,好像此时有部摄像机对着他。
“失主找到了吗?”我翻着林大姐的“事迹材料”问。
从背后那扇被寡妇打开的窗子里吹进来的风,把我手里的纸吹得直响。那五十万现金是谁的?是乡村教师为身患白血病的留守儿童募集到的救命钱,还是土豪迎娶儿媳妇的聘礼?两者的差异,何止千里!
“算是找到了吧。”小李代替林大姐回答,“那么一大笔钱,只有找到失主,才能更好地传递社会正能量。公安局也挺重视这事的,跑了市里的好几家银行问,那段时间取过那么一大笔钱的,只有王秃子,可王秃子愣说他的钱都发工资了,没丢。”
“也许不是一次性取出来的,是分了好几批才凑到一起的,准备拿去买房,一次性付款也说不定。”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分析着。比如那个伟大的寡妇,她不就是这样的嘛!
小李不以为然地撇撇嘴。
“号码都是连着的,银行有记录,可王秃子就是不承认!又没人查他的税,承认了又能怎么样?他怕什么?现在他不承认,公安局也不能愣把钱塞给他,林大姐这事就只能这么悬着……乔诺姐,您看怎么写效果好就怎么写,我们保证配合!我们林大姐能不能成最美清洁工,就看您了!”
我去!怎么又是这套?我是记者,又不是作家!能不能最美,关我屁事啊!
“乔记者,找没找到失主对俺这事有啥影响?”林大姐突然插进来一句。
如果我是猫,我想我已经闻到了鱼腥味。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吧。我看了林大姐一眼,故意笑得内涵丰富。
“俺见着失主了……”林大姐果然开口了,看到我和小李吃惊的样子,她赶紧补充道,“是背影。他往墙根儿那一站,把袋子往旁边一放,一看就知道是要尿尿的,俺哪好意思看?就把脸背过去了。估摸着他完事了,俺一回头,人早就没影儿了,只有袋子在那。”
“要是再看到他,还能认出他来么?”我问。
“俺……”
“林大姐,乔诺姐是咱自己人,最了解咱环卫工了,有什么说什么,没事!我先接个电话哈!”小李扫了一眼嗡嗡作响的手机,接了起来。
我最了解环卫工?哪方面?肉体还是灵魂?
七年前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清扫队盛产劳模。我当时被他逗笑了,后来听他说完,又觉得这事其实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清扫队的活又脏又累,还被人看不起。冬天冻得想哭,夏天热得想死。下一场大雪就能摔伤好几个,下一场大雨就有掉进排水井里溺毙的。凌晨三四点开始工作,那时马路上跑着的,不是酒后驾车的,就是疲劳驾驶的,遇到了,立马被撞飞,哼都不哼一声就去见了上帝,还找不到肇事者。最要命的是,这工作待遇还特别低,搬砖头一天还能赚一百五十块呢,清扫工一个月才两千出头……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光站着就够你受的,何况还得扫呢?前脚扫完,后脚就是一地的烟头、口香糖、塑料袋,这几年养宠物的多了,狗大便也多了……你要是说两句,对方能回你十句,说那就是你的工作,他们不乱扔东西,你就失业了,满嘴歪理。赶上脾气不好再喝点酒的,就能动手打你……”
他激动得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水。我注视着他的目光里,忍不住多了几分温柔,就连他身上洗得发白的制服,都显得格外俊秀英挺。顺便说一句,他长得非常好看,是那种看着特别舒服、让人觉得特别踏实可靠的好看,还带着一股不容侵犯的正义与严肃。这或许得益于他曾是一个十七岁进城扫大街的清扫工,以及后天在领导岗位上的顽强进化。
我得承认,那时初出茅庐还是实习记者的我,在失恋的作用下,完全被他身上成熟男子的凛然气势震慑住了。我已经无法再去纠结“您觉得您这么做合适吗”,取而代之的只是赞赏。但我可以保证,那只是单纯的赞赏,从未幻想把这份赞赏带上床。而他的记忆和我的版本则有些出入,在他看来,我那时的眼波,早已是一汪春色。这个淫荡的玩意儿!
就是这个淫荡的玩意儿,不着痕迹地向我阐述了清扫工的种种艰辛不易,让我在身不由己地对他满怀敬意之余,还顺便对他的个人履历做了一番粗浅的了解——省劳模,自学高中课程,高自考本科学历,在党校完成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人民好公仆……结果不用问也知道,这篇采访写得情真意切——按照主任的话说就是:多有新意!多感人!让人过目难忘!——还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我顺利转正,他则成了环卫局的一把手。
同样来自农村扫着人民路的林大姐,该如何因着捡到的那五十万元现金,在劳模辈出的茫茫清扫工的队伍中脱颖而出呢?我都替她愁得慌!
小李挂上电话,我和林大姐齐刷刷地望着他,似乎他有必要把通话的内容传达给我们似的。
“他们已经到了,正听市长作工作报告呢,咱不着急了,慢慢聊。”小李说。
我情不自禁地扭过身望了一眼窗外。五楼左起第三个窗户的房间里,此时应该没有人了吧。
“乔诺姐,您当年的那篇文章激励了环卫局的多少职工啊!不想当市长的环卫工,不是好环卫工!现在还激励着我们大伙呢……”小李说。
要不是有人给小李发信息,真不知道他还会蹦出什么恶心的话来。可我怎么说才能让别人相信,我真不认为他的升迁和我的采访报道有任何关系。他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干出来的,我只是实事求是地报道而已。但这似乎也并不妨碍那篇报道出来后,他从内心深处涌起请我吃饭的冲动,于是那个烧烤摊前便留下了我们频频举杯的倩影。我想,他大概就是在那一晚,酒醉后的我痛斥我的初恋情史时,爱上我的吧——“你让我心疼。”反正后来他是这么说的。那时我一边吐一边哭,反复质问:“为什么?他为什么离开我?”为了不让我跌进自己呕吐的秽物中,他使劲揽住我的腰,念叨着:“你们这些小孩呀,你们这些小孩呀……”
我喜欢那时候的我们。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出入任何场所。我们心无旁骛。我们天地坦荡。我们谈情。我们也说爱。我们朝着苟合狂奔而去。我带着义无反顾的勇气与决绝。他,他却悬崖勒马……他那时没告诉我,他快要当副县长了,于是我只好怀着对一个男人最深沉的敬意与爱意,视死如归地结婚去了。
我以为我的人生从此可以看到尽头:买房子、结婚、生孩子、换大房子、孩子上学、为孩子准备房子、等着孩子结婚、等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再帮孩子换大房子……生活中就他妈的只剩下孩子和房子了。如此无望。但是——妈的,“但是”万岁!人走起运来,神仙都拦不住!我怎么会料到我竟嫁了一个那么争气的丈夫!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他就和报社里的男同事旧情复燃了,我得以迅速成为前妻。真是谢天谢地,我不用因为输给一个女人而含羞饮恨了。
从民政局出来,枣红色金字小本儿变成了枣红色银字小本儿,我成了一个有房无贷有车无孩的离异人士。点上一支烟,迎着阳光,盯着枣红色银字小本儿,我笑了,笑了好久,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个黑影一闪,成了我的世界里唯一的天空。他一下子把我抱住,死死地把我抱住,像是要把我嵌进他的身体。我一只手拿着烟,一只手拿着离婚证,两只手僵硬地伸向天空,像极了祈祷。我想,这其实就是祈祷吧。我其实一直是在祈祷着什么的吧。
这可能是他这一生之中最疯狂的举动。那时他刚从影视拍摄基地一期工程的工地视察回来,坐着他的专车走在人民路上。灰头土脸满身疲惫的他,一眼看到我站在民政局的门口,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连忙喊司机停车。车还没停稳,他就窜下来,都没确认司机是不是已经把车开走了,就疯狂地朝我跑过来,然后一把抱住了我……那一次,他真疯了,疯得跟电影似的。
他说,在我结婚的日子里,他快疯了。他想我,他想我,他想我!问题是,在我结婚的日子里,要疯的是我好不好?就算我是一个这样的姑娘,也没必要非得经历那样的丈夫吧?而且,我还是那么地想他,想他……
和前夫离婚的当天,成了我和他大喜的日子。那天,我和他,在我曾经的婚房里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庆祝仪式,庆祝我们正式成为货真价实的奸夫淫妇。一切不可思议得就跟电影似的。我问他,现在你不怕伤害我了吗?他说,怕。
“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总会想不顾一切地干点自己想干的事。”他说。
我就是他想干的?是不是之一?那么,那个影视拍摄基地算老几?
“我每天都在想,难道有了影视拍摄基地,我就必须失去你吗?那个基地是我们两个人的梦……”他说。
那晚之后,我把门钥匙给他,用这种方式婉转地向他表明我对这段奸情的忠贞不渝。可这货居然拒绝了老娘!说是怕万一被别人看到了,不好解释。他还让我用我的身份证再去办一张电话卡给他,美其名曰“恋爱专号”。我当然会甩给他一连串的“为什么”,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我:“半年前,我还在环卫局时,领导找我谈话,这次换届,我会进班子,在各方面都得注意一些……”
所以他才和我保持距离,还送了我一套《史记》作为结婚礼物?我去!!!为什么没有听到这些时,我可以谅解他,听到他说了这些之后,我反而觉得恶心呢?我的爱情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的?怎么可以——这么脏!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等我娶你。”他说。
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亲爱的寡妇赫然出现在门口。她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托着腰,慌慌张张地奔向我身后的窗子。她这是怎么了?
“齐建立被抓了!”小李突然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抬起头说。他手里的手机就像一个炸弹。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别人这么连名带姓地叫他了,我一时还真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只听楼道里传来潮水般汹涌恐怖的脚步声,全都是冲着会议室来的。大门砰砰地被撞开,椅子被撞倒,暖瓶茶杯被撞碎,有人跳上桌子,有人掉了鞋子,有人被扯住了头发正在大呼小叫……我本能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是为了迎接那些破门而入的同事。不,不是迎接,是躲避,他们太可怕了,让我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碾碎。此刻他们不像我的同事,更像是被什么东西操纵着的铁甲战士,疯了一样地扑向我身后的窗子——那里,正是我无数次眺望他的地方,观察市委大楼的最佳位置。
他们举着手机兴致勃勃地拍照,他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纷纷,他们眉飞色舞地交换各自刚刚或者早就掌握的情报。他们谁都没有在听别人说了些什么。他们的目的只是说。那些话一字不漏地进了我的耳朵:寡妇是他的情妇,他在卫生局教育局电视台都有情妇,他在ABCDEF市都有房子都有家……王秃子给他送过钱,李秃子赵秃子张秃子都给他送过钱,胖子瘦子麻子矮子他们都给他送过好多钱……他们说的是谁?他吗?怎么可能呢!
在我的眼里,这个喧闹的会议室,此时就像电影一样,它喧闹它的,我的世界却是安静的。如此安静。我寻找着,寻找一个人,一双眼睛,告诉我,那不是真的。这不过就是一场墙倒众人推的闹剧,他还会像前任一把手落马时一样,最终依然傲然屹立在人们的视野中!他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
“俺捡的那五十万,是市长落在那的。俺打老远就认出他来了……”
“林大姐,你怎么不早说呢?齐建立哪来的这么多现金?这就是他腐败的证据!举报他!举报呀!举报有奖!”小李英明神武地为林大姐指点迷津。
我被人群挤了出来,脚下被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低头一看,是那个同样不知什么时候被挤出来的寡妇,此刻正狼狈地倒在地上。一汪液体在她的身下逐渐漫延,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闷住了的惨叫,随即,她不知从哪摸到一只男式布鞋咬在嘴里,死死地咬住,不再让自己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寡妇要生了!”有人叫道。
那人那么叫完,也就叫完了,欢快地从寡妇身边跳过,扑向可以看到“第一现场”的窗口。那人来晚了,再不快点,就把什么都错过了。寡妇倒在地上,痛苦地扭曲着身子,一只手护着肚子,生怕被激动的人群踩到,另一只手伸向四周,总想抓住谁求助,但又总是恰好被专心致志的人群小心翼翼地躲过。终于,她看到了我。
“救救我!”她用眼睛对我说。
我看着她。她的脸因痛苦变得狰狞,眼里却是那么的无助。她怀的是他的孩子?他的孩子!
“齐建立出来了!”
趴在窗户前的人群,像是被某种力量使劲从后面推了一把,再一次朝前涌动。如果这是一艘航行中的大船,这下,注定是要倾没了。有人喊,别推了,再推就掉下去了。那个声音同样被淹没在激动的人群中。从高楼上掉下去有什么稀奇?从高位上掉下去才是奇观!
我迅速忘掉寡妇,身不由己地朝那个地方涌去,望去——他,真的出来了。一阵事后被描述为“妖风”的风吹来,把他脖子上系着的领带卷到他的脸上,像是打了他一记耳光。人们后来说,那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他的恶行恶状了。可人们好像都不记得了,那阵风也从那扇用于直播的窗子钻了进来,同样吹打着我们,吹打着我中午新做的头发。
被风搅乱的头发,把我的视线分割得支离破碎。我,望着遥远的他。他手腕上那块黑色皮带的手表,因着手铐的存在,显得格外耀眼。也许只是在我看来。表,是我送给他的。他特别喜欢那块表,他说他会用这块表,记下我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这对白美得真跟电影似的。
“啊!”
寡妇终于迸发出了野猫被剁掉尾巴般的惨叫,嘴里咬着的布鞋滑落一边。人们被她的喊叫吸引,好像才刚刚意识到她的存在,终于有空俯视一下这个羊水破掉的待产妇了,可那目光却仿佛在看着陌生人。不,她是无法享受到对待陌生人的那种礼遇的!那目光是我身为一个记者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也许只有上帝才能解释里面为什么写满了“这个孩子是有罪的”。
“谁去看看怎么回事?”主任清了清嗓子问。
(作者提示: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请尽快自首。)

章元,巨蟹女,天津土著,中国作协会员。已出版发表中短篇小说《背日葵》《她和她的万家灯火》《我是你的白内障》等,长篇小说《空窗》《如此性感》《去年在我们的房间》等,戏剧作品《你喜欢星宝吗》《阿门,洋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