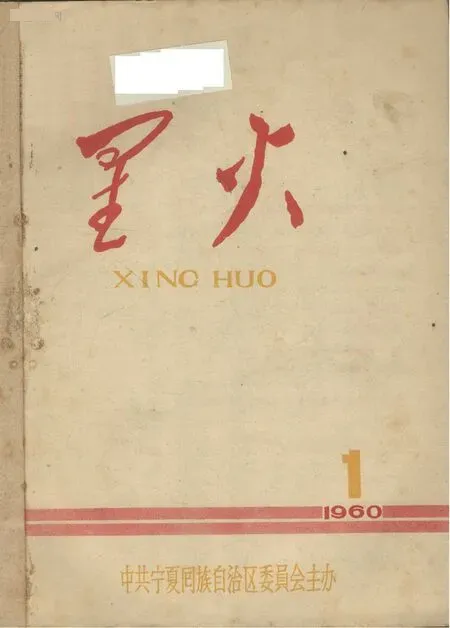冯秋子印象记
○鲍尔吉·原野
冯秋子印象记
○鲍尔吉·原野
头一回见冯秋子是在哪一年已经忘了,在楼肇明老师家——月坛北街——北京有没有这条街我也忘了。在座有止庵、苇岸、老愚、林燕和我、我妻子。楼老师之颜面一如既往地红润,白发四立。他拿起一本书放下,又拿起一本书。总之他始终拿着书,快速评说这些书的内容。止庵笑容里带着赞赏。苇岸低头思索。冯秋子自始至终没说话,笑容像瓦罐的清水。她双手放在一起。对蒙古人来讲,这是尊重主人的仪态。她衣着朴素,质地色调却考究过。
之后,我不止一次对妻子说:冯秋子多像牧区的女人。这话好像说了十来年。她的脸庞有瓷器的气质,有笑意(有人带笑容缺笑意),宁静,仿佛久远,也有点像陶器或玉器。为什么是牧区的女人呢?跟有些人说不清这件事。牧区的女人宁静(不只是贤惠),谦卑(不止于劳碌),仁慈,对苦难以及生命敏感,总之冯秋子像一个牧区女人。这个印象跟没文化、蒙古袍、挤牛奶没关系,指血统因缘。
跟她见第一面之后,我揣测她不可能仅仅是这样的人。就像爱睡觉的动物一般比较强悍。它的特点不是睡觉,而在奔跑搏击。胆小的动物都不爱睡觉。冯秋子安静的另一面应该和大的力量关联。
果不其然,2001年,我读到她的散文集《寸断柔肠》,这个书名不怎么好,书好。这本书怎么说呢?我想用批评家的语言描述一下,有困难,粗浅说一下吧。她的写作好像用石匠凿子对准人的太阳穴敲击,我读的时候会有战栗的感受。她写作,我猜想她的灵魂从科特迪瓦木雕式的头颅中冲逸而出,鞭挞天地,带着刀剑与镣铐的寒音。她追慕英雄,她写旷野无际,写罡风莫测,写见不到血痕的痛苦。冯秋子像一个刚刚经历海难的女人,远视大海。
这样,我看到她静穆平和的另一面,就像老唱片的A面与B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AB面,或ABCDEFG面。有人貌似富贵,另一面贫贱;有人装大文化,另一面机会主义。冯秋子在作品里扭住一个(几个)东西不放松。什么东西?那些践踏人之尊严后想从历史视线溜走的闹剧,被掩盖的老百姓的悲伤。她诅咒谎言和假隆重,她护卫伤口,不让别人在上面堆放油毡纸或MTV。她的宁静实际在表达自己的坚持——朴素、劳动着、信仰。
这是一篇印象记,我接续写印象。有一年(她儿子巴顿刚上小学),我去和平里她的家里做客,筒子间,我们坐在地毯上谈音乐。后来,冯秋子到走廊那一边的共用厨房炒菜,我在边上说话。巴顿大声谈论世界足坛的一切事情压倒我们的声音。冯秋子几度呵斥,用铲子敲击装满蒜薹的马勺。巴顿眼里带着泪光,哽咽道:我不让你俩说话。他比我们还委屈,真诚的泪水在眼眶里摇摇欲坠,真是可爱。
今年,我们在普兰店又见一面。舞厅里,她与何玉茹拉手跳一支坚定的舞,像女童,也像模仿火车轮子。后来她跳独舞,她跳舞跳得好,并不悲伤。
林贤治说冯秋子“更像一个诗人、钢琴家、大提琴手、夜行者、洗衣妇、迷幻的占星者”。顺这个喻体说,她还像在草地上找到一根针的人、镂刻圣器的工匠、露天电影放映师、擦拭银器的女工、裤脚被露水打湿的牧妇。冯秋子内心里与宽广干净的事物相依为命,信仰如群星在她头顶闪烁,故而,她的话越来越少。
她言语凝重,说出的话仿佛克服了许多困难才送达我们耳边。但不刺耳,发声用气息,而非嗓子。她边说边想,于是听她说出上一句之后,我想下一句她会说什么呢?有时,她废止话语,笑起来,长眼睛像一条线,像牧区的女人。

鲍尔吉·原野,姓“鲍尔吉”,蒙古族,著名作家,出版著作60多部,多次获得国内文学大奖,现为辽宁省公安厅专业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与歌手腾格尔、画家朝戈并称中国文艺界“草原三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