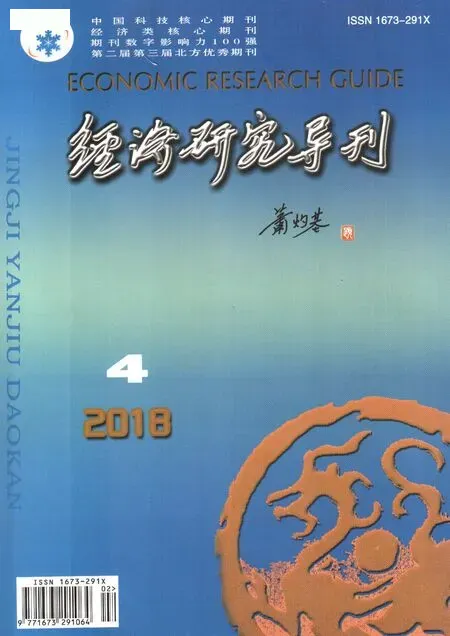《2006海事劳工公约》履约:船员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以影响评估分析为视角
张辰旭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从立法沿革上看,国际劳工组织自成立以来通过的劳工公约中,有超过1/5都是针对船员的。近些年,世界航运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未能得到及时更新和修改的早期公约及相关的标准不能与当今行业的实际需求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有害无利。从实践现状上看,国际劳工组织2006年之前的大部分海事公约,在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中的推广程度不一,给已批约国的政府和船东反而带来了经济上的劣势;且这部分公约一般只专注于单方面的问题,时有重叠或冲突。因此,公约的应用范围和为船员提供保护的力度都遭到了削弱。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船员的全方位的保护,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自2001年始,着手修订、完善、合并其于之前制定的海事劳工公约及协定;经过近五年的酝酿,2006年2月23日,在巩固和更新以往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件的基础上,《海事劳工公约》终告完工并获得通过。
《海事劳工公约》自2013年8月20日起,正式生效。2015年8月29日,我国正式批准加入《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2015年11月12日,中国向国际劳工组织递交了中国批准《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的批准书,公约自2016年11月12日起对我国生效(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一、公约关于船员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
该公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证船员的体面工作,以及保证船务公司(船东)在公平竞争中的经济利益,其内容覆盖了船员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全球超过150万船员的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证。具体在社会保障方面,根据《海事劳工公约》标准A4.5第一款的规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常见问题问答》4.5的第a段和第b段的解释,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指的是:“对由于病痛、残疾、生育、工伤、失业、年老、家庭成员死亡所导致的工作收入损失,无法负担医疗、无法为受赡养人提供支持以及处于贫穷状态、受到社会排挤的海员,以现金或其他方式给予保障。”
然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原本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健全程度差异很大,想要在国际层面上就社会保障问题达成统一有一定难度。鉴于此,公约首先承认各成员国自身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前提下,公约对各缔约国提出了至少应向住所在本国的船员提供医护、疾病津贴、失业津贴、老年津贴、工伤津贴、家庭津贴、生育津贴、病残津贴和遗属津贴这9个分项社会保障中的3项这一最低要求作为补充性的社会保障,以实现各缔约国对其原先的社会保障体系不造成更大影响的利益诉求。其次,公约要求如果在各缔约国未将船员作为普通居民(ordinary resident)囊括入原先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则应当将船员及其受赡养人囊括进该体系,并提供不低于岸上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再次,如果船员居住国和船员工作船舶的船旗国不同,两国应通过双边合作等形式,确保船员处于某一国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内。
二、现行船员社会保障制度及立法不足
从我国相关立法的层面上来看,《船员法》虽经过多年酝酿,仍然未能够最终出台,船员相关的法律只有在《海商法》中单列的一章(第三章)中的10个条文,就船员的界定、船员资格的获取、船长的权力、义务及责任等问题做了简单的规定,篇幅不足千字;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多个问题,《海商法》并未详述。针对这一不足,2007年开始施行并于2014年修订的《船员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没有针对船员的专门立法这一缺憾。该条例中的第27条、第52条的内容涉及船员的社会保障,分别规定用人单位应与船员签订符合社会保障制度要求的劳动合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责任。遗憾的是,受到部门职责和分工的限制,《船员条例》并未涵盖更多的关于船员社会保障的条款。除此之外,有涉船员社会保障制度的散见于《劳动法》《社会保险法》《海上交通安全法》以及各航运公司规章中。这其中,从法律位阶上来看,《船员条例》是行政法规;《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在效力上虽然较高,但其调整对象过于广泛,难以对船员这一特殊职业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保护;《海上交通安全法》同《海商法》类似,对船员权益保护的规定只有几条,远不能提供全面保护;而各航运公司的规章大多从船东立场出发,许多条款并不能真正起到保障船员权益的作用。由此可见,在立法和制度层面上,不仅相关规定的内容过于简单,而且法律位阶并不高,难以为船员的社会保障提供有力支持。
而《海事劳工公约》对我国的正式生效,对我国的船员社会保障制度又带来了新的挑战。《海事劳工公约》中涵盖了37个旧公约的内容,而在这37个公约中,中国只批准了其中的4个(即《1920年(海上)最低年龄公约》(第7号)、《1921年(海上)未成年人体检公约》(第16号)、《1926年海员协议条款公约》(第22号)和《1926年海员遣返公约》(第23号))。可见,在中国批准《海事劳工公约》之后,需要在国内立法层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履约的要求。具体而言,对照《海事劳工公约》的相关规定,在船员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中国与《海事劳工公约》的差距主要体现在:(1)关于船东财务担保的法律规定缺位;(2)海员医疗报告表格没有统一标准;(3)没有一套关于船上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的国家导则和船上职业安全和健康保护和防止事故的统一标准;(4)缺乏海员使用岸上福利设施及建设港口福利设施的规定。
三、船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评估分析
(一)船员社会保障制度对船务公司的影响分析
根据《海事劳工公约》的规定,除了船员居住国之外,船旗国同样有承担船员社会保障的义务:“如果海员受到不止一个涉及社会保障的国内立法的管辖,有关成员国应开展合作以便通过相互间的协议确定适用哪一国立法,并考虑到各自立法中对相关海员更加优惠的保护种类和水平等因素以及海员的选择。”这一规定,其立法初衷无疑是希望能够拓宽承担义务主体的范围,为船员的社会保障提供多一重保险。然而,实际操作中是否能够如其所愿呢?
可以设想,船务公司在这一前提条件下选择船员时,有两种选择:其一,倾向于选择来自社会保障制度完备的国家的船员,但这一部分船员的起薪也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船务公司的工资支出;其二,倾向于选择来自社会保障制度相对较差的国家的船员,虽然相对地维持了用工成本的稳定,然而与此同时也承担了大部分的为船员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一种用工成本的增加。因此,船务公司一定会想方设法逃避这一义务。
而《海事劳工公约》中恰恰没有关于两国均应承担提供船员社保的责任的情况下,两国之间应如何分配责任的具体规则,只是将这一问题交给两国间的双边合作解决。这一出发点是希望能给公约的施行增加灵活性,但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这反而给予船务公司可以利用的漏洞,将责任完全推卸给船员的居住国,致使《海事劳工公约》的立法目的不能实现。
(二)船员社会保障制度对船员服务机构的影响分析
船员服务机构在船员劳动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其第三方的中介角色,船员服务机构具有同时掌握船务公司和船员两方面的信息这一显著优势,如果加以合理利用,可以有效协调、解决二者间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问题。另外,船员服务机构可以根据其所了解的用工方船务公司的实时需求,向船员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协助船务公司和船员进行双向选择和沟通,在一定程度上优化配置船员这一劳动力资源。根据《船员条例》第41条的规定,船员服务机构还应当根据每个船员的具体情况为其建立船员档案,记录船员的任职、健康、培训、安全纪录等方面的情况,这些信息的记录和更新对于政府海事部门对整个海运业的把控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船员条例》第44条的规定,船务公司与船员间应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建立正式劳动关系,而船员服务公司应监督、促进这一过程的依法完成。换言之,《船员条例》的初衷是将船员服务机构固定在中介这一角色上,仅仅提供为船员和船务公司牵线搭桥的服务,船员建立劳动关系的对象是船务公司,故船员的社会保障责任应当由船务公司承担。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尤其在对外劳务合作的过程中,外国船务公司作为境外雇主,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和《船员条例》的适用前提,因此无法与船员订立劳动合同。于是在实践中,只能由船员服务机构与船员订立劳动合同,并向外国船务公司进行劳务派遣。
虽然这样的操作造成了由船员服务机构承担船员的社会保障责任的局面,这与立法原意是不相符的,但在船员服务机构这样一个中介平台的帮助下,船务公司无须自己雇佣数量庞大的船员,承担这些船员的社会保障责任,负担其养老保险、住房、培训等多项费用,只需按需从船员服务机构雇佣个体船员,负担其在船期间的劳务费用即可;另一方面,对于船员而言,外派船员的劳务收入要远高于船务公司所开的工资收入,个体船员的工作自由度也较隶属于某一船务公司的情况而言要高得多,休息休假都可以随心安排,着实也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选择。因此,越来越多的原本挂靠在某一船务公司下的船员辞职成为个体船员。
然而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的船员服务机构不仅未能担负起纠正因船务公司和船员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反而以收取不合理的高额费用等形式扩大经营,谋取利益,虽然个体船员对此怨声载道,但迫于船员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现状他们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样的“扒皮”行为,承担因此而增加的应聘支出,船员队伍的整体福利也因此而降低。虽然短期来看社会的总体福利并未变化,只是从船员转移向船员服务机构。然而,从更为长远的目光来看,如果船员服务机构变本加厉,进一步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最终将使得个体船员回到船务公司,或通过其他渠道寻找岗位。如此,对于整个市场而言,交易成本大幅增加,不管是船务公司还是个体船员的决策灵活度、自由度都受到了限制,社会总福利事实上是下降的。
另外,这一部分船员服务机构通常对于船员的社会保障是不承担责任的,这就导致了个体船员的社会保障既不能依靠船务公司,也无法依靠船员服务机构。由于船员这一职业的高风险性,商业保险公司也不愿意为个体船员提供保险,而个体船员独自面对商业保险公司是缺乏话语权的,由此商业保险也成了死路一条,个体船员的风险保障落入无人管无人理的尴尬处境,其抗风险能力显著下降。
(三)船员社会保障制度对船员的影响分析
在船务公司、船员服务机构和船员三者的共生关系中,理论上应处于核心地位的是船员,因为正是船员的存在将另外二者联系在了一起,也正是船员劳动力这一资源的存在创造了现在的市场。然而在实践中,非隶属于某一船务公司的个体船员由于势单力薄,事实上处在弱势地位,与相对强势的船员服务机构和船务公司相比,没有议价能力。而且由于这类船员的数量日趋庞大,将具有极强的替代性,存在遭到歧视的可能性。
船员本身职业流动性大的特点,进一步放大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各地区社保待遇不一、程序手续要求不一、异地就医结算难等问题。另外,远洋船员还面临着境外就医过程中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并未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范畴这一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除了需要在法律和规则层面上进行完善,给予必须的制度支持之外,从各国具体履约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谁来负责这一制度的执行,以及,谁是最终的负责人?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国家海事局肯定是承担主要履约义务的政府部门,这也是符合我国的行政传统的,海事局可以一定程度上在相关制度层面修改与《海事劳工公约》的规定不相一致的条款,也可以在实践中扮演政府监管者的角色。在海事局对《海事劳工公约》的解读中,也对如检查发证制度中交通运输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如何进行分工合作进行了规划。但是,我们在各国的实践中看到,履约情况或履约准备情况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在船员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中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力量是船员工会。
船员个体的弱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船员这个职业的流动性大的特点决定的。而船员工会恰恰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将零散的个体船员集中、团结起来,将其力量汇聚,并作为一个整体与船务公司或船员服务机构进行谈判和议价,在权利维护和福利争取等方面也更有话语权。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的工会文化式微、工会组织松散的国家,船员工会和个体船员的话语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工会的日渐行政化,使得船员工会距离其成立初衷渐行渐远。
四、船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建议
通过以上的影响评估分析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在《海事劳工公约》对我国正式生效后的履约过程中,《海事劳工公约》关于船员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规定对船务公司、船员服务机构、船员及监管机构所造成的影响。就我国现行的船员社会保障体系而言,由于船员工会组织不够发达、角色相对单一,使得落实船员社会保障的重任由国家海事局一力承担;船员服务公司依靠对船员进行“扒皮”而保持经营的运行方式,吞噬了《海事劳工公约》所划拨给船员的这部分福利。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拟对《海事劳工公约》对我国正式生效后的船员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出以下建议:船员社会保障制度落实的一大难点在于船员的流动性大,由此带来监管成本的提高;可以考虑通过发展船员工会联系散落的船员以降低这一成本。船员服务机构常年以侵占船员队伍福利的方式畸形存在,行业的不规范操作比比皆是;可以考虑通过加重船员服务机构在船员社会保障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使得该行业自主进行优胜劣汰,降低这一部分的监管成本,从而提高整体的监管绩效。
[1] 王秀芬.国际劳工组织的船员立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研究——以《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2.
[2] 常玉文.《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之剖析[J].海大法律评论,2007,(10):312.
[3] 李桢.海事劳工公约下的船旗国管理评析[J].中国海事,2011,(1):32.
[4] 罗楚江,李桢,张仁平.中国批准《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的履约建议[J].世界海运,2016,(4):26.
[5] 王长青,李伟.《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对我国海员外派的影响及建议[J].中国海事,2013,(9):36.
[6] 王霖.谈在政府层面如何加强海事劳工公约履约[J].中国海事,2015,(4):35.
[7] 王亚男,李澜.船员外派法律关系构成之法理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11,(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