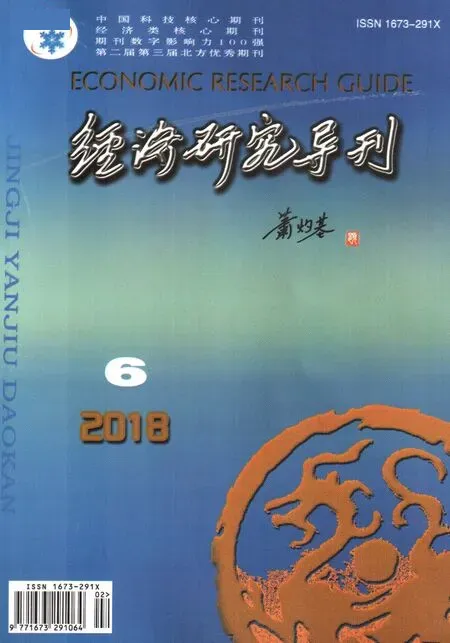忆故乡的族田制
——古代中国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
王勤谟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离退休干部局,北京 100821)
笔者的故乡是宁波市慈城镇(旧慈溪县县治)黄山村。村南北各为一座孤山——前黄山和后黄山,相距约三华里;东西为两条可以行舟的小河——东浦河和西浦河,相距也约为三华里。黄山村南面六七华里有一条大江——姚江(也称前江),北面一二华里有一条较小的江——后江,东西浦河即为后江的支流。后江在黄山村西面稍远的丈亭镇流入姚江,姚江向东,在宁波市三江口与奉化江汇合成甬江,东流入海。清钱塘人蒋坦1860年于黄山避难时,在所写的《黄山小志》中说:“黄山距慈溪县城八里,烟火数百家,风俗朴厚宛然一秦时桃源也。”
黄山村王氏家族的族田制一直存在至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由于笔者当时年纪小(生于1929年),有所感受,但也知之不深。不过,现在经历过族田制的人已不多了,因此,笔者还是把知道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作为一段供参考的史料。
一、黄山古村的两个特点
在介绍族田制前,先简略介绍黄山村当时的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黄山村只有王氏一族。虽有非王姓的人,但他们都是为王姓服务的人。在这些人中,除几个小学教师外,一般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有的进入家庭服务,如长工、保姆等;有的是独立经营者,如木匠、泥瓦匠、裁缝、厨师、轿子店、杂货店等。
古代中国,直至民国,乡村是自治的,由乡里的士绅管理。黄山村的管理,也就由王氏家族管理,而管理王姓家族的则是祠堂。笔者在当时没有听说过黄山村有乡长、村长,甚至保长、甲长之类的行政管理人员,即使有,似乎也不起什么作用。那么为什么说是祠堂,而不是像影视片中所说的族长?这是因为管理王氏家族的人,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族长,二是一批执事。族长由辈分最高而又年龄最大的人担任。一般辈分高的人是比较穷的。因为穷,结婚晚,生儿子晚,所以辈分大;而有钱的人结婚早,生儿子早,辈分低。因此,族长在族里名义上是最高管理者,实际上的管理权却在名望高、但辈分低的执事手中。
王氏祠堂在北面后黄山南面的山脚下,南北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东浦河支流,王氏族人的住宅就分布在这条小河支流以北,王氏祠堂的东西两侧,这些住宅的主房都是楼房。与清朝时北京的房子不能高过皇宫一样,黄山村的房子也不能高过祠堂。这些住宅基本上都是占地面积很大的各支系聚居在一起的大宅院,并都有一个名称,如大夫第、侍卫房、旗杆门头、白屋、西甸洋、池墩等。大宅院内分户而居,但户与户之间又有弄堂互相连通。
第二,黄山村自王氏家族于明朝定居以来,至20世纪30年代约有四百多年历史,是一个久盛不衰的“诗书继世长”的“士村”。“士村”是笔者的杜撰。在中国的传统乡村中有着从事各种各样工作的人,农耕、手工业、商业、运输、宗教、文艺、武人、士人等等。笔者把大多数人从事农业的乡村称之为农村。同理,把基本上培养士人的乡村称之为“士村”。黄山村的子弟,自幼读书,他们的前途,或出仕,或为儒商,因此,笔者称之为“士村”。
以笔者的上代为例,笔者属于大夫第支系。清朝时,大夫第始祖王严理(1756—1824年)至其孙子,三代共28人,均有功名和官衔。其他支系也类似。
还有,日本人冈千仞的游记也记了这一点。1884年,日本维新人士、汉学家冈千仞访华期间,应同船回国的笔者的祖父王惕斋的邀请,在其家里(宅名“白屋”)住了半个月。在冈氏的《观光纪游》中说:“观王氏家庙。壁书先中书君家训十二条。族人登科第者,皆书联额揭壁。族约尤严,曰降入非流者,不得与祭。”“子弟至八九岁,必延师学举业。”冈氏抵黄山村时,“白屋”的王氏族人,有5人相迎,也均有功名和官衔。冈氏在日记中,对其中两人的评语是:“砚云,举人,有才学,笔谈致晡。”“并卿尝为福建霞浦县令,有学问。”
二、王氏家族的族田制
在旧中国的农村中,族田制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占有形式。费孝通抗战时期通过在云南的实地调查,认为在云南这种族田特别发达,从他们调查的绿村来说,全村所有田总数的27%是属于团体地主的。族田一般来自祖先的遗产或族人的捐献。
黄山村的族田制,就笔者所知道的情况,大体有以下几点:
首先,黄山村里的田,一般由王氏族人雇长工耕种,但每户拥有的数量都不大,如笔者家屋前屋后共有十亩田。族田一般在远处,并由当地农民耕种交租。其次,王氏祠堂有族田,其下各支系,甚至支系下的支系也有族田。族田来源是祖先的遗产。再次,王氏家族的族田是名符其实的族田,不像有些地方的族田,只是某个乡绅的私田,借口供众人使用,挂在祠堂名下,逃避纳税。
族田归属不同,用途也不同。
第一,祠堂族田的收入,用于王氏族人的公共开支。笔者知道的主要有:
一是对祭祀的管理。首先,每年春节在祠堂祭祖。其次,在各级祖宗的祭祀日去他们的坟墓处扫墓。有慈溪县三地王姓的大祖宗,要坐船去,有黄山的王姓始祖。至于黄山始祖下各支脉各级祖宗的扫墓也要进行,但不一定由祠堂来组织了。最后,有权决定人死后能否将其神主牌供奉在祠堂里。
二是对婚、丧、祝寿等的管理。凡族人有这些事时,族里就会派出一整套人员来帮助办理,如管收礼的、管运输的、办酒席的、组织乐队、司仪等等。对送礼的标准,按性质,如婚礼或丧礼等,又按关系远近,也有统一规定。一般不让超过,以免互相攀比,增加其他人的负担。
三是办教育。清朝废科举后,黄山村王氏家族,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黄山王氏蒙养义塾原址上创办崇本学校。参与创办并主持校务(监堂)的王义观(秀才)受变法维新思想影响,按照新学的要求安排课程。1922年春,学校因经费无着而停办。黄山王氏宗祠执事决定将祠管部分产业田划归学校,并倡议向津沪等地族人募捐兴学。于1923年春复校,改校名为私立崇本完全小学。
四是维持社会秩序。当然,这里要维持的是基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秩序。笔者亲眼看到过的一件事是,一个晚辈的人骂了一个上辈的人,那个上一辈的人心有不甘,要族里明断是非。族里受理,这叫“开祠堂门”。笔者去看了,听完双方诉说后,族长骂那个下一辈是一个犯上的不肖子孙,责令他向上一辈人跪下叩头赔罪。那个下一辈人也就当场执行了族长的判决,这件事就此平息,据说被罚的人不久就抑郁而死,因为这是大丢面子的事。
五是春秋两季,在黄山庙举行奠祭,并组织演出。
六是其他公共管理事务。如消防,有一台“救火车”,由两人分立左右一上一下地压水。笔者曾亲自见过一次一所住宅起火,抬出这台“救火车”喷水救火。但是威力太小,这所住宅还是被烧得精光。
第二,各支系下的族田,由其下的各房轮流收租。黄山村成为一个“士村”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的。1884年冈千仞在黄山村看到的王惕斋家族是一个豪门富户,他们支持子弟读书自不成问题,也就是冈千仞所说的“已无衣食之忧,偃然自足”。但是,其一,在黄山村还是有经济条件差的人家;其二,富户也不一定能一直富下去,会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家道中落。为使家族子弟始终朝着“士”的方向发展,就有必要保证家族成员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要有最低生活保障费用。其中,一个依靠就是族田制。也就是轮到的人,收一年租吃几年。有的在外就业的,轮到他收租时,因为并不在乎这些地租收入,就让给他在村里的收入低的兄弟房去收。
在《古镇慈城》2009年3月号上刊登了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的一篇文章,文中对黄山王氏家族的族田制有一个较为具体的介绍,录于下:
“宗法社会特别强调祖宗基业,好多田产是属于祖宗的。制度规定祖宗产业后代不得变卖、分家,只能按年轮流享用,轮值到那家有收取田产租子的权利,也有承担那年祖宗生忌日祭祀和清明扫墓等义务。我们家祖父名下,自己只有三亩半田。但是,每年可以轮到平均收入多于25亩的租子(隔年起码有50亩)足够全家口粮。笔者想,这也许是维系子孙‘叶落归根’的主要措施,保证他们退休、失业回家总有一口饭吃,不致无依无靠。”
收租的人需要负担一定的义务的情况,笔者印象深的是小时坐船去参加三地王姓的大祖宗的扫墓活动。这个祖宗的墓地,除坟墓外,还有房子,谓之庐墓,有看墓人住在那里看管。房子也较大,可以摆开很多张八人坐的桌子。扫墓后,收租的人要从地租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办酒席,请扫墓的人吃一餐。规定是:一席十个菜,中间有个甜菜,最后一个是汤。笔者每次参加这种酒席,吃到中间都会有人起来和该年的收租人吵架,大声骂他酒席质量办得差了,扣的罪名都是对祖宗不孝,理由是酒席质量办得差就是花在祖宗身上的钱少了,自己落下的钱多了。
三、结语
黄山村王氏族人族田制的彻底崩溃是在日本侵华战争后,由于日本人的入侵,族人特别是在村里无正常收入的族人,生活越来越困难,就变卖祖宗田地等资产以度日,没有了公共资产,这种在宗法制社会遗留下来的族田制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知道,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1883年,该年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疾病保险法》,而后又在1884年和1889年相继出台了《工作保险法》《养老、残疾和残废保险法》。笔者认为,在古代中国各地推行的族田制,实质上也是一种带有自助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今天,我们在发扬和继承我国的优秀传统过程中,很有必要挖掘古代中国各种类型的含有社会保障制度内涵的做法,以便从中获得启发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