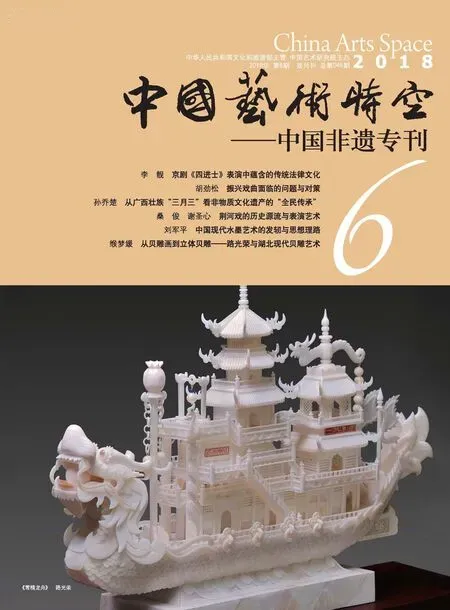日本狂言表演与传承
中国艺术研究院 / 李玲
【内容提要】2018年8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一场日本狂言演出引起人们对狂言的关注。狂言以家庭戏班为传承单位,这种亚洲传统戏剧生产方式依然能够在现代舞台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保持着良好的循环。传承600年的舞台表演艺术如何不依赖国家财政拨款援助而自力更生?本文从狂言独立演出的历史、戏班传承及政府培训项目、演员的成长几个方面介绍日本狂言表演与传承的状况。

2018年8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狂言戏《棒缚》
2018年8月10日,为庆祝《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40周年,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日本狂言演出,由现年87岁的狂言人间国宝野村万作带领其家族及弟子演出三个狂言戏《棒缚》《川上》《茸》,翌日在日本大使馆举办狂言讲座。狂言演出一票难求,讲座也排长龙,许多年轻观众慕名而来,为的是一睹因电影《阴阳师》而出名的野村万斋之音容笑貌。野村万作(87岁)、野村万斋(52岁)、野村裕基(18岁)祖孙三代同台演出,以家庭戏班为传承单位的亚洲传统戏剧生产方式依然能够在现代舞台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传承600年的表演如何不依赖国家财政拨款援助而自力更生?以下我们从几个方面去了解世代延续的日本狂言表演与传承。

2018年8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狂言戏《川上》

一、独立演出与普及传播
狂言与能戏合称能乐,能乐演出需要狂言演员的辅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出能戏里通常有狂言演员扮一个当地人角色,他上台讲述此地风物或历史故事,戏份不那么重要但不可或缺,作用是为了填补能戏前后场之间主角换装的时间,当然也交代故事情节,这类表演称为“间狂言”;另一方面是两出能戏之间演一出狂言戏,古代演能要演出一整天,神、男、女、狂、鬼五个类型的戏按序演一遍,中间以狂言的喜剧欢乐调剂沉重肃穆的能戏故事。狂言与能相辅相成,关系紧密,但从戏剧类别及演员身份等级角度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狂言在能乐中是被雇用地位,受到严重忽视。主要原因是因为能乐在江户时代被武士阶层垄断,被幕府指定为官方“式乐”,能戏的歌唱舞蹈,即谣曲和仕舞,是当时知识分子,即武士们必须习学的素养之一。能乐演出在一年四季祭日庆典活动里也有机会开放给普通老百姓观看,但主要为上层阶级服务。在几百年武士道德和价值观影响下,以谐趣取乐为主题的狂言并没有获得与其演出份额同等的重视和尊重。明治维新后,幕府体制瓦解,能乐组织受到严重打击,艺人被遣散回乡。正如江户改名为东京,旧城池发展为近代都市,皇族与旧藩主为代表的华族依然指挥着文化发展的风气。1876年天皇御览能乐演出,20世纪初日本学术界对能乐及世阿弥的研究开始起步,传统舞台表演在欧化戏剧改革的热潮后逐步恢复,但狂言仍然处于从属、配合能戏演出的地位。“二战”结束以前的能乐演出,一到两出能戏之间的狂言演出时,往往是观众离席休息吃饭、熟人闲谈的时间,完全无视狂言演员的存在。因为多半能戏观众的观演经验依然保持着旧时代传统,他们看戏是为了温习自己平日所学的谣曲,狂言则可看可不看。
现在我们看到的狂言演出,可以与能戏合作共演,以能仕舞、一出能戏、一出狂言戏的形式组合成约3个小时节目;也可以独立演出,以狂言解说、两三出狂言戏组成两小时节目上演。后者的独立演出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以后,首先,日本战败后的民主化改革使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经济发展与娱乐需要欢迎喜剧和笑声;其次,学术界对能乐的关注延伸到狂言,对狂言的基础研究、剧本整理都逐渐完备;再者,战后日本政府重新修订教育体制,狂言剧目《附子》《柿子山伏》作为古代文学范例被列入课本教材,那么狂言戏是怎么演的呢?于是狂言剧团展开了“学校巡演”模式,好玩好笑的传统表演受到师生热烈欢迎,面向学生的普及演出极大地提高了狂言知名度。狂言之所以能够独立组团演出,除了以上大环境发展的契机外,新一代狂言从业人员的努力和创新也尤为重要。

日本国立能乐堂外景
昭和年代出生的新一代狂言演员比他们的父辈更敏感地体会到经济上的雇佣关系以及传统观念中的上下等级带来的压力,以及对个人发展空间的限制,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压力,日本战后崛起的新一代狂言演员做出了超越前辈的新尝试,开拓了一条能够独立演出、独立发展的新道路。由于狂言演出不需要舞台装置,道具不过是扇子和黑漆木桶,三四个演员用包袱皮背着演出服装就能翻山越岭下乡演出。日本战后贫困交加,物资严重匮乏的时代,狂言演员就靠灵活精简的演出方式到偏远农村演出,条件虽然差,但能吃饱饭。这段往事很像中国的“国风苏昆剧团”当年为维系昆曲命脉而漂泊江湖流浪的岁月。当时的野村万作正当青春,他与同辈艺人及哥哥万之丞等年轻人积极参加戏剧创新,引发能乐界及社会媒体的关注,例如1954年的《夕鹤》(木下顺二作)、《东是东》(岩田丰雄作);1955年的《彦市的故事》(木下顺二作)、《月光下的皮埃罗》(阿诺德·勋伯格作曲)、《绫鼓》(三岛由纪夫作);1957年的《智惠子抄》(高村光太郎作)等作品。
这些超越古典戏剧形式的新尝试一度引起相对保守的能乐行会的批评,甚至几乎被行会开除,但他们坚持不懈,打破了一些狂言界不成文的禁忌,例如“不允许与其他艺术门类同台共演”“狂言不同流派不能同台共演”等。他们敢于利用新兴娱乐手段,野村万作年轻时以狂言师身份拍摄的雀巢咖啡广告风靡一时,实际代表着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中追寻本国传统文化的动向;在古装电视剧中饰演历史人物也是他们的强项,依靠多元的探索,战后日本狂言表演不仅独立于能,而且展示出戏剧舞台表演的多种可能性和充沛的活力,获得社会舆论和观众的高度评价。

狂言创新剧目《楢山节考》

张继青与野村万作合作演出《秋江》
二、子承父业的家庭戏班与国家培训机构
日本狂言表演艺术的传承由为数不多的几个私人家庭戏班承担,政府并不会拨款资助这样家庭戏班营业,对荣获俗称“人间国宝”称号的最高级别艺人则有每年200万日元的资金配给。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将近13万元,看上去挺丰厚的,但实际用途只限于培养艺术继承者及道具、设施的维修等方面,不能随便乱花,考虑到日本物价,要翻修自己家的练功舞台,这笔钱都未必够。政府不提供大锅饭怎么办呢?答案是靠自己赚钱吃饭!如果说狂言艺人在江户时代相当于政府公务员,靠幕藩制度领薪水,那么在幕藩制度被推翻后,依赖的是能戏主角提供的打工机会,到了昭和时代后期,他们开创了狂言独立演出形式,推动狂言经济走上成功的“民营化”道路。

野村万作
能乐协会是日本能与狂言专业演员的行会组织,2018年度能乐协会中狂言职业演员人数为140人,其中大藏流76人,和泉流64人,分别分布于东京、京都、大阪、名古屋、神户、九州等地,演员主要集中于东京和京坂地区[1]。这140位职业狂言演员分别属于12个狂言家庭,例如大藏流的“人间国宝山”本东次郎,他的狂言家庭剧团包括亲属7人、弟子3人,2018年3月有15场演出;同样是“人间国宝”的和泉流野村万作家,直系血亲只有万作、万斋、裕基3人,弟子有12人,2018年9月演出计划有10场。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由家庭成员与弟子构成的狂言家族既是文化集团,也是经济集团。狂言家族要维系传承,首先要保证子息繁衍,生育男儿为要务。重男轻女仍然是传统艺能界不得不遵从的习俗,当然女孩儿幼年也跟随父亲、祖父学点基本功,扮个娃娃生也能上台演一两回,但上了小学后一般便不再上台。男孩子从两三岁时开始接受训练,循序渐进地按照狂言演技进步的台阶,在不同年龄段完成相对应的剧目,例如三四岁首次登台时演《韧猿》中的小猴子、《伊吕波》中的小娃娃;成长阶段演《金津地藏》中的小地藏菩萨、《麻痹》里的主角太郎冠者、《重喜》中的主角小沙弥重喜等;在15至20岁之间完成演出《三番叟》《奈须与市的故事》《钓狐》等大戏,相当于得到狂言学习的毕业证书,同时也要通过行会组织的考验,才能正式加入能乐协会,成为职业狂言演员。
仅靠直系家族或旁系亲属的兄弟、伯叔侄甥的戏班毕竟单薄,因此需要招收徒弟来稳固本家系的艺术传承,弟子如果足够勤奋精进,不仅能成为演出的左膀右臂,而且原来的大家族也可以产生长男继承的本家与次男的分家,弟子家如果积累深厚,也能派生出独特的传承,例如野村万作年纪最大的徒弟石田幸雄出生于1949年,他的儿子石田淡朗生于1987年,淡朗毕业于英国盖德霍尔音乐与戏剧学校,同样活跃于狂言舞台。狂言弟子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能乐从业者的亲属,从小耳濡目染受影响;二是在学校教育中因参加狂言兴趣小组或大学里的狂言俱乐部而立志以此为业,拜师学艺;三是参加政府艺术培训机构,毕业后跟随某个狂言师傅学习,相当于中国戏曲的“团带班”模式进一步磨练,最终成为职业表演者。在这三个方面,政府艺术培训机构培养的弟子非常重要。

摄影:政川慎治
20世纪70年代,日本文化厅艺术文化专门调查会提出建议,认为国家有必要组织培养“能乐三役”,即除主角演员之外的配角能乐师、乐师(包括能管、小鼓、大鼓和太鼓)及狂言师这三类演员。1983年国立能乐堂建造完成,翌年即创办“能乐三役”培养项目,每隔3年招生一次,招收初中毕业水平以上,年龄在23岁以下的男性。研修课程为全日制,共6年,前3年是基础训练课程,后3年为跟随师傅的专业表演实习,早期有8个月的考验期,不适合者被劝退。培养项目不仅门槛低,而且课程不收学费,还有奖学金制度,教材是免费的,授课教师是最高级别的演员或“人间国宝”,学习条件优越。在高消费的日本,面对昂贵的大学学费,选择从事传统艺能行业是个不错的选择。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设立的研修课程,看上去与现代艺术学校的教育制度类似,但授课仍保持着传统艺能“口传心授”方式。国立能乐堂每次招生,都与“能乐三役”的各个流派家系制定计划,缺少小鼓演奏者,就招小鼓学徒;缺少狂言演员,就招收愿意演狂言的学生。哪个家族缺人手,哪家师傅就去能乐堂当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了就可以收归自己门下,相当于私人定制的徒弟,国家出资的免费私塾学堂。从培训项目的效果来看,从1984年开始,这个传承人培养项目目前实施到第十期,前九期总共培养了27位专业能乐演员[2],数量看上去少,但人才没有流失,每一个学生都归入某个家门,接手艺术传承的实际工作,资金花在刀刃上。例如这次来访演出的野村万作家弟子深田博治、高野和宪都是国立能乐堂第四期“能乐三役”毕业生,他们是万作家戏班的中坚力量,担任日常演出和扶掖后辈的重要任务。
日本国立能乐堂是能乐演出的专设剧场,培养艺术传承者的同时,致力于策划能与狂言的演出、调查研究及资料收集等事业。国立能乐堂每年策划大约50次不同类型的能乐公演,即每个月均有4次能和狂言表演。至2009年国立能乐堂建立25周年为止,能乐的最大传承范围——包括240出能、260出狂言戏,绝大部分已经在这里上演过了。除了国立的能乐演出剧场,日本各地区中心城市又有自己的能乐堂,历史悠久的神社寺院所属的室外能乐舞台,偏远地区也有文化会馆,全社会及教育体系、媒体对传统艺能的重视及完备的链条式演出服务渠道都相当成熟,这是表演艺术传承事业得以世代延续的重要保障。

摄影:政川慎治
三、经济的民营化与艺术精神的民营化
现代狂言表演艺术由各个狂言家族戏班通过学校巡演、地方演出,组织观众会员俱乐部,开设狂言教室等自主经济方式,构造了一个狂言艺术生存、传递和展示的链条。一种古典表演艺术技能,一种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的积淀,由一个家庭内部保有和管理着,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和责任。独立操纵的经济形式给予狂言艺术传承者独立管理经济的自由,但与经济形态上的“民营化”相比,艺术精神上的“民营化”更是狂言从业者的前提,这意味着他们要克己勤奋、一心一意地为艺术事业奉献终生。
以今年8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的野村万作一家为例,翻看祖父万作(1931—)的自传《生为太郎冠者》、父亲万斋(1966—)的著述《我是万斋》,以及孙子裕基在NHK电视台记录他学艺成长的纪录片中,都会发现每一代人都在艰苦的训练修行和成长中充满对命运、对生存的疑问,生而注定要担负继承家业的重担,如何从两三岁开始的循环往复的演艺生涯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自由?甚至更早的前辈,万作的父亲第6代野村万藏(1898—1978,1967年被指定为狂言“人间国宝”,其表演艺术为现代狂言发展基石之一)也有相同的困惑:可怕的练功,练功时可怕的父亲,无处可逃的命运。
祖父传父亲,父亲传儿子式的直系血亲传承是牢固紧密的师徒关系,家庭内部的师徒关系甚至超越了祖父、父亲或儿子的身份角色。生于狂言世家的继承者,对自己为师的父亲都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纠葛。幼年期鹦鹉学舌般“口口相传”“口传心授”的教授方式灌输给幼童的不仅是普通记忆,更是一种非日常的特殊精神压力。狂言大藏流“人间国宝”山本东次郎在他的著述《狂言的言灵》中这样说:
回首往事,父亲的训练真的非常严厉。当然因为那时候小,对责骂和挨打心存畏惧。但除此以外,我觉得我还畏惧着一个的巨大存在,它隐藏在父亲的身后,操纵着父亲的言行。父亲似乎在向我灌输着超越练功的更大更沉重的一些东西,我被这无形的存在所压倒,所逼迫,于是认真地完善训练和演出。[3]
父亲及师傅的权威、传统的礼仪行为、严谨克己的气氛,令孩子体会到一个超越日常的世界,产生畏惧之心。然而这种畏惧随着年岁和技艺的增长逐渐转化为一种灵魂深处的责任和宿命,为通往艺术自由之路打下基础。这大概是世代相传的家学比职业学校教育制度下的艺术培养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传承者对人生和艺术命运有高度的认识、反思和追求,落在自己肩头的责任既是家族几代的厚重遗产,也有民族文化传承的大义,痛苦与叛逆当然也是必经阶段,超越了这个阶段,才真正完成艺术精神的“民营化”,达到艺术的自觉与自由。因此我们看到野村万作从艺80多年,从未离开过狂言舞台,他以轻妙洒脱的表演艺术著称,荣获紫绶宝章、文化功劳者等艺术界最高荣誉,被指定为狂言“人间国宝”。而他的儿子万斋个性鲜明,不仅在传统狂言界承前启后,运用传统表演程式编演创新剧目,更创立多栖艺术家身份,在影视、舞台导演方面有所建树。万斋近日被任命为东京2020年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综合总导演兼创意总监,这意味着这位具有高度现代感的古典艺术家将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向全世界展现日本现代精神风貌。这个狂言家族的第三代,18岁的裕基也完成了狂言毕业戏,默默地继续着修行:当检场、当配角、演主角。
结语
狂言表演艺术父子相传、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特点与中国戏曲传统的传承方式相似,日本传统艺能传承依靠具有封建性及身份等级特点的家元制度来实现艺术技艺的传承与管理,这一传统制度使古典艺能与现代生活维持着一定的流通和疏离,保持着艺术传承的权威性、稳定性和持续性。良好的演出经济和成熟健全的艺术经营管理排除了非艺术因素的干扰,使艺术传承者的追求和思考得以贯彻。狂言经济的利润并没有动摇恪守传统艺术规范的根本,相反,它带来自信心的上升,为艺术伸延和独立思考提供了自由空间。有着高度艺术自觉的艺术继承者掌握着平衡传统与创新的主动权,具有独立管理艺术的自由,而这份自由,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世代相传的莫大的历史责任、压力和由此产生的动力。在心存畏惧、百般谦逊的艺术道路上,传承与创新并行不悖。
注释:
[1]根据能乐协会官网统计。
[2]根据国立能乐堂官网https://www.ntj.jac.go.jp/training/outline/group07.html统计。
[3]山本东次郎著:《狂言的言灵》,玉川大学出版部2002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