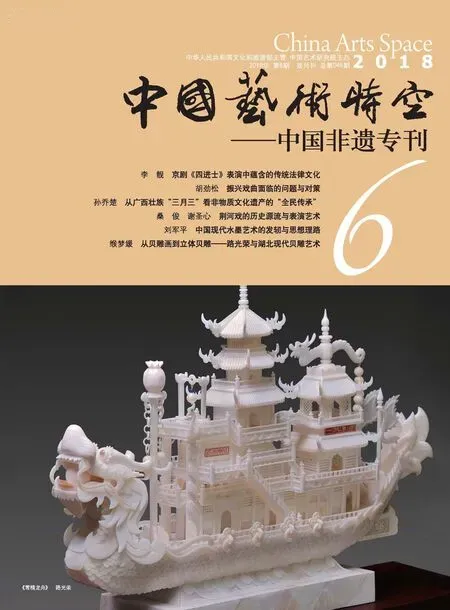当代视觉艺术中时间性的表达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 任惠云
【内容提要】时间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如何让这抽象的时间具体形象化,从古典绘画到当代艺术,艺术家们一直不停的思考和探索时间的关注和表达,努力地在艺术创作中将抽象的时间形象化、具体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时间的传统概念也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同时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表现形式与边界也被一次次的打破、扩张,当代视觉艺术家们对时间性表现的不断尝试和试验给我们呈现了更多的表达可能性,也给时间性的具象化表达注入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

基弗作品
人类自然科学探索和人文艺术创造一直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和探索充满好奇。对于这些本质性命题,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在其作品里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表达。
时间是一个较为抽象地概念,是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此时间即我们认为的一般意义上的钟表时间。在视觉艺术中的时间是视觉世界在艺术创作上呈现一个凝固的“视觉瞬间”,这个“视觉瞬间”是对历史记忆的叠加,或是回忆,或是纪念,或是警醒等等生命个体的自我体验,我们称之为观念时间。所以我们这里所谈的时间,不是简单的事件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不是一个定格,而是一个可以往返来回的过程,一个可以激起观者某种情绪的通道。
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关于时间的,是关于时间主题的不同表达方式。绘画更是一种对于时间的特殊挽留,它使恐惧于时光流逝的个体生命获得精神上的寄托。这种恐惧来自人类对生命时光延续的极大渴望与个体生命存在的生老病死现实规律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因此,留住渐渐逝去的时光或使时光倒流早已成为人类的通常愿望和祈盼。

塔皮埃斯作品
从古典绘画到当代艺术,艺术家们一直不停的思考和探索时间的关注和表达,努力地在艺术创作中将抽象的时间形象化、具体化。时间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而视觉艺术呈现的是某个定格的场景或瞬间,并永恒存在。在艺术史的发展进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段,关于时间性的表达层出不穷,从最初的绘画、雕塑,再到如今的影像、摄影和各种装置、观念及行为等等的丰富表达方式对时间的探索和思考形式各异,复杂多样。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时间的传统概念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表现形式与边界也被一次次的打破、扩张,当代视觉艺术家们对时间性表现的不断尝试和试验中也给我们呈现了更多的表达可能性,也给时间性的具象化表达注入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
当代视觉艺术家们对于时间主题的思考和表达,试验了许多突破性的创作,这些尝试有基于对现成物的巧妙借用,也有通过关注画面的构成关系所带来的时间性表达等等。总之当代视觉艺术家们均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延续了一种时空观念,不断地对历史与文化进行拷问。
对现成物的借用,通常会给人传达一种强烈的时间感,这种现成物的借用,其拥有的历史存在感会唤起人们对于时间的思考。现成物的借用使时间的寓意变得更为浓重而富有仪式感,更能感受到时间流淌中生命个体的渺小,传达时间洪流中个体生命的尊严和态度。西班牙当代艺术家塔皮埃斯的创作题材取自日常生活的元素和废弃物,他把人们扔掉的日用品:沙子、土、水泥、绳子、床单等,用清漆、颜料、乳胶等混合堆积成大型画面,反复表现人体局部、空床空椅、残垣断壁等等。这些最后视觉的呈现通过现成物的视觉转换,改写了现成物的普遍存在意义,迸发出历史性的象征色彩,成为直接诉诸情感的载体,让观者体验到了被时间抹掉或夸大了的微不足道之物所传达的全部信息。在一次题为“使命与形式”的演讲中,塔皮埃斯强调:“如果不使创作活动取决于人的内在运动和对时间、地理、文化诸种环境的反映,那我就很难想象出这样的创作活动。”可见,他对当下现实的关注,传达出他对时间性表达的终极思考。
时间是物质的运动和能量的传递,表达物质的生灭状态,这些现成物在艺术家的创作中走向了重生永恒。颓败的自然、残破的建筑是德国当代艺术家基弗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景象,基弗虽未经历“二战”,却是生长于“废墟”,他作品中出现的风景大多是废墟和荒芜贫瘠之地,这些都来自他深刻的童年记忆。他的作品中大量运用铁丝、灰烬、石头、照片、稻草等等材料来作画,他直观地将现成物的物质性和时间性彰显出来,观者可以用视觉度量到物质的体量和时空的浩渺。他的作品外观沧桑灰暗,肌理斑驳,里面隐藏了痛苦的回忆与悲鸣。基弗的作品既是叙事的,更是表现的,无论创作手法还是最后呈现的面貌都很当代,但表现主题却晦涩而富有诗意,隐含着一种痛苦与追诉意味的历史感,他意图用绘画来表述德国的历史和命运的磨难,唤起人们对时间逝去的沉重记忆。基弗说过,他不是在怀旧,而是要记得。他用他的方式记载对自我、历史及民族的反思。虽然基弗不断地回顾过去,但他更愿意展望未来。他对时间概念是:越是回到过去,越是走向未来。在双重矛盾的运动下,时间得以延伸。所有的历史都受到时间的支配,并最终消失。从衰败毁灭到复苏再生,这种对生命的永恒追求,一直是基弗的坚定信念。
塔皮埃斯和基弗的作品都给观者带来了时间流变的反思,物质属性的转换、蜕变,都俯首于时间的巨轮之下,艺术家希望捕捉这些瞬间或绵长的真实存在,让观者直面看似平淡但无意中被回避掉的生命体验。时间的不断前行,带动着万物的变化,吞噬万物的同时,带给人们绝望和无助,不断地将此时此刻成为过往,永远消逝,但视觉艺术给人类带来希望,为时间轴上逐渐消逝的万物带来重生的力量。

朱德群作品
时间表达物质的生灭排列。以时间性作为思考方式的作品往往会给人带来恐惧、死亡等等的思考和关注。“二战”后意大利重要的艺术家布里,在他作为战犯在美国战俘营的时候,他弃医从艺,开始了内心深处的绘画创作,因为条件艰苦没有绘画材料,他选用包扎过伤口的带有血痕的破布或粗糙的麻袋片进行创作。画面上排列不一的各种质地的麻布,麻袋片,纱布,夹杂着暗红的翻卷残破的毛边边缘,让观者想到的是撕裂、伤痕、创痛,感受到一种关于创伤的恐惧和伤痛。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着关于死亡的态度和看法,这些血迹斑斑的废布料,除了历经使用的磨损,更是承载着对于苦难、伤痛的记录和诉说,还与战争中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和创伤引起强大的共鸣。
西方当代视觉艺术家对时间性的表现,做了许多突破性的大胆尝试。同样,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家们也积极致力于对时间主题的表达,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时间性的呈现进行试验。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传统国画和书法中,其特有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是中国传统视觉艺术中的灵魂。中国式的时间观,是时间和空间的合二为一,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可以往返的时间。中国传统书法最能表达时间性,毛笔在纸上的运动过程有无限可能,表达了无限的时间走向。赵无极曾说:“书法为我造就了与西方画家不同的基础。”所以在他的绘画创作上,以西方的现代绘画形式和油画色彩技巧参与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意蕴,创造了色彩艳丽明亮、笔触激烈有力,富有动感和光感的新的绘画空间,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时间观念。观看赵无极的作品应遵循中国传统平面艺术特有的欣赏方式,目光随着线条的动势而移动,我们的视线将沿着画家设定好的走向在整个画面中游走移动,时间性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达到了中国传统艺术天人合一的虚空境界,领着观者进入一个看似无形又有形的无限世界。
与赵无极的作品不同的是,朱德群的作品中,那些躁动乱窜的密集线条,使画面的动感更强,是否很难从中分辨出运动的整体方向和顺序,但这看似杂乱形如狂草的线条始终脱离不开那条无形的时间轴。朱德群还特别注重色彩和光线,他认为有了光就有了空间结构的色彩变化,他将时间和光线重新安排,以期达到光影冲突中的平衡。他作品中的光线稍纵即逝之感也是对时间、记忆的一种暗示和启迪。赵无极和朱德群对画面的结构关系的时间性表达,沿着中国传统时空观,将时间、空间、线条、色彩等一系列要素,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协调统一于画面之中,将平面走向深度、由时间构建空间,让个体生命真正融入画面中。

赵无极作品
永远向前是时间的增量,总是正数。关于时间的思考和追诉永远也不会停止,当代视觉艺术对时间性的探索和表达也会一直延续和突破。当代视觉艺术家对时间主题的探索和思考,以及在各自的创作中呈现的时间性,令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感知它的存在。对时间的思考和追问不仅仅是哲学家的事,也值得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来思索和关注,也是对当下所处社会及生存状态的思考,不断对历史和文化进行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