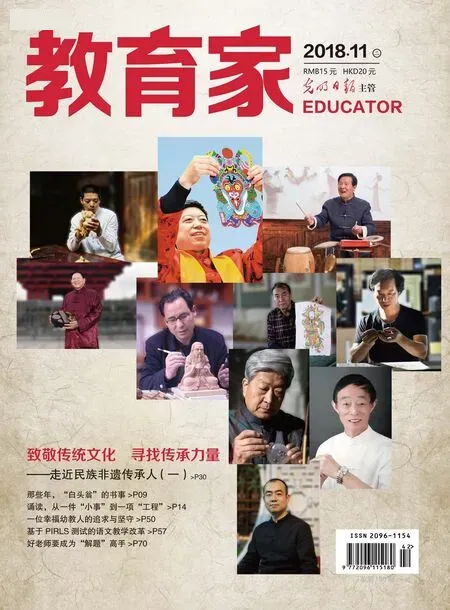那些年,“白头翁”的书事
文 |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今年七十二岁,发苍苍,视茫茫,妻子称我“白头翁”。提起我的简历不怕您笑话:四年小学,两年初中,两年高中,三年种地,五年村小,1976年起,做了四十多年的小学语文教研员,至今门庭未改,从一而终。
我自幼嗜书,直至现在还爱书如命。我觉得,印在纸上的文字,历来就有种魔力,这种魔力能使人上天入地,跨越古今。守着一堆书过日子,是幸福的。为此,买之,藏之,读之,我这一辈子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下面就说说我这个“白头翁”与书的故事。
收入再少,也要买书
1968年,那是个老驴拉磨的年代,我读高中。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随着浩浩荡荡的“知青”队伍开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的天地”里,我扶过大犁,赶过大车,挑过大粪,抡过大镐,一干就是三年。由于冥冥中的一个机缘,生产队想让我当“挣工分的教师”,只供饭,不给钱。我斩钉截铁地说:“干!”
三尺讲台横亘在我生命的原野上。为了守着学生,守着心中的希望,我把整个身心都扑在学校的工作上。然而,“吃了一把草,硬要挤出两杯奶”毕竟是不现实的,渐渐地,我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了。捉襟见肘的我,为了拥有“一览众山小”的从容与自信,每天拿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劲头来读书。读书得有书,没有书怎么办?买!为了买书,我外出开会抽时间跑书店,外出学习抢时间逛书店,外出办事挤时间找书店。四十多年来,衣、食、住、行上我舍不得花钱——出差常常是乘火车坐硬座,坐轮船买散席,住旅店睡加床。但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用得着的书,不管多少钱,我非要把它买到手不可。
邂逅为缘,追求是梦。1974年,命运让我认识了徐淑杰。我们从相遇到相识,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爱,从相爱到相伴,相处一年的时间便结婚了。记得结婚前夕,我和她到哈尔滨添置衣物,在哈尔滨第一百货公司门口,我把仅有的一百元钱从兜里掏出来,每人分五十块,她到楼上买衣服,我去书店购图书。下午四点钟,约定的时间到了,我抱着两摞子书兴冲冲地奔回百货大楼,却见徐淑杰两手空空,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呆呆地望着来往行人。原来,我们刚一分手,她就把钱丢了。我跑过去,拉住她的手。我笑了,笑得有几分苦涩,有几分内疚。她也笑了,眼角分明闪着泪花。
2001年金秋十月,我去昆明讲学,在哈尔滨上火车的时候,想买点水果,一打听,非常贵。正当我犹豫不决之际,一位小摊主看出了我的心思,指着一纸壳箱子烂梨说:“师傅,您给五毛钱全拿去。”俗话说“烂梨不烂味”,我付了五毛钱,捧着一纸壳箱子烂梨,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用小刀作了精心的“处理”,带上了火车。在车上,开始我偷偷摸摸地吃,因为不好意思。后来我就大大方方地吃,梨是我花钱买的,怕啥!最后我是狼吞虎咽地吃,因为不吃全烂了。就这样,从哈尔滨到昆明,“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花了五毛钱,吃了一路水果。归来时,我在北京图书大厦选了五百多元钱的教学用书,这些书,我既没有邮寄,也没有托运,而是上车下车硬扛回了哈尔滨。
退休后,可能是年龄的缘故,我喜欢买旧书了。
哈尔滨南直桥下有一处旧货市场,我经常骑自行车去那里的地摊买书。长长的一条街,人行道上铺满了大大小小的书,有正的,有反的,有横的,有竖的,有薄的,有厚的,任你翻,任你选。相中了的书还可以砍价,在讨价还价声中,我常常满载而归。
买旧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家里有两本《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一本是上册,另一本是下册,就缺一本补编。一次,我去市场闲逛,无意中在地摊上发现了一本破旧的书,这本书既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我仔细一看扉页,正是《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补编》,我如获至宝,高兴极了,向小贩举书示意,他伸出一个手指头。别说一元钱,就是十元、一百元我也要买,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住房再挤,也要藏书
平生喜藏书,拱璧未为宝。当民办教师的时候,我有一个柳条编织的小书箱。课余时间,在陋室里,打开书箱,躺在床上,怡然自得地翻阅从城里带来的那几本书,觉得很幸福。三更有梦书当枕,书箱虽小,放在床边,深夜里,睡着了,心如秋月朗,古今多少事,上下五千年,尽在鼾声中。
1978年,这一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快,早春二月刚开学,“而立之年”的我就被调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当了小学语文教研员。那时,我已经藏了不少书,企盼有一个书架,给那些贴墙而卧,饱受浊尘、蚊蝇之扰的书找个栖身之地。妻子说:“家什倒有,想办法找一找。”在妻子的启发下,我寻来八个装肥皂的木头箱子,用旧报纸里外裱糊了一番,算是书架了。这八个木头箱子,两个一摞,一溜排开,靠在墙边,外加一桌一椅,顿觉小屋蓬荜生辉,雅气十足。
1988年,这一年对我来说特别难忘。一是我当上了特级教师,二是金秋十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从北京回来,妻子说:“你也算咱们县里的教育名人了,名人用肥皂箱子装书,岂不贻笑大方?”在妻子的提醒下,我慷慨解囊,从旧货市场买回一个带玻璃的旧碗柜,经过精心改造,终于使我用上了此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橱。
1992年,这一年我获双城市重大贡献奖,并享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搬进了政府奖励我的商品住宅楼。生活条件改善了,有了一间独立的书房,名曰“天地书斋”。妻子说:“哪有住楼房用碗架子装书的!今非昔比,鸟枪换炮,马上淘汰!”在妻子的督促下,我去双城最大的一家家具店购了一组高档的组合书柜。这组书柜长四米,六个门,整整占据了一面墙。书柜对面挂有两幅字画:一幅是著名演说家李燕杰给我的题词“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碧空云卷云舒”;另一幅是我的朋友写的“藏中外教育,聚古今思想”。书房中间摆着写字台和老板椅,在鲜花的映衬下,室内显得格外青春、典雅。我经常在书柜间逡巡摩挲,在走动中整理思绪,换得自豪与快意。
2008年,这一年我退休了,离开了魂牵梦绕的教师进修学校,家也由县城搬到省城,过着酒盈杯、书满屋、心静如水的生活。
经历了四十多年鸟儿衔草絮窝般的积淀,我有了一万余册藏书,亟需再添置一组书橱。妻子说:“家具城卖的书橱质量差,款式俗,不如咱们自己量身定做。”在妻子的建议下,我把木工请到家里,选了上乘木料和顶尖油漆,亲自设计图纸,亲掌绳墨规矩,两周后,也就是在第二十四个教师节那天,一组紫檀色的上下直通的书橱便矗立在我的书房里了。驻足顶天立地的书橱前,我仿佛是在一扇小小的窗户里窥视浩瀚无垠的海,又好像坐在书做的船上,向那片大海的深处驶去,真是惬意极了。
时间再紧,也要读书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十分喜欢朱熹这首流传千古的读书诗,它告诉人们:由小小方块字集成的汉字书籍,就像一面巧夺天工的“水镜”,清澈深邃,闪耀浮动,能够映出自然和社会的“天光云影”,通过阅读鉴赏,可以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思想活水”。所以,对我来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认为,世上万物,皆属身外,唯有一样东西能点入肌肤,融入骨髓,让我们耳聪目明,风度高雅,气宇轩昂,志存高远,这,便是书。
每当落日余晖消失,白天嘈杂、纷乱退却的时候,四周静谧而美好。沏上一杯弥漫着清香的绿茶,要么慵懒地席地而坐,要么靠在床头,在灯光的笼罩下,手持一卷好书,鼻翼轻轻翕动,深吸一口淡淡的油墨芳香,然后在轻柔的音乐声中,让躁动的心归于沉寂,静静地沉到书中去,沉到那些美丽的文字或是深湛的思想中去。一书在手,万事皆忘,这就是我读书的感觉。
哈尔滨有一家最大的书店叫学府书城,毗邻黑龙江大学。走进书店大楼,我就像飞翔在花丛中的蝴蝶,眼睛都看不过来了。这个书架前转转,那个书架前晃晃,翻翻这本,瞧瞧那本,在浏览中,一旦发现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的书,我就找个没人的角落,或站,或坐,或蹲,或卧,左手一口馍,右手一本书,兜中一瓶水,一读就是一天,直到书店打烊我才悄悄离去。
我读书不成体统,属“杂学”类,名人传记、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当然,我更爱看一些“闲书”,诸如《奇门遁甲》《周易》等,虽然有的书并没有真正读懂,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但这种“蜜蜂采蜜”式的阅读,对开阔我的视域确实大有裨益。
黑龙江省图书馆是我休闲的天堂,每逢周日,我这个“白头翁”便早早地挤进人群,在阅览室里抢个位置,拿出笔记本和放大镜,进行我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生活。
我觉得这样做好处很多。首先,做读书笔记就不能书看完了就算了,而要好好想一想,书中哪些东西是值得记、应该记的,这样一想,就无异于锻炼了判断、概括等方面的能力。其次,要写读书笔记,就不能只看一遍了事,而是要看两遍三遍,这样就加深了对书本内容的理解,也加深了印象,不容易忘记。再次,更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做读书笔记的目的,就是今后在思考同类问题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翻阅、对照、查核、归纳、总结,加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甚至形成一种观点和见解。退休十年,我已做读书笔记二十余本,厚厚一摞子,加起来足有几百万字。
时间是一个无头无尾的系列,昨天已经逝去,明天还没到来,可以抓得住的就是今天。我常这样想,补昨天之非,创明天之是,必须通过今天的努力;要想今天胜过昨天,明天又胜过今天,也只有努力于今天。今天有时间读书吗?有!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明月当空时,灯火阑珊时,夜深人静时,每天晚上睡觉前翻看几页书,这是我的习惯。
有人说,苍茫的天空中,鹰是最美的风景;有人说,广袤的旷野上,树是最美的风景;我这个退休的“白头翁”说,愚昧的人世间,书是最美的风景。书籍可以嫁接人生,阅读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改变。读书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读书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读书不能改变人生的物象,但可以改变人生的气象。让我们以书为友,天地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