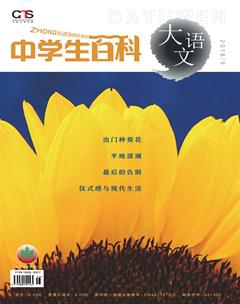读《我的阿勒泰》
李兰

爱书之人读书如同行山,穿越陡峭或蜿蜒的山间小径,留下深深浅浅的足迹,才能看到远方美丽的风景。我们常常会为足迹的重叠而欣喜,因为寻觅与分享,是读书最大的愉悦。
不知道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身在繁华绮丽的都市?还是热闹活泼的小镇?抑或荡漾着青草香、泥土味的乡村?不知道你的生活是三点一线,除了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都在题海中奋战?还是放学后在热闹的街市上闲逛。在河边的垂柳下疯跑?抑或每次上学都要走过窄窄的田埂,或穿越一片低矮的小树林?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最真实的世界无外乎就是我们行走于其中、可以真实触摸的这个世界。我们在荧屏上看到和听到的,基本都是“别人的世界”。所以虽然透过智能手机,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刷新闻,刷朋友圈,看电影,甚至通过视频聊天,随时链接另一个时空的生活,但是,我们真正能体验的还是屏幕外的生活。
然而读书不同。
读书可以让你体验认知边界以外的生活。它不只是可以像视频那样带动你的视觉和听觉,连同触觉、嗅觉、味觉,甚至是心灵和精神层面的感受,它都可以触及。而且,视频里给你的是整体性的“音”与“像”,如果镜头不给予特写,你脑海里的细节印象就会是笼统而模糊的,除了屏幕正中那个正在聚焦的对象所发出的某个特别的动作或者声音之外,画面中存在的其他细节都会在无意间被你忽略。
可是读书不同。
文字涉及的全部细节都将被你“看见”,没有涉及的细节也可能被你的想象捕捉到。你得到的不只是一個音与画的世界。更是一个所有感官都舒展开的从宏观到微观都充实丰盈的世界。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告诉你,读李娟的这本《我的阿勒泰》就会有这种感觉。
如果你没有去过新疆,没有去过戈壁沙漠,没有去过莽莽丛林,读李娟的文字,你就会有身临其境之感;而如果这些地方你全都去过,那她的文字就能让你重回故地。
朱天文说:“我在台北,我读到了李娟,真不可思议我同时就在李娟那唯一无二的新疆。”——唯有阅读才会给你这样逼真的进入感啊。
李娟笔下的新疆,美得让人屏息。
我曾经一个坡接一个坡地爬到过最高处,那里应该算是这附近的一个最高点吧。到达顶上时.视野开阔坦荡,群山起伏,满目都是动荡的事物。风很大。
我离开山顶,往下走了一截子,绕过山顶和林子转到那一面,结果大出人意料的是——如此高的山,那一面居然只是一个垂直不过十几米的缓坡,青草碧绿深厚,连着一处没有水流的山谷,对面又是一座更高的山。山谷里艳艳地开着红色和粉红色的花,而在我们下面木头房子的地方,花一般都是白色或黄色的。当然。野罂粟就是红色的,摇晃着细长柔美的茎,充满暗示地遍布在草地上:森林边上生长的野牡丹花,也是深红色的,大朵大朵地簇拥枝头——但要是和这片山谷海洋一般的红色花相比,它们的红却都显得那么单薄孤独。
我站在这面山坡的缓坡上,站在深过膝盖的草丛中间,越过眼下那一片红花海洋,朝山谷对面碧绿的缓坡上遥望,那里静静地停着一个白色毡房。在我的视野左边,积雪的山峰闪闪发光。
开阔坦荡的视野里有红的花海、绿的山坡、洁白的毡房、闪亮的山峰。这几乎合成了印象派浓墨重彩的大幅油画,色泽浓艳明亮,引人入胜。
她笔下的新疆。欢乐得让人羡慕。
每一棵树上都牵满了灯泡,每一张桌子上都堆满了食物,院子角落里篝火熊熊,上面支着的大铁锅沸水翻腾,浓郁的肉香把夜都熏得半熟了。人们走来走去,面孔发光。女人们去掉了臃肿的外套,身子灵活,举止轻盈,走过后,留下一股子掺着牛奶和羊膻味的体香。还有的女人抹了“月亮”——那是我们这里的女人们最常用的一种牌子的香水,虽然这种香水闻起来更像是驱蚊水,但是到了这会儿。它的那种强烈刺激的气息也只让人喜悦地感受到女人的青春和激情……每个房间的门都在不停地开,不停地关。开门的一瞬间,房间里华丽的宴席、强烈的灯光、歌声、欢笑、一股白色的热气……所有这些猛地、耀眼地从门洞突然涌出来,又在那里突然消失。
男人们都围坐在一间间温暖华丽的房间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任何一个话题都能到达最热烈的气氛。然后就是唱歌,一个人接一个人地轮流唱,再合唱,有人弹起了双弦琴,他满面红光,神情傲慢。拨弄了一阵子弦,和着旋律唱出了第一句——无比骄傲的一句——口型夸张,上嘴唇与歌声的铿锵一同用力,他的眼神都烧起来了!他突然扭头向你这边看过来,一下子捕捉到了你,令你浑身透亮,无处躲藏……
这种欢笑中蒸腾的热气感觉都能穿过纸背。朝着你劈头盖脸地扑过来。
她笔下的新疆。古老得让人敬畏。
滴水泉如同这片大地上的神明。它的水。一滴一滴从无比高远之处落下,一滴一滴敲打着存在于这里的一切生命痕迹的脉搏,一滴一滴无边无际地渗入苦寂的现实生活与美好纯真的传说。
那些所有的,沿着山缘,沿着戈壁滩起伏不定的地势,沿着春夏寒暑,沿着古老的激情,沿着古老的悲伤,沿着漫漫时光,沿着深沉的畏惧与威严……而崎岖蜿蜒至此的道路都被抛弃了。它们空荡荡地敞在荒野之中,饥渴不已。久远年代的车辙印如梦一般遗留在上面,它们比从不曾有人经过的大地还要荒凉。
荒野的古老,似乎是那种生命诞生之前的古老,人在这样的古老面前显得渺小而单薄。正如王安忆所说:“她的文字世界里,世界很大,时间很长,人变得很小,人是偶然出现的东西。那里的世界很寂寞。人会无端制造出喧哗。”
李娟笔下,新疆的变迁也让人感叹。
那时候,富蕴县也有很多街道和房子,但都被树林藏得深深的……而县政府的办公楼像童话中的小屋一样半隐半现在绿荫之中。我们估计在政府里办公的人还没有政府大院里的啄木鸟多。
那时候,每条马路的左右都各自生长着两排大树,两排树中间各夹有一条清澈的水渠。最早的时候,自来水供应不稳定,我们曾饮用过渠里的水。树梢在高空挤在一起,伞一样盖住整条马路。起风时,会有碎碎的蓝天晃在头顶。满街弥漫着浓郁的树脂和花絮的味道。
我一九九一年离开的时候,树都还好好的。一九九五年回来时,路边的双排树成了单排,水渠沟成了排污水的通道,里面的水别说饮用,洗衣服都不行了。一进城的那条路两边的树则全没了,只稀稀拉拉站了几棵死眉烂眼的小松树,跟盆景似的。一九九八年再回来,达坂上看到的额河已由蔚蓝变成了乌绿,浅了许多。森林没了,骷髅架子似的新楼突兀地一座座立了起来,清一色全是白的。
县政府最新拓建了一片广场,盖了几幢大楼。那片林子早没了,只剩最后的两棵大树一左一右站在政府大门口。不过那是上个月的事,不知现在还在不在。那条河呢,也被预制板封死了,作为下水道在黑暗中流淌着垃圾和残羹剩饭。我们透过大院的铁栏栅看去,庄严整齐的办公楼前那片广场上贴着两片整整齐齐的草坪,听说是进口的,一平方米很贵。
看着那样浓密的绿、那样纯粹的美一点一点地消失,难过的心情就像是看李娟笔下被锯倒的数——
我还没怎么看明白,那边伐树的电锯声越来越猖狂。接下来又一阵狂风骤雨似的群呼,那树便浑身颤抖着,慢慢向街道倾斜——是慢慢倒下的!我看得很清楚——这种倒不像是别的什么倒一样,说倒就倒;这种倒,缓慢得极不情愿,像临终者漫长的弥留之际那样迟疑而令人不安……这种倒落,比生长还要艰难,好像空气中有许多东西在对它进行挽留,而它也正在经历重重的障碍才倒向大地,慢得,慢得……慢得令人肝胆俱裂!
那样美丽的新疆如果沦为电锯掠夺后零落潦倒的遗迹,这种痛又岂是“肝胆俱裂”可以形容的!
凡是读过这些文字的人,都无法不惦记阿勒泰的美;凡是读过这些文字的人,都無法不产生想要呵护这种美的冲动。
所以说,文字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它能记录美,更在于它能激发出人们心底的热情和行动的能量。
李娟写新疆的系列散文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她的文笔了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她的视角非常特殊,她笔下人物的性情都十分动人。
想想看,一家子汉族人闯入维吾尔族人的聚居地,开了一爿小店,卖衣服、瓜子、花生、糖果、汽水、木耳、香烟、美酒、盐巴、面粉……当裁缝,当修鞋匠,当店小二……这样的一家人怎么可能不面对一系列的麻烦事?首先肯定是语言不通带来的交流障碍,接下来还会有文化习俗差异带来的各种无奈。可奇妙的是,我们在李娟的文字里看不到由于这些“差异”所产生的生硬冷淡的隔阂感,而是各种可爱的误会、各种温情的理解、各种妙趣横生的努力沟通。比方:
小孩努尔楠的声音属于那种音量不大,穿透力却特别强的类型。娇脆、清晰,像是在一面镜子上挥撒着一把又一把的宝石——海蓝、碧玺、石榴石、水晶、玛瑙、猫眼、紫金石、霜桃红、缅玉……叮叮当当,晶莹悦目,闪烁交汇……你缓过神来,俯首去拾去捡的时候,另一把又五光十色撤了下来,真正地应接不暇。而对我来说,这小孩声音的最大魅力还是在于:他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而他才不管这些呢!他只管说,很认真很详尽地娓娓道来,表情专注得似乎很是把正说的这事当成一回事。他眼睛黑白分明地望着我,时不时夹着一两个手势来补充或者加重语气。有时也会停歇三两秒下来,似乎在等我表态,想知道对他所说的那件事情的看法如何。看我不说话,又独自解释,或者补充了下去。表情还是极其认真而郑重的,好像说的是些与生态环境,或者和平、发展有关的事情。最后我终于迫使自己从这迷惑力极强的语言氛围中清醒过来,努力地,仔细地辨认着那些似曾相识的哈语词汇……
终于听懂了——
他在反复地说:“……苹果有吗?瓜子有吗?糖有吗?汽水有吗?……”
我说:“钱有吗?”
说了这话,立刻后悔得想踢自己一脚!多没水平的话!多煞风景,多俗气!
果然,他听后愣了一下,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微张着鲜艳的小嘴:“钱?……钱……”然后表情立刻沮丧下来,满脸一副被伤得体无完肤的样子。
我连忙赔上满脸的笑,转身抓了满满一把杏干,又抓了一把瓜子。统统塞给他。小家伙噙着眼泪嘟囔着接过来,慢而小心地,一个不漏地把东西从柜台上抹入胸前的小口袋里。然后仍是一副难过万分的样子,转身一步一步,委委屈屈地走了。
之所以“差异”能以如此令人捧腹的方式弥合,就在于沟通的双方都抱着孩童式的天真和坦诚,都抱着一种开放的好奇和真挚的友善。
在这样一个地方,一块塑料布就能支出一个小店,除了冬天饿极了的牛偶尔会来“踢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还真就能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会因为别人误会他偷了一条裤子而连夜跑十几公里雪路,赶到这人家里来解释。
这段路大概有十几公里,一路上除了白的积雪和蓝的天空,全世界就什么也没有了。由于雪灾的原因,今年的雪比往年哪一年的都厚,山侧的雪更是厚达二十多米,路两旁的雪墙有些地方足有两米厚,至于脚下这条路,被过往的马匹、雪爬犁踏得瓷瓷的了,也是半米多厚的雪壳,深深陷落在雪的原野中。我们想到昨晚那个孩子就是沿着这条路又着急又委屈地往我们家走来的,一路上他会不会因为被误解而感到孤独?这条清白之路……
照很多人的想法,既然知道自己没有做什么错事,任何解释都是根本不必要的。被冤枉后该做的事,就是与冤枉者为仇。但他们究竟想到了什么呢?
似乎在这样一个干净到透明的地方,就算是做一件非常小的事,心里都会带着满足感,带着医意,哪怕是睡觉都可以睡得叫人心生羡慕。
这山野里,能睡觉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随便找处平坦的草地一躺,身子陷入大地,舒服得要死。睡过一个夏天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你。
有时睡着睡着,心有所动,突然睁开眼睛,看到上面天空的浓烈蓝色中,均匀地分布着一小片一小片鱼鳞般整整齐齐的白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像是用滚筒印染的方法印上去似的。
那些云,大小相似,形状也几乎一致,都很薄,很淡,满天都是——这样的云,哪能简单地说它们是“停”在天空的,而是“吻”在天空的呀!它们一定有着更为深情的内容。
但事实上,透过这些诗意而轻盈的文字,我们可以望见文字背后的孤独、清贫、艰苦和荒凉,但由于隔着一颗颗质朴玲珑、善良可爱,且始终对生活充满着热爱和感激的心灵。我们还从孤独中看到了深邃的哲学之美,从清贫中看到了单纯的简约之美,从艰苦中看到了智慧的坚韧之美,从荒凉中看到了阔大的时空之美。
因为边塞生活单调,日子漫长无聊得就像是一块面无表情的岩石,反倒是生活的磨难在这块顽石的表面勾画出了别致而又意味深长的花纹。看李娟写苦难常常就像在看憨豆的滑稽小品。
他走了。我可惨了!被丢在荒山野岭,家还是那么远,保不定又碰到个骑马的坏小子……包里还揣着几千块钱,准备看完弹唱会后顺道下山提货的……不敢再往下想了。那时已经穿过一大片过去年代的木结构坟堆,来到河边。河水又浑浊急湍,实在看不出浅水段在哪里。只好顺着刚才的马蹄印子慢慢下了河,胆战心惊地感觉水到了小腿,水到了膝盖,然后又漫过大腿……到腰时,我简直一步也迈不出去了!汹涌的水流绵而有力地把我往下游推挤。此时自己浑身所有的力量也就恰好只能抗衡这样的冲击了。要知道水淹得越深,身体的受力面积越大。我现在已经站在河水中央,谁知道下一步会逐渐浅下去还是踏入一个深渊?我紧紧抱着我的包——刚才那个小色狼都没让我这么害怕过!……天晓得最后我怎么过去的!反正还是过去了。接着又过了一条更加惊险的河。当我踌躇满志走向第三条河时——和前两条相比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小小的水沟——就在那时……事后的情景是这样的:我从岸边歪歪斜斜站起来,吐了一口浑浊的河水。眼镜还在,真是奇迹。
我常常想,该有多强大的内心,才能将这种程度的惊险和辛酸都化为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举重若轻,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跟你娓娓道来?
所以,其实借由读书我们不只是在体验另一種生活,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遇见文字背后的那些高贵而美丽的灵魂。他们会为我们重新打开面前这个熟悉到乏味的世界,这个在我们眼里已经失去了温度和新鲜感的世界。这些文字,能够让我们重新发现世界的鲜活有趣,发现世界的浩渺和深广,更能够让我们单只是为了“活着”就心存希望、心生喜悦、心怀感激。
就像李娟说的,“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满不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
有人说,李娟就是新疆的三毛,也有人将李娟跟阿勒泰的关系比喻成萧红跟呼兰河的关系。李娟的文字温暖而纯真,轻松愉悦又隽永迷人,我常常捧着她的书忍不住笑出泪来,弄得家人还以为我中了邪。
下个月我想跟大家聊聊野夫的《乡关何处》。读完李娟再读野夫——嗯,大家还是自备面巾纸比较妥当。下个月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