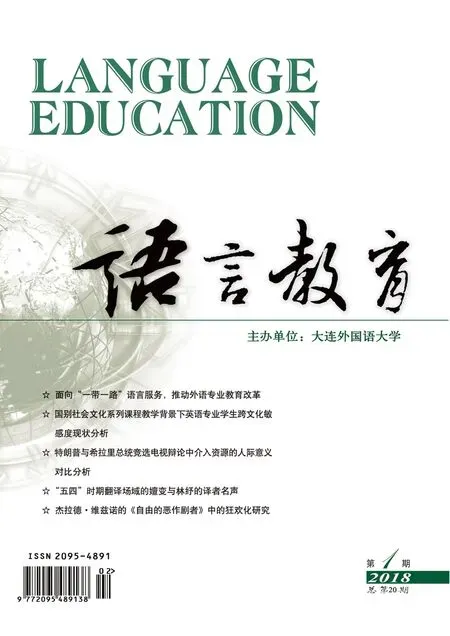“五四”时期翻译场域的嬗变与林纾的译者名声
廖 涛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中山)
1.引言
林纾是近代中国译介西洋文学的先驱,却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众矢之的。他的译者名声在“五四”时期发生逆转。不少论者认为林纾的后期译作较之前期逊色的原因是其个人思想退化。林纾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新旧思潮在“五四”时期激烈交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翻译场域亦随之嬗变。林纾作为翻译活动的实践者,同样受到场域力量的影响。本文拟从翻译场域的角度分析林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译者名声变化的原因。
2.翻译场域
“场域”(field)是布迪厄(Bourdieu)社会学的核心术语之一,指的是“拥有相对独立运作规则的社会空间”(Bourdieu, 1993: 162)。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借鉴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翻译问题。场域并非可触及的实体,而是用来描述和解释社会关系的一个概念。人具有社会属性,在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社会结构影响人的行为和思想,人也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布迪厄认为阶级背景、环境、语境对于个体的影响从来不是直接的,这种影响总是以场域结构为中介(斯沃茨,2006: 138)。任何场域都是相对独立的关系系统,与周边场域相互渗透。所以,我们要考察翻译场域之中的规则,就需要观察它与周边相关场域的关系和互动(王悦晨,2011: 9)。场域是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译者在翻译场域中所占位置的高低取决于其占有的资本(capital)。翻译场域与权力场域及文学场域有着密切的联系。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中力量格局的变化会导致翻译场域规则的变化。场域概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社会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刻解读与翻译活动相关的种种关系和规则。
3.林纾在“五四”前翻译场域中的位置
林纾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位不审西文,却享有盛誉的西方文学翻译家。他以合作翻译的方式走向了文学翻译之路。“林译小说”已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该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林纾在翻译场域中的位置取决于其占有的文化资本。资本与场域是相互关联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场域也离不开资本,场域只是一种网络结构,如果没有资本,空洞的结构也是没有意义的(宫留记,2009: 105)。
3.1 林纾的文化资本
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来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他对马克思及韦伯的资本理论进一步改造后,把资本的表现形式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不同的资本类型之间存在可转换性。行动者在特定场域中所处的位置是由其在该场域中拥有的资本决定的。翻译场域和文学场域相互交融。在林纾生活的时代,大部分读者不能直接阅读原作,译作往往被当成原作来阅读。林纾不谙外文,其作为译者的象征资本主要从文学场域转化而来。
文化资本包括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特纳,2001: 192)。林纾的文化资本是其在所处的社会文化制度中被认可的文化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林纾出身寒门,要博取功名,唯有走科举应试之路。1882年,林纾中举。举人头衔让他获得了制度化文化资本。制度化文化资本是指在学术上得到国家合法保障的、认可的文化资本,它表现为行动者拥有的学术头衔和学术资格(宫留记,2009: 127)。这种头衔让他结交到更高层次的人士,更多地参与文学活动,从而扩大了影响力,获得了更多的文化资本。
林纾中举后曾六次参加礼部试,均告落第,从此不再图仕进。放弃科举之后,他笃学古文、研治宋学,终成晚清古文殿军。他的古文能力获得桐城派清末领军人物吴汝纶的赞赏。桐城派以“以古文为时文”,在清末文坛占统治地位。吴汝纶称赞林纾的古文,“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林纾,1927: 25)。布迪厄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隶属于自己的正统文化。它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位置指的就是行动者在场域中根据握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的差别被分配的地位(宫留记,2009:52)。林纾卓尔不群的古文表达能力便是一种正统文化,这使其在晚清的文学场域中处于有利位置。
3.2 开文学维新风气之先的翻译家
“林译小说”开文学界维新风气之先。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曾赋诗“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马祖毅,1998: 424)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林纾反帝救国的翻译动机。这一点与维新派变革维新,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
1894年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1895年康有为率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发起了“公车上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维新思潮迅速传播开来,进而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影响了晚清政坛。在进行政治改良运动的同时,维新派也发起了文学改良运动,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其中,“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最为深远。而译介西方小说又是“小说界革命”的重中之重。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在《国文报》发表《本馆付印说部缘起》,力倡译介欧美小说以开启民智。梁启超主张“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地译之(张俊才,2007: 60)。”
梁启超首先是位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他的文学活动直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维新派对晚清权力场域的影响力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达到顶峰。布迪厄把场域所处的社会空间称为“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指的是在社会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能力的结构空间(Bourdieu, 1993: 37-40)。权力场域是所有场域中最重要的一种,发挥着类似于“原场域”(metafield) 的功能,在所有场域中起分化与斗争的组织原则的作用 (Bourdieu, 1992: 111-112)。文学场域在权力场域中属于被支配的地位(Bourdieu,1993: 37-40)。维新派凭借在权力场域的影响力,获得了文学场域中的话语权,构建了当时文学及翻译场域的主要规则。林纾积极响应当时的维新潮流,在诗集《闽中新乐府》中表达了反帝爱国、变法图强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1900年,他在上海《译林》杂志的创刊号序言中写道:“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止唯有译书”(王宏志,2007: 92)。
林纾进入译界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王寿昌、魏易等合作译者看中的是林纾具有的而他们所欠缺的翻译场域中的象征资本——良好的古文功底和文学界的影响力。王寿昌邀请林纾共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对他说:“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杨荫深,1939: 486)于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就通过这种独特的翻译方式在中国面世了。该译本行世后即引起轰动,“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不胫走万本”(郭延礼,2005: 211)。文学界名流对该译本的赞叹不可胜数。严复作了“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高度评价(陈平原,1989:28)。邹振环把《巴黎茶花女遗事》列为影响近代中国的一百种译作之一,认为它是对中国士人产生影响的第一部西方小说,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开创了一代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风气,还在于这部小说的译刊,从一定意义上使清末士人的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邹振环,1996: 122)。首部译作的成功奠定了林纾在译界的地位,为他在翻译场域积累了文化资本。从此,林纾在译坛耕耘了二十多年,共译书179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者,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及译坛泰斗(张俊才,2007: 77)。
“林译小说”引发了国人对西方文学的兴趣,不仅引入了新的文学观念,还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思想,在促进中国社会向西方学习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晚年谈到他在1915年写的《康南耳君传》时说道:“我那时还写古文……那时叙事文受到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胡颂平,1993: 280)。周作人称晚清译界代表人物严复、林纾、梁启超三人中,他最喜欢的是林译小说,甚至还曾经模仿过他的译文(陈平原,1989: 177)。他在翻译集《点滴》的译序中写道:“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郑振铎,1935: 1228)。钱钟书坦言自己就是读了林纾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学的兴趣,《林译小说丛书》带他进入了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新世界(钱钟书,1981: 22)。
林纾的翻译推动了中国文学的革新,孕育了新文学的胚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文学基础。受新文学形式的影响,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的规则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点是林纾始料未及的。
4.“五四”后的翻译场域与林纾的译者名声
场域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完全自主和孤立的场域是不存在的。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对翻译场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中国思想界新旧思潮交织纠缠,一度处于混乱的状态。虽然封建帝制被推翻,但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政治革命在思想界的延续。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中的力量格局。受制于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的翻译场域亦随之变化。林纾在“五四”前翻译场域中拥有的文化资本逐渐衰落。
4.1 “五四”时期翻译场域的嬗变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中国建立了现代的政治体制,但国民的思想观念却与之相去甚远,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任务尚未完成。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袁世凯极力推行尊孔复古,为帝制复辟运动提供思想文化支持。新文化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因而,一开始便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新文化人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弘扬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新青年》以思想启蒙为办刊方向,创刊之初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1917年初,胡适和陈独秀分别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引发了旧文化派和新文化派的论战,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新文化派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文言文一直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文化资本。士大夫阶级凭借这一资本垄断了知识场域和文学场域。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冲突。白话文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贵族的文学,发展大众的文学,为思想启蒙运动铺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迁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1987: 95)。新文化派对旧文学展开了颠覆式的批判。这一现象印证了场域中的斗争占位规则。在特定场域中掌握更多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倾向于采取保守性策略来维护场域中的力量格局;而掌握较少资本的行动者则倾向于采取异端的颠覆策略来打破现有的力量格局(布迪厄,1997: 147)。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推行白话文,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就不能普及到普罗大众,思想启蒙运动也就无法展开。经过激烈的“斗争”,新文化派最终获得“五四”时期的话语权。“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白话文成为通行国语,确立了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且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传统文学的典范以文言文为正统语言,要选取古人的白话文作品作为新文学的典范并非易事。胡适断言“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认为创造新文学唯一的法子“就是赶紧多多地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胡适,1998: 56)。因此,他和陈独秀等人在文学革命之初提出了以翻译为文学革命先导的主张,希冀通过文学翻译输入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体裁、文学思潮、创作技巧等等。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翻译作品在《新青年》上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新文化运动中成立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便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翻译在文学革命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认可。新文化派提出的用白话文创作、只译名家名著、用白话文翻译、以及“直译”等主张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主流规范,晚清以来的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的格局得以转变。
4.2 林纾文化资本的丧失与译界地位的没落
林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新文化派的口诛笔伐,成为众矢之的。新文化人痛批林纾使用文言翻译、漏译误译、随意改写和删减原作、选择不入流的原作等问题。1918年,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文批评林纾的翻译“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 (陈福康,1992: 209) 。1919年4月,傅斯年在发表于《新潮》上的《译书感言》一文中批评林纾:“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陈福康,1992: 217) 。梁启超评论林纾的翻译说:“有林纾者,译小说数百余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於新思想无与焉”(梁启超,1989: 72)。
林纾的翻译在“五四”时期遭人唾弃固然与其循常习故的文化立场相关。倘若我们把这一现象放到当时的社会场域中审视,可以发现林纾和新文化派之间的争斗,实质是对当时文学场域中话语权的争夺。单就翻译问题而言,林纾按理不应被新文化派如此痛恨。至于林译小说中出现的误译,林纾在1913年的《荒唐言》的《跋》中写道:“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而译,此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咸纠粗心浮意,信笔行之,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 ”(钱钟书,1981: 30)。林纾的口授译者校核不严,对误译问题也难辞其咎。意译是晚清的翻译风尚,不少译者在改写原作方面和林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所谓上海的翻译家;他们翻译一部作品,连作者的姓名都不注出,有时且任意改换原文中的人名地名,而变为他们所自著的;有的人虽然知道注明作者,然其删改原文之处,实较林先生大胆万倍”(钱钟书,1981: 19)。林纾使用的古文体有别于桐城古文,介乎严复和梁启超二者之间,不太古奥,也不太通俗,不太新也不太旧,大体可以用“平正简洁”四字概括(陈平原,1989: 177)。在白话文运动开始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新青年》刊载的译文还是以文言文为主。晚清翻译的删节改写,在初期《青年杂志》以至《新青年》仍有遗留(赵稀方,2013: 39)。1915年的《青年杂志》上刊登了陈独秀用五言古体翻译的泰戈尔诗《赞美》。新文化派另一领军人物刘半农在《新青年》诞生之前的若干翻译作品中基本上是用的浅近的文言文,直到1917年后才改为以白话文为主,在翻译方式上也是从意译转为直译(郭延礼,2005: 397)。此外,新文学派对林纾原著选择和林译小说意义的指责也有夸大之嫌。林纾前期选择的原作中不乏一些名著,即便是后期,分明也有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有孟德斯鸠的《鱼雁抉微》等书(钱钟书,1981: 38)。
林译小说影响了“五四”时期的一批作家,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场域是充斥着斗争的社会空间,而斗争可以改变或者维持场域中的力量格局。在“五四”前的文学场域中,林纾的翻译是反封建的、激进的力量。1905年出版的林译《迦茵小传》,因未删去迦茵未婚先孕,并生下私生子的情节,而遭到卫道者的攻击。文学翻译为林纾在晚清文学场域积累了文化资本,提高了个人影响力,从而使其获得了正统文化的认可。他在1906年被聘为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的教员。林纾早年接受的是封建教育,身上留下了传统文化观念的烙印,虽然后来步入维新派的行列,但始终认同君主制度。他在文学场域获得话语权后,便从激进力量转变为维持场域格局的保守力量。在新文化派推动民初文学场域变革的运动中,林纾担扮演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表示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陈平原,1989: 9)。他站在封建正统文化的立场,呼吁“力延古文之一线”,讥讽白话文运动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 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 则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郑振铎,1935: 6)。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改变了权力场域格局,受权力场域支配的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的格局随之变化。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思想广泛传播,林纾仍旧抱住所谓的正统文化不放,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因而他成为新文化派“文学革命”的首选对象。他在译界的名声终于随着其文化资本的丧失而逆转。
5.结语
在“五四”前的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中,林纾出色的古文能力是其博得名声的文化资本。林译小说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顺应了当时在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掌握话语权的维新派以文学改良促进政治改革的主张,是进步和革新的力量,因而获得了很高的名声。“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文学场域的变革,使古文失去了正统文学语言的地位。林纾在翻译场域中的名声随着其文化资本的丧失而没落。场域概念为研究林纾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社会空间中与翻译活动相关的各种力量博弈对译者的影响。
[1]Bourdieu, P.& L.Wacquant.1992.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Bourdieu, P.1993.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 on Art and Literature[M].Cambridge: Polity Press.
[3]陈独秀.1987.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4]陈福康.1992.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5]陈平原.1989.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美]戴维·斯沃茨.2006.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7]宫留记.2009.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8]郭延礼.2005.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9]胡适.1998.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A].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胡适文存[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0]胡颂平.1993.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C].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1]梁启超.1989.饮冰室合集(专集34)[M].北京:中华书局.
[12]林纾.1927.畏庐续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
[13]马祖毅.1998.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4][法]皮埃尔·布迪厄.1997.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5]钱钟书等.1981.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16][美]乔纳森·特纳.2001.邱泽奇 张茂元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北京:华夏出版社.
[17]王宏志.2007.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8]王悦晨.2011.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J].中国翻译,(1):5-13.
[19]杨荫深.1939.中国文学家列传[M].上海:中华书局.
[20]张俊才.2007.林纾评传[M].北京:中华书局.
[21]赵稀方.2013.新青年的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 (1):38-44.
[22]郑振铎.1935.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23]邹振环.1996.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