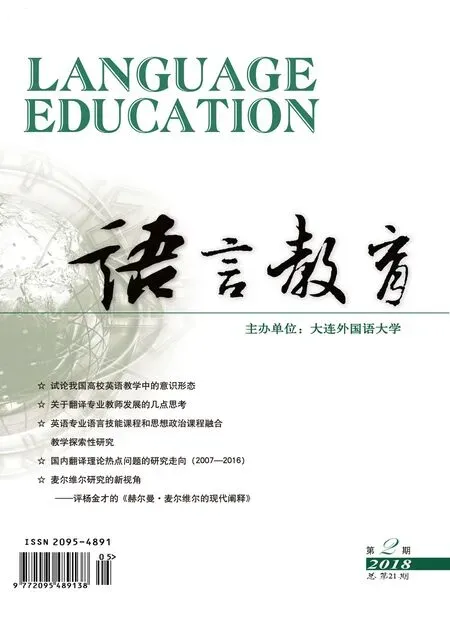法的自创生理论视角下的立法文本模糊语翻译研究
李 晋 居 方
(1. 南京审计大学,江苏南京;2.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南京)
1. 引言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履行我国加入WTO时所做出的法律信息公开的承诺,加强我国法制化建设的对外宣传工作,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分别组织专家进行了法律法规翻译并设立了网站予以公布。全国多个省市在积极开展地方性法规规章立法工作的同时,也开展了相应的翻译工作。比如江苏省自2005年就启动了地方性法规规章翻译工作,至今共完成一百多部江苏省及其所辖市的法规规章翻译工作。立法文本作为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执法所依据的标准,其文本语言应该清晰准确,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因此,立法文本的译文应当准确地再现立法意图,清晰地传递立法文本原文的信息。然而,追求概念精确、逻辑完美的立法文本语言中存在着大量模糊的词、句和逻辑关系,对译员开展翻译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关于立法文本中模糊语言的翻译,不少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杜金榜(2001)指出法律语言存在着模糊性,司法结果又要求确定性,如何从模糊性过度到确定性是法律语言研究者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从准确性和模糊性的关系、模糊性存在的原因、模糊性的消除、司法语言确定性的表现以及法庭活动中语言运用的特点等方面讨论了法律语言模糊性的消除过程。董晓波(2004)认为立法语言是一种具有规约性的语言分支,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法律规范的概括性,法律现象的特点及语言自身的特点等原因,立法语言无法避免模糊性,因此立法文本采用立法解释,高度程式化立法语篇和求同型近义词的堆积使用等手段消除立法语言模糊性,制衡法官自由裁量权。熊德米(2008)指出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法律术语的不确定性上,译者要确认法律术语和概念在异域法律语言中的对应层面,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来实现法律意义和概念功能的对接。对于如何在翻译中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来处理模糊性语言,众多学者认为其根本在于准确把握模糊性语言的机制,准确领会其使用意图,实现功能上的对等。现有针对法律模糊语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翻译提出了积极的指导意见,但是现有研究还未能全面解释法律模糊语言的形成机制,还需要对法律模糊语言开展进一步研究,丰富现有理论,为翻译提供更全面、有效的指导。本文从法的自创生理论视角对立法文本中模糊性语言的产生机制进行研究,发现法律语言的自治性,法律系统的进化和法的三值逻辑是立法文本使用模糊语言的内在需求,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翻译中如何采取相关措施,保证翻译质量。
2. 语言的模糊性
法律语言是法律的外在形式, 法律语言的产生受到立法传统、法律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其特殊的用语习惯,但是法律语言依然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具有人类语言的根本属性。为了有效地使用语言进行沟通和交际,人们总是期望使用有针对性、清楚、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思想,但是实际上,模糊性语言的使用贯穿了整个语言交际的过程。用语的模糊性并不是指语言使用不当而造成的语义含混不清的消极效果,而是指采用无法准确定义,内涵和外延不确定,可能有多种解释的语言所产生的效果(杜金榜,2001:305)。从认知论的角度来看,语言源自人类思维,语言的模糊性源于人类思维的模糊性,包含了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对象——客观事物的模糊性和人类对客观事物认知的不确定性和由此产生的概念的模糊性(陈红桔,2006: 212)。
人类用于反映客观事物的语言是一个符号体系,它所包含的符号数量是有限的。而人类用数量有限的语言符号所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数量却是无限的。在丰富多彩的世界里,客观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且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属性,这就像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是自然现象,因此客观事物的内容是复杂而具体的。另外,语言的产生主要基于人类过往的经验,而语言所需描述的客观事物不仅包括过去、现在,也包括未来,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面对客观事物数量上的无限性,内容上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的属性,使用固定、有限的语言符号必然难以清楚、准确地反映出相关内容。因此,在人类语言面前,客观事物必然显现出模糊性。其次,从Zadeh(1965)的模糊集合理论来看,人类的认知和思维过程是复杂的,而认知与思维的复杂性与高精确性是互不兼容的,其结果必然是难以找到精确的概念来反映客观事物。在思维和认知的过程中,语言符号和所指的客观事物之间并无直接、必然的联系。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形成了概念,而概念的表达要借助语言符号。因此概念成为了连接客观事物和语言符号的桥梁。但在构筑概念这一桥梁的过程中,众多因素,如政治、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地理等都会对概念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概念向语言符号的转化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语言习惯、用词与语法规则等都会对符号的形成产生影响。
3. 法的自创生性与模糊语言
由于语言具有模糊的基本属性,因此立法文本中也存在模糊的语言,从表面上看,这与法律追求的清晰、准确、“定分止争”的要求互相矛盾。但是,事实上立法文本中模糊语言的存在却是源自法律的内在需求。从法律和社会的关系来看, 法律是特定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社会中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葛洪义,2000)。一部好的法律应当是“适应社会发展进步、人类文明进程的法律”(张仁善,2001)。随着社会功能的不断发展和进化,社会变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对于社会变迁而言,法律既是一种“反应装置”,也是一种“推动装置”,法律在与社会的“反应—推动—再反应”这一系列互动过程中实现与社会的同步化(Friedman,1972: 11)。然而在同步化的进程中,面对高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法律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要使法律发生变化,通常需要形成社会的和政治的压力,甚至这种压力出现之后也可能受到抵制和阻止,除非它们的力量强大且具体”,因此法律必然难以承接这种变迁(埃尔曼,1990)。从托依布纳(2004)提出的“法的自创生理论”视角来看,法律自身具有的滞后性缺陷,在面对社会变迁的压力时,正是依靠模糊语言来给予立法文本的规定性以可延展的空间,从而实现法律在社会变迁中的动态调整。
3.1 自治性与模糊语言
托依布纳(2004)认为法律是一个自治性、超循环的、认知上开放的自创生系统。法律实现自我创生的基础是法律的自治性,当一个法律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规范、过程、特性—构成自关联循环”的时候,就达到了法律的自治,而“当按照这种方式形成的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连接成一个超循环时”,法律就达到了“自创生的自治”。自创生理论中所指的自治性——不同于形式主义法学中的自治性,以“教条”(doctrine)的方式划定了法律、社会、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边界,也不同于工具主义法学中的自治性——使用“隐含式的直线型因果关系(unilinea causality)模式”来解释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布迪厄,1999;Teubner,1984)。为了给法律的自治性更宽广的空间,实现法与社会系统中其它各子系统的沟通,托依布纳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借助“结构耦合”的方法,将法与社会系统联系起来,因此,自创生理论中所指的自治性是与社会系统相联系,与社会变迁相同步的自治性(Luhmann,1992)。法的自创生过程和自治性都是通过“自我描述”来实现的,而这种“自我描述”又依赖于语言符号的表达以及信息的传导(托依布纳,2004)。在社会变迁中,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语言和信息表达中所用的精确的法律文本语言必然“是缺乏生机的”,无法胜任沟通法与各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描述任务,而模糊语言由于其内涵与外延上的不确定性,可以承载其它社会系统的信息并将其“内化为法律系统的信息”(张玉洁,2014: 159)。
3.2 法律系统的进化与模糊语言
法律系统的自我创生在自治性的基础上,不仅着眼于法律要求什么、禁止什么的问题,更重视法律如何做到这些的过程,为了保持与社会压力的要求相一致,法律系统会随着社会各个子系统的不断发展和进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之中。托依布纳(2004)认为这一进化过程是一个“盲目”的过程,它“明显地受法律自创生与有关社会系统自创生的双重选择性的调整”。面对社会变迁与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法律进化,如何在进化的需求和法律所追求的稳定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法律系统在进化过程中完成自我描述、自我调整、自我重构是自我创生实现进化的重要步骤。
作为具有自治性的法律系统,信息输入独立是它的主要特征,法律系统在信息获取方面主要通过自主信息筛选,向系统输入信息(Hejl,1984)。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压力传递到法律系统时,法律系统与外部环境通过语言符号的信息载体功能、信息输入功能和信息输出功能实现两者的相互沟通。在进化过程中,法律“系统按照一种转换功能的标准把输入转换为输出,这种转换功能使这些系统能够自我保持在一个通过进化达到的复杂性水平上”,从而实现法律系统稳定的进化过程(卢曼,2009)。而在这一进化过程中,精确语言由于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缺少额外的信息承载空间,只能发挥信息载体功能和信息输出功能, 而不具备信息输入功能。相反,模糊语言的内涵和外延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天然的“开放性”使其获得了额外的信息承载空间,可以将外部环境变化对于法律系统的压力通过模糊语言传递到法律系统内部,经过内化过程后再输出到法律外的其它社会系统(魏德士,2003:88)。
3.3 三值逻辑与模糊语言
法律文本语言对于准确性或确定性的追求,是基于传统的二值逻辑,也就是非真即假,不合法即非法的二值编码。受到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与哈特的“新分析法学”的影响,二值编码的概念期望通过过滤法律系统所获取的信息,将事实性的“无意义信息”过滤出法律系统,从而保障法律系统的规范性(冯健鹏,2006)。然而,面对社会变迁与社会子系统的高度分化,法律系统的“不确定性”日益明显,对于法律确定性的追求已经成为一个“法律神话”(Frank,1970)。托依布纳(2004)也指出法律系统的自治性源自法律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像法律本身一样古老”。法律的不确定性在语言层面的表现之一就是模糊语言的运用,而模糊语的使用的逻辑前提是“真、假、既非真亦非假”的三值逻辑(恩迪科特,2010:82)。托依布纳所说的法律的自治性是对法律系统内的信息做出“真值”判断,对法律系统外的信息做出“假值”判断,通过具有既非真亦非假的值域的模糊语言来完成“假值”判断向“真值”判断的转化,实现法律系统和其它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系统际沟通(张玉洁,2014:160)。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通常需要运用具有模糊性的语言符号,并通过对符号的处理,来实现真、假值之间的转化。作为信息载体的模糊语,在社会分化所形成的社会压力作用下,将法律系统外的信息向法律系统内部的传递,需要对模糊语进行筛选、加工和再生处理。通过筛选可以将符合社会分化压力需求的具有既非真亦非假的值域的信息保留下来。加工阶段对模糊语所承载的信息重新分类,使其在法律系统内获得有效分类。而最后的再生则是在外部社会压力下,将模糊语最终内化进入法律系统内部(张玉洁,2014:161)。
4. 法律文本模糊语言的翻译
4.1 系统际沟通与模糊语言翻译
在法的自创生理论中,法律的自治性特征要求将法律系统和其它社会子系统联系起来,实现系统际间的沟通。面对社会分化加剧所带来的社会子系统的变化,法律文本需要一定的弹性来实现应对社会变迁的动态调整。而模糊语言正是提供这种弹性的最佳方案。以《江苏省国防教育条例》为例,第十条“民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结合拥军优属、安置转业退伍军人,开展国防教育活动。”译为“Article 10 The departments of civil affairs, personnel affairs,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shall conduct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activities to support the army and exten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families of servicemen and martyrs, and the activities to emplace the demobilized servicemen and veteran”。该条款中提出的“拥军优属”通常指地方拥护和爱戴人民解放军军人,并优待军人家属。但是解放军军人的概念是广泛和变化的,有现役军人,退役、退休军人,伤残军人,牺牲的军人等多种。今天活着的军人明天可能牺牲,今天服役的军人明天可能退役。家属也是一个广泛和变化的概念,可以包括父母、配偶和孩子等多人,同时家庭成员也会不断变化,父母可能去世,孩子可能出生,夫妻可能离异。“拥军优属”使用了极简单的“军”和“属”这两个模糊的词,反而更全面地概括了两个对应的概念。但是在译文中,译者加入了“martyrs”(牺牲的军人)这个精确词,使得读者很容易根据这个词的词义而判断该词之前的“servicemen”指在服役的军人,这样就大大缩小了译文的概念范围。此外,“martyrs”的概念在911事件后有所变化,常被媒体用于描述我们熟知的“人肉炸弹”等恐怖分子,容易引起译文读者的反感。因此此处的译文不如简化为“support the army and exten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families of servicemen”。
法律的自治性要求实现系统际间的沟通,这对立法文本译者理解原文和把握读者接受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译者在解读立法文本时应当注意到,法律文本的阐释要实现法律系统和不断变化的其它社会子系统间的联系。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当认识到目的语读者同样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变迁,译文应采用适当的策略或手段,以保证译文与目的语读者所在社会子系统间的系统际沟通顺畅。在上文案例中,译者在翻译中把原本模糊的语言译成了精确的语言,其本意是使译文更准确,但实际上译文破坏了系统际间的沟通,译文效果反而不佳。在立法文本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根据法律的自治性要求,认真分析原文的模糊性特征、原文社会子系统和目的语社会子系统,充分认识到模糊语的作用,发挥模糊语的优点,使立法文本译文与各社会子系统联系起来,进而使读者更容易接受,最终实现系统际间的沟通。
4.2 法律系统的进化与模糊语言翻译
法律系统在应对外部社会子系统变化压力而自我进化的过程中,法律文本使用模糊语具有的额外的信息承载空间,将外部环境变化输入法律系统内部,并借助模糊语的开放性特征,通过内化过程后再输出到法律系统之外。在模糊语的翻译中,译员应采用相应的模糊语以完成“输入输出”过程,保证系统的不断进化。比如在我国法律翻译中,“未成年人”的译文存在争议,常见译法有“the minors”或“people under 18 year old”。一些译者和学者认为,前一种译文过于笼统,其意义和“teenager”、“juvenile”相近,不能体现出其特定的法律概念,而且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是指年龄未达到18周岁的人,而瑞士、日本等国法律规定20周岁以下为未成年人,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法律则规定21岁以下为未成年人,“the minors”译法可能混淆该词在不同法律间的概念,因此我国立法文本中的“未成年人”译为“people under 18 year old”更加妥当。
“18岁以下”是我国读者所普遍接受的“未成年人”这一客观事物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却不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认识。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认知具有本质上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语言作为认知过程的反映,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翻译就一定要去除这种模糊。法律系统中的模糊的作用是应对外部社会子系统的变化压力的,其额外的信息承载空间有利于将外部环境变化内化到法律系统中,实现自我进化。我们应当注意到“未成年人”这一概念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子系统中均存在不断进化的过程。在我国历史上有“加冠”的说法,相当于今天的成年仪式,加冠者的年龄是20岁,那么历史上未成年人就是指20岁以下者。随着社会变迁,人的智商和体质等都发生了变化,成年的时间也相应提前,当前我国法律就规定未成年人指18岁以下者。西方具有相似的情况,英国在诺曼征服后一般以21岁作为骑士的最早法定年限,成为骑士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加冠”,那么未成年人就是指21岁以下者。而今天西方各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年龄规定各不相同,有16岁、18岁、20岁或21岁等多种标准。面对社会中概念发生的变化,法律文本也需随之进化,但是法律文本又有着语言稳定性的要求,因此使用过于精确的表述,如“people under XX years old”,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就需要改变语言形式,难以维持语言的稳定性。在立法文本及其译文中,一些语言表述,如“minors”一词,避免使用精确的语言来划分不同概念间的界限,从而保证了文本具有稳定的语言形式,而且其概念具有可不断进化的空间。在立法文本翻译中,译者应当将法律系统的进化纳入翻译策略选择过程中去,在译文中保留模糊语的信息承载空间,保证社会子系统的变化因素能够顺利进入法律文本译文,反之,法律文本译文也可以适用于约束和规范不断变化的社会子系统。
4.3 三值逻辑与模糊语翻译
法律系统的运行主要通过表达程式来实现。在二值逻辑的前提下,法律主要采用“条件式程式”(conditional programme),通过“合法、非法”的二值逻辑来做出判断,而这种基于二值逻辑的“条件式程式”,无论它所罗列的条件如何全面,都无法涵盖社会中的所有情形,特别是在面对社会变迁和系统分化时,它无法做出及时、全面、有效地解释(卢曼,2009)。而在三值逻辑判断的前提下,具备开放性特征的模糊性语言可以全面有效地囊括各种条件,促进法律系统的自我创生。以《江苏省禁毒条例》为例,第27条“公安、经济和信息化、工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通信管理等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发布涉毒广告、涉毒销售信息、传授制毒方法等违法行为”译为“Departments of public security,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commerce, cultur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news publication, communications administration shall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investigate illegal acts concerning publicizing advertisements concerning narcotic drugs, sales information concerning narcotic drugs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producing narcotic drugs.”。禁毒工作极其复杂,法律无法一一列举符合条件的监管部门和监管对象,因此该条款原文为了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在监管部门和监管对象的描述中加入具有三值逻辑判断性质的“等”字。而在译文中,“等”字似乎被译者理解为了一个冗词,被从译文中剔除了出去。译文对于禁毒工作的规定更加精确,但是使译文丧失了原文具有的弹性,关闭了法律系统自我创生的大门。因此,此条款的译文中应当添加“等”字的对应译文“so on”。
法律的自创生性的基本特征是法律的不确定性,这种“真、假、既非真亦非假”的三值逻辑在语言层面的表现之一就是模糊语言的运用(托依布纳,2004;恩迪科特,2010)。译者应当认识到,只有通过对法律系统内的信息做出“真值”判断,对法律系统外的信息做出“假值”判断,通过具有既非真亦非假的值域的模糊语言来完成“假值”判断向“真值”判断的转化,才能实现法律系统和其它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系统际沟通,有效实现法律的自创生(张玉洁,2014:160)。在翻译模糊语的的过程中,译者要慎重,避免做出不当的二值逻辑判断,避免因社会变迁而频繁地修改和破坏法律制度已经设定的权利和义务方案,使译文和原文具有同等或近似的信息承载力和语言弹性,进而更好地实现法律和法律外系统的沟通,保证法律的自由、安全和预见性(博登海默,1999)。
5. 结语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强调法律语言的准确性,立法文本中的模糊语言常被视为一种语言弊病来处理。目前对于立法文本中模糊语言的研究多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展开,而从法律语言专业角度开展的研究较少,导致我们对于法律模糊语言的观点及其翻译策略有失偏颇。本文从法律的自创生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模糊语言在法律中的作用,认为立法文本中的模糊语言并非都具有负面作用,它们在实现法的自治性、法律系统的自我进化和避免二值逻辑判断的局限性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积极地看待模糊语,不要视其为冗余成分而随意删除、变更或增译,而要采用合理的翻译策略,保留模糊语的积极作用,实现立法文本中模糊语言对法律自我创生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