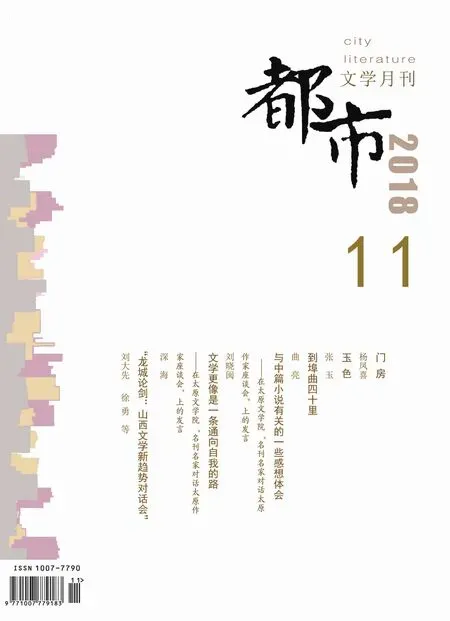文学更像是一条通向自我的路
——在太原文学院『名刊名家对话太原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深 海/ 文
大家上午好!我是《长江文艺·好小说》的编辑深海。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刊物。《长江文艺》杂志目前有两份刊物,原创和选刊,都是月刊。《长江文艺·好小说》是文学选刊队伍里的新兵,她创刊于2012年10月,是方方老师当长江文艺社长主编后力主创办的,主张“开放、包容、坚持、尊重”的理念。选刊虽然是新兵,可我们的原创却被誉为“新中国文艺第一刊”,它创刊于1949年6月,明年,它将迎来自己的70周年生日。
《长江文艺·好小说》在栏目设计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常用的栏目有:“再发现”、“好看台”、“推手推”、“青春季”、“江湖汇”、“民族风”、“翠柳街”。曾经还有过“e 视界”和“微天下”,这两个栏目后来基本上取消了。
“再发现”,顾名思义,就是打捞过去的遗珠,就是去发现过去发表没有被选刊选过的好作品。当然这个主要是从当代的文学大家、名家开始选,逐步把时间拉近。这个栏目一推出来就广受好评。
“好看台”,分中篇和短篇两个部分,这个栏目是我们刊物占比重最大的部分,主要是近期发表的小说作品。
“推手推”,主要是发现有创作潜力、势头较好的青年作者,或者已经写了多年有所突破的作家的作品。2013年12期我们推手推栏目发的是弋舟的小说,5年后,他获了鲁奖。
“青春季”,主要是从作品内容来判断的,不管是哪一代人的青春,写得好,我们都会选。
“江湖汇”,主要是放一些在题材上不那么好分类,可是又很有可读性,有趣,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民族风”,主要是给少数民族作家或写少数民族生活甚至只是以少数民族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设立的一个平台,当然,也是优中选优。
“翠柳街”,是编辑写简短评论的一个栏目,这个评论主要跟当期发表的作品相关。方方老师当初坚持要设这样一个栏目,她就是想“逼”着编辑多思考,多动笔,编辑光看稿选稿还不够,还要写,这个写的过程,对编辑自身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提升的机会。
这些栏目里,只有“再发现”、“好看台”、“翠柳街”是每期固定栏目,其他都是根据作品情况来定的,有什么作品就上什么栏目。
今天来的作家里,可能并不都是写小说的,也有写散文、诗歌、非虚构、评论的,我们《好小说》只选小说,但是中短篇的“非虚构”我也选过,只是比较少。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选刊编辑的一些工作体会。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我们现有的文学选刊都有哪几种,我就不一一细数了,我想说,各个期刊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坚持。这些选刊在所选作品上只会少量、部分重合,大多都有不同,否则的话,选刊一出来,目录都差不多,那还需要那么多家选刊吗?所以,其实,每家选刊也都在互相观察,尽可能降低重合率,给更多写作者入选的机会。当然你说完全避免重合也不可能,有些特别好的作品,有一两家甚至三四家选刊同时选的情况也是有的,只不过这概率相对较小。
我觉得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者,尤其是在创作上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写作者,一定要关注同时期优秀创作者的动态,而观察他们最好的窗口之一就是选刊。不仅仅是读,还要分析,它为什么能入选?它到底好在哪儿?选刊里的小说,经过原刊的一二三审,选刊的一二三审,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这些作品能够被选一定是有原因的,而这些原因,我想,也是我们应该关注和学习的地方。
作家都关心“写什么,怎么写”,也许,这些作品被选的原因,也在回答这个问题。我选过东北一个女作家孙焱莉的小说《桃花吐》,她写乡村生活,留守女性,这个题材新鲜吗?多少人写过啊,可是她写得不一样,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们《好小说》今年7期选了。她写得非常动人,我觉得她把人物都捧到了自己的心里,就是那种感觉,无比真诚。生活有时候是很残酷的,可是小说中的那个老母亲,种地,种桃,守护着家园,女儿,还有孙女,那种在严酷的生活里依旧自然流淌的爱,有种朴实而坚韧的美。它甚至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法国印象派画家柯罗的油画《枫丹白露的回忆》,还有米勒的《晚钟》。特别是《晚钟》,一片收割过后的麦田,一对衣着简朴的农民夫妇正站在那片土地上低头祷告,土地供给他们的并不丰富,可他们的感恩却是虔诚的,远处隐约可见教堂的影子,而你似乎能够听到教堂的钟声正和夕阳一起散播于整个画面之中。在艰辛和痛苦之中,我们在《桃花吐》里那个老母亲的身上也能够看到《晚钟》里那可贵的真诚、朴实,爱的温馨,让生命得以延续的秘密。作家写出了人物对生活、生命本身的虔诚,让作品有了一种庄重的力量。无常总是存在的,小说中女儿的丈夫,一个货车司机,就因车祸意外身亡,无常很容易把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打破。打破了以后还可以重聚吗?什么力量可以使它重聚?《桃花吐》给了我们一种答案,一种既现实又古典,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答案。当初,当印象派被哂笑跟排斥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柯罗和米勒他们用画笔替我们永远留下了欧洲最后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图景。我们的乡村也正经历着类似的基因突变,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农耕文明几乎彻底被瓦解,如果在新的文明中,这种虔诚与和谐从乡村、从我们的文化里、从作家的笔下消失了,我想,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甚至是隐患。
我选过一个四川作家叫杨不易的作品《老金的博物馆》,讲一个退休厂长,不适应身份转换,结果落入了骗子的圈套。骗子干什么的?开私人博物馆,这在前些年是个非常时髦的事儿,各种土法上马的私人博物,很荒唐很荒诞。老金跟骗子发生交集就是因为骗子要在自己的博物馆里给老金办一个个人成就展,代价呢,是老金两万块把家里的一个青花瓷瓶卖给骗子,而老金自己觉得那个瓷瓶并不值钱,他很兴奋,觉得自己赚大了,结果,后来传来消息,那个瓶子在香港拍卖了一个亿。这个人物是有代表性的,你看他那么在意自己个人的历史,却把一个承载着家族历史的物品给贱卖了,这个指向一下子就让作品有了深度和展开的空间,这个作品可以说首先在题材上就取胜了。
我在咱们山西的文学刊物《黄河》上选过一篇《木铎传奇》,作者任兆琮,我上网查了下才知道,他是一个古堡旅游项目的负责人,他把古堡的历史,用一种奇幻的方式写了出来。主人公是一个幼小的孩子,体弱,顽皮,充满灵性。为了能顺利长大,父母把他送进了寺庙,由老和尚照料和教养。一代一代的人消失了,可是寺庙老和尚的木铎却一直都在,它身上该有多少记忆,多少历史,这个木铎有一天突然变成了一个翩翩少年,陪这个小孩子玩耍,成了他的伙伴以及导师。小说这样写,一下子把容量打开了,里面有民族历史,有传承,有反思,有人物命运,很有味道。小说的语言也很生动,它是用一个小孩子的口吻展开叙事。木铎变成的少年把那个孩子和读者一起带入了古堡的地道,在那里,古堡的历史被展开,英雄开始复活,重新有了灵魂,而这些都成为那个幼小的孩子成长的营养,心灵之光。后来,在他长大成人的过程里,他也经历过很多残酷甚至荒谬的事情,可他心里的那个光始终都在,没有泯灭,这个光,在他身上被传了下来,也将继续传下去。这是古堡存在的意义,也是文学存在的意义。
我在咱们《都市》上选过一篇小说《土卫七十的七天》,作者叫陈景军。我们知道土星的卫星目前发现的应该只有63颗,小说以“土卫七十”为写作背景,有明显的科幻色彩未来色彩——这是一百八十年后的人类故事,它思考的是地球被完全破坏之后,人类将归于何处。在作者笔下,科技进步,对于人类的整体以及长远命运而言,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骗局。这个想法很主观也很大胆,而且这个题材不好写,可这个作者架构了一个不错的故事,完成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样的写作是需要想象力和勇气的,也是值得鼓励的。
孙焱莉,杨不易,任兆琮,陈景军,这些名字大家熟悉吗?
是的,他们既不是大家,也算不上名人。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好小说》真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不论是不是名家,哪怕你还是个文学新人,我们都重视文本本身,只要是好小说,我们都会给予支持和关注。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其实很希望看到一个好作品的作者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发现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选过《山东文学》的一个小说《1993年的离家出走》,写西北农村女性生活的,那种挣扎,惨状,写得有点狠,跟作者一联系才发现,他竟然是个90后,笔名鬼鱼,本名周才。后来在《山东文学》的一次笔会上遇到他我还在感慨,那么老道的开篇,真不像一个90后写出来的。我相信,这个写作者坚持下去一定能写出来,我也相信,他将来应该也不会忘记,第一个选他作品的是《长江文艺·好小说》。还有像陕西师大硕士在读的宋阿曼,也是90后的作者,她的一个短篇《第九个人》,我们也是首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说到开篇,中短篇小说的开头真的很重要。有一次活动,一个同行问我每个月要看多少刊物,我数了数告诉他,二十来本吧。他吃惊怎么看得过来,我说也不会每篇都看完,差不多看到六七百字的时候,如果语言、故事、那种味道都还没有吸引我,就会放弃了。结果他说他一般也就看个三百来字,没感觉的话,就不会往下看了。所以你看,如果你的开篇不吸引人,有时候,一个好稿子也会错失被选的机会。
这是开篇的重要性。另一个我想说,选刊跟原创在选稿时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有时候,原创发头条的选刊不一定选,除了对艺术性可读性和思想性的追求,选刊恐怕更注重“创新与超越”。我们,至少我每个月看到的原创期刊发表的作品,很大比例还是规规矩矩的写作。创新和超越其实就是对规范对既有范式的突破。我前面讲到法国印象派,印象派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被奚落嘲笑的一个画派,是被沙龙拒之门外的,可是现在呢?他们的价值还在被不断发现。特别是印象派后期的两个画家凡·高和高更,当年这两个人都穷得连生计都成问题,凡·高疯了,割掉了耳朵,死得悲惨,可他其实到现在还活着,不是有一部用他的画作串联成的电影《星空之谜》,几百个艺术家联手打造的,很感人。还有消息说,最新发现,凡·高的耳朵是被他的好朋友高更割掉的。这有没有八卦的成分,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到现在,他们仍然是被关注的焦点。高更是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里的主人公原型,生前画作卖不出去,死后作品拍出天价,3亿美元一幅画,那幅画叫《你何时结婚》,我忘了是14还是15年拍的,但他创造的这个历史至今无人超越,估计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都难以被超越吧。为什么讲到创新与超越要讲到绘画,看艺术史会发现,绘画艺术在创新与超越上总是引风气之先,对文学和音乐以及其他的艺术创作都会产生很大影响,这大概跟这种艺术形式更直观不无关系。这可能有点说远了,话说回来吧,有时候也不需要一下子有多大的超越,有多明显的创新,有一点就已经可以吸引我们选刊编辑的眼球了。
说到这个“新”字,我想,恐怕是很多写作者之痛,因为“缺乏新意”是我们被退稿的主要理由之一。其实,“写什么”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文学是人学,这个已是共识。可是人的处境呢?我觉得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人其实始终都处于“困境”之中,各种困境各种矛盾,因为人始终处于各种“关系”当中。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人的生命自由与现实生活桎梏之间的关系,等等。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中,我们发现,历史永远是神秘的,无论我们如何尽力,各种挖掘、考证,运用各种科技手段,科技越发达似乎对过去的探知就越深入越准确,可是仍然无法真正还原它;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里,人是无法改变世界的,因为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你只有通过改变自己才有可能改变世界;每个人最切身体会的困境就是,人的生命自由与现实生活桎梏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就是生存与自由之间的矛盾。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结果呢?你不可能一直看,那个宣称要去看看的人,最后落脚在了哪里?她生活得怎样?大家不妨继续关注。当然,去看看之后的生活,与之前的生活应该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看,人所无法摆脱的这些关系,人的处境,从来都没有变过,变的是什么?场景。人的故事发生的场景变了,以前发生在马车上的事情,现在发生在高铁上,甚至可能发生在手机里,也正因为如此,有了这些变和不变,文学有了永远不会消失也不会缺乏的关心和表现的对象跟写作的材料,也有了创新的可能性,材料无限,创新其实也是。
所以很多时候,“写什么”不是问题,“怎么写”的确是一个问题。怎么写?我觉得“场”很重要。你站在一个什么角度什么立场以何种观念来看你写的人物和故事,你让这个故事发生于何种场景,这些都很重要。有一个新开的综艺节目叫《幻乐天地》,据说是斥巨资为王菲量身打造的,我看过几期,它其实有点像中短篇小说写作,有要表达的主题、有要契合的歌曲内容和情调,怎么样让人物和故事在唱演之中立起来。最近一期,要表现一个孤独的男人,演员跟导演一上来就探讨,这个场景要放在哪儿,他们放在了宇宙空间站,他们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一个最合适的“场”。还有一个表现流浪狗的唱演片段,里面有一个镜头打动到我了,一个小男孩把一只被丢弃过很多次的小狗抱回了家,成了伙伴,很开心,可是小男孩的妈妈怀孕了,二胎,这个情节只有在当下这个二胎时代是合理的,计划生育时代就很难让人相信了。妈妈怀孕了,爸爸不顾小男孩反对把小狗装进了一个纸盒子带走了,小男孩在后面追,小狗透过纸盒上一个长方形小孔往外看,一开始还以为像往常一样是个游戏,是小男孩在跟它玩耍,当它突然意识到这是又一次被丢弃,它一下子安静了,观众却紧张了,小狗哀伤的情绪,在从小孔投进来的一点点光亮里,被聚焦了,更有冲击力。小狗身处黑暗的小纸箱里,它观察生活的视角很小,可是这里的小,却把重要的东西放大了,并赋予了更丰富的空间和内涵。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这个节目有多好,其实很多片段都很差,好的特别少。我是想说它跟我们小说创作有些相似之处,让我更加体会到“场”的选择太重要了。
在“怎么写”方面给我印象很深的作品我想讲几个。
有人说,“天才就是长期而耐心”地察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一个天才的写作者应该也是如此。首先我想说说钟求是发在《收获》上的那个短篇《街上的耳朵》,你看他怎么写少年的暗恋,本来约着打架的少年,在江南小巷,因为看到了女孩美好的背影,架也不打了,这一念的改变,这个少年的命运也被改写,他没有去打架,本来约好跟他打架的人把别人打死了。少年宣扬着自己的暗恋,女孩并不知道,女孩的未婚夫却为此打上门来,这一架打得少年丢失了一只耳朵。到了老年,曾经暗恋的女孩去世,老了的少年乘着夜色去吊唁,结果,第一次看到女孩的正面像,原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人,跟他保留在记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曾经令他魂牵梦萦的背影相去甚远,而这两男人呢,却在真相大白之后,约定要在女人的遗像前再打一架。很日常很普通的一件事,一些人,可是,中间不断出现反转,尤其是结尾的反转,让小说的蕴含更加丰富了,少年长到老年,这是一段漫长的时光,时光流逝,带走了很多东西,可是,那最真诚最宝贵的留下了,让读者久久回味。
还有女作家李月峰的一个中篇《离你有多远》。一个女人死了,可是,她短暂生命中出现过的有可能对她产生较大影响的每个人对她的全部记忆加起来,也无法勾画出她的人生,更别说有谁能够真正了解这个曾经在他们身边生活过的人。她写出了人的存在的那种孤独感,荒凉感,看得人很难受,因为,我们从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某种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忽视的真相。小说是发在《上海文学》的,我跟上海文学的副主编崔欣老师说,看了李月峰的这个小说,我才发现自己活得好肤浅。
还有一个我选的刘荣书的一个中篇《刺客传》,写乡村愚民买凶杀人的故事,他写得真好,首先在结构上非常用心了,上下两篇,分别以杀人者和买凶者的视角展开叙述。透过杀人者的“场”,我们看到买凶者的穷凶极恶,买凶的是三个人,他们意见不合,其中两个还是害怕,只想伤人,不想把人杀掉。可是,三个人中跟被杀对象村主任有血缘关系的人,村主任的侄儿却是坚决要杀掉村主任的那个人。他怕的是村主任的报复,“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你看他对这个村主任的怕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对法律的恐惧,这也可见村主任在当地的霸凌有多严重。而从买凶者的角度,我们更能看清杀人者的愚昧跟荒唐。整个作品充满潜藏的对比,现实和历史的对比、买凶者与杀人者的对比,不仅充满黑色幽默,也只有在这种对比中,这个特殊事件所牵连的时代背景、现实问题,才更加让人触目惊心。大家可以找来看看,我们选刊今年第一期的中篇头条,我在“翠柳街”栏目写了篇评论。
还有我们9期刚选的李敬泽的短篇小说《夜奔》也很值得一读,我们都知道李敬泽的散文是很厉害的,汪洋恣肆,才华横溢。他的那种天马行空的习惯,在这篇小说里依然明显,只不过,你会觉得始终有一种你看不见却又十分强韧的力,总是能把飞出去的思绪给拉回来,而拉回来的时候,必然会弹到你,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就像什么呢,蹦极!小说主要的场景就三个,一个是雨夜,出租车,司机,主人公“他”以及痛哭的女人,这个场景被作者充分地渲染,尤其是女人痛哭的情景,被渲染到了极致;一个是聒噪的令人烦闷的会场,一个是宋塔。这三个场景,前两个是实的,是小说主人公“他”亲历的场景,第三个场景宋塔,被拆了又装,是被人讲述然后被“他”想象的场景,事实上,那代表的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存在,一段坚固的历史。而“他”就在这三个场景之中来回地弹跳,弹来弹去,弹出一个“不可断绝”的大悲。很多人蹦极也会哭,有的人是吓得哭,有的是爽到哭,如果不用这种蹦极体验式的方式来写,他那句“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恐怕很难成立。
因为时间关系,以上提到的作品,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几篇小说我并没有回头重读,都是凭记忆来写的,这当然说明它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毕竟有些已经过去几年了,难免错漏,在这里我先请作者和大家谅解。最后我想说,做选刊编辑,每年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我还有一种感觉,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也应该是有意识地自我锻炼和提升修养的过程。刚才张院长讲到“向外和向上”,我十分认同,这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向外”使我们开阔,“向上”使我们成长,我想,还有另一个维度也很重要,那就是“向内”的探索,“向内”,使我们深刻。甚至,对于写作者而言,“向内”的探索更为重要,因为,我们理解自己越深,理解他人才能越深,理解自己越全面,才能理解更多的人。文学更像是一条通向自我的路,它指向的,应该是写作者内心的理想、独立和自由。我们对自我以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感受是不是真实与深入、认知和观念有没有更新升级、表现的艺术水准达到了什么程度等等,这些因素都决定着我们作品的质量和状态。
最后,祝大家创作丰收,不断进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