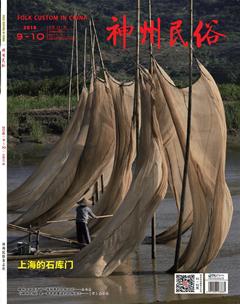岭南“家族——族风”的文化内涵
刘英凤 刘凤梅 林凤海
[摘 要]在岭南,许多世家大族十分重视良好家风、族风的传承,家训、家诫、祖训、族规蔚为大观,广州市花都区塱头村黄姓家族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文章以广州市花都区塱頭村为例(也穿插相类似的例举作扩展),从家族村落、家族精神、家族规范、家族教育四方面就其文化内涵作简要分析。
[关键词] 岭南家族;岭南族风;文化内涵
家族与家庭两者在严格意义上的区分,是较为困难的。因为两者都是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群体,虽说组成两群体的成员数量上不同。不过,如果将两者再作比较性的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它们间的差异性:家族应该是各个家庭组成的族群,而族群一般是经历史发展过程才形成的。
家族的基本面就是它的族群效应——家族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家庭(数目众多家庭的集合),而是这种“量”的“累积”形成了各个家庭都不具有或较弱化的“整体性”:家族可构成自然村落的格局;家族精神有着显赫的宗祠建筑物;家族以较强的社会“规范”约束其属下成员;家族以较公共的教育方式与“社会体制”接轨。总之,家族的“整体性”更突显其“社会性”,它所营造的“风气”已不仅仅属“族风”范畴,简直就成了社会“风气”。
笔者以广州市花都区塱头村为例(也穿插相类似的例举作扩展),从家族村落、家族精神、家族规范、家族教育四方面就其文化内涵作出分析。
一、家族村落
如果说,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最小组织体的话,那么,家族就是以这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最大单位。从形式上看家族村落,它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存在过的先母系氏族后父系氏族社会组织体那样,所区别的是前者是以“一夫一妻”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
家族村落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以一姓为基点,通过历代的不断繁衍而形成同一姓氏的村落。家族村落完全是适应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生存而发展的,它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大体是绕着村落周边的自然供给的条件而展开的。这一社会组织体之所以能继往开来地长期存在,即令发展也是在维系自然村落的整体格局前提下作“量”的扩容,就在于它是完全适应着整个社会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始终维系着“自然经济”的“体统”的。从管理角度看,家族村落的管理是顺从“自然经济”和“血缘关系”的双重制衡,形成了奇特的自然性和宗法性;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它是以传统的风俗、习惯、礼仪、礼节(可统称为“族风”)为基本形式的代代相传而不断延伸。不要小视这些形式,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和传承的“自然基因”,在它那里,隐藏着各式各样的“文化密码”。
塱头村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它于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在此“立村”,当时只有两三间小泥屋。历经600多年的历史发展,现村占地面积为4.8平方公里。村为塱东、塱中和塱西三社,三社分属三个亲兄弟组建。每个社长800米,纵深850米,坐北向南。每社都设有门楼,每条古巷都有木闸,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空间。其中塱东和塱中相连,与塱西由小河涌相隔。村前地坪宽阔,地坪上有了口古井和三口半月形水塘,占地约3.5万平方米。塘基种满荔枝树、龙眼树和榕树,与村头、村尾、村后数棵参天古榕和木棉环抱村子。
塱头村的建筑坐北朝南,布局较规整,材面建筑保存较好,排列整齐,规模宏大。建筑占地6万平方米。现保存完整的明清年代青砖建筑近200座,其中祠堂、书室、书院共有近30座,炮楼、门楼3座,其余为民宅。现存古巷20多条。巷门口石额上阳刻卷名。现民宅大多有人居住,有600多户人家,人口3000余人。村民都姓黄。
现代人将塱头村看作是“古村落”,而且是中国不多的“传统文化古村落”,这说法并不言过其实。因为要考究单姓血缘村落体现的家族传承,该村落给人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烙印和美好回忆。
二、家族精神
家族精神虽说直观于“家训”上,实质体现在家族先辈的“示范效应”上。后辈在默读“家训”的当下,脑海中很自然浮现先辈“如何如何”的鲜活故事。正统的大家族,还要以族谱的方式记传下去。在塱头村中经纬阁门楼,陈列着黄姓族谱和先祖事迹。从中可见,家族不同于家庭的是,形成“示范效应”的先辈一般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前后相继“组群”的。
根据塱头村的黄姓族谱,村民奉北宋末年的黄居正为始祖。黄居正生于北宋末年,娶妻米氏,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他被钦点为武状元,后外任礼部尚书。他为官清廉,秉公办事,后被奸臣陷害,举家迁至南雄珠玑巷避难。此后族人又从南雄珠玑巷迁至广东各地,至第七世祖黄仕明迁至花都此地立村。
据先辈事迹记载,对塱头村组建和发展影响至大的先祖分别是第七世祖黄仕明、十四世祖黄皞和二十二世的黄谷诒。
相传,第七世祖黄仕明选择此地建村还有一段神秘色彩的故事。当时,黄仕明专邀一风水地理师指点,说是塱西头为一块风水宝地。在那南有泽地、北有土岗,“将‘朗加上‘土字为‘塱,去‘溪字留‘头字,居屋建于岗头临水之边,意为‘头啖汤,就叫‘塱头村可也。”黄仕明听信即举家迁到塱头。不久,家族果然人丁兴旺,未出百年,建起宅居十余座,垦田近千亩,开泽地数十亩为鱼塘,修路十多条,塱头村初具规模。
十四世祖黄皞冒死赈灾,木鹅圈地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据传,皇帝曾赐他一只木鹅带回家乡,准他将木鹅放到河中任漂三天,木鹅漂到哪里,两岸边的田地便归他所有。黄皞不忍占百姓太多土地,于是暗遗小孩潜水将木鹅引入以水塘中停下。
故事仍在延续。据传,到了二十二世的黄谷诒,他当时也是清朝花县十大富翁之一。但,他不恃气傲,乐善好施。族谱有载:“道光年间,赤地千里,灾民无数,黄谷诒带头捐出大量金银给朝廷赈灾。”道光皇帝得知后,封他为员外郎,奉直大夫。
塱头村的先祖“组群”形成正气,何愁后辈不去效仿身体力行呢?塱头村先祖“组群”“精神”的象征物是“黄氏祖祠”。该祠初建年代不详,1871年重建。坐北朝南,三间三进。人字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碌灰简瓦,青砖墙,红泥阶砖铺地。据传,该祠是由先人黄宗善(即乐轩公)亲手创建的,曾于清朝同治十年由塱东、塱中、塱西三社共同出资重建。当年,凡是刚成亲的新婚夫妇必先到黄氏祖祠拜祭先人。它成了黄氏后辈举行重大祭祀活动、重大议事之地。
在岭南,“宗祠”作为象征物,用来寄予乡民寻根念亲、崇先敬祖这种永不消散的感情,成了一种很普遍的乡村文化;与岭北乡村相比,无疑它是独有的特色。
在客家族群的居住地,人们就会看到宗族无论大小都会建立起自己本族的祠堂。祠堂放置祖先的牌位,俗称“祖公牌”、“神主牌”,置于祠堂上厅的神案上。一块神主牌代表一位祖先,历史悠久的大宗族祠堂,往往分几层陈列着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神主牌,麻麻密密,蔚为大观。在祠堂里,还盛行在节日(如春节)挂祖宗像的做法,表示对祖先的崇敬和思念。在这期间,人们早晚都要到祠堂祖像前烧香点烛、虔诚供奉。在过去,男婚女嫁时,也要在祠堂或祖厅的祖像前表示虔诚之意。
在潮汕,乡民对宗祠的建设和打理,也象客家族群一样投入十足的热情。就连久居海外的潮人也不示弱,宗亲观念尤其强烈,思乡敬祖之情十分浓厚。清嘉庆年间《澄海县治》就有记载:“望族喜营屋宇,大宗小宗竞建祠堂,争夸壮丽,不惜次费。”现在海外潮人也不减当年,积极参加元宗族或家族的公益活动,修祖坟、建宗祠、修族谱、祭祖宗等等,样样都不缺。“追根溯源,慎终追远”,成了宗祠文化不变的主题。
三、家族规范
家族“规范”与家庭“规矩”相比,有着更强的约束力,因为它面对的是家族名下的众成员,且规范要落到实处,必须一视同仁以示公正。在这方面,家规有时虽严但往往因人而异总让人觉得有欠公正。其实,家族“规范”的公共性还具有家庭“规矩”难以体现的社会性,这社会性集中体现在它往往与现时社会通行的宗法体制和礼仪规范相“接轨”。在这方面,塱头村就有着突出表现。在一般人的观念中,“礼仪”是人与人之间的言谈举止“循礼”的表现。在这里,人们所见所闻:连“建筑”设计也循“礼”,真正“礼”为“宗规”。
走进村中清道光年间建造、二十二世的黄谷诒曾居住的“积墨楼”,他与儿子住在分巷而立的八间大宅中。只要你细察,会发现其中一边是镬耳屋,另一边是普通的人字屋。这区别原来是从前老早已定的“建筑格制”所分明的:有功名的儿子才能住进镬耳屋,经商的则要住在人字屋。而在大宅上的青麻石同样有讲究:每间宅子的青麻石高低不同,寓意长幼有序,父亲居住的青麻石石阶最高,足有2.2米。
在塱头村,对于举行祭祀也十分讲究。黄氏家族人有几大传统祭日,清明节是大祭,重阳节则要祭拜第一世祖黄居正的夫人米氏太婆的衣冠冢,另一个是农历七月廿全村黄族人祭拜立村始祖黄仕明太公墓。黄族人将这天称作“吊鸭节”,因黄仕明太公是养鸭高手。正所谓“爱屋及乌”,连鸭也要吊唁。重阳节,在这里也有故事。每逢重阳节,年过六旬老人都围坐宴席。在宴席中,有一道必不可少的传统佳肴叫“鱼酱”。相传,这鱼酱已有数百年历史。那时的重阳节,村中会给老人分鱼。鱼要切开每人一份,由于斩件有大有小有头有尾,份份难以均匀,于是有人建议干脆将鱼连骨带肉煮成酱,再拌以猪油和黄豆调料,结果味道出人意料的好,也方便老人嚼碎。这一举多得的“鱼酱”,就成了数百年来敬老设宴必不可少的传统佳肴。
看来,始祖来自中原的塱头村后辈人就不一样,他们是深受儒家倡导的道德礼治影响的。在《左传》中说到懂礼重礼的意义,懂礼的会事业兴隆家族昌盛,而失礼,小则办事不利,大则身家性命难保。对这,现代人是难以理解又不好接受的。但那时人则是接受不违的。在塱头村就有个典型例证:在村里立有一座贞节牌坊。牌坊高约3米,花岗石结构,正面门额阳刻有“外平人瑞”,意为“太平盛世人寿极高”,横额上款刻字“乾隆壬子年(1792年)季冬吉日”,下款刻“一百零三岁黄卓篪建坊”,石额顶上还有阴刻“圣旨”,背面阳刻“百岁流芳”。这座牌坊是为塱头村十一世祖(塱头第五代)黄宗善的儿媳崔氏夫人所立。她的丈夫在30岁时染病身亡,当时崔氏夫人才24岁,她活到103岁去世,79年间始终未再嫁。乾隆皇帝下旨立此碑以作纪念。这事,放在当时是可赞的,因为她守“礼”。若摆到现代,很可能为人不解而叹息。
其实,族风已经不只是“族内”成就的某种风气,它时时都与社会相“连通”,其“公共性”则更突显为“社会性”。当一个“族群”、一个“村落”、甚至一个“区域”的“自营风气”再无力量应对“社会风气”时,需要作出改变自己的选择才是明智的。在唐代,在潮汕出现的“韩愈现象”就较为典型。
据记载,韩愈贬潮,在潮为官仅8个月,他即时“重申唐律,奏请赦免天下奴婢”,“兴学昌教,重振州学”,崇尚儒学,提倡举止优雅风气,社会风气真正得到了转变。而韩愈也因此“赢得江山皆姓韩”,“居潮八月却千古名传”的美誉,被潮人尊之为“吾潮吾师”。韩山、韩江、韩山师院、昌黎路、昌黎小学等都有韩愈的身影。潮州还保留着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祠宇,即韩文公祠。潮汕地区的这种“韩愈现象”一来说明韩愈的作为确实能够发挥“名人效应”,二来也说明一个区域的“风气”的“改变”往往迫于比之更优的社会“正气”。当然,这种“改变”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因为“正气”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原来维系的生活习惯、风俗,而是更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四、家族教育
塱头村乡民历来信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统价值观,崇尚“耕读文化”,尊师重教。在村内,令人称奇的是巷巷有书室、处处立学堂。什么“云任公书室、谷诒书室、文湛公书室……”除首尾相连的书室外,还有书院,现全村仍保留着30多座书院、书室。据介绍,以前每一列住宅的房头都会建一间书室。村民有了钱,除了修祠堂,就是盖书院、书屋。这真是塱头村内别有风味的一道风景线——处处见书院,处处闻书声,处处飘书香。
难怪塱头村被称为“科举乡”、“进士村”。据计,源于塱头村历史上共有70人中科举,秀才50人,举人7人,进士13人。在村中,“七子五登科”“公孙八科甲”“父子两乡贤”的故事广为流传。具体说的是黄皞严教七子,其中有五子举人、进士。后来黄皞和第五子黄学准为国为民作了许多好事,得到皇帝赐给“乡贤”之称,因此就有了“公孙八科甲、父子两乡贤”的美誉。[1]
在珠三角,在同姓家族一条自然村落,数百年来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确实罕见。不过,与黄姓家族营造“读书求仕”之“族风”相通,要数客家大族群了。
客家人的祖先,多有官宦、土族家人,偏又居于山区,这就更促使该族群要极力营造“得文化传承、重文化教育、要走出山区”的浓厚持久的“族风”。举凡客家人大都有一族规:凡中了举,便能在自己家族祠堂前竖起一对高高的石笔(又称石楣杆)。时至今天,在客家聚居地仍可以看到那些历经沧桑、蔚为壮观的石笔林。
为了使后代子孙念书有保障,客家宗族长辈都把办私塾当成件大事,规定在祖传地中专拨一笔稻谷支付私塾先生的教书薪金,并把众多祠堂作教学之地,学教之风自然形成。清时,法国神父顿里查斯曾在《客家词典》中也作过描述:“在嘉应州,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市,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數十间小学,学校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也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是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为了教育,为了子孙后代能走出山区出人头地,祠堂也改变了它原先设定的功能。客家人承袭儒家传统,恪守“天、地、君、亲、师”的信条,从未改变过。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广东省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十八巷书声琅琅 六百年耕读传家”,参见广州日报2017年10月31日。
作者简介:刘英凤(1965-),女,教育学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岭南文化、教育心理。现任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主任。
刘凤梅(1977-),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