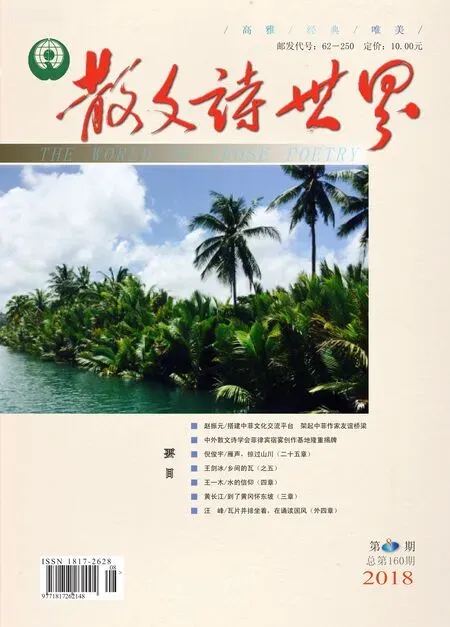以一朵花的名义行走(二章)
贵州威宁县第八中学 王近松
哈喇河的梨花
三月,站在三棵树梁子,除了奔涌的河流和那俯身的石头,还有满山遍野的梨花。
在哈喇河,以一朵花的名义行走,带着梦想,带着亲情、友情、亦或其他感情。
几只蜜蜂在梨花间嗡嗡地闹着,母亲在地里俯身劳作。
梨花像雨,温润梦乡;梨花像雪,洒落在地。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多久没回故乡了。总记得芭蕉叶长在悬崖的红土上,梨花一瓣一瓣,芭蕉丝一层一层,命运的步伐一步一步。
今年哈喇河的梨花似乎比往年更漂亮,就像往事比岁月更深沉。
姑妈拍的梨花图,我写的旅游文字,哈喇河的梨花又一次惊现春天的芳华。
总在梦里,或者背包远行的夜里想起故乡,想起父亲,母亲和梨园。
三岁时,小手握一枝梨花就能安静地坐上几个时辰;五岁时,小手握一枝梨花就说要去海南找个姑娘做媳妇。
人长大了,梨花谢了又开,岁月走了不回。
在哈喇河,壮观的除了顺沟而下的雾,还有一朵朵梨花组成的春景。
故乡的梨花,总和人一样,有诸多的情节!
我以梨花为情,写亲情、友情,亦或爱情;
我以梨花为序,写童年、梦想,亦或远方。
以一朵花的名义行走。带着梨花的凄凄切切,带着家人的期望,还有我深爱的文学,选择行走,一生无悔。
父亲的君子兰
院里种着各式各样的盆景,最具情调的是父亲窗前的君子兰。
父亲在地里奔走了半生,没有文化,没有过高的追求。
他的一生像春天翻拨的黄土,翻来翻去都得接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父亲37岁的时候,我从外面带了一株君子兰送给父亲,弥补了我未曾送过父亲生日礼物的空白,对于父亲来说,填补了他对美的追求的缺口。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空缺要去弥补,就像父亲常说:“没出的玉米窝,总得补上新种。”
院里种着银杏、古柏、桂花,之前父亲总喜欢泡一杯茶,蹲在屋檐下注视着远处的山口,好像在与远方对话,又没有明了的话语,现在,父亲无事就端着茶杯,围着君子兰左看右看。
父亲这一生没有丰功伟绩,也没有什么超人的建树,历史学家也不会把他写进历史。
在我看来,父亲的这一生好比一株君子兰,只能借着外在的环境去展现自我,时光赋予他的往往是我们都不能忘记的。
父亲作为农民,他的一生足以写几部小说,就像每年春耕秋收在地里拉线、挖窝、盖地膜一样,那些恰是一代中国农民对人生价值的自我书写和自我定义,他们的一生像千千万万株君子兰,拥有高洁的品质。
父亲的一生就像那株君子兰,朴实而高贵。
如果回到三年前,我依旧还会再买一株君子兰送给父亲,一直种在父亲的窗前,种在清晨和傍晚。
后来,我喜欢香雪兰,是因为我的初恋把它当作生命之花。这一生我所见过的花不计其数,最爱的还是那株君子兰和初恋的香雪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