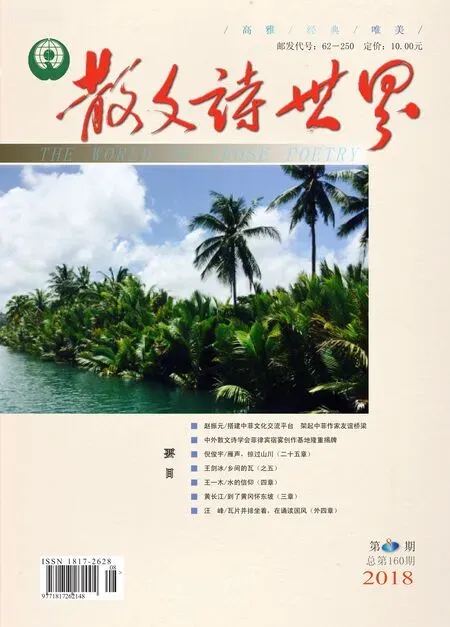心飞翔(四章)
四川 郭 伟
我是谁
或是在人间,或是在天堂,我的思想到处游荡,无所事事,不知所止。
一会儿我是我的堂兄,一会儿我是我的同学。我戴着一顶草帽,中间一圈已经脱线,外圈下垂形成了一个梭形缝隙,有时也可从那里往外看,看天看地,看人事变幻。像镜头取到的景像,总是青山绿水间一段风景。风也从那个豁口吹进来,不时刷新我的视线。我坐在塘边养鱼,投下鱼饲料,看鱼儿轰抢,嘴巴能在水里发出声来。也有几条是红鲤鱼,特别抢眼,特别灵动,我不时摇摇红裙,努力炫耀自己。我爱它们,爱它们自由自在,爱它们没有理想,不必努力奋进。
我的思想一会儿转换为另一个人。我的视线一会儿是从医生的眼眶后看出来的,一会儿是从教师眼眶后看出来的,一会儿是从护林员眼眶后看出来的,一会儿又是从农民眼眶后看出来的。这个幻象,是从过去搞尸体解剖时,产生的一个幻觉。这个灵感虽奇妙,又令人心生恐惧,生怕别人偷窥了内心的秘密。一会儿我是将军,一会儿我又是一个学者。我戴着墨镜,装得很酷,总是与人有距离。或者直接说是高高在上,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有时又很不自信,没有知心朋友,没有人理解我所做的一切,也没法理解我做的一切。
我把《人民日报》中最漂亮的书法作品,沿着外框剪下来,工工整整贴在记事本上,装订成册。文化的千年万载传承,不辩是颜体柳体佑军体,还是张癫的飘逸灵动,或是魏碑的苍劲古拙。每个汉字都是有灵魂的,本是一幅幅画构成。今天,我们通过这些文字才得以与古人的灵魂沟通,而有些新字又是古人生产生活水平提高后,随之推进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成果。造字绝不是一地一人,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仓颉造字的神话,纪念着一个造字较多,统一规范的集大成者。
我们的民族反复不断做着剪辑、重组工作——文字如甲骨,文字已石化。但是,还是那些字,从宗教走来,不断创新着思想、科技和文化。
坐在清冷的书堆旁,想着为国家民族,想着大道理,做着大事情,却被周围的人嗤之以鼻,没有关注、友善的目光。大家都坐在小餐馆里,喝着空山的小作酒,加上少许冰糖、橘皮,装在壶里加热以驱寒,同时也蒸发掉少许乙醇,又甜又醇又可口。不久,还是酩酊大醉了。回程的路上,吐得满车窗。我的双眼站在窗外,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或者一层薄得透明的纱窗——目光可进,气味可出,伸手却不可及。我面色苍白,阳气尽脱,眯眼不睁,心慌乱跳。
那种放纵,那种无拘无束,是人生甘居南山豆荚丛下、塘边柳树旁,无限量、无拘束享受着各种菜花朴实的香,也是青蔬初长的菜香。
我是上世纪来过世间的人。知道生命充满竞争,死可以复生,但自己必须牢记生的密码。死在一个谁都可以进去的地方,谁都可以干预自己复生。那里如果是一个大厅,一间办公室,各自把密码藏在哪里呢?其他人如果知道你的密码,则可能在不经意间丢弃、毁坏,也有人抱着多给自己保留一些空间和时间的目的。
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那个秘密被揉成一个小纸团,夹在一根金丝楠木的桠豁里。
灵魂来到大厅,我从一二三开始重新学习,并开始搜寻记忆密码,回顾上世,安排今生。
心飞翔
突然,我有了想入世的想法。纵身一跃,从窗口投下,我便失去了重量,似一叶飘飞,又似双手为橹,可以在空中划动而改变方向。但实际上没有改变,一切都不能改变。没有自主,没有方向,自由飘游。似乎日月向头顶方向慢慢移动,星辰向头顶方向慢慢移动。
我肢舒展,我心清静,思想静止,任其自然。
心里有一个想法,不是结局如何,而是何时终止。应该没有可怕的结果,也应该没有可喜的结果。万物移动得那么缓慢,需要时间才能度过空间。
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我,要两天才能落地。地是什么?可以承载我么?可以阻止我下落么?会不会硬着陆?一切都不知道。任其摆布,随其自然。
两天是个什么概念?是季节,还是逗号?还是一把剪刀,咔嚓一声就能把一切过去剪断——包括记忆?
我想过改变一下姿势,但无能为力,或者有些微变化,周围还是一片星云。在十分浩瀚的宙宇中,那不算速度,更不算距离。
天地之距有多远,两天——答非所问。耳边没有呼呼风声,没有极光,没有彩霞。
何时落地呢?如何落地呢?
火 浴
父亲引我到过一个深山民族中,听说叫火族。那里没有男人,女人们都身材窈窕,面相姣好,身着蓝底白花长衫,纤肢曼舞。见客来到,她们手把手围成一圈,突然如柴禾丛立,外覆茅草,点火即着,她们仍然面带微笑,端庄大方,态度从容。首先着火的是衣裙,火星在茅草间乱窜,淡烟四起。她们或静立不动,或轻幅跳舞——没有疼痛,没有恐惧。
我十分惊愕。以手撩开一片茅草,拉出一个女孩。她非常淡定,见我左眼有泪痕,轻轻帮我擦拭。
身边只留下这个姑娘。
回头一看,一片灰烬。其他姑娘呢?火化消失了?乘遁地法走了?变戏法幻形了?
这就是凤凰涅槃?
沙滩情
梦不告诉我,何时落地,更不告诉我,怎么落地。
沙滩柔软得似少女的胸脯,任由人们嬉戏玩耍。男女、孩子的差距在这里变得最小,因为人们这时包藏得最少,而暴露最大化,生动的造型,白净的皮肤,尽展造物的审美观。无拘无束,自由奔放。任沙滩轻轻地把我们托起,任水浪为我们轻轻地按摩。似温柔的一个个抚摸,一个个深情的亲吻,直达深埋沙中的躯体之上。
如果没有法规的约束,情感不知向何方延伸,是不是能穿越坚固的地球,穿越寒暑的四季,穿越无端的人心。
海水河水能融为一体,有没有电流相通?沙滩为何能堆在一起,有没有磁石相连?它们又怎能容忍礁石矗立其间,怎能容忍乔木、荆棘生长其间?虎鲸的雄性体味与海风的咸碱味,岩花的香味与人体的汗香,甚至企鹅海豹海狗鹰隼花雕腌骚味,融为一体,难以分离。
地可兼载,气可兼纳,水可兼溶,而心不可兼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