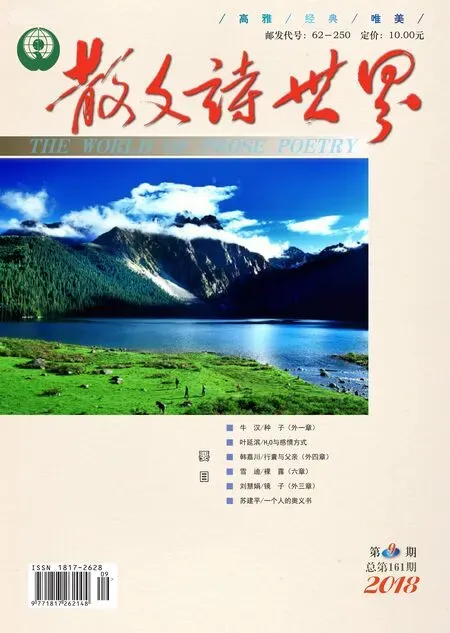那些欣悦在眉山的虔敬(四章)
重庆 郑 立
静读三苏祠
静读三苏祠,读一口时间的酒窖。
碑廊,一坛千年的陈酿。云屿楼,一楼交杯换盏的坦然。
半潭秋水,一撑船坞,一眼苏宅的古井,也是杯中之物啊!
与酒关联的传奇,已经绵软。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命运的酒杯,苦涩与甘柔,淬火在骨血。
来凤轩、启贤堂、式苏轩、景苏楼……支取了我一千年的俸禄,缭绕在酒香。
取出三分水、二分竹、一分醉,我牵出了一匹时光的老马。
洞彻的烛火,汪洋恣肆,不仅是词赋。
炫然的亮泽,明白畅达,不仅是文章。
细密在百坡亭的针脚,淡而不遇的踪迹,静读眠在宋朝的酒曲。
蓄秀在披风榭的曲水,酽而不洇的墨影,静读走在眉山的虔敬。
一轻再轻,让我内心的宁静渐渐化开,不惊扰坐在石台上的那一个神思披拂的人。
一声鸟鸣,东坡盘陀陷入时光的清寂。一粒荷叶上的露珠已把我擎举,我试着与眉山对饮。
万念归乡,热泪盈眶。在三苏祠,我静读窖藏的灵魂。
一祠时间的嫩叶起于我的微醺,一祠千年的瞻望止于我的沉醉。
流放,僻远,蛮荒。沉沙淘金的屐痕,心气如虹。
新遇,超然,流芳。蒸骨煮髓的坦荡,心韵如钟。
彭祖山随想
抵达一棵乌桕树,一棵香樟树。
在养生殿前,“道道非常道,生生即永生”,我找到了血缘之亲。
那是人间九道修竹滴翠的坡拐之灵。
那是人生九十九个仰天虔敬的石台之魂。
那是人心九百九十九步自然弹拨的石阶之韵。
哦,长寿的风影。彭祖山,以610米海拔,以158米垂直高差,与我一一相逢。
三千年,如此恍惚。跃出一尾大阳鱼,潜入一尾大阴鱼,勾勒一幅立体天然的太极图。
彭祖祠、彭祖墓、仙女平台、九天揽胜……一山负阴抱阳的超然。在一片初生的茶叶上,粒粒微尘,悄然落定。
藏寿于心,长寿于行。
时间或早或迟,会悄悄地把我抹去,不留一丁点儿的痕迹。
有了佛光普照,一个人便有了祈望的高度。
最真的善念,在齐天双佛的神往,在慧光寺的瞻望。
有了道法自然,一座山便有了翠绿的维度。
我最深的怀想,根在一尊木鱼石,身在一棵木鱼石上的黄梁树。
在柳江古镇听雨
站在柳江古镇的意外。
喊一杯茶,在临河的窗边坐下。
一百零八棵古树,一袭古今的屏风。
八百年的水墨烟雨,在我凝眸的一瞬。
被古意唤醒的形式,都是未曾过度开发的水墨。
被现代吵醒的内容,从淅淅沥沥里回归了古雅。
听风观雨。曾经的明月镇,醉在一杯“老子不醉”的酒里,屡废屡兴。
听雨望江。耳目苍然的水码头,敞在我时起时伏的遇见里,患得患失。
我听忽暗忽明的古栈道,一朵历史的落花,在风口上归隐。
我听或隐或显的吊脚楼,一裾时光的灯影,在水色上恍惚。
还听见石板长街的柳姜场,以八百年的和悦宽容了我的肆意妄为,包容了我的万念俱灰。
雨与古镇,两情依依。雨与水,浑然天成。
著了雨色的闲慢,忘在时间的节奏。楼头的风铃捂住岁月的耳朵,走出了古今。
我听清一尾小鱼误入烟雨柳江的感慨——
醉生。在足浴鱼缸,变幻莫测的是惊艳。
梦死。在柳江河水,原汁原味的是嘘唏。
走完了曾家大院繁体的“寿”字,我到了湿漉漉的南宋。
被瓦屋山擦亮
纵目御风,擦亮蚕丛氏最后的归处。
人间天台,擦亮太上老君神话的去处。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嵋翠扫雨余天”,擦亮苏东坡的诗境。
八十灵泉,仰天伏地的承诺。七十二飞瀑,飞流三千尺的飘逸。六十万亩杜鹃,爱情如歌的箴言。三十万亩珙桐,生命若锦缎的奇幻。
被瓦屋山擦亮的内心,坦然在奔荡的纯净。
雾凇、雪凇,透灵濯魂的虔敬。冰挂、雪挂,飞针走线的欣悦。冰柱、冰瀑,冰心雪骨的澄澈。
被瓦屋山擦亮的眼神,深邃在时光的繁枝。
兰溪、鸯溪、鸳鸯溪,淘洗心音。佛光、圣灯、三日争辉,炫颤灵魂。野牛街、燕子洞、迷魂凼,尘封密码。
被瓦屋山擦亮的智慧,谦卑在历史的光影。
一张中国最高最大的“方桌”。
一部大自然的天书,一声源于我内心的惊喜。
瓦屋山,任白昼的韵律和黑夜的脉搏无言地抒写,任浩瀚的星辰和人间的烟云无声地擦拭。
沉寂得太久了,贡嘎山被擦成了天边的一朵云。
宁静得太久了,峨眉山被擦成了心头的一缕风。
那些欣悦的虔敬擦亮了眉山,任阳光喷薄,任月色穿越,任指向至善的手印抵达了救赎的福音。
那些大美的漩涡擦亮了眉山,华西雨屏、西南花苑、南情北景……尘世间走散的脚印,在落日里入梦,从日出里醒来。
我来不及擦拭自己。瓦屋山已擦亮了我的虔敬。
一方雅女湖的蓝手帕,在我翘望的眼前,暗香扑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