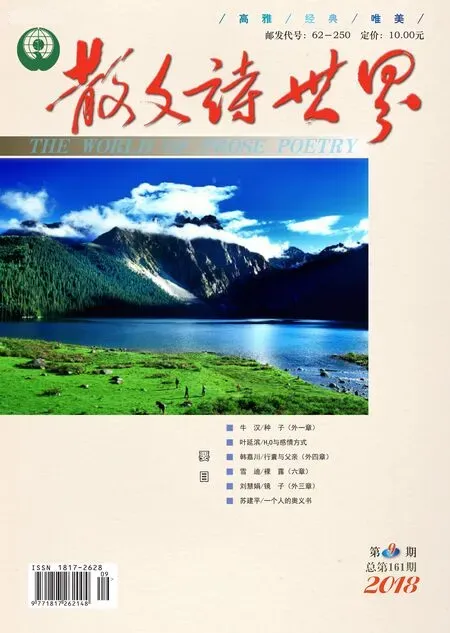农具咏叹调(八章)
甘肃 刘彦林
连 枷
拍打菜籽,拍打麦子,也拍打黄豆,更拍打高粱——拍打是它一生的宿命。
甩动连枷的那双手,握紧连枷把卖力地拍打,是想让它的手掌下跳出最饱满的籽粒。
所期待的惊喜,连同汗珠跌落时溅起的回声,让丰盈的村庄把灿灿的笑雕刻在幸福的脸庞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拍打中,连枷的容颜涂抹上了时光的色泽,更在拍打中把身子骨拍出嶙峋和斑驳的烙痕。
转动横轴,磨损了曾经的坚硬;摔动的连叶的有力手掌,如今也瘦削疲惫不堪。
那牵系木棍的枸皮,断了再接,接了又断,但仍然执着地谋划着:明年,后年,还能继续拍打……
挥动连枷的手臂,已擎不起一家人的希冀。
而家庭的接班人,已把它闲置在老屋的阴暗处。
土地出租后,场院上再也见不到菜籽、麦子、黄豆和高粱的身影。
连枷真老了,腰身佝偻,走路颤巍……
所有的美好,只能在梦里一遍遍地温习——夕晖般的余年,只能靠回忆韶华来延续!
碌 碡
从山岩上凿下来的那一刻,石头的命运被改写。
石匠挥动铁锤,铁锤助推凿子,凿子雕刻石头,脱胎换骨成为崭新的碌碡。
碌碡的生命,从此丰富而多彩。
把坑洼的地块碾平,把虚浮的土压瓷实,宽阔而平整的土场,用来安置从田地里运回的庄稼。
成熟的小麦,透着成熟的清香,透着泥土的馥郁,透着阳光的亮色——这成众的孕妇,饱满的穗头里储存的粒粒金黄,才是父亲眼中足量的黄金白银。
让她们顺利生产,是碌碡义不容辞而又神圣不可亵渎的责任。
被牛鞭催促着,碌碡神圣地行进,有山歌的伴奏,有木制拨架的咿呀声,有麦子弹跳而出的沙沙碎响。
被阳光朗照着,碌碡庄严的使命就是让麦粒诞生,让麦粒脱离胎衣的包裹,让更多的惊喜擦亮那张晒黑的脸膛。
吱吱呀呀,堆积的农事,一点点沧桑了曾经的容颜。岁月的风刀,一次次在坚硬的肌体上刻下苍老和皱纹。
当碾麦场被弃之不用,只有选择退让到杂草丛中,靠回忆温暖日渐苍凉的心事。
一首古老的歌谣,突然就戛然而止……
石 磨
不是水流推动木轮带动的那合石磨,也不是被蒙着眼睛的毛驴拉动的那个石磨,而是脸盆口般大小的两扇手推石磨。
小巧,轻便;灰色,坚硬;冷漠,隐忍……
它石质较细,铁錾凿出的纹理,像荡漾开来的道道水波,也像葵花盘上走向规整的图案,更像岁月的手掌拓印下的指痕。
它胸膛上的花纹,和另一扇石磨肚腹上的花纹,一经面对面地接触,就成了一对生死相依的锋利的牙齿。
咬碎玉米、黄豆、小豆,让它们在磕磕绊绊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粉碎那些饱满的颗粒,把一堆堆粗砺的心事研成粉末,把生活的疙疙瘩瘩一口口咬碎,从小孔流淌出的日子流淌着醉人的醇香。
奶奶青筋暴突的手推过,母亲布满老茧的手推过,我和姐姐稚嫩的小手也推过,把单调的日子推出欢声笑语,把恬静的乡村生活调配出丰沛的诗情画意。
在粉碎时光的年轮上,石磨的牙齿越来越钝,再也无法让坚硬的谷粒俯首称臣,更无法把心中的块垒磨成粉尘。
让它一再品尝过苦荞滋味的奶奶,已不见当年硬朗的身影。老态龙钟的磨盘,只有选择淡出村庄的视野,隐身屋后那堆茂盛的荒草,如今更像春光特制的一处坟冢。那里掩藏的,可否是它最美好的记忆?
木 叉
即使弯曲成一件农具,仍然保持着树木生长的姿态。
一把可握住的主干,像一个站立而生的人;两边的细枝伸向前方,像一个人舒展的臂膀。
挑着成熟的庄稼,像拥抱着一生的幸福。
碾麦场上,怎能缺少它瘦削和忙碌的身影呢?
摊开麦子,可以挑动沉甸甸的麦捆;翻动麦子时,可以把那些金黄的心事翻晒;在摞草垛时,可以把秸秆高举到想达到的位置——用麦草搭建一座房子,安放童年最钟情的游戏,多么浪漫而有趣啊!
就在挑、翻和甩的劳作中,把自己劳累得越来越沧桑,越来越失去曾经的骨气。
当联合收割机替代了挥汗如雨的收割和碾麦场上的繁琐劳作,曾经翻晒出那么多惊喜的木叉,也被搁置在老屋的墙角,蒙上了岁月的尘埃。
也有些木叉,从那一刻起被人力强行折断,塞进了火焰熊熊的灶膛,把光辉的韶华付之一炬。
当再也很难见到木叉时,我的怀念如冲上天空的炊烟,把我期待的眼瞳呛出了朵朵滚烫的泪花。
镰 刀
把自己弯成一种姿势,是为了保持更锐利的刃口——这世界上最有锋芒的牙齿。
啃咬是一种伤害,却是一生躲避不开的命——让被命运之神划归刀下的生命,都要经过那个动词从肌体上划过,然后走向境遇的下一个生命的岔口——也许就是这样的宿命。
从一块生铁,到经过铁匠的锻打和淬火,再到一把锋芒毕露的镰刀,生命的意义便有了更丰富的蕴涵。
砍,是离它心灵最近的词汇;痛,是它聆听最多的呼喊——让对方温柔地受伤,这种爱的方式是多么悲壮,又多么的刻骨铭心啊!
一经出手,便再无退路,只能让痛的长度减到最短。
那就在粗砺的石头上多磨砺自己吧。让发丝和棉花,也感受到自己迅捷而过的洒脱。
不停地让对方受伤——麦秸、玉米、豆干、高粱,它们积攒的疼痛越多,锅碗瓢盆的协奏曲里,就会甩出几句酸而有味的山歌;茅草、艾蒿、柴火、刺藤,堆垒的垛子越高,冬天的土炕上升腾的温暖就更持久……直到把身板消磨成一弯可供怀念的月牙。
多年后,独自回到墙旮旯,想起让众多植物对自己俯首称臣的景象——自豪,宛如一颗经久耐用的酸梨果……
皮 鞭
皮鞭可以甩出一声脆响,也可以抽打出一生之痛。
牛皮细如麻绳的一绺边角料,细到毫无用处;拴在木棍的一端,用来驱赶拉车或犁地的耕牛——用自己的皮抽打自己的肌体,不知牛在心里作何感想。
只有童年的牛,才不被皮鞭垂怜。一旦到了拉犁的年龄,它的肩头就多了牛的使命——把每块田地耕耘到软滑,让饱满的种子安心地在泥土的子宫,受孕、孕育、萌芽,诞生出一株株养活人的新生命。即使累得浑身发软,步履也不能慢下来,因为有一根皮鞭,就挥动在自己的身后。
皮鞭是驱赶,也是激励;是催促,也是吓唬;是愤怒,也是疼爱……
那个轧制皮鞭的人,本意并不是为了抽打;那个挥着皮鞭的人,比任何人都疼惜牛,理解牛,宽容牛。只不过,生活的重压,肩头的重担,日子的盼头,全都压在他瘦削的肩膀。他只有让皮鞭一次次对牛发号施令;他只有让皮鞭一次次地抽打牛,却把自己的善良抽得鲜血淋漓。
拿着皮鞭的那只手,也感到了追悔不已,尤其是当一头壮年的牛,被他一次次抽打到瘦骨嶙峋的垂暮,最后还打进了一头牛生命的黄昏,他都有剁掉自己那只右手的冲动。他的一生在鞭打快牛,他怎能不被深深的忏悔淋湿,被太多的无奈掩埋呢?
背 篓
一把锋利的镰刀,能让竹子瞬时分解成细长的篾条,柔软到无骨,乖巧到逆来顺受。
两只粗糙的大手,让一根根篾条在手上翻飞,听话地缠绕成精巧的器皿,承载可以背负而走的东西。
背篓的一生,就是把一个地方的沉重,执着地挪移到另一处,并稳妥地安放。
要装载的东西太多,有麦粒、土豆和玉米棒子,也有高粱沉甸甸的穗头,更有用来肥沃田地的粪土。可以背运的有供猪仔、耕牛肥壮的野草,也有盖房子需要的石头和泥土,更有把贫穷的家从故乡背运到陌生地的坚韧和聪慧。
它承载过几代人的童年,也承载背井离乡后的思念,更承载过父母对生活在小城里的儿子一辈子也丢不开的挂牵和惦念。
终身都在依靠脊背的背篓,如今被迫隐身于岁月的皱褶。
当沧桑一次次掠走了一个人的青春韶华,我只能一遍遍地念叨背篓土气的名字,并用拙劣的文字把它的模样细致地描摹在心灵的壁板上。
像一盏永恒的油灯,驱赶走心头葱茏而丰茂的灰暗与烦忧。
榔 头
截取半尺来长的一节木头,楔入一根细长的木把,就是一个田间劳作的好帮手。
模样简单,相貌丑陋,一脸土气,仿似其貌不扬的庄稼汉。
对于麦地里众多的玉米茬子,却是爱憎分明;对于密集的土坷垃,更是虎视眈眈。
恩爱麦田,是一生执着如一的选择;呵护麦田,是年复一年永恒的坚守。
不怕雨淋,也不怕暴晒,更不怕风霜雨雪肆无忌惮。
把压在麦子头顶的泥土,挥动拳头捶打得服服贴贴,砸得粉身碎骨,心里才会升腾起无尽的自豪。
风里来,雨里去,年年岁岁,信念不曾改变分毫。
艳阳天,冰雪天,风风火火,每一次都不惜气力。
只要庄稼们需要,就会忙碌在田地里。直到颗粒归藏、粮仓饱满,才获取到幸福的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