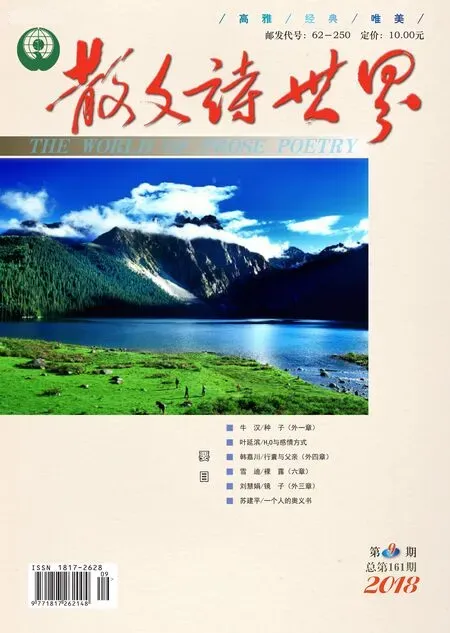八月旅迹(九章)
成都外国语学校 胡华强
威信:走进红色的高原
从川南切入那条红色路径。威信,在群山的怀抱里静候有缘的过客。
街市喧嚣,刺目的阳光下流淌着高原的凉爽。在网络里穿梭的红男绿女,乡音并不拒绝远人。高原只是个地理概念,挡不住一切遥望的视线。
路灯是红色的旗。路口有红色的标语。广场上,巨大的红灯笼是悬在小城头顶的太阳。
这里,红色是飘动的云,是流淌的河,是耸立的山。
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在群山高处俯瞰众生。
电话机。文件袋。蓑衣斗笠和草鞋。静默在游人的敬意里,无需唠叨那段远去的时光。
密集的枪声早已息了。飞溅的鲜血早已凝了。无数远道而来的脚印在时光的风雨中早已湮灭。凝固的红色毕竟是红色。谁改变了谁,谁拯救了谁?这些命题可以无解。火把只是过路的火把。滴落的火星埋入高原的泥土,在合适的温度和水分中醒来,重新燃烧成口号、拳头和热血。
在高原苍茫的峡谷里,红色渲染了灵魂,并蔓延成一片红土地。
鸡鸣三省:我们的家园
站在这个点上,所有的前方都是故乡也都是他乡。是归来也是远行,是回首也是遥望。
鸡鸣诗意在世俗里,在故乡的庭院呼唤远行的脚步,向流浪的风传递平安。炊烟,一边安慰归来的青山一边送别远去的绿水。
母亲伫立的身影,把三省都变成家园。
风分不清方向。云分不清方向。路分不清方向。飞鸟分不清方向。乡音分不清方向。血脉分不清方向。
所有的传说都在这条峡谷里回荡。那面晃动着白光的绝壁,阻挡离别也接纳忧伤,把一声呼唤反复折叠,变成一声鸡鸣,唤醒高原的太阳。
无论涉水的路径还是跋山的纵横,高原就是高原。云贵川是别人的称呼,高原就是我们的家园。
远来的脚步,从高原的黑夜疾行而过。火把穿不透厚重的夜色,呐喊逼不退尾随的足音。血在黑里不能显示血色,梦在黑里不能辨识方向。
只盼高原的西风扰乱旌旗。只盼一声鸡鸣唤醒大西南的黎明,照亮迷失的途程。
鸡鸣三省。红日照亮我的家园。
威宁:在草海触摸一片蔚蓝
在红土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穿越,突然跌进了一片纯净的蔚蓝。
凉风过滤阳光,过滤远远近近的喧嚣,将无边的透明弥漫在四围起伏的地平线上。威宁草海,静静镶嵌在高原的褶皱里。
你用二十万年的寂寞等待我的找寻。在两千多米的海拔高度,在一片透明里被一声鸟鸣填满时空。
一片轻盈的羽毛驾着凉风泊于涟漪之上。轻微的颤动,如脉脉的眼风,洞穿和扩散。
这蔚蓝如此纯净——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视线在时空里任意切割,蔚蓝还是蔚蓝。混沌的谜一样的蔚蓝,在威宁被一片水草托起。
谁分得清那鸟是浮在水里还是飞在天上?谁分得清那树是站在泽中还是立在岸上?
那支竹篙,谁分得清是在架在蓝天划动水面的涟漪还是撑在水底点破蓝天的静默?
被鼓动的船歌朴素羞涩,如岸上村落的炊烟,在水与草纵横的迷阵里自甘沉溺,响穷草海之滨。
远方有楼群窥视的身影,鬼祟而贪婪。在蔚蓝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可以隐形逼近。
鸟的翅膀可以阻挡。鱼的游鳍可以阻挡。渔歌可以阻挡。竹篙可以阻挡。只有欲望可以出卖这二十万年的蔚蓝。
草归草,海归海。当炊烟匍匐于粼波之上,海水浑浊时,招引的岂止迫不及待的跫音!
花溪:我在公园里晕头转向
不知道有几个入口。不知道那些入口朝向何方。一个外来人从烈日下遁入一派阴凉,晕头转向。
四面都是水。有的河流像湖,有的湖泊像河。水在卡斯特里疯狂,又在荷塘里静默。野草与鲜花纠缠,一会儿在水里,一会儿在岸上,共同繁荣着这个夏季最后的热烈。
英雄的墓地是隐蔽的景点,像远去的黯淡时光。名人的典故被镌刻在镜头前,在远景里幻为虚像。时光在夏日的蝉鸣鸟声中慵懒,甚至有些自甘堕落。喧嚣踏碎太阳的阴影,驱不散又聚不拢。
在贵阳之南,花溪河畔,卡斯特藏着秘密。
有谁能知道地下有多少条暗河?有谁能确定眼前流水的方向?有谁能明白满园文字里说的是谁的心事?有谁在乎静水深流中也有凝重的目光?
在公园里迷失方向,需要借助GPS导航。循着一个名字而来,却不知道要带着什么而去。一段半老不老的时光,在八月初的一个下午,睡意朦胧!
荔波:小七孔的传说竟没有夹带爱情
先是逆流而上,接着又顺流而下。溯游从之还是溯流从之,都不见伊人。
从《诗经》的十五国风里悻悻而出。树是山的陪衬,山是水的陪衬,水是绿的陪衬。
一沟翡翠在林壑间游荡,在乱石间逡巡,在六十八级台阶上跌宕白玉的幻影,然后又复归为绿。那一沟绿啊,被小七孔温柔地拥抱,在黔桂结合的僻隅,静若处子。
七个少女,与一个叫做阿吉的瑶家少年,竟然没有发生爱情的传说。只为了堆砌一座桥,这在天下所有需要门票才能欣赏的风景里,都很不正常。
小七孔石桥,连通了西南与华南的脚步,连通了云贵与两广的脚步,连通了大山与大海的脚步。求生的脚步,求利的脚步,求爱的脚步。这些世俗的脚步,被七孔石桥举起,被七孔石桥目送到远方。
小七孔石桥,是为这一潭翡翠而存在。它既是为了连通,也是为了拒斥;它既是为了迎接,也是为了远送;它既是为了热闹,也是为了宁静。
而阿吉仍然没有在传说里酿出爱情的情节。那一潭翡翠,已绿成永恒的沉默。
蚂蚁般的游人,涌来涌去。在这条沟里,他们其实什么也没看见。
镇远:一只清代的邮筒在守望时光
一个圆柱体静静地站在街边,身旁是熙熙攘攘的人流。绿色隐约,那来自西方充满洋味的符号也早已古典成了时光的记忆。筒身上盘龙环绕,拱卫着“大清邮政”的威严。
门楣上的匾额,“镇远邮驿”四个隶体大字像一位长衫马褂披辫子的老者,怪异地打量着门市里晃动着的各型手机。
镇远不远。这一片山水就在你的怀抱之中。
山水之远近,在于人心。心远了,再多的驿站都是战场,再多是信息都是箭镞,再多的信使都无法安抚远去的山水。
一只邮筒,被命运遗忘,却担负起守望时光的使命,见证三百年风雨的晦明。
黔西南的岁月终于宁静。舞阳河的水在无声流淌。除了廊桥风雨带着些许异乡情调,所有的脚步都如行走在故乡。那些倚门回首的青春面庞,以及凭窗而望的慈祥耄耋,都是我血脉相连的亲人。
心有祥和,虽远何镇?血脉相连,何以镇远?邮路穿越千山万水,不如穿越人心。
——那只沉默的邮筒,似乎在这样对我述说!
雷山:在千户苗寨,我只能望见一片瓦屋顶
翻山越岭,风雨无阻。站在那个山坳上,我望见了一片黑压压的瓦屋顶。
对面向阳的斜坡上,一面巨幅的黑色绸缎展开。用黑色瓦片织就苗乡风景,用隐约沉沉的铜鼓叙说历史,而铜鼓声我读不懂。鼓声中的情绪在空旷的峡谷中,化为一群飞鸟,在热风中划出弧线。它们飞翔的意义谁能解读?
芦笙。铜鼓。风雨桥。银饰。歌舞。牯藏节。真与假的传说。荤与素的习俗。
站在一条长路的岔口打望。谁能看得清苗家的炊烟是如何在山风中袅袅升起?谁能听得懂苗家歌声是如何演绎苗岭的时光?谁能辨得出糯米酒里的香甜由几分汗水和几分欢笑酿成?
我们排长长的队。我们在沿街的食物和小商品中择路穿行。我们的眼睛在一群银饰晃动的欢舞者之中就已迷失方向。我们像一阵盲目的山风湮灭在那一片黑压压的瓦屋顶的海洋里。
然后,我们消失于苗岭的苍莽,就像我们从来没有来过。
秀山:有虎耳草的地方才是边城
有个地方叫做边城,人们蜂拥而至。有一条河,有一个渡口。有隐隐的远山和一座白塔。因为那里传说着翠翠的爱情故事。
拿着门票,在摩肩接踵的喧嚣中,没有听到一声竹雀的鸣叫,没有听到一句呼渡的应答,更没有听到半夜里隐隐飘来的歌声。
而且,那里并不生长虎耳草!
在洪安,烟雨蒙蒙的洪安。远山隐隐,雀鸣声声。有一条从经典里淌出来的河,叫做酉水。有一个无名的渡口,只有待渡的木舟。这里没有白塔。白塔不是在那个雷声轰轰之夜倒塌了吗?
端午节的热闹暂时沉寂。翠翠的故事散落民间。
河岸边到处是茂盛翠绿的虎耳草!
风雨桥上仍有羞涩回首的眼神。而茶峒沉静在烟波的彼岸。
边城不是遥远,而是自持。边城不是迎迓,而是远送。边城是一段民间的故事,聆听不需要门票。
不管那出走的少年何时回来,他仍是少年。尽管等待的翠翠已过百年,她永远是书中爱做梦的村姑。
这个涨水的季节,会让人想起木排,想起险滩,想起离别,也想起思念,想起虎耳草!
一条龙舟挟着鼓声穿过烟雨,正赶往下一个端午节!
酉阳:谁在龚滩等谁?
那句广告语刻在石头上——我在龚滩等你!
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我更知道“我”为什么要等“你”。
下午的烈日从对面的山脊射下来,酒旗在热风中飘飞。悬崖上的龚滩在孤独地燃烧,与谷底绿得深不可测的乌江,相看两不厌。
乌江从未等过龚滩。龚滩等到的乌江转瞬还是那条乌江吗?
一千七百年的历史随时间逃亡。一千七百年的悲欢跟文字私奔。在这亘古的时空里,谁也没有等过谁。
客栈的木窗没有等过江面飘过的帆影。街上的石板没有等过匆匆而过的脚步。曾经的繁华没有等过喧嚣之后的寂寞。甚至,眼前的龚滩,也没有等一公里之外的龚滩。
一个文绉绉的江湖的码头。“我”在等“你”!——“我”在等盲目的脚步带来的金钱,等“你”怀揣艳遇的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