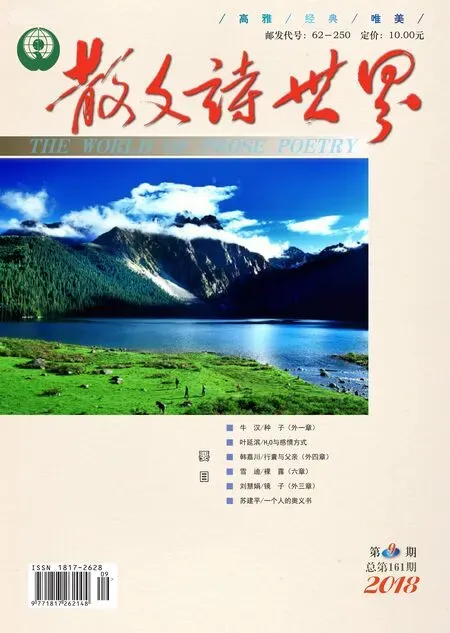物都路感想(外三章)
山东临沂大学 鲍伟亮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物都路车流不息,透过不断被尘土敲打的分割线,我看到——苍茫人世。
以斑斓形容出的色彩,绝对是有迷惑性的。物都路斑斓的车流下,每一寸的筋肉都得到精准操控,方向盘上潜藏着蛇的勇猛与狡诈。
经济的心脏复苏,齿轮般咬合的运输链鞭笞着安逸,飞奔有了更大动力。四面八方,剑气如虹,货车纵横出光速,三轮车傲视轿车,离心运动的货物足以获得五百米的加速度,而原形毕露。
物都路上,尘土是燃起的狼烟。以生存命名生活,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亡命徒。如果一条狗蹿向马路对面,不需要质疑是否疯了,毕竟,它已经箭一般地射向了死亡。
灯火万家,车终将平复沙尘,以绝对静止的状态溶于灯火,如同咖啡滴向牛奶。人间世,每一份疯狂的背后,都有着一杯牛奶咖啡的温暖置于心间。
长路,便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世。
五月的种子应在三月播撒
光的背后潜藏着等质的黑。落入黑夜的太阳,终将在土壤中重新成长,完成黑白的交接。如果,心扎根黑的土壤,眼睛是催化剂,是否会长出一轮太阳,聆听暖风的讯息?
拾级而上。成长,背负以盛大与复杂。心,离去得从容,却期待着故地的呼唤。长大来得猝不及防,不及表达的友好淹没在时光的洪流,走了,远了。除非没有熟悉过,由熟悉到陌生的路上注定要承受更多荆棘的问责。
风云涌动,气流如同绳索的漩涡。过了便是过了,五月的种子不适合五月播撒,如果雨水不至,窒息在泥土的黑中,归于黑。将播撒提至三月,给种子以春雷、春雨、春阳,化去秋后的冰、刺骨的冷引发的宏大意象。暖色,更适合随着记忆入画。
五月的种子应该在三月播撒,五月的叶子应该在三月成长,以苍木的世界,去容纳,树苗的阳光。秋水等待微风,风终将赶到,而等待与等待碰撞,等到的终是空白。
契约,关于离别
生活不堪重负,突然,如少时,有人摸了你一下头。
——题记
生活,是一座山,一条河,还是一声呐喊,或者是一阵寒风呼啸?
时光,任蛛网挂满窗台,年轮锈迹斑斑,铭刻着村口老槐树的兴衰。
天空与雄鹰碰撞,钢铁遇见了烈焰。缘分,便是重压下的一口气,譬如肩膀破碎的前一秒、溺水者最后的呻吟、呛着北风最后的一眼,想起了屋檐下的双燕、蛛网黏过蚊虫、老槐树最喜欢炊烟袅袅。
一只手掌,茧子肥硕,命运的螺纹缱绻苟且。撼动日光与人流,拍去你衣衫尘土,如同冷夜的拥抱,驱走的陌生抵得上几壶老酒?也许有泪停泊在眼眶,感激风霜后上帝给予的灯火,照亮腐蚀的皮肉。
那如果手掌摸向头,你会不会顿时怒气纵横,不死不休?心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挑衅者蠢蠢欲动,忍无可忍,世间留下拳头,锋芒毕露。
也许老了,记忆渐渐僵化。是否记得,曾经……
他说:如果,天涯海角,突然你被摸了一下头,不要将心闸关闭,悄悄开一个缝儿,或许会换回一个拥抱。
他说:离别,不要说再见。不见不散,就如同东山冉冉升起的太阳。有人摸头,你要反手一个拥抱。
故事的背景唤作青春。一条生活的铁索,一个玩笑般的故事,这是属于彼此的契约。
期限:无期。
命运书
生活,藏匿着雕刻者。
时光的锦帛,遗存命运的刀痕。将岁月一帧帧展开,魏晋风流,汉唐遗风,月季丛中,轨迹交错的人生缠满缘分的蛛网。
雁过留声。雁,埋葬在未知的坟茔,传唱的故事如同提线木偶,忘却了典故的由来;声,响彻云霄的浪花,在风中滔滔不绝,撕裂锈迹斑斑的枷锁。
分毫不差的雕刻,掩盖了命运的诘屈?缘分的哲理无从解答艺术品的造价;抓不住的尾巴,源于放逐的视角?风雨是巨人脚下易碎的玻璃。
山上有月,月下有人;江边有柳,柳旁有舟。哪怕命运是风之影,成全与拆分,终将展现真实的形体。
雕刻者,骨子里有山河脉络的魂魄。抓住命运的刻刀,雕绘命理的纹系,巧夺天工。不拘一格且和而不同。
一滴泪,接近于汗水的排列,足以清澈所有的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