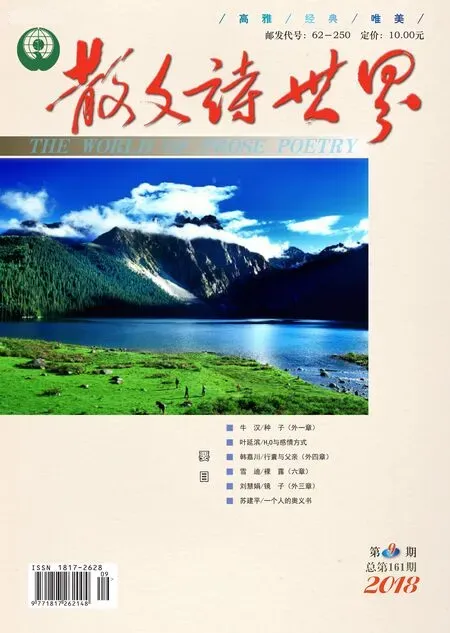一个人的奥义书
浙江 苏建平
A
关于神秘,首先来自于每个人的自身。正如撰写经书的人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无需任何逻辑,和任何道理。
那照耀万物的光,那照亮你眼睛的光,它来到你的时间中,哺育又收割。
在同样的情况下,你被抛到了世上。
制造你的人,满脸欣喜。围观你的人,也满脸欣喜。他们哺育又收割你,等待有一天你来哺育又收割他们。
B
在人世,你必须要有一颗徽章。独独属于你的徽章。
遥远的时代,祖先们生活在丛林中,他们的徽章往往由弓箭、石刀、兽皮和尚未脱胎成文字的咿咿呀呀组成。
更近的祖先们,已经拥有了名字。此外,他们还发现了金属的奥秘,以及发明了刻在金属上的老鹰、狮子、神龟等等图案。
可是你啊,如今只拥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历史曾给过的家庭神秘,又被历史及时抽走了。如今的你,住在公寓房里,像你的名字,蹲在一份档案里。它差不多构成了你的全部。
C
你从味觉开始学习。
那么多感官正排着队等候你:触觉,视觉,听觉。所有这些感觉,泥沙俱下,生猛而美妙。
而黑暗,同时也包括在学习当中。尽管,你学习的是有关光的知识。在你周围,已经有人把光分门别类。
你拉开一个个抽屉,把它们装进了自己的抽屉柜子。
D
挫折,第一次挫折,是你的同类给你的一件礼物。
它往往诞生于一个黄昏,一个课间间隙,一次郊游,一条街道,一个恶作剧,一群人,一群熟悉的人。
那样一种情景下,它突然来临,仿佛一阵飓风,使你措手不及。
那个东西是如此陌生,并且让人生疼,你还无法命名它。
有一天你把它叫做“刺”。
E
星光照着你。可是星空尚未来到你的心中。关于这一切,蒙着面纱的一切,未及命名的一切,你把它们归入了问号的学问之中。
你的一生都会追着问号跑。
问号后面还是问号,蜿蜒而无尽头。
直到问号追着你跑。
直到人生歧义丛生。
F
种子萌芽。枝叶扶疏。亦花亦果。而众人皆在采摘。
幼兽奔跑,脚底生风,毛发逐日丰厚。
它们的牙齿间滴下血滴。
轻若尘埃的蜉蝣却朝生夕灭,只留下一些舞蹈的影子,倒映在水面上。
这一切多么新奇。它们在你的身边跟你一起生长,不断暗示一些日后被称为秘密的事物。
G
你惊讶于身体的变化:长出喉结,或者血跟着月亮流。更重要的是,喉结开始迷恋血,而血迷恋骨感的喉结。
在人生成谜又谜样翻出的阶段,你目睹了喉结与血的一场场婚礼。
俗世的婚礼。跟钱有关的婚礼。跟桥有关的婚礼。跟生育有关的婚礼。庄重和轻佻并举的婚礼。
你喝着酒。事实上,你尚未开始喝,已经有了醉意。对你来说,这又是一个尚未抵达的谜。
而谜,总是迷人的。
它的凶险,可以称为蜜,甚至蜜里藏刀。
H
你在夜间梦。
它到来的时候,你的内心惊讶不已,一如看见大海、丛林、沙漠深处的景观。
可那还远远不够。那么多人教导你要在白天做梦。梦一张排行榜。梦一个鹊巢。梦金子与银子。
更多的人说:梦明天。梦明天的明天。梦无数个明天。似乎明天比宇宙的尽头还要漫长。
那也许对。但肯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觉。
这错觉渐渐构成了你,并使你从“一”开始,去梦无限。
I
礼仪来自于复数的生活。一遍又一遍,你在反复经历中,慢慢地掌握了它的要义。
树木本性简单。你曾用简单的目光看它们,是如此地接近树木的本性。如今,你用复数的眼光观察,声色越多,知识越多,你离树木却越来越远。
那是一种代价。你要付出的代价。
这一切缘于:空气复杂。
一旦你精通于天平和砝码的技术,那关于温度和湿度的艺术,便逐渐远去,像鸟儿敛起翅膀,隐入暗夜中。
J
晕眩的时刻,刀子般的时刻,死而复生的时刻。
一个陀螺在转。
它在转,可是你看不到在转的陀螺。它在你的眼皮底下转。它在你的四周转。它转入你的身体内部。它的目的是:把你变成一个陀螺,兴致勃勃地一刻不停地转动着。
它和你都在熟视无睹中转。
如此,事物开始显露本相。
K
你终于走进了别人曾走进的殿堂。
正如你出生时那样,众人以星捧月,将你送达目的地。所有人都编写了你的剧本,有你认识的人,还有你不认识的人。
年长于你的人颔首:这个时刻他们乐于看到,并且以适当的笑话来暗示你一些即将来临的细节。
年轻于你的人奔跑:为盛大的典礼奔跑,为空气中的气息奔跑,为身体里的潮水奔跑。
你自己却获得了模糊而不确切的崭新知识:一种长跑结束,另一种长跑刚刚开始。
L
你终于走进了那个座位。你命中注定卡在那里的座位。
一个钥匙。一个门牌号。一个流水线上的编号。一个电话号码。一张严肃的照片。一张工资小纸条。一张饭卡。一张时刻表。一个个晴天和雨天。有时候一些谈话。有时候一些聚会。慢慢地一些关于你的名声。慢慢地一些渐渐成形的捕风捉影。它们如影随形。
你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变成熟人。
你也一步步变成自己的陌生人。
M
你终于把自己的血化成一个小东西:哭泣的小东西,柔软的小东西,疾病正在等待的小东西。
一个你给了命、会续你的命、又将要你命的小东西。
蛮横无理的小东西。
像早年的一份试卷,
也像一张你时时要填写的表格。
错误总是躲藏在一个个看不见的陷阱里,等待你去如履薄冰。
N
你终于戴上了面具。那个你从早年开始编织的面具,在众人手把手指引下编织的面具,类似于皇帝新装的面具,成为了你成人的另一个加冕礼。
从这一个面具出发,你迫使自己学习隐身的艺术,学习曲线的艺术。这些艺术遍布于看不见的空气中。学习它们,那等同于一个伟大的发现,像你早年发现鸟儿飞行的轨迹一样。
正如物理学课程告诉你的:在看不见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不同的场。
深水暗流。
时光不居。
你走上又走下台阶,打开又合上一扇门。在你自身的静默里,总会有一种意想不到但又意料之中的声音发出来。
O
一些事物有了新面貌,或者,它们开始书写另一种词典——
星星的闪烁不再重要,在夜晚,你从中感受到了更深的寒意。
蛇在暗处蜕皮。从你小时候一直蜕皮到现在。但它们潮湿的踪影,日渐成为一个谜。
数字迎来了膨胀的时刻。它们不停地自我繁殖着:你案几上的报表,你抽屉里的银行卡号。它们渐渐远离数学,走向信仰。
新墙在变旧。老墙在龟裂。老房子在一夜之间失踪。每天,你发现一个个座标,脚跟贴着脚跟,悄悄地改动了。
它们都在耐心地等待你的这一天:习焉不察。
P
而一些困惑也接踵而至——
你出发,到达一个地方。当你置身其中,你发现它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地方,仍然冠以老名字的新的地方。
导师们从空中不断下降,现形成为肉体凡胎。你注定要遭遇一些扑面而来的风尘,它们早已在伺机锯挫你的眼睛。
而酒,不再亢奋,不停地与你内在的器官拔河。
有时候,年少时曾经恐惧的黑暗,竟变得如此亲切,比生活中的油盐酱醋更为重要,不可或缺。
它让你在独处时品尝到一种黑的甜。
Q
世界正在脱胎换骨。
这印象来自于你的一个梦:蜘蛛在织网。梦中,无数的蜘蛛,在织同一张网。那张网密密麻麻,越来越庞大,伸向无穷无尽的远方。在蛛丝的结点上,树起了一盏盏的路灯。而路灯,重建又毁灭,毁灭又重建。
你回头看时,发现一只只蜘蛛越来越小,渐渐可以忽略不计。
你也化成了其中一只蜘蛛。
你难以描述这一景象:
在肯定自身的劳作里,
却找到了消失的自己。
R
从窗口望出去,电子屏幕上跳动着色彩繁复的图像、线条、字幕。一些粗壮的口号晃动着手指,忠实地化身催眠师。你注意到,如果看上十分钟,你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便增加一分。
而那些确定的树木隐身在雾状的灰色中。它们如何理解日益不确定的阳光?它们歌唱的器官在哪里?它们该怎样表达树心处的愤怒?
远处的塔吊在给大地做手术。
近处的车辆在给大地喷涂漆。
城中,奔跑的甲壳虫取代了歌唱的甲壳虫。
S
你居住在高楼上——而居高楼者,必离大地远。
你居住在高楼上——而居高楼者,星空不曾近。
T
你拐过了很多弯,每个弯都埋着不一样的凶险,有时是一锅粥的凶险。
你走过一条条走廊,正如一位智者所说,一条有人拖了一辈子,却越拖越脏的走廊。
你认识过的朋友们,已经在名单上不知不觉被时光磨损。直到你后知后觉。却从未先知先觉。
你大把的时间,跟厨房的油污一起冲入了下水道。
你学过的一些字,正在改变性别。整容术正在大行其道。修辞术依然在扮演自己的角色。魔术的戏法仍然攻陷一个个堡垒。
先哲的经书道出了所有的秘密:《易》。
你被偶然地投入到了世界必然的“易”之中。
U
那一天,城市很堵,火车声隐隐传来,下起了雨,两只鸟在雨中飞来飞去,它们的巢连同大树,一起成为失踪的案件。
你在窗前,毫无表情。
那一天,有个小孩成为了孤儿,成为孤儿的时候,他在草地上跑,不认识铁和锈,不认识血和肉。
你在窗前,毫无表情。
那一天,报纸的国际时事新闻第四版上,两个国家抡起了拳头,炮火烧焦了土,烧焦了树,烧焦了镜头,烧焦了呼吸。
你在窗前,毫无表情。
那一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天空下,米饭照样煮熟,鱼虾照样生仔,剧目照样上演,木鱼照样敲响。
世界照样庸常。
你在窗前,你的表情剥夺了你表达某种表情。
V
你住在这个小城。南方的小城。体量很小却野心勃勃不停扩张的小城。跟你出游时所见的无数孪生般小城的小城。
从早到晚兴致勃勃的小城。二十四小时不再睡眠的小城。到处混乱却生机勃勃的小城。
习惯于将小事情放到放大镜下的小城。
将你固定住的小城。有时候卡你一下的小城。给你粮食的小城。给过你童年给过你青年,又给了你中年的小城。
你住在这个小城,越来越以沉默对之。
W
不能言说的事物,一旦说出,就成为一种危险:公园里人满为患。商场里人满为患。银行里人满为患。大街上车满为患。空气中欲满为患。
树叶上积着灰尘。一场雨已经不能解渴。
小动物们不停地迁居,或者排着队走进了生物教科书,仅仅生活在纸上,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永生。
一个个你向着你走来。
一个个你穿过了你,你也穿过了一个个你。
你和你们相互叠加,相互喂养。你和世界一起肥胖起来。
而肥胖,意味着转折与觉醒——
X
所以,每一天,你都在收集碎末。收集钢铁,收集合金。收集草木,收集蝼蚁。收集干燥,收集潮湿。收集元音,收集辅音。收集盈余,收集负数。收集记忆,收集遗忘。收集生,收集死。
这是全新的功课。
在功课中,小虫般的文字抖动着微弱的触须,上穷碧落下黄泉,作出使命般的探测。
Y
你居住在高楼上——还有多少蚁巢蛇穴?
你居住在高楼上——还有多少近亲远邻?
Z
你看着这个不断加速的世界:旋转,奔跑,飞翔。你也加入了这个合唱:更长的手,更快的脚,更亮的眼,更大的脑。
简单的世界失去了本性的简单。
清澈,透明,纯洁,这些词汇穿过你巨大的肚腩,正在从词典中撤离。也许它们会去而复来?
这取决于你的心灵,以及你们的心灵。
智者说:一沙一世界。而一世界,它首先站在一个个人上,站在沙子般的个人之上。
有一天,你终于发出了这样的喊声——
“偏食的世界啊,请校正一下你的肠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