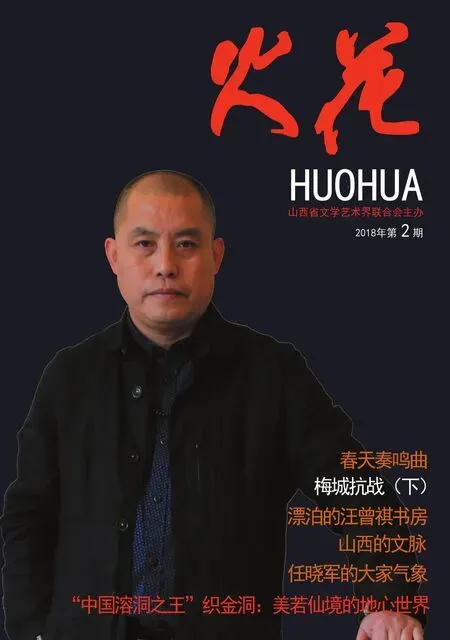归途,雪花飘落的方向
舟自横
一
回到故乡的第二天清晨,就下了今年的第一场大雪。
一片片雪花,是上天馈赠的白羽毛,转眼间,进入冬季萧瑟而破败的逯家沟,瞬间便出落成一只白天鹅。雪花在飞翔,村庄在飞翔。
清冽的气息从天而降,内心被还原成苍茫的素洁,在视线和阳光被遮蔽的时刻,却闪着光,幽微而柔软。
在远离故乡的小城,曾写过一组《每一场大雪都来自于故乡》的组诗。如是,无论我身处何地,遇见的纷纷扬扬大雪,带来的仿佛都是故乡的影子。这是一种牵挂,也是从尘世里转身,找寻我散失的灵魂。因此,我相信,眼前的大雪既是我的感召,更是对我身心的洗礼。
屋内蒸汽弥漫,表嫂在忙着做早餐,我和表哥在外面扫雪。
故乡人家大多用栽植的红柳做篱笆墙。多年过去,红柳也越来越高,现在已是银装素裹,高高的枝条被雪压得摇晃着,像迸溅出清脆音乐的玉笛。站在牛舍里的一头老牛,望着白茫茫的天地,似乎若有所思。
村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更听不到孩子们的欢笑声。到处是寂静,还有寂静里深掩的凋敝和疼痛。表哥的小孙女,也就是他在外打工的小儿子家的孩子,欢快地屋里屋外跑来跑去,像一只翩飞的蝴蝶。看着她形单影只的样子,我忽然觉得她其实很落寞。这种落寞,是我的童年对我的暗示。
小时候,看见下雪,我们二三十个小伙伴便迅速地集结到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欢天喜地。雪花是天地的精灵,孩子也是天地的精灵,当两者相遇,乡村的冬天便仿佛像白色的植物焕发出勃勃生机。现在想起,浅浅的童真仍然溢出内心。
童年的雪花,越飘越远。或许,它们被风吹落到我目不能及的某处,或许被我丢失到漂泊异乡的路上。它们和我一样,行走,挣扎,修补着身子里的裂纹,最后被时代风干。
表哥没有戴帽子,头上热气蒸腾,雪花化了又落。我们拿着竹扫帚,在院子里认真地清扫着,刚刚清理干净的地方,不消片刻工夫,又落满了雪花。
表哥今年近七十岁了,是退休教师,身体十分硬朗。可以说,我人生的轨迹都与他有关。他年轻时喜欢读书,并订阅和购买了很多文学刊物和书籍。在这一点上,他在农村显得与众不同。在他的影响下,我从童年开始,便对书香有着亲近感。他的一本本书籍,给了我遥望外面世界的梯子,并向梦想的道路和星光靠近。
他有五个儿子,四个在外地打工或者工作,只有二儿子在家种地。他和表嫂不但要照顾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孙女,还要帮种地的儿子忙里忙外。
多年前,他一个在外有公职的儿子,就希望他们去那里生活,可表哥却舍不得离开这方水土。
抬起头,看见街边挺入云天的杨树,在大雪里“白发须髯”,沉默、知足,像尘世的隐者,更像村庄朴素的亲人。其实,表哥也和它们一样,根系深扎进泥土,与故乡须臾不可分。
二
有些文字,写出来心会隐隐作痛,因此提起故乡,我一直闪烁其词,避让着“亲人”这个词。尽管如此,故乡依然不时地捂在我的心口上,给我温暖,并让我面对浮躁的人世保持着达观和清醒。
故乡,我最牵念的人是我的老叔。
在表哥家匆忙吃完早饭,便急着去老叔家。
昨晚回到逯家沟,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因此没去惊扰他。
其实,在故乡,我的亲人所剩不多。父母早逝,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在外地打工,最亲近的是一个叔叔和一个舅舅,其余的都是表兄弟。在这些人里,我最惦记的是我的老叔。于我而言,他不仅仅是我血脉相连的亲人,从他身上更能折射出村邻的良善和劣性以及世风的浇漓。
他多少有些弱智,别说不认字,就是人民币一多就数不过来了。但他的个性人人皆知,比如他不会轻易去别人家吃一口饭,也不会给他人添任何麻烦。他七十多岁了,没有儿女,婶子前几年去世。早些年,村里就让他和婶子去敬老院,他说什么也不干,称去那里没有自由。好在,现在村里对他很照顾,每年土地承包出去的钱和“五保”钱,收入一万五千多。不过这么多钱,每年也不够他花的。事实上,我的纠结也正在于此。
老叔家与表哥家,南北间就隔着一条土路,有一二百米的样子。远远地,看见两间低矮的土坯房,在大雪的包裹下,像个若隐若现的大蘑菇。而房顶蹲伏的烟囱,恍若翘望的人,孤独而凄清。
他家的房子和乡亲们一样,都是菜园挨着庭院。菜园的南边,有个简陋的小木门,推开来悄无声息。菜园面积很大,据说他每年种植的土豆和玉米自己都吃不了。菜园里站立着一些向日葵和玉米的秸秆,它们的果实奉献给了人世,叶子早就掉光了。看见庄稼,我就能够想象出夏日里,这里绿意丰沛,阳光明亮,雨露细润,以及植物间的私语。它们没有倒下,它们是土地精魂的遗骸。
走进菜园中央,我便赶紧大声喊着老叔。我知道,他喜欢养狗,不止一两条,并且都很凶。对此,我没少说他,其实养一条陪伴他就可以了。他养狗很费钱,买的时候花高价,平时喂的狗食也是非常人家可比。
没有听到狗叫,我老叔却忙着迎出来,让我进屋。
我问那些狗呢,他说给卖了。对此,我是不怎么相信的。我猜想可能是怕我看见,他就提前把狗放到别人家“寄养”几日。
屋子逼仄,有股发霉的味道,墙壁像几块漏风的厚铁,压得我心里难受。听表哥说,村子里明年准备给他盖两间砖房,如此最好,我也可以出一部分钱,让他住得舒服一些。
他越来越老了,雪飘来飘去,终于停留到他的头上。他有点窘迫地站着,打开新买的冰箱,说吃的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但不怎么想吃肉了。
去年他曾经得过一次病,多亏几个乡亲在医院照顾,尽管是村里拿的护理费。让人感动的事不少,让人纠结的事也挺多。我还听说过,有人看见一个叫王六的,同老婆孩子与我老叔这个连数字都不认识的人打麻将,那次我老叔输了好几百。还有村邻向他借钱,几千几千的,至于还与不还,还多少,我至今也不得而知。每每听到这些,我胸有块垒,欲说难言。
我老叔共有六个侄子,我行四。我大伯父家和二伯父家的几个堂兄弟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林甸县。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去过那里。那时候,大伯父和大伯母还健在。除却那次我们见过一面外,现在仍然音讯不多。多年来,我老叔也很少去他们那里。亲人之间的来往,几近断绝。
我老叔小时候,我父亲对他最是疼爱,我的两个伯父搬到林甸后,他和我父亲留在了逯家沟。因为我的姥爷和姥姥一直居住在这里。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老叔就是生产队的羊倌。我父亲后来卧病在床,家里有重活的时候,我便替代他去放羊。他对我也最好。后来到外地工作后,我经常接到老家的电话,但对方不说话。但我知道是我老叔。他之所以不说话,一是想听听我的声音,二是怕我训他,三是怕我知道是他而感到麻烦。其实,对于这些我心知肚明。我就经常给他电话,但不知什么原因,他老是换电话号码。可能是有些村邻,手机不想用了,连手机和号码就卖给了他。
此时,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叔,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所有的亲人们。我们就像浮萍,随着滚滚红尘而四散去了。没有相互间的守望,有的只是专注于各自脚下的巴掌大的一方水土。
庙堂之高也罢,江湖之远也罢,每个家族都是一部大书。但我的家族,谱牒散佚,籍贯模糊,因此我一直就觉得自己恍恍惚惚迷失在风雪里,根系已经被深埋,姓氏的源头模糊不清。
三
雪后初霁,闪烁的阳光在皑皑的雪地上纵情飞舞,像亿万只蜜蜂嗡嗡作响。远处,大平原坦荡而苍茫,其中的沟沟坎坎如无数匹白色的骏马在驰骋。
下午两点左右,吃两顿饭的乡亲,开始做饭了。稀疏的炊烟在冬天里显得格外洁白,袅娜、丰满,像刚刚洗浴过的少妇。雪落大地,而炊烟是村庄向上洒出的一束束雪影,攀爬,盛开如莲,为天空描摹出笑纹和俏丽的眉毛。我们的归宿是大地,炊烟的归宿是天空。
和老叔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路上,不得不眯着眼睛,辨识着村庄的容颜。
我们村子名为逯家沟,是有来历的。村子历史不长,和黑龙江大多数村庄一样,历史也就七八十年左右。我姥爷十七岁的时候,与三个本家从吉林来到现在的黑龙江讷河县。因为都姓逯,落脚的地方就被命名为逯家沟。之所以被称为沟,是因为村子四周的土地有些渐渐隆起。我生于斯长于斯,并且看着长辈们相继在这里入土为安。
当初我离家的时候,逯家沟有个大家一百九十多口人,现在老老小小加到一起才三十多口,青壮年大都出去打工了。再者,孩子在外地上学的也不少。由于附近学校撤并,况且学校离村子甚远,有的家庭从孩子小学一年级开始,干脆就把土地承包出去,在县城购买或租住房子。男人打工,女人陪读。
如今,我对村子里每家的房舍以及它的主人的音容笑貌都记忆犹新。但现在的境况是,很多家的土坯房已经东倒西歪,破败不堪。一缕缕炊烟在消逝,一个个姓氏在散失。
二十多年过去了,除却因为年纪和疾病正常过世的十几人之外,村子里因家庭纠纷自杀的就有两三个。在外地早逝的也有四个,他们的年纪和我不相上下。这四人中,有三个是因为疾病,有一个是因为车祸。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童年小伙伴二歪因为婚外恋而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还没有出狱。
不知不觉间,我家的老屋就在眼前。它后来的主人全家都出去打工了。
厚雪遮掩不了老屋的沧桑。门窗破损,墙体歪斜,屋檐敛目,屋顶的积雪好像随时都能把它压塌。它在汹涌的雪潮下,像只颠簸而破败的老船,摇晃着,挣扎着,却躲不过时光的漫卷与撕扯。
老屋才盖四十多年。我之所以叫它老屋,一是因为北方的民居寿命短,二是这所房子是我家自己盖的,三是我父亲是在这里去世的。
阳光刺眼。再次抬头看着老屋,好像看见了一个人影,背对着菜园,与老屋对视。他是我的父亲,是我记忆里的父亲。
老屋凝结了父亲的全部心血。
父母结婚后,买了一个破旧的房子暂时栖居。那些年,只要家里有一毛钱,也积攒下来,以备购买盖房子的木料。实在住不下去了,父亲决定盖房子。那年我六岁。
在我的老家,盖房子一般都是在六七月份。按理说,只要是材料齐备,盖房子并不是多大的难事。偏偏那年,遇上几十年少有的大旱,连县里的各个部门都组织职工,到农村帮助救灾。而盖房子在当时算是个大工程,恰恰遇上社员都要把主要精力用到抗旱上。生产队只是帮助我家把房架立起来了,大多活计还得靠自己干。
父亲有恐高症。砌墙的时候,我母亲和姐姐就把土坯放到筐子里,他在上面用绳子拽上去。他站在越砌越高的墙上,汗水不停地滴答。风吹过来,他的身子像单薄、摇摆的纸人。有一次,他差点掉下来。后来我成人后,才明白,在平原上,老屋的高度恐怕是恐高的父亲一生登临的最高度。这个高度,是他对家庭爱的累积。
住进新家的第二年,父亲因过度劳累而一直卧床不起,直至去世。白天的时候,我去上学,母亲和姐姐也大多在外面忙碌,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老屋,看到了父亲满面的愁苦和浑浊的眼泪。
老屋也目睹了我家后来发生的一切。父亲早逝,老屋易主,母亲随我来到城市,却患心肌梗塞而撒手人寰。老屋后来的主人,原来是生产队和村里的会计,很是张扬。他自己酒后就多次说过,他一跺脚逯家沟就得乱颤。没想到,他在知天命之年却漂泊到外地打工。
时间和时代的大背景,决定着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走到老屋房西,忽然看到有几只麻雀从屋檐里飞进飞出。它们的身子是跳跃的音符,在雪影的映衬下闪着光,为乡村平添了韵律和生气。
然而,它们还记得它们主人的模样么?它们还记得乡亲们的谈笑声吗?或许,它们比我的父老乡亲还要孤单。
四
表哥的孙女来喊我们回去吃饭。老叔不肯去,看我近乎于哀求的神情,他才勉强答应。
厨房里热气腾腾,一股农家菜香扑面而来。屋子里,坐着我老舅和表妹夫。
老舅也七十多岁了,一直独身。他原先是生产队的赤脚医生,据说中医还不错。他的近视眼镜,应该能够代表逯家沟的文化厚度。我小时候,他和我姥爷、姥姥在一起住,我天天赖着他家不走。等到我上小学后,他的医药书我没少闲翻,特别是一些《说岳传》《隋唐演义》等评书演义类书籍更是让我爱不释手。人的命运有时候仿佛是天意。如果,没有我老舅和表哥,可能我最终不会走上舞文弄墨这条道路。
他一生好酒,并常常大醉。我老叔对他很有意见。去年我老叔住院期间,我老舅也被“公派”去照顾病号,然而我老舅却天天喝酒,气得我老叔看都不看他一眼。我老叔刚才还对我说,最可气的是,等他出院后,我老舅竟然把一个塑料盆拿走了。听到这些,我就忍俊不禁。
表妹夫比我小一岁,我们属于童年玩伴。他父亲与我父亲一生交好,我们两家处得很近。他的母亲,我称作大姨。他的父亲去世后,他母亲就到了居住在查哈阳农场的另一个孩子家。我回故乡的时候,曾经特意去看望远在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她老人家。
互相问候是避免不了的。都说大雪来得及时,明年一定是个好年头。
屋子中央,炉火熊熊。炉子里飞出细碎的光,忽明忽暗,如落到墙上的蝴蝶在扇动着翅膀。对于这样的场景我是如此熟悉:我的父母和我们几个孩子围拢在火炉旁,笑意盈盈,满面红光。炉火的暖,是滚烫而软糯的暖,是低处的暖,来自于露珠升起,来自于溪水流淌,来自于小麦扬花和炊烟的腰肢,来自于大地深处。
南方的朋友以为,北方下雪是寒冷的标志。而我却一直认为,飘落的雪花,就是燃烧的火苗。因为每年的第一场雪后,每家每户就开始生炉子了。更为令人迷恋的是,下雪的时候,亲友们在火炉旁相聚,亲情和友情燃烧着,十分熨帖和惬意。所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大概就是这样的心境吧。
不一会儿,菜就端上来。冻白菜蘸大酱,酸菜炖大鹅,五花肉炖冻豆腐,土豆炖土鸡……这些令人日夜垂涎的家乡菜,让我大快朵颐。
美中不足的是,我最爱吃的冻豆腐和我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冻的没什么两样,毛孔不多。原因不言自明,那就是冻豆腐,只有借助雪才能堪称完美。下雪后,把切好的豆腐装袋,然后放到雪堆里,想吃就拿出一块。这样的冻豆腐,炖出后浑身是毛孔,吸足了汤汁。这样的毛孔里,隐藏着大自然的秘密。
喝酒的时候,平时沉默寡言的表妹夫话语多了。他说他家小子订婚了,等结婚一共得花三十万。我一听这个数字就大吃一惊。他说,这还是少的,多的都达到了五十万了。女方不但要现金,还得要个城里的楼房。
“父母一生都在给孩子扛活。就是有出息上大学的,也是不少花。”表哥说。农村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但彩礼也越来越重,大多家庭为了孩子得倾家荡产,老人还债一直到不能动弹为止。
我本想说些什么,但还是忍住。农村的一些风气,早已今不如昔,过去有大的农活邻里互助,现在必须花钱雇。世风的火焰正在把心冶炼成铜板。那些淳朴、厚道、热情、善良,好像在渐行渐远,留给我们一个怀念和喟叹的背影。
我知道,我的叙述和思考是多么孱弱和无力,任何形容词都难以掩饰内心的焦急和凌乱。因为我深深知道,所谓新农村建设,如果仅仅是漂亮的房子和街道,仅仅是富足的生活,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得不偿失和背离某种初衷了。
“下雪了,该杀年猪了。”表嫂说,他们忙活一年,就是盼着孩子们春节都能够回家团聚。我想的却是,如果父母健在的话,年轻的外出打工者能在春节时候,回到故乡一次。然而,他们的子女,若干年后还会回到逯家沟吗?
我眼角有些湿润了。父母在,故乡就在;父母不在,我的故乡也在。这是我的宿命。仔细想想,我和雪花是多么相似。地气和蒸汽缭绕、上升,离开故土,但最终还是要回归于大地。雪的生成与回归,也是我的必经之路。一片片雪花飘落的方向,就是我的归途。我们都走在回程的路上,身子越来越低,直至渐渐融入苍茫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