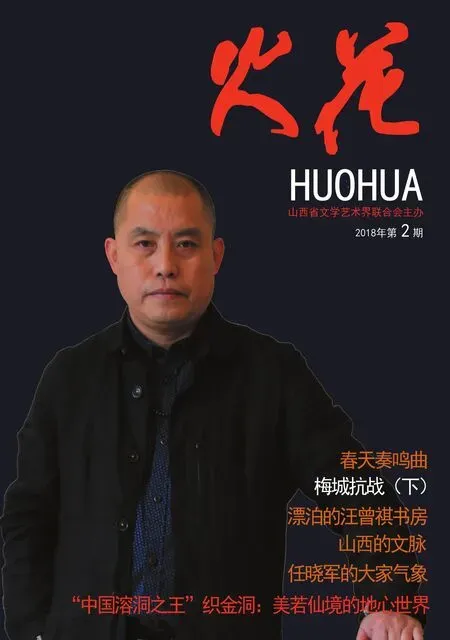连枷如歌
李笙清
母亲托人捎来一小袋刚打下的黄豆。送走客人,我给老家打电话,电话那头,母亲笑呵呵地说:“小清啊,别小瞧这些黄豆,这可是你爸打了半天的连枷打出来的呢!”
电话挂断了,看着这些浑圆饱满的黄豆,我的耳畔仿佛响起悦耳的连枷声,在遥远的乡场上,它们像乡村竖琴上美妙的音符,经久不息,富有节奏。打开记忆的窗子,似乎已是很久以前的画面了,每当稻谷成熟收割后,在稻田摊晒时,就用弯弯的、两头裹着铁尖的冲担挑到平整宽敞的打谷场上,均匀地铺好,就轮到连枷上场了。
连枷由手柄和竹芭构成,都是由乡镇的篾匠们制作。其制作方法是用绳子将五到六根竹片用棕绳扎成一组长方扇形的竹芭,将一头固定在一长方形的木头上,再装上一根顶端用火烤弯成圆筒形的粗竹子作为挥舞连枷的把手。使用时,打稻的人手握连枷的竹长把,抬起连枷,向后一甩,再猛地一抖手腕,连枷顶端的那个用竹片连成的竹芭沿着长柄顶端的轴迅速地转动着,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随着长杆的下降,最后重重地落在稻穗上,动作协调,宛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在连枷一上一下的连续拍打下,稻穗从稻秆上得到脱离。在过去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的乡村,连枷作为一种十分原始的农具,其主要作用是脱粒,除了打稻,还能拍打麦子、蚕豆、菜籽、黄豆、绿豆等农作物,由于广泛使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小时候看父亲打连枷,一下一下地在稻穗堆上移动着,那距离就像尺子量过一样标准。间隔些时,父亲会“嗨”地吆喝一嗓子,那连枷便似乎更加有了力量。乏了,父亲就坐在禾场边的石磙上,抽上一根烟,喝上一碗大叶茶,那举止神态便充满了惬意。抽完烟,父亲朝掌心吐上一口唾沫,使劲地搓一下手掌,又一次抡起了连枷,那“啪”“啪”的声音便有节奏、有力度地响了起来。
打连枷讲究技巧,手要攥紧,如果在扬起、落下的过程中手松了,就会滑动,手掌和手指上会很快磨出水泡,所以说打连枷,有些膀阔腰圆臂力大的汉子如果没经验,还比不上瘦弱的婆娘。如果光凭蛮力,掌握不了力度火候,往往打不了多久,就会气喘吁吁,打出的行距也不一致,有些稻谷根本离不开稻秆,结果很多地方都要重新再打一遍。有经验的人打连枷就不一样了,随着他们腰身的扭动,连枷高高扬起,这时候是不用使出全力的,关键在于那套在顶端竹轴里的竹芭在转动中落下的时候,只有发力于这个瞬间,才能将稻谷从稻穗上快速地打落下来。那时候,我常常坐在打谷场边的草垛上,看那些婶子们打连枷的确是一种享受。她们的腰身灵活起伏,总是有节奏地扭动着胯部,动作不疾不徐,连枷挥动之间显得轻巧而充满灵性,起、扬、甩、落等步骤拿捏得极有分寸。多年后我还常常痴想:乡村女人大多拥有婀娜的腰身,大概是与打连枷有关的。
在父亲歇息的时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有时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抡起连枷,在父亲的指点下拍打稻穗。可当我挥动连枷时,那上面的竹芭却总是不听使唤,稍不留神,就会碰到自己的头,不是破皮,就是起包,虽然疼痛,但却充满了童年的乐趣。记得有一次打连枷,不小心被竹芭打破了头,在村里的诊所缝了四针,从此留下一个小小的伤疤。当父亲背着我回到家里,爷爷奶奶足足数落父亲一顿饭的时间,母亲更是在一旁不住地埋怨父亲:“孩子只有连枷的一半高,你让他打什么连枷?”此后很长时间,我远离了连枷,一是家里从此不让我碰它,二是连枷也让我有了一种畏惧心理。
秋天收割季节,乡村宽敞平整的打谷场可以说是最繁忙的地方,村民们排着队等候打稻。有的白天排不上,就在夜里打,一时间,禾场上灯火通明,连枷声声,欢声笑语,好不热闹。特别是几个人并排相对一起打连枷,连枷此起彼落,动作协调,那场景十分壮观。每当我回忆起打谷场上的连枷声,总会联想到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描述的那种连枷声中生动火热的打稻场面:“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内心里便充满了向往。
等我上中学时,打稻的活儿改成了石磙碾。石磙一头大,一头小,两端有洞,套上特制的木架,就可以用牛拉着在稻穗上运动起来。在牲口的牵引下,石磙一遍遍从谷穗上呈圆形碾过,碾过一遍,农人用木制的扬叉将稻穗翻过来,让石磙再一次碾过去,经过反复多遍碾压后,谷粒与稻草已得到剥离。后来,乡村里有了脱粒机,在电动机欢快的轰鸣中,稻穗脱粒省事多了,那曾经响彻在打谷场或院坝上的古老的连枷声,只能在乡亲们打黄豆、绿豆和油菜籽时,才能偶尔听到。有时候回乡下,看到那柄经历过风雨沧桑的连枷挂在壁上,上面竟有了灰尘,便忍不住拂拭干净,看着那被握成棕红色的把手,我的鼻翼,仿佛嗅到一缕熟悉的汗味。有一次去一家民俗博物馆参观,看到那缺齿的水车,斑驳的风斗,舂米的石臼,锈蚀的犁铧,还有耥耙、蚕架、木耧……想到这些古老的农具正一件件被岁月收藏,一点点躲进乡村记忆的深处,心里便会滋生出一些怀旧的感伤。
如今,家乡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田在日渐减少,很多都开挖成了精养鱼塘,套养鳝鱼和螃蟹,随着乡亲生活的日渐富裕,连枷正在逐渐淡出乡村的生活,正如远在都市的我,在远离村庄多年之后,也在一天天淡出乡村的视线。尽管岁月在无尽地流逝,阡陌、稼穑只是记忆中原始的风景,但那动听的连枷声,就像回味无穷的故土乡音,那抑扬顿挫的声声音符,总是牵动着我难舍的乡土情结,一辈子都耐人寻味,一辈子都无法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