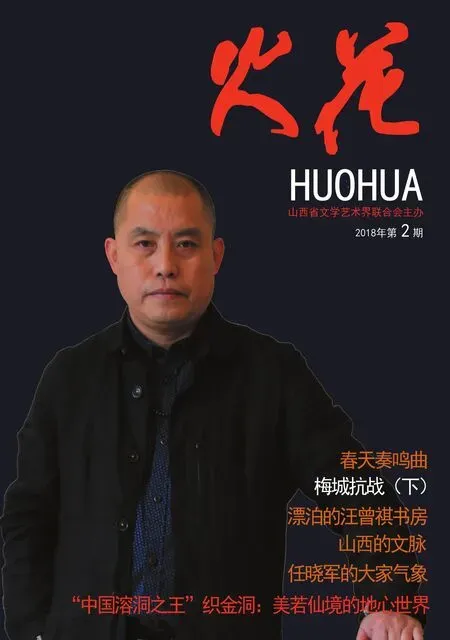朱墨春山(八)
王克臣
顺义县城南街,五行八作的人多。卖豆芽、芽豆的,卖豆腐丝、豆腐的;吹糖人、捏泥人的;绱新鞋、锥破鞋的,焊洋铁壶、锯盆锯碗的。只要能赚钱,混口饭吃的差事,就都有人干。
贾半仙和闺女连汤嘴刚刚回到家门口,一伙人围了上来。
高个子说:“马先生,您到哪儿逛去了?”
矬个子说:“我们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好容易把您盼回来啦!”
小白脸说:“您比星星月亮还难盼!”
乱乱哄哄瞎吵吵,闹闹腾腾听不清。
贾半仙一面应答,一面往院子里走,放下竹竿,慢慢坐下。
其实,这三位并非旁人,就是穷南街的仨痞子:高个子是铁笊篱,矬个子叫佟帽子,小白脸就是琉璃耗子。
全顺义县城的人都知道贾半仙是个算命的,那么,这三位好汉到底是否为算命而来,难说。
贾半仙听声音就知道这仨货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心里清楚,脸上却丝毫不易察觉。他郑重其事地坐下来,嗽嗽嗓子,慢条斯理地说:“你们谁先算,报上生日时辰?”
铁笊篱说:“我先来,生日忘了,时辰还记得。”
贾半仙心里“咯噔”一下,慢慢悠悠地说:“好,那就说说时辰?”
铁笊篱说:“那时候,我家里没有钟表,后来我妈告诉我,阴凉到粪箕子。”
贾半仙想笑,却没有笑,知道是个玩儿闹,没有必要跟这样的人较真儿。于是说:“嗷,明白了,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明人不做暗事的大好人。”
铁笊篱听了,无言,他能说什么呢?莫非说自己是坏人,是一个偷鸡摸狗的坏人?因此,只得像公鸡啄米一样,不停地点头,顺势说:“老二,这次,你说。”
佟帽子说:“我,我是老爷儿爬被窝垛的时候。”
贾半仙说:“啊,巧,真巧,他是阴凉到粪箕子,你是老爷儿爬被窝垛的时候,合着都是大白天。这么说,他是明人不做暗事的好汉,你是光明正大的君子。哈,哈哈——”
琉璃耗子说:“大哥是好汉,二哥是君子,这么说,只有小弟我,顶多是个鼓上蚤时迁了?”
贾半仙翻了翻二五眼,说:“哈,这位兄弟,水泊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顶数这鼓上蚤时迁的名声不太好,是个梁上君子。什么叫梁上君子?就是小偷。依我看,你好比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拼命三郎石秀。”
铁笊篱说:“他呀,小白脸琉璃耗子,顶多就是白日鼠白胜!”
贾半仙说:“不不,白胜是条好汉不假,可是呢,有变节行为。依我看,这位,白白净净,灵灵巧巧。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天巧星浪子燕青,确确实实是条硬汉!要夺,夺谁?夺东洋人!要抢,抢谁?抢小鬼子!东洋小鬼子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不该夺他、抢他?夺他的粮草,抢他的军火,依我看,这还不够,还得要他的命!三个五个,一群两群,中国人这么多,个把小日本儿,还禁得住咱中国人撕巴!”
佟帽子说:“贾半仙呀贾半仙,你哪是给人算命?简直是在做抗日宣传!”
铁笊篱、佟帽子、琉璃耗子一同哈哈大笑。还说什么呢?没的说,只得拿起脚儿,走人。
当贾半仙送出来叮嘱“请慢走”的时候,铁笊篱、佟帽子、琉璃耗子早已飞出了栅栏门。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难度的日子,好过的年。日子一天天地度,年是一年年地过。小的长大,大的变老。生老病死,天经地义,连老天爷也无可奈何。
蔡玉明送出金花,逃出苦海。可她一个人依然拉扯着银花、五丫头、成子,怪不容易的。
蔡玉明三寸金莲,挖土,脚疼;拉套,肩痛;薅苗,蹲不下腿;耪地,猫不了腰。干嘛嘛儿不成,吃嘛嘛儿没有,这样的日子可咋过?
连汤嘴说:“我说玉明,要不那个啥,趁我爹这趟来,还没走呢,叫我爹给你算个命吧!”
蔡玉明说:“穷人穷命,命里注定。”
“就算命里注定,也得看看老天爷,到底给了你一个什么命!”
“老天爷啊,你咋那么偏心眼儿呀,凭什么把好事都给富人,把苦难都留给穷人?”
“老爷儿不总是正晌午。富人不能代代富,穷人不能辈辈穷!”
“老天爷啊,穷人啥时能熬到头呀!”
“依我看,还是叫我爹,给你好好算上一卦!”
蔡玉明叹了一口气,说:“依我看,算不算都一样,瞎子点灯白费蜡。”
连汤嘴听到“瞎子点灯白费蜡”时,稍有不悦,她爹就是瞎子,这不正戳人痛脚吗?这跟秃子讳光、瘸子讳颠、胖子讳肥、瘦子讳干,不是半斤八两嘛!也许,就为这样一句话,连汤嘴便毫无兴趣再提算命的事。于是,她改嘴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瞎子算命两头堵,算也五八,不算也四十。”
蔡玉明听到这里,感觉味儿不对,赶紧转换话题,于是说:“我家金花这孩子,甭说朱二先生、朱太太掏的压岁钱,就连三十黑间,吃到大钱饺子里的钱,都穿在肋骨上攒着,托人给我捎家里来。这孩子!”
连汤嘴说:“人比人死,货比货扔。富人家千金,整天介描眉画眼,搽胭脂抹粉,没扎过一针,没攮过一线,更别说下地抡大镐、蹬铁锹啦!唉,哪儿像你家金花!”连汤嘴一面叽里咕噜说,一面稀里糊涂往外走。
蔡玉明赶忙颠着一双三寸金莲,追着说:“不送了。”
连汤嘴头也不回,迈开双腿,推开栅栏门,绕过老槐树,颠儿了。
事有变故,原本昨天不想做的事,今天突然就改变了主意。
蔡玉明就这样,连汤嘴劝她算命,她说“瞎子点灯白费蜡”,招惹得连汤嘴满脸的不悦。可是,睡了一宿觉,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大早,颠着一双小脚儿,急急匆匆来到连汤嘴家。刚刚推开栅栏门,巧得不能再巧,正遇见连汤嘴的爹贾半仙从茅房往外走。
俗语说,瞎子耳朵灵。贾半仙听到栅栏门响,试着问道:“谁?”
蔡玉明忙说:“我,朱瑞礼家的。”
贾半仙说:“朱瑞礼家的?朱瑞礼不是死了吗?”
想不到,这样一句话,像锥子一样刺痛了蔡玉明的心。她只好说:“是,是这样,我想求您给我算算命,咋就这么……”她说到这里,将那个“苦”字,哽噎在喉。
贾半仙说:“好吧,就请你到屋里说话。”
当贾半仙把蔡玉明引到内院时,连汤嘴从破玻璃窗一眼看见了她,急忙奔跑出来,说:“快,快进来!怎么着,变卦了?”
蔡玉明说:“变卦了,我想让老爷子给我算上一卦。”
贾半仙说:“你要算一卦?”
“算一卦。”
“生日、时辰?”
蔡玉明想了想,报上生日、时辰,静静地等候。
连汤嘴站在蔡玉明的身后,撇着嘴,心里说,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让你算,你不算,今儿又找上门来!于是,她闪身走出屋子。
贾半仙右手扳着左手指头,一一扳倒,上嘴唇轻轻碰着下嘴唇,轻得不能再轻,发出一丁点儿声音:“年干、年支,月干、月支,日干、日支,时干、时支。年柱、月柱、日柱、时柱。”然后,声音渐渐变大,一直到能听得清清楚楚:“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金、木、水、火、土。它们的阴阳和五行属性:甲阳木、乙阴木;丙阳火、丁阴火;戊阳土、己阴土;庚阳金、辛阴金;壬阳水、癸阴水。”
蔡玉明心里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听得明白?您就干脆说,我到底是个什么命?心里想说,却并没有说。依然静静地坐,耐心地等。
贾半仙仰起脸,一双死鱼般的眼睛,朝天上翻几眼,正要开口,外面有人咳嗽一声,开口叫道:“听说马先生光临,蓬荜生辉!”
贾半仙压低声音问:“谁,什么人?”
蔡玉明轻声说:“赵太爷,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一面嘟囔,一面颠着小脚儿,向外迎了出去。
赵太爷呵呵笑道:“听说马先生光临,有失远迎,失礼失礼!”
蔡玉明说:“马先生正给我算命!”
赵太爷说:“那不正好,我想跟马先生讨几招儿!”
贾半仙掮起屁股,说:“哪里,哪里?客气,客气!”
赵太爷说:“你们照旧,照旧!”
贾半仙坐下来,接着说:“刚才,我说到阴阳五行。这里的学问可大啦!”
蔡玉明催促道:“您呀,拣我们听得懂的,干脆,您就直说吧!”
贾半仙沉稳了一会儿,说:“赵太爷在这儿,他在河南村辈分最高,德高望重。我当着他老人家的面,说话要有根有据,拿捏好分寸。”
蔡玉明原本还要催,可是,看贾半仙那神情,深沉严肃,好像有什么不便开口的话题。她的心里怦怦地跳,开始紧张起来。
贾半仙脸朝天花板,翻了翻眼皮,舌尖儿伸出,舔了舔嘴唇,依然没有开口。
赵太爷说:“我要碍事,先回避一下?”
贾半仙说:“不不,您不要走,有您作证,这话才好说出来。”
赵太爷说:“那好,那好!”
贾半仙又嗽嗽嗓子,说:“根据阴阳五行细抠,你 夫殉子……”
蔡玉明问:“什么叫 夫殉子?”
贾半仙说:“说白了,就是 死了丈夫,并不算完,接着还要给儿子带来灾难。”
赵太爷急忙说:“马先生,我不是拦您,这话可说得太严重!”
蔡玉明听了,早已吓得不省人事,瘫软在地上。
赵太爷见了,慌作一团,铆足劲儿地叫嚷:“快,快来人,快来人呀!”
连汤嘴跑过来,带着哭腔叫道:“这是咋说的,玉明,你醒醒,别吓唬人!”连抻胳膊带拽腿。
赵太爷慌忙俯下身子,喘息地说:“掐,掐人中!”
好一阵忙乱,终于听到蔡玉明的喘息。
连汤嘴不无埋怨地说:“爸,瞧您,您跟她说什么啦?吓死人了。有话不会拐弯抹角地说,您直来直去,女人家家的,谁受得了!”
赵太爷说:“你爹是没敢直说,想拐弯抹角,可这弯儿怎么拐,角儿怎么抹?说着容易,做着难呀!”
连汤嘴连连说:“好了,好了,赵太爷,您先坐,我先把玉明送回家,回头再跟您说话!”
蔡玉明鼻涕眼泪一大堆,只得由连汤嘴随意摆弄了。
连汤嘴把蔡玉明连拉带扯,总算弄回了她的家。安顿好了,这才往自家赶。
蔡玉明仰卧在炕上,望着天棚。天棚上的破洞,像一只只黑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
银花、五丫头、成子都依偎在她的身边。
银花趴近妈妈的耳畔,轻轻地说:“妈妈,心口还疼吗?”
蔡玉明使劲儿攥攥银花的小手。
五丫头说:“心口,还疼吗?”
蔡玉明轻轻抹去五丫头的泪花。
成子爬过来,将脏兮兮的小脸贴近妈妈,轻得不能再轻地说:“还疼吗?”
蔡玉明转过眼珠,疼爱地望着成子,摇摇头,泪珠子又一次滚出眼窝。
成子叫道:“妈妈!”
蔡玉明扭过腰身,将成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银花、五丫头同时扑入妈妈的怀抱。一家四口,哭成了泪疙瘩。
董凤才家和蔡玉明家,一墙之隔,有个风吹草动,就别想瞒过。蔡玉明家闹成这样,董凤才两口子咋能不知道?于是,孙秀英前面走,董凤才后面跟,走进蔡玉明家。
孙秀英说:“咋啦,翻江倒海的!蚊子叮着了?蝎子蛰着了?”
蔡玉明说:“没有的事!”
孙秀英说:“那,那咋了?天不是没有塌下来嘛!再说了,天真的塌下来,也用不着咱,比咱们个子高的有的是!”
蔡玉明扑向孙秀英,紧紧地抱住她,大哭道:“天真的塌下来了!”
孙秀英说:“有什么为难事,你跟我说。是不是有坏男人想欺负你?”
董凤才说:“谁?”
蔡玉明说:“不是,我求求你们,救救成子!”
蔡玉明的一席话,使董凤才、孙秀英两口子感到莫名奇妙。
董凤才说:“谁欺负你的孩子啦?我找他家去!”
孙秀英说:“咱们怕过谁!”
蔡玉明一句话没说明白,把两口子急成这样。她不得不从头说起。于是,蔡玉明就把马瞎子给她算命的事,一五一十地从头说了一遍。
董凤才一拍大腿,说:“嗨,为这么丁点儿小事,不值得,不值得!”
孙秀英说:“忘说了,瞎子算命,就是瞎蒙,套你话,两头堵。不能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还有完?他说你家成了大财主,你也信?他说你家穷掉地上了,你还信?”
蔡玉明说:“你们知道马瞎子是谁?他是连汤嘴的爹,县城南街很有名,都称他是贾半仙。”
孙秀英说:“你看,你看,就算他是半仙,还是个假的!”
蔡玉明说:“人家都说他灵!他给我算成夫殉儿。就是说我们当家的朱瑞礼,是我给妨死的。这还不算,还要妨死我的儿子!”
孙秀英说:“他马瞎子说西山煤是黑的,你信;他说是白的,你也信!”
董凤才说:“秀英,马瞎子的话,你不让她信,她就不信啦?我看这样行不,能不能请请孔大学问。他不是算命的,可他有学问,听听他怎么说,多少靠点儿谱。那,那找谁去请呢?”
孙秀英说:“那,找陈快腿,她有面子。你这就去找她,求她给跑一趟!”
董凤才说:“好吧,你们姐儿俩先聊着。我快去快回!”说着,腾腾地出了屋子。
蔡玉明说:“人家马先生说得在理,我越琢磨越对。我们当家的朱瑞礼,前脚走,后脚儿我就得了一场大病。再说呀,要是我家成子再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叫我怎么活呀?”
孙秀英说:“你家朱大哥去世,你得了一场大病,那是你着急,急出一场病。”
蔡玉明说:“马先生说,我家成子,必须更名改姓,要不,这孩子长不大。”
孙秀英说:“听他的?忘说了,听马瞎子话,上东坝。没有几句真的!”
两个娘们儿正说得热闹,突然,院子里搭言道:“说谁呢,上东坝?”
孙秀英说:“来了,孔大学问。玉明,你别动。”
孙秀英刚要挑帘子,孔大学问已经进来了。
董凤才说:“孔老爷子,您跟她们聊着,不陪您了!”
孔大学问点点头说:“你忙你的。”然后,扭过身子,“咋啦,有啥过不去的火焰山?”
蔡玉明只好又把贾半仙的话从头至尾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孔大学问边听,边点头。等蔡玉明说完了,这才说:“算命算命,连哄带蒙。信则有,不信则无。可是呢,多多少少有些根据。要不,也不会流传这么多年,是不是?”
蔡玉明说:“那,您信不信?”
孔大学问说:“我信,也不信。可是呢,凡事,都有因果。有因就有果。人病了,你往前查查,必有原因。咳嗽了,或者衣服穿少了,或者夜里没盖严,着凉了。就说你前些日子,大病一场,那是因为你着了一场大急。着大急,是因;得了一场大病,是果。”
蔡玉明、孙秀英两个娘们儿听了,不住地点头。
孔大学问说:“世间有些事,没必要知道,就不要打听。知道了,反倒是病。”
蔡玉明说:“您说说,什么事不该打听?”
孔大学问说:“比如,你家院子中间,有一棵树。这不挺好吗?”
蔡玉明说:“是啊!”
孔大学问说:“可是,到了算命人手里,他就会借题发挥,小题大做。”
孙秀英说:“不管他怎么借题发挥,小题大做,咱都不听他的,不就完了吗?”
孔大学问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蔡玉明说:“秀英,先别打岔,听着!”
孔大学问说:“还说你家那棵树。我问你:那是棵什么树?”
蔡玉明说:“梨树。”
孔大学问说:“这棵梨树,长了这么多年,谁也没有憎嫌过它。如果没有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也许它会一直长下去。可是,要是有人说出了什么,这就麻烦了。还能不能老老实实在那里长着,那就难说了!”
蔡玉明说:“我不信,我家那棵梨树,长得好好的,这么多年,碍谁什么了!”
孔大学问说:“你们都不识字,不识字有不识字的好处。有时候识了字,反倒糊涂了。要么咋说人生识字糊涂始!”
孙秀英说:“什么什么?听不懂。”
孔大学问说:“你们要不憎嫌,那我就说了。就说玉明家,院子中间,长着一棵树。你们要是识字的话,就会想到一个字。”
蔡玉明说:“那是什么字?”
孔大学问说:“你家的院子,好比四四方方一个‘口’字,‘口’字中间再加一个‘木’字,这个字就念‘困’,困难的困。”
蔡玉明说:“不认识,不认识那个字。”
孔大学问说:“这就是不识字的好处。假如再扒根问底,那问题就更大了。有些事,坏就坏在打破砂锅问到底。”
蔡玉明说:“您越说我越糊涂。”
孔大学问说:“我问你,人家也种树,可人家种的什么树?人家种的是桃树、杏树。桃树结桃,寿桃寿桃,为人增寿;杏树结杏,‘杏’跟‘幸’同音,当幸福看。”
蔡玉明说:“那,我家院子里的那棵梨树,咋解释呀?”
孔大学问望望蔡玉明,定了定神,这才说:“‘梨’‘离’同音。马先生早知道你家院子里有棵梨树,‘梨’之‘离’也,说你 夫殉子。信,就说他灵;不信,就说他蒙。”
蔡玉明说:“我信。别人爱信不信,我不管。本来嘛,要不信的话,咋那么多不顺心的事统统都叫我赶上了?我咋就那么没德行!”说着说着,又抹开了泪水。
孙秀英说:“你看,你看,你的洗脚水倒多!”
孔大学问说:“不到伤心处,绝无双泪流。你说,要董凤才、孙秀英两口子帮你,说清楚,到底请他们帮你什么?”
蔡玉明抹抹泪水,说:“我要他们救救我的孩子!”
孔大学问说:“严重了,严重了。怎么救?你说清楚!”
蔡玉明说:“就按照马先生说的,叫我家成子,更姓改名,不再姓朱,改姓董。叫什么名字,听董凤才董大哥的。”
孔大学问说:“那就是抱养。抱养孩子可不是说说就行的,那是一件大事。”
孙秀英说:“你和你家成子都得认可。”
蔡玉明说:“我家成子刚刚六岁,小屁孩儿,句句都听我的。”
孔大学问说:“这事你甭找旁人,就找陈快腿。”
孙秀英说:“我和凤才倒好说,他听我的。我叫他打狗,打狗;叫他骂鸡,骂鸡。再说,我俩这么多年,做梦都想有个孩子,这可倒好,半路途中,得了个大儿子!”
蔡玉明说:“其实,我也舍不得。唉,我就是命苦。要不,我哪儿舍得把儿子送出去?”
孔大学问说:“好了,好了,老董家抱儿子的方式,我就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
蔡玉明送走了孔大学问,这才说:“秀英,回去跟你当家的提提,也算救我家成子一条命!”
孙秀英说:“对谁家都是一件大好事。你放心去找陈快腿,求她帮帮忙,也让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知道知道。天不早了,我也该回去看看鸡呀猫呀狗的了!”
蔡玉明送走了孙秀英,急急忙忙去找陈快腿。
孙秀英回到家里,一群鸡咕咕叫,追着叫着要吃的。她走进套间端起破瓢,抓几把棒子粒,走出门,扬起手臂,往天上一撒,哗啦啦撒了满地,说:“就知道抢着吃,咋不抢着下蛋去!”
小花猫朝她咪咪叫,蹦着跳着要吃的。她打开抽屉,抓一把碎干鱼,放入粥碗拌拌,说:“猫串百家吃肉,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你咋就不逮只耗子,叫我瞧瞧,懒猫一个!”
小狗子向她汪汪叫,蹿着闹着要吃的。她生气地说:“狗行千里吃屎,你也等着喂,趴窝里消停等着吧!”
董凤才从里间走出来,笑笑说:“我以为跟谁说话哩!”
孙秀英说:“也是的,咱们家只能听鸡咕咕、猫喵喵、狗汪汪,连个跟大人说话的儿子都没有。”
董凤才轻声说:“这不怨你。忘说了,春不种,秋不收。我连一粒种子,也没能耐给你播进去!”
孙秀英说:“这怨不得你,我这破盐碱地,你播进多少种子,也不发芽。”
董凤才说:“横不能这么多年,都种盐碱地里了?”
孙秀英剜了他一眼,说:“你就会耍贫嘴,回家半天,咋连鸡都没喂?”
董凤才说:“就等着你回来喂呢!”
孙秀英说:“别闹,别闹,我告诉你一件真事:蔡玉明要把成子送给咱们家,给咱们当儿子!”
“真的,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天下哪里会有这等好事,不费一枪一刀,就得个大儿子!”
“真的?”
“不是蒸的,难道是煮的?一会儿,蔡玉明就带着成子过来。”
蔡玉明找到陈快腿,把刚才的事向她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陈快腿说:“这事容易,不过,你还要做些准备。”
蔡玉明说:“做啥准备?你说。”
陈快腿想了想,说:“要不,你就甭管了。你先回去,待会儿我跟杨二嫂一块儿到你家去。”
陈快腿的腿快,进了杨二嫂家的门,二话不说,单刀直入,把蔡玉明打算把儿子过继给董凤才家的事,从头到尾叙说了一遍。
杨二嫂说:“你就当个中间人得了!”
陈快腿说:“蔡玉明当家的死了,她一个老娘们儿家家懂个啥?过继儿子,咱要做得跟亲生的一样!”
杨二嫂说:“那怎么做?”
陈快腿说:“裤兜漏。”
杨二嫂说:“裤兜漏,啥叫裤兜漏?”
陈快腿说:“豁出你家一条破裤子,我告诉你咋弄你咋弄。”
杨二嫂翻箱倒柜,找出一条旧裤子,说:“听你的。”
陈快腿说:“裤腰改了,能盛进两个人;裤裆开了,能钻出一个人来。”
杨二嫂照着陈快腿的话,很快把旧裤子改了,然后说:“看看,行不行,还咋的?”
陈快腿拿过杨二嫂改过的旧裤子,在手里抖了抖,说:“好,好,就是裤裆嫌小了点儿,不要紧,到时候我有办法。”她看看杨二嫂,“咱们俩先演示一遍。假戏真做,要做真,不能太假么假事!”
杨二嫂说:“咋演示,你说咋就咋。”
陈快腿说:“你把这条裤子穿上,甭系裤腰带。你呢,好比就是孙秀英,仰巴脚儿躺在炕上。我呢,假装把孩子从你的裤腰塞进去,然后,让孩子再从你的裤兜子掏出来!”
杨二嫂说:“哈,你出的馊主意!”
陈快腿说:“这可不是我出的馊主意,你去问问,这叫什么?这就叫‘裤兜漏’,少见多怪!”
蔡玉明回到家里,把银花、五丫头、成子揽在怀里,默默地垂泪。
银花说:“妈妈,是谁欺负您了?”
蔡玉明摇摇头,摇落了两行泪。
成子伸出小手为妈妈抹去泪水,奶声奶气地说:“谁欺负妈妈也不行!”
蔡玉明听儿子这样一说,心里动了一下。此刻,她简直有些后悔了。是啊,她有这么好的儿子,将来,家里有这样的顶梁柱,怕什么呢?她不该把这么好的儿子送给旁人家!她痛恨自己,恨不得用力抽自己俩嘴巴。
成子眼巴巴地看着妈妈,说:“我听话。”
蔡玉明忽地把成子紧紧搂在怀里,泪水蹭湿了成子的脸。
成子搂着妈妈,叫道:“妈妈!”
突然,蔡玉明将成子用力一推,说:“去吧,命里注定。”
成子用力搂紧妈妈,嚷道:“妈妈,啥叫命里注定?”
蔡玉明说:“你不懂!”
正说话间,陈快腿和杨二嫂掀帘进来了。
陈快腿说:“在外边喊了半天,咋没有人言语一声呀?”
蔡玉明推开成子,赶紧下炕,说:“净顾得闹,没听见你们在外边叫。坐,坐!”
杨二嫂说:“陈嫂都跟我说了,咱们可得假戏真做。”
蔡玉明说:“啥叫假戏真做?”
陈快腿说:“我进她家一说,她还就真的把这当成一件事,当时就找了一条旧裤子,把裤腰剪开,改成了能装进两个人的大裤腰。裤裆开了个大口子,能钻出一个人来!”一面说,一面把那条改造过的大裤子提给蔡玉明看。
蔡玉明愣愣的,看不出啥馅,说:“你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直来直去,我实在摸不着头脑。”
杨二嫂说:“到时候,你跟成子,就听她的安排。她叫你们娘儿俩咋做,就咋做。她还会给你瞎驴骑?”
陈快腿说:“听明白了?你咋二大妈抱面罐子,稀里糊涂!好了,好了,让银花看家,你带着成子,咱们一块儿去董凤才家!”
蔡玉明像是木偶,只好听凭陈快腿、杨二嫂两个娘们儿摆布,带上成子,一同走出家门。
董凤才正和媳妇瞎闹,突然听见屋外的脚步声,慌忙迎出来。
杨二嫂嘻嘻哈哈地说:“来,快说正事吧。不然的话,黄花菜都凉了!”
蔡玉明说:“秀英早就知道了,我是想把成子送给她家,更名改姓,给她当儿子。”
陈快腿说:“你当着大伙,再说一遍,这个玩笑,可万万开不得!”
蔡玉明说:“我当着众人的面,说话不算数,天打五雷轰!”
杨二嫂说:“不是叫你发誓许愿。”
蔡玉明说:“那叫我干什么?”
陈快腿说:“到时候,我叫你咋,你就咋,好吧?”
蔡玉明说:“好!”
陈快腿说:“凤才,你先出去。”
董凤才说:“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
陈快腿说:“这儿,没你的事!”
董凤才说:“好,好,都是你们老娘们儿的事!”
陈快腿说:“你别总是老娘们儿老娘们儿的,你哪天离开老娘们了?去,去,赶紧走。”
董凤才一面支支吾吾,一面走了出去。
陈快腿说:“杨二嫂,你把这条裤子,给孙秀英换上。”
孙秀英说:“别,别,到套间换去!”
陈快腿说:“到什么套间,就在这儿换,别瞎耽误工夫!”
杨二嫂笑笑,说:“本来嘛,都是老娘们儿,你怕什么呀?”说着,连拉带扯,把孙秀英的裤子给拽了下来。
孙秀英换上了又肥又大的裤子,不知陈快腿唱的哪出戏,只得由她摆布。
陈快腿指指孙秀英,说:“你,仰巴脚儿躺在炕上,别动。”又指指蔡玉明,“你,把成子从秀英的裤腰塞进去。”
蔡玉明不知啥馅,只得按倒成子,往孙秀英的裤腰里塞。
小小年纪的成子知道什么,吓得哇哇直哭。
陈快腿催促道:“玉明,使劲儿塞呀!杨二嫂,你过来帮她!”
成子全身被塞进了孙秀英宽大的裤子,可是,他的头仅仅钻出一半儿,卡住了双肩,怎么也出不来,急得蔡玉明和杨二嫂满脸的汗水。
蔡玉明催促陈快腿,说:“快!”
陈快腿从炕上拿过剪子,照准孙秀英的裤裆,左边噌噌豁一剪子,右边噌噌豁一剪子。扔到地上,伸出两只手,掐住成子的双肩,连抻带拽,把成子从裤兜子掏了出来。还没有放稳,成子已经连哭带闹,连喊带叫,颠儿了。
孙秀英坐起来,把那条又宽又大的裤子甩在炕上,噌噌换上自己的衣服,叫道:“这事闹的!”
陈快腿说:“蔡玉明,咋不管住你家孩子!”
蔡玉明急起直追,叫嚷道:“成子,你往哪里跑?”
杨二嫂说:“也怨我,没有拽住成子!”
陈快腿说:“谁都不怨,假戏真唱。‘裤兜漏’,这假不了。孙秀英,你记着,此后,成子改姓董,就是你的儿子,老天爷也改不了啦!”
蔡玉明死说活说,把成子劝好了,蔫蔫地跟着她到董凤才家里去。可是,妈妈在家里教好了的话,不知是忘了,还是叫不出口,那“妈妈”二字,总在嘴里打转,始终没有滚出来。
孙秀英拉着成子的小手,说:“成子真好,听话着呢!”
成子乜斜了孙秀英一眼,仍然不肯开口。
蔡玉明抚摸着成子的小脑瓜,把嘴巴贴近他的耳朵,轻轻地说:“叫她妈妈,听话,叫,叫!”
成子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孙秀英无可奈何地说:“没关系,一回生,两回熟,惯了就好了!”
蔡玉明说:“这孩子!”
孔大学问的耳朵真长,董凤才家里“裤兜漏”的消息,很快就听到了。他一面往董凤才家里走,一面琢磨该给成子取个什么名字。一不留神,竟然走到了董凤才家的门口。
孙秀英说:“孔老爷子,家里坐坐?”
孔大学问抬头一看,正是孙秀英,嘻嘻笑道:“你看,你看,本来就是想到你家嘛!”
孙秀英说:“那不正好,正赶上凤才在家,你们老爷儿俩好好聊聊!”
孔大学问进了她家院子。
孙秀英向里招呼道:“凤才,快出来,你瞧谁来了?”
董凤才听到叫喊声,立即趿拉着鞋向外走,见是孔大学问,忙说:“孔老爷子,啊呀呀,快进,快进!”
孔大学问:“成子呢?”
董凤才说:“秀英,你把东院那娘儿俩叫过来,就说孔老爷子来了!”
孙秀英答应一声出去了。
孔大学问说:“咋样,这成子?”
董凤才不知如何作答,只好说:“还行!”
孔大学问说:“叫爸爸妈妈没?”
董凤才哈哈笑道:“哪有那么痛快的!”
孔大学问说:“忘说了:柴米的夫妻,饽饽儿郎。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吃没穿,媳妇都不跟你过。平常有了闲钱,就得舍得在孩子身上多花个仨瓜俩枣的。小孩子家家懂个啥?多塞几回糖糖果果,嘴就甜了!”
正说着,孙秀英带着蔡玉明和成子进了屋。
蔡玉明回过头抻抻成子,说:“成子,快叫孔老爷子!”
成子叫道:“老爷子!”
孔大学问痛痛快快地答应道:“唉,这孩子,真伶俐!”
蔡玉明拽着成子,走到董凤才跟前,说:“这是你爸爸,快叫爸爸!”
成子怯怯地低着头,左脚踢着右脚,不说叫,也不说不叫。
孔大学问哈哈大笑,说:“咋?”
董凤才说:“慢慢再说。”
孔大学问说:“《弟子规》里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成子大概还没有想好,等想好再叫,也不迟。”
这话原本是给蔡玉明台阶下的,可她哪里懂?
蔡玉明懵懵懂懂地说:“那是,那是。”领着孩子蹭到炕脚子,坐着听别人说话。
孔大学问说:“名字取了吗?”
董凤才说:“还叫成子吧?”
孔大学问说:“那可不行,小名是小名。光叫小名,左邻右舍,乡里乡亲,谁听得出来成子过继了。这孩子姓了董,成了你董凤才的儿子,就得取个姓董的大名。名不顺,则言不顺。成子原来姓朱,过继之后,就该姓董。天经地义,不可支吾其词。”
蔡玉明听孔大学问一通高论,似懂非懂。可是,当她听到成子真的要改姓董,不再是朱家的孩子,鼻子一酸,一汪泪水涌了上来,她赶紧扭过脸去,抹了一把。
董凤才看在眼里,佯装没有看见。
蔡玉明说:“有孔老爷子在,该咋咋吧!”
董凤才顺口搭音,说道:“也好,也好!”
孔大学问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望望天花板,慢吞吞地说:“《礼》曰:子生三月,父亲名之,即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体,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义,序长幼也。夫人非名不荣,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应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观其志也。”
董凤才说:“老爷子,您满口曰诗云,之乎者也,我们瞎字不识,您就明明白白地说,成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好,就成了。”
孔大学问:“名字是可以随便取的吗?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授子一艺;授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
董凤才说:“啊呀呀,您就说得了。什么富呀贵呀,什么好听顺嘴,就叫什么。”
孔大学问:“刚才你说富呀贵呀,倒叫我想到一个好名字。就用这个‘贵’字,做一个世世代代的贵人。叫‘董世贵’,如何?”
董凤才说:“好!”
蔡玉明说:“这么说,我们成子有了‘董世贵’这个名字,可就成世世代代的贵人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说相似,又不似;说不同,又相同。成子是男孩,珍子是女孩。成子一年长一岁,珍子也一年长一岁;成子属羊,珍子属鸡,成子比珍子大两岁;成子姓了董,叫董世贵,孔大学问给取的名字;珍子叫高桂珍,她爹给取的名字;董世贵聪明,高桂珍伶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