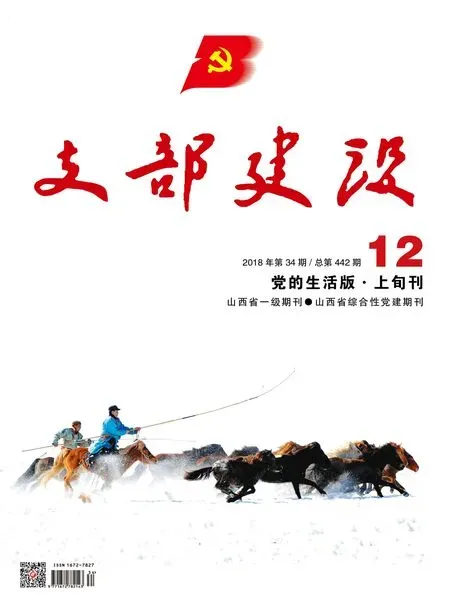《大湄公河》:大文本与新史诗
■ 王朝军
一如《大湄公河》这个名字,黄风和籍满田二位长期深耕于报告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非虚构文学领域的踏实践行者,已然借笔下湄公河之“大”完成了他们写作的转折和突破。这是一种不拘泥于我们通常所认知的报告文学的广义性写作,是一种包罗万象、又有准确而沉稳的着力点的大气象写作,是一种超越他们以往所有作品、又独具这唯一性的里程碑式的写作。当我们还在为《静乐阳光》下的苦难与希望而唏嘘时,还在为《滇缅之列》的忠魂礼赞时,还在为《黄河岸边的歌王》俯首沉思时,《大湄公河》以其并不华丽却雍容磅礴的气势,给了我们重重一击。原来,他们在这里等着我们,在《大湄公河》的急湍险滩处等着我们,在这丰沛得无以复加的大文本中等着我们。沧海巫山,聚水揽云,若是真的“取次花丛懒回顾”,可千万别怨我,要怨就怨这黄、籍二君。
发生在2011年10月5日的震惊中外的湄公河惨案,是创作《大湄公河》的缘起,“13条鲜活而无辜的生命”让他们在悲痛之余,意图用手中的笔,为这转瞬逝去的生命画出魂来。我想这样的初衷,包括两位作者也是不能否认的。但写有个写法,“怎么写”,或许就在这个要写的念头刚刚蹦出来时,便成为萦绕在他们心头的问号。接续以往,势必落入窠臼;创新创意,那就得拿出点不畏难的精气神儿来。这或许就是他们三次深入湄公河采访的动因所在。有了这些扎实的底子做准备,形之于文本,便有了底气,也便有了方向。
二位的选择很是精妙。两条线索,一乃事件本身,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大量运用虚构的手法,来描写几乎是每位遇害者的生前身后——当然,这里存在个主次先后详略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在其中看到了中国传统小说叙事中类似《水浒传》式的联缀式叙事的影子,黄勇、杨德毅、文代洪……一个个,因亲缘或工作关系的纽带而渐次出场,又因处于同一事件的旋涡中,而在叙述中相互交错,相互联结。翁蔑、坤沙、糯康等,这些施害者,虽然着墨力度稍逊,但也有极为细腻的刻画和描写。反而是双方“短兵相接”时,作者并没有刻意地渲染其惨烈和悲情的一幕。我想,这便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了。他们力图避免的是,将惨案单纯地描述为一种祥林嫂式的浅薄的悲悯,而是要在更广阔的纵深,探究湄公河惨案的“源头”。这便涉及到第二条线索。即围绕湄公河展开的对其地理、历史、经济、文化、风俗的全方位叙述。这样一种叙述,也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对既有资料占有基础上的类似文化大散文式的演绎。无论哪章哪节,都可以独自成篇,又有机地缀在《大湄公河》的整个图景之上。在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从这一条线索出发的叙述,并没有割裂与湄公河惨案的联系,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比如,在作者宏阔而富有节制的叙述当中,罂粟这种“恶之花”的身影常常从不经意的角落闪现,自英国殖民者四百多年前将罂粟带入这片土地及流域后,其恶的一面就被一再地发酵和膨胀,祸害了一方的生灵,也扰乱了一方的社会发展。抚今追昔,新的替代种植和新的秩序正在悄然建立,大湄公河将不再是罪恶的温床,而是越来越沐浴着阳光和佛光的所在。同样,湄公河惨案在此流域的历史长河中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惨烈事件,它的意义或许要在湄公河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中不断求索和确证。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湄公河惨案是一堵墙,一面大到全中国人都无法释怀的血迹斑斑的墙,那么对湄公河地理、历史、经济、文化、风俗的探究和铺陈,便是穿透这堵墙的一线坚硬的光,它以其勇力和智慧,为湄公河不断的涅槃新生而一往无前。
这是湄公河的智慧,是湄公河流域各个国家的智慧,同样也是黄、籍二人的智慧,他们高标的视野和胸襟,抚触的是整个湄公河,是来自历史源头的河流之铮铮声响。当文学与历史与现实与生命与大地与河流与人类,与承载这一切的内容相遇时,有谁会怀疑它不是一部“大文本概念”的史诗之作呢?尽管我很少用“史诗”为一部作品定论,但现在看来,就《大湄公河》而言,它无论从容量上,还是文体的实践与跨越上,称为“史诗”都当之无愧。或为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以虚构为特征的史诗作品,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虚实相间的新的意义上的史诗,或干脆称为“新史诗”。
而在“新史诗”这个宏大语境下,我们专注的就不能仅仅是其结构、布局与气象上的史诗性,因为任何一个史诗性的文本,支撑其架构的永远是看似琐碎却经过精细打磨的有机零件,这些零件必须在文本中榫卯相契、严丝合缝地运转,才能够在巨大的史诗流中蜿蜒前行,得到有力的坚实的确认。确认的工作很难,但我庆幸发掘到了些许,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生活化的细节和语言描写。这无疑是文本的重要特征之所在。黄风与籍满田都是北方汉子,而他们笔下的人事,又都在南方乃至异域,能否在细节的处理上贴近南方及异域的风物民情,是他们必须跃过的一道坎。在这方面,应该说他们是成功的。除了极富生活化和烟火气的朴素甚至带着粗粝感的描写之外,他们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也做足了功夫。而且无论是虚构部分,还是非虚构部分,都能得到印证。比如在讲述刘少创带领中科院遥感考察队深入藏地考察湄公河—澜沧江源头时,就以一个非常幽默化的场景描述——曾有驴友野人一样归来,见到一颗小西红柿,竟大老爷们的倒了相,抱住西红柿哇哇大哭:“我的爹!我的娘!我从小就爱吃你!我以为见不到你了!”——道出了“这褐色的地方”对于外来者的艰苦和不易。而在庄重严肃的讲述过程中,时不时也会用大白话解释或“打趣”一番,比如在讲到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人们有着共同的血液和文化基因时,最后加了句话:“也就是说,都是一个根巴上结出来的,攀老根的话都沾亲带故。”不禁让人会心一笑,顿生亲切感。诸如此类,比比皆是,可以说是用散文化的笔法稀释了纯粹叙说历史文化的单调与乏味,让文本变得生动有趣起来。至于对人物及故事的虚构性描写,除了对生活与情感的生动刻画及方言土语等地域性元素的跟进之外,异域风情的切入,也是一大特点。再有,便是树碑立传式的群像式雕琢。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在这一事件的铺展中得到了其应有的位置和价值,作者在其中体现的人文关怀和生命情怀值得点赞。由于篇幅所限,此不一一赘述。
当然,一味的夸赞也不是我的风格。即便是瑕不掩瑜,我也更愿意指出文本的某些虽不影响观瞻的瑕疵,使它在持续的“成长”过程中更为成熟。
其一,是引子部分的结尾处。当读者还沉浸在华平号船老大黄勇给大家带来的情境思绪中时,一场充满希望的行程在作者的讲述下已悄然转变为可能是“最后一段旅程”。这应该是一种暗示,如果行文到此为止,则会予人以遐思,或者说悬念。然后即转入第一章对于湄公河流域地理历史的宏大叙述中,岂不更好?这样一来,读者虽然对“故事”的结局心知肚明,但却因叙述的转折或“摊破”得到了“含而不露”的阅读体验。即如相声艺术的包袱活儿,系包袱在前,解包袱在中,抖包袱在后。窃以为如此为宜。
其二,是某些章节对湄公河惨案中“13名船员遭屠杀”的交代及湄公河流域激流险滩等处的描写有无意识重复之嫌。我之所以更愿意归结到“无意识”,是因为可能是作者在书写时的无心之失。但文本内容的重复或再描述,的确会对文本本身的可读性造成一定的伤害。
其三,是在湄公河惨案叙事中的叙述视角问题。主要出现在第六章“愿大佛保佑”一节。前文均是从黄勇的视角展开,可到了劫匪劫船的时候,直接就转入了全知全能的视角,一下子将翁蔑、扎西卡等人的名字都交代了,而且描述了许多在黄勇视线所及的范围内根本看不到的行为。如此一来,的确突兀了一些。
由此可见,若想成就一流的文本,仍需“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笨功夫。所幸,我看到的还不是黄、籍二位的最后定稿本,相信他们会沉潜下来,为《大湄公河》成为高峰式的经典巨作继续前行。而且我也相信,这个时间点离我们将会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