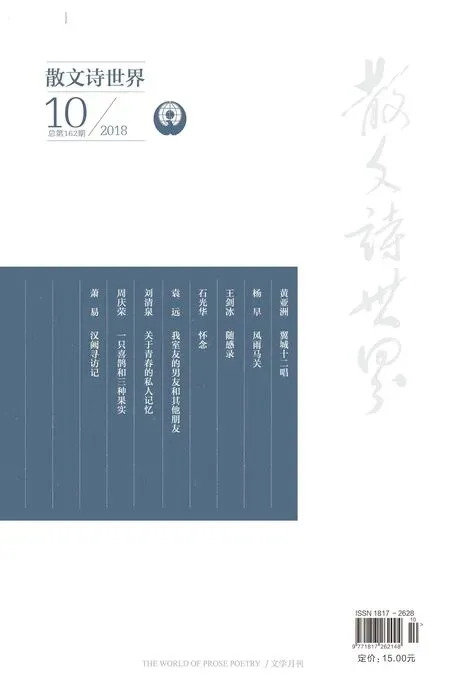随感录
王剑冰
一
一个偶然,凌晨四点的时候,我走出家门,冬天的夜还是有些寒冷,想着这时尚没有人声,却看到了早起的人。
一个小店,昏暗的灯光里,一个男人正在狠劲地揉着一块面,那面似乎很不听话,因而男人就左一下,右一下地下狠,下狠也解决不了战斗,男人于是加上了拳头。
女人则用木柴点着一个炉子,木柴棒子插得乱七八糟。那火一会儿红一会儿灰,一会儿又不见了,聚成浓浓的白烟,反熏到了女人的眼睛。女人揉着眼,咳嗽着,动起了大扇子,一下一下地,终于让火苗撒起欢来。
这是一个早点小摊,在一个小巷子里,必定每天夫妇两个都在重复着这早晨的项目。很多熟睡的人不知道他们的这个项目,只知道他们后来开始收钱的项目。
包括我。
二
一只蚂蚁正在上树,一只蚂蚁跟在它的后面。
前面的蚂蚁爬爬停停,似在寻求最好的路径;后面的蚂蚁也爬爬停停,似在等待着前面的蚂蚁寻求最好的路径。
两只蚂蚁的后面的后面,是一群的蚂蚁,循着前面的蚂蚁的路径迂回而行。这是一只什么队伍,要到什么地方去?一概不知。想不明的是,为什么还要有两只先行,是怕中了埋伏,先要两只探路,还是两只蚂蚁同后面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倒是自己的行踪引来了敌人?
看着的时候,就有时光悄悄走过了。一个影子斜了过来,那是一片叶子,所有的蚂蚁都没有被这影子拦住。前面的蚂蚁若果真不知道有敌人在后面,自家的窝门可要处于危险的境地。
我拿起了一根折断的小棍,待两只蚂蚁走过,横在了一群蚂蚁的路上。那群蚂蚁过来,果然顺着小棍横向里爬去,少部分越界后又跟回了大部队。横着走了好远,到头的时候,才发现是断崖,队伍发生了不小的混乱。这个时候再看那两只蚂蚁,早没有了踪影。
我不知道这个忙帮得对不对。
一个具有一定能量的人的不经意的一个举动,竟改变了一个领域的一次大的事件。
三
一个女子推着一个童车正在穿越马路。
宽大的马路上一辆一辆的车子挤挤挨挨,女子推着童车像推着小皇帝的龙辇,毫无顾忌地穿过一辆又一辆正在慢行的车子的缝隙。
对面是他们的目的地。
孩子在车上正襟危坐,口里含着一个空空奶嘴,那般悠闲无所顾及。女子只管径直地往前推着,一些汽车倒犹犹豫豫,抢过一些车头的时候,还会听到偶尔尖利的刹车声。
在童车走过的曲折路径,所有童车前面的车子都停下来行注目礼。
女子推着童车的状态,全仰仗于这小小的童车,假如没有了童车,女子或许没有这么自信的举动。
四
每天早晨,一个盲老汉都会从巷口走到巷尾,去打一碗豆浆或者别的。
盲老汉边走边哼唱着小调,多是过时的流行歌曲:三月里来好风光,洪湖水呀浪打浪,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一得儿呦……
老汉使用竹竿的方法有些特别,他先将竹竿点在自己的正前方,然后向右边划,直划到路边的路沿,再重复第二个动作。老汉是靠路的一边走。一旦找不到路沿,竹竿会停下来,点划几下,以确定是路沿坏了,还是到了哪个家属院的门口。那正唱的曲儿也立即收住,待再往前走时,接着再唱。
看不到路的盲老汉,像一缕阳光,从巷子的这头走到那头,感染了巷子里起早的人。
有时那根竹竿会别在一辆自行车的轮子里,车子的主人会说,向左,向左,对了,直走。有时竹竿会拨着一辆汽车,但你看到那竹竿不是乱捣,拨着的必是车轮部分而不是车身。司机会摇下车窗说,向右,向右,对了,直走。老汉稍稍停顿后,继续他的小曲:三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
我多次在早点摊前看到这个盲老汉,唱着那重复过多少遍的小曲,用一根竹竿,划船一样,在晨光如溪的小巷,将自己划向前去。
五
女人摸摸男人的下巴,你的胡子还挺硬。
男人说,我不单单是胡子硬。
女人的手很气愤地在男人脖子上划了一圈,继而动员了柔软的玉臂,将男人的头环压下来,男人的头便像安了一根弹簧,在女人的胸前弹了两弹。
男人说,把我的头碰疼了。
女人就咯咯地笑。去吧你!女人说。
我撞上了两座大山。男人说。
你恨不得撞上十万大山!女人说。
哎,你的头上有一条伤疤耶。女人吃惊而认真。
小时候淘气,跌下来碰到一颗小石头上了。男人摸着头像又摸着了那时的疼痛。而疼痛却已经在女人那里颤了一下,哎呀,你让我的心口好难受。
怎么难受?
疼呗。
去吧你,你会疼?
真的,不骗你。
男人被感动了,说,让我揉揉。男人的伸了过去,手还没到,就被女人挡了回来。
想趁机揩油啊!女人说。
明天我们都游哪里?哎,正经的,跟姐禀报禀报。女人挡回去那只手顺势就叼住了它,在自己的手里玩弄着。男人的另一手扣了上去,像一只黄雀。
先去石林,然后去九乡。
都没听说过,俺们那儿有个九间,在山顶上。
女人的手又把黄雀叼住了。黄雀挣脱出来,放在女人的膝盖上,而后顺着膝盖向里爬。爬到一半行程,被女人按住了。你真会带我玩,回去我要感谢你。
男人迷茫地说,感谢还要等回去吗?
我坐在临过道的C位上,飞机起飞不久一场好戏即在我的身边上演了。接下来我便知道了那男人属于吃公家饭的那种,女人是他的下属单位的。哪个单位的?别急,而且我还知道了男人的大号,女人猛然叫出来的时候,男人立时止住了她,并且看了看我,这个名字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因为和前一段网上很火了一阵的那个名字一样。你更想知道了?你呀,让我想想以什么方式告诉你。
六
偶尔在街头听到了这样一件事,这家老人的女儿在加拿大找了个老外做女婿。女儿一直邀请老人到加拿大去住一段。老人一直没有成行。女儿女婿在这年春节就回来看老人。老人别提多高兴了,一大家子整日欢乐有加。后来又一同乘车去少林寺游玩。
回来的路上,老人有点感冒,随手将擦鼻子的卫生纸扔出了窗外。不想老外女婿立即大呼小叫地让停车,大家以为什么事呢,车子停了,老外撒腿就向后跑去,直到找到那团纸并扔进垃圾筒才回到车上。车上的人早就大眼瞪小眼了。
车子驶出了郊外,老人又随手扔出了一个纸团,老外女婿又让停车,老人不愿意了,和女婿争辩起来,说这是野外,不是市里。车上的亲戚也说不必太认真了,这不是在加拿大。车子也没停。
习惯是难以改变的。老人又一次下意识地把纸扔到了窗外。老外女婿又看到了,再次要求停车。争执了半天,还是停了,老外女婿这回是把卫生纸捡了回来,并且一把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老人这回是恼羞成怒,这哪是女婿呀,分明是个找茬的。还让去加拿大呢,在中国气就受够了。你不能拿外国的习惯来套中国的习惯。老人见人就唠叨这件事。这洋女婿一点都不懂道理,你再讲文明也得给人面子吧?
我听了,暗自一笑,走了。老外十分自然的行为,却给人带来了许多的委屈。内中的道理,是一下子讲不通的。
七
在一个小理发店理发。
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经营着这个不大的店面。来往的人倒是不少,多缘于两人的服务与手艺。两人也没有什么分工,不是一个人理发,另一个洗头,就是一个人忙着,另一个人扫地。而只有一个顾客的时候,倒是女的忙,男的在电脑前玩着游戏或看着报纸。
两人还有说不完的话题。女孩一说到高兴处就唧唧咯咯地笑,笑得连活也干不了,就停下笑一阵子。然后说,“哥哥可真逗。”
确实听了女孩是叫了哥哥的。需要什么的时候,女孩会说,哥哥,给咱把什么什么拿来。哥哥就即刻伸手去递。听口音,两人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像是开封东的哪个县。哥哥的叫法是一重一轻,前一个哥挑起来,后一个拐着弯落下去,有一种甜甜的又犯嗲的味道。但女孩确实总是这么叫了,男孩也是认认真真地答应着,也就不觉得是故意拿腔拿调了。
快吃饭的时候,两人会商量着吃什么,女孩说,“哥哥看着买吧。”男孩就出去了,女孩继续忙活。
那天一个人就说:“你们兄妹两个还挺和谐的。”女孩就笑起来,说:“哪呀,那是俺那口哩。叫哥哥叫惯了,改不了口。”说了就又笑,“哪有哥哥妹妹开一个店的呀。呵呵。”
原来是个小夫妻店。叫惯了的“哥哥”,使这个小店充满了和谐,使两人的情感蜜上更加了一层甜。
走出去的时候,“哥哥”的甜音还耳边响着。
八
一个收废品的正在拆解一件旧家具,他想将其更细碎地装在车上拉回去。
而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最后割破了手指。不得不电话叫来儿子帮忙。儿子来的同时还带来了一辆现代。打开盖和后门,折腾了半天,才将那些破烂解决掉。老人捏着手指,笑眯眯地看着现代远去。
老人整这一下子可挣二十五元钱。而儿子跑过来再跑回去的费用也够了。但儿子似乎理解这位父亲,知道父亲的快乐就在每天的一堆废品上边。老人说,儿子可孝顺了。
我早起吃小吃,将这一幕就此记录下来。这个早晨我很满足。
九
冬天的街上闲人很少,都被刀子样的寒风堵在了屋子里。出门的人无不行色匆匆,忙着自己要办的事。但如果你哪天走出门外,却说不准会听到一阵悠扬的笛声,在哪个角落飘然而出,给这个冬天染上一缕畅快的春意。
我出去的那天特别冷,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来一场纷纷扬扬的雪。我把衣帽捂得严严的,戴了厚厚的手套。转过街角的时候,忍不住缩了缩脖子。就在这时,我听到了笛声,那种带有水音的声音让我猛一振奋。厚厚的帽子竟也没有能够阻挡住这种脆亮的声音。
回首望去,竟是两个衣着朴素的乡人,一边走,一边吹着手中的笛子。他们的肩袋里,也插着长长短短的笛子。不用说,他们是以这种方法卖那管乐器的。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又会有多少人能买下他们手里那价钱并不昂贵的竹笛呢?我跟在他们的后边,走了长长的一段路程,一直到了另一个街口。一路上,确实是没有人向他们过问过什么。甚至没有多少人回过头来发出一声赞叹。不是因为他们吹奏得不上档次,他们的演技确实够得上一个水平。我多少还懂得一点乐器。是人们见的太多了,听的太多了。而更多的人是玩不转这种看似简单的乐器的,别人的嘴一用力,手指一动弹,一串美妙的乐声就从竹管中飞了出来。而你不行,得练。这些人从冬到夏,从夏到冬,无论场合环境,每天都在不停地练习着,熟能生巧,总有一天会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遇到的这两个人,一个年轻,一个年长。浑身透着岁月的风尘。他们已经在这样的街道上,不知经过了多少日月了。而他们又卖出去多少竹笛呢?这种商品,不能说是假冒,也不能说是伪劣,它不会损坏人们的身体健康,反而会给人们带来某种愉悦。他们不会挣到什么大钱,卖出去一支是一支。他们由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可以说他们走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应该说他们是把阳春白雪撒遍大江南北,再说得高一点,他们是把祖国的这种民族艺术推而广之。
我就曾在这样的沿街“吹卖”的人手里买过一支很不错的笛子,仅仅花了五元钱。我真的算不出来,这些人是如何赚到钱的。相比起那些倒卖车票的,偷拿巧盗的,制假贩假的,他们着实是不能发到什么大财,而在各个城市的街头,你确确实实会见到这样一些为了手中的那点儿“艺术”而不辞辛劳的人。
笛声依然。在我从另一个小街拐过来时,我又听到了那种像树叶欢舞、像水波荡漾、像百鸟鸣叫的乐音。雪就在这时静悄悄地下来了。雪很凉,一片一片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自然也落在吹笛人的手指上。而笛声,却迎着那种飘落直直地盘旋而上,直到消失在无边无际的云端。
风,更猛了。
十
哪一天,街上来了一个土医生,专门拔火罐。
生意还不错,慢慢就聚了人气。路边小凳子一摆,就有男男女女坐上去。
坐上去了一会,就有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瓶子像长什么似的挂满全身。说是全身,也不夸张,肩上,背上,腿上,脚上,没有不能挂瓶子的,还有屁股上也会长两三个。也没有人觉得丑,远远就能看见一条腚沟子露着,裤子褪到屁股下。当然,大都是中老年男女,治病嘛,没啥不好意思。
只是觉得,这医院里的镜头放在街上,是有些什么,游泳池里的跑出来,行吗?倒有些弄不懂了。
反正一吃过早饭,就见那靠墙的街边,便有男男女女聚到一起来亲近火罐。有的火罐还是竹筒做的。人人都是那一身的瓶瓶罐罐,然后说着拉着,或默默坐着。土头土脑的白大褂拽拽这个,晃晃那个,像在检验肉皮的承受能力。若你没见过拔火罐,猛一看到,还以为是什么行为艺术,或家族式的表演。
有人说,这种方法,在家里也能做,可人们宁愿聚堆,也不愿相信自己。
十一
你找后台去吧。女孩说。
我找后台干嘛呀,修这么个小玩艺还值得找后台嘛?我拿着手里的东西竟有些愤愤然。
你不找后台我们这里解决不了。
那我要是不找后台呢?
对不起您要不找后台我们也没办法。我劝你还是去吧,又不远,就在这根柱子后面。
绕过去我知道了她说的后台与我理解的后台有着多么的不同。谁来找有关修理的问题,前台甜滴滴的女孩都会让你去找后台,因为前台只负责接待,后台负责修理。
十二
饭馆吃饭,边吃边看空调上手写的字,“立木,不要碰我!”
口气很委婉,告诉人们不要随便去动空调,免得你也动,他也动动坏了。可是这立木是什么意思?空调后边立着一根木头,不太稳定吗?又想,立字下可能不是个木字,加了提勾也不是个小字,立小也说不通,难道立木是店里的人,总是爱动它?湖北有地方管三轮车叫麻木,难道还有管空调叫立木的吗?
不明白。
临走问收拾桌子的女孩。
女孩笑了,甜甜地说亲,亲都不知道?哦呵呵呵……
我赶忙起身。
可笑死我了!笑完她又补了一句。
现在什么时代,一个亲随便出口,也不分男女老幼?
可顿时我想明白了,那个立木是个上下分得过大的“亲”字!
我自己也笑了。我从来没有像立早章那样记过立木亲,如果这个记过,怎么也不会出这个笑话,让那女孩靠此快活一阵。
立木亲,我记住了,分得再开也知道是亲。立木顶千斤,只有亲人,才能顶千斤,这多年,才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