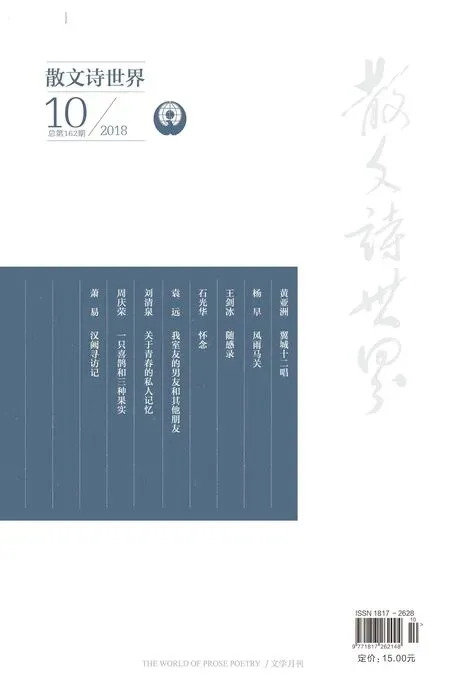城市风景 四章
毛国聪
星巴克
9月11号中午,我去星巴克取一盒朋友送的月饼。
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男人,长发披肩,脸色苍白,在高台凳上悬腿歪坐。
他脚穿黄皮鞋、身着印有英文字母的花T恤,左手握叉,右手握刀,低着头,紧盯着青花瓷盘里一块黄澄澄的白面包,活像一尊雕像。
一阵轻微的刺耳声,好像锯子锯中了铁钉。
我诧异地斜眼望去,他正用叉子挑起刚锯下来的一小块面包送进嘴里。他微微扬起头,一边含嘴慢慢咀嚼,一边茫然地盯着我。
我提着月饼离开时,发现他像宽巷子的一位街头行为艺术家,一动不动,左手握叉,右手握刀,低着头,紧盯着青花瓷盘里剩下一小半的黄澄澄的白面包,好像在思索是在这里干掉它,还是打包带去美国继续享用?
宠物狗
我正在犹豫,接不接裤兜里呜呜呼叫的手机,突然听到一阵狗吠声。
街那边,一只穿着大红夹衣的松狮犬,歪着头,汪汪乱叫。
街这边,一只没穿衣服的泰迪犬,也歪着头,汪汪狂吼。
它们边叫边跳,好像患了一年的相思病。
秋风乍起。银杏叶纷纷坠落。奥迪与思域交错而过。来来往往的行人放慢了脚步。我还在犹豫。
松狮犬在捶胸顿足,好像遭遇了伤心事。泰迪犬绕着主人不断转圈,好像发现了似锦前程。
可它们的主人紧紧攥住如花的绳子,害怕被抛弃似的高声呵斥。
他们愤怒的表情,让人觉得他们不是在呵叱自己的宠物,而是在鄙视对方。
一位披头士,被灵感打了一巴掌似的伫立在杂货铺前,把狗吠声、人声、秋声、汽车声谱成了一首交响曲,谋划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巡回演出。
我隐隐听到了四周此起彼伏的犬吠声。
泰迪犬终于被主人搂在了怀里,松狮犬终于被主人带进了服装店。
我从裤兜里拿出气呼呼的手机,按下接听键。
堵车
前面的标致一直在生气,后面的福特早已呆若木鸡。
左边的大众好像被开除了,右边的东风无一事,正在试图妆点万重花。
宝马、路虎、捷豹、雪铁龙,变成了温顺的食草动物。悍马被驯服了。金鹰折断了翅膀。指挥官退休了。领航员喝醉了酒。东方之子成了一尊雕塑。自由人钻进了囚笼。
今天不吉利。
隔栏那边,奔腾着的小贵族、迷你、精灵、逍客、自由舰,豪情万丈地凯旋而去。
路上没有人,只有汽车。
我不想讴歌,只想着猛烈的交叉火力。
我渴望天籁、风雅、皇冠,
我祈求途安,
我希望这一切都是幻影。
良夜
我拒绝了太阳的光辉,消失了刺目的光明。
我不愿看见白天的冷漠,不幻想那些明显的善行。
我遮蔽了整个世界,我是绝对的孤独者。
敞开胸膛,让鬼魅出没,让恐怖走遍每一个角落。
我甘愿成为黑暗的替罪羊。
让热泪在怀里流淌,让喃喃昵语只向我的灵魂述说。
我不是死亡的冥床,我是睡眠和美梦的卧榻。
我狂欢、呐喊,我忧郁、悲伤,我抒情、浪漫,我吟风弄月,缠绵缱绻……
失明的眼睛在我面前熠熠闪光,匆忙的脚步在徘徊犹豫里找到方向。
我是良夜,
在阳光到来之前。